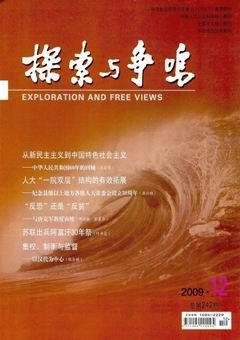勞倫茨·馮·斯泰因的社會—國家思想
徐 健
內容摘要 勞倫茨·馮·斯泰因是19世紀下半葉德國“整體國家”學說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他的社會—國家思想在德國的思想語境中,吸收了19世紀初浪漫主義“有機國家”學說和黑格爾的現代國家觀,并通過對工業化時代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思考,以及德國政治現狀的考察,形成一種學理綜合。斯泰因的社會—國家思想,尤其是他對政府行政提出的見解,具有鮮明的現代啟示意義。
關 鍵 詞 勞倫茨·馮·斯泰因 社會國家 人格思想 社會行政
作者徐健,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博士。(北京:100871)
對社會與國家之間關系的討論古已有之,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托馬斯·阿奎納到馬基雅維利、托馬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等,經典作家對兩者關系時有高論。然而,在西方政治思想及思想家的譜系中,德國偏向保守的政治思想往往因不被視為主流而被遮蔽,勞倫茨·馮·斯泰因的名字自然也就被淹沒了。
勞倫茨·馮·斯泰因,1815年11月15日出生于當時屬于丹麥的什列斯維希公國的艾肯福德,1890年9月28日逝世于奧地利維也納,是19世紀下半葉德國“整體國家學說”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他運用哲學、歷史學、法律、經濟學、政治和社會學方法對國家與社會、經濟與正義問題進行觀察。他的三卷本名著《法國社會運動史》(1850年)不只是描述法國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而是研究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其深度后人很少能望其項背。該書奠定了德國現代社會學的基礎。不僅如此,勞倫茨·馮·斯泰因還是杰出的國家學和行政法學家,其先后出版的8卷本《行政學》著作對政府行政提出了許多不朽見解,獲得了極高聲譽。
一
在近代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的譜系中,對社會與國家關系的認識有兩種不同的路向:一是強調政治自由的孟德斯鳩傳統,其政治界定社會、權力制衡的思想為社會和國家分離的觀念奠定了基礎;二是洛克傳統,主張在自然權利的基礎上視社會為一種外在于政治的綜合性實體。[1 ]無論是哪一種路向都以社會契約論為出發點,其根本都是強調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和對立,這兒是國家,那兒是社會。不僅如此,國家還只是一種社會設備,是由人一步一步按照社會演進的需要發展而來的。社會有如基礎,國家即于此基礎上發展而為的特殊的權力機構。因此,國家的作用,普遍被認為只是仲裁個人之間利益沖突的工具而已。國家執行最低限度的強制性工作,把社會中不同利益集團間的爭執限制在和平與法律所必需的最低范圍內,而它本身則嚴守社會組合與階級紛爭所必須遵守的游戲規則。
在勞倫茨·馮·斯泰因的眼中,國家與社會也存在著對立關系。他認為國家是人格化的有機體,通過內在的自律、意志和行為可以充分施展個性。國家是獨立的機制,是由思想組織起來的統一體。這個擁有思想的國家的目的是要建立全體的自由。那么,什么是社會呢?社會是自然生命要素中的等級社團,是物質生活的組織,它滿足于各自的利益,追求個人的自由。而個人自由在現代社會中是依靠財產來保障的,個人在獲得財產、取得獨立的同時必然會帶來他人的不自由和依附地位,因此社會就被分成了有產者和無產者、獨立者和依附者、自由階級和不自由階級。國家和社會就這樣始終處于難以擺脫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國家努力克服社會的原則,支持無產者參與國家公益,并通過行政保證其生存,另一方面有產者試圖控制國家政權,以便借助權力的保護占有社會財產并維持其社會統治,國家被看成社會權力的工具。”[2 ]
在國家與社會的斗爭中,國家是沒有光明前景的,因為它首先是一個純粹的概念,是抽象的存在,在現實中它只能通過人類社會來實踐,表現為具體的國家機構和國家權力。因此在階級社會中,國家淪落為一種工具,國家權力屬于有產者,有產者控制國家制度和國家行政。換言之,憲法和行政用以維護社會現狀,它是建立在保護有產者統治、無產者依附的基礎上的。
顯然,斯泰因所理解的國家與社會的對立,不完全是古典自由主義意義上的。因為斯泰因所定義的“國家”是以思想為原則的,這樣的國家不可能只是社會的衍生品。它是超越社會的,是最大的政治團體,它本不應該與社會對立,因為它本身就是社會。國家與社會這兩個概念沒有對峙的關系,不是國家與社會的并立,應當是“國家之為社會” [3 ],國家是作為社會的國家而存在的。只不過這個超越社會的國家在現實世界中被社會的利益原則俘虜了。因此,這樣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不會是古典自由主義式的簡單否定,它們彼此相互依存,歸屬于一個更高的原則——人格。國家與社會實際上代表著人性中的兩種可能性,前者是道德自由,后者是利益滿足。在斯泰因那兒,國家與社會終于找到了契合點。而這個“人格思想”,實際上正是斯泰因真正意義上的理想國家。
二
斯泰因對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理解有其思想源流和文化傳承,它處于德國的思想語境中,吸收了19世紀初浪漫主義政治思想家亞當·米勒的“有機國家”學說和黑格爾的現代國家觀,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學理綜合。
德國的現代國家理論形成于1800年左右法國大革命時期。1790—1796年間,僅討論國家問題的出版物便達到900種之多。德國自由派的思想是分裂的,對國家的態度不一而論。以卡爾·羅泰克和特奧多·韋爾克為代表的南德自由主義者接受啟蒙思想,信奉古典自由主義的國家觀;而其他的自由派人士如弗里德里希·達爾曼等卻表現得模棱兩可,一方面拒絕把國家建立在理性原則之上,相信國家是人類生活的基本組織,是超越一切的神圣秩序,另一方面卻也承認社會的自由和權力。隨著法國革命趨向激進,德國思想的主流越來越懷疑現代國家起源的古典理論——社會契約論,保守的歷史“有機國家”理論就在這種環境下悄然誕生了。該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正是亞當·米勒(1779—1829年)。
1804年,米勒出版了《對立學說》,奠定了“有機”理論的基礎。該書認為,一切生活建立在自然和精神、社會和政治彼此矛盾的對立和緊張之中,并將通過對立面的“聯姻”達成更高級的整體,美好的生活和進步運動將誕生于一個社會有機體中。多樣性的統一是對立思想的核心,“整體性包含多樣性,而多樣性則是整體性的表達”[4 ]。1809年,米勒又出版了另一名著《治國術原理》,建立了浪漫主義的國家學體系。在他看來,國家應該是從歷史進程中產生的超個人機構,而不是依靠理性在繪圖版上創制出來的;國家不再只是形式和秩序,而是鮮活的運動和積極的概念;國家不再局限于實現經濟、軍事、政治和法律目標,而是帶有普遍意義的、富有生命的完整的有機體。“國家的整體性”指的是社會中各個自由的、具有內在緊張關系的成分之間,通過力量均衡所達成的有機的共同生活,也就是說,它是超越社會各個沖突階級之上的,維護和保障著全體的利益。
斯泰因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認識首先接受了米勒的“有機”理論,他也承認國家是自土地與血統中生長出來的,充實而有生命的。其次是米勒的對立學說,只不過米勒在他那個時代所看到的對立,更多地存在于傳統社會的各個等級之間,而斯泰因所指稱的對立則是在有產者與無產者,以及作為自由原則體現的國家與利益原則表達的社會之間。畢竟在斯泰因生活的時代,工業社會已經到來了。再次,米勒的“整體性”國家在斯泰因理論中也有表達,這就是具有“人格思想”的國家。人格以及人格的自我認定將成為社會自由運動的承擔者,消弭社會中的一切對立因素,并在國家這個共同體中達成整體的自由。最后,斯泰因的國家學說不是靜態的,一如米勒所倡導的那樣是一種鮮活的運動,把社會不自由導向國家自由的“社會運動”,其任務就是要“把社會秩序和運動納入國家一切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中”[5 ]。
但是,斯泰因的國家觀并沒有止步于浪漫主義的政治理想,而是在此基礎上繼承了黑格爾的現代國家思想。
德國思想中的國家概念到黑格爾這兒上升到了唯心主義哲學的層面。應該承認,黑格爾的國家觀是吸收了洛克和孟德斯鳩關于國家和社會的研究成果的。他首先承認市民社會對自由的肯定,因為“它堅持個人不可讓渡的平等權利,增加了人的需要和滿足他們的手段,組織了勞動分工,推動了法治”[6 ]。但他又深刻地認識到,市民社會作為需要滿足的體系也會產生自身的危機,一方面社會成為角逐私利的場所,另一方面出現財富分配不均和等級差異。為了克服這個由“孤立原子”組成的市民社會的內在矛盾和沖突,必須由一個代表普遍理性的國家來出面調停。這個能“促進普遍利益”的完善國家,應該不是一種作為暴力機構和行政管理機構的國家機器,而是作為人們共同生活基礎的倫理與文化共同體,具體的自由和權利只有在這樣的理性國家中才能得以實現。
顯然,黑格爾的現代國家觀已經超越了浪漫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有機國家”理論,它是建立在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深刻認識和批判的基礎上的,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現實意義。浪漫主義者如亞當·米勒等雖然也批判勞動分工的墮落傾向,批判兵營式大工廠是傷風敗俗的怪物,但卡爾·施密特認為,浪漫主義是從情感—審美角度來批判的,它在根本上是否定資本主義社會的正當性的。
斯泰因同樣也繼承了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他對自由的認識是辯證的,一方面,他也相信理性主義和進步觀念,認為資產階級社會所創造的個體自由是從未存在過的,它依靠財產來保證每個人的利益和自由;但另一方面,他又揭穿了古典自由主義關于社會自由的美麗面紗,批評資本主義社會的經營自由、市場自由和勞動契約自由。實際上正是它們導致了財產關系的分裂,造成了社會的不自由。真正的自由,按照斯泰因的理解不是不負責任的、沒有聯系和約束的。如同黑格爾強調國家是“倫理的整體,是自由的實現”,斯泰因也認為“人格”國家是自由的真正體現者,它承認和保護每個人的權利,但代表的是全體的利益而不是某個個體或集團的利益。實際生活中的國家權力的重要任務是使依附階級獲得財產,形成獨立意識、具備負責任的能力。
三
斯泰因生活的時代與米勒和黑格爾不同,他處于變動的時代。19世紀三四十年代,工業革命所引發的社會后果開始顯現。資產階級社會誕生了,歐洲文藝作品的主題明顯圍繞著資產階級社會展開,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就是那個時代的產物;社會發生了劇烈的階級分化,形成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與工業社會相伴的社會問題也接踵而至,社會公平、社會正義成為時代的政治口號。法國成為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而斯泰因人生中風華正茂的時期也正是在巴黎度過的。為了撰寫法律史論文,他從基爾大學去了巴黎,但從此卻改變了專業方向。他密切關注法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現狀,認真學習社會主義理論,并與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先驅們密切交往。他一生中所有重要的著作都與歐洲的社會主義及工人運動相關。
斯泰因的國家理論并未停留在他的思想理念中。如果說黑格爾對工業時代的資產階級社會做了大膽的思想預測的話,那么可以說斯泰因在黑格爾的基礎上繼續前行,對資產階級社會進行了現實的思考,對黑格爾的理論體系做了符合時代要求的完善。斯泰因國家理論的特點是他把經驗和理論、實證科學和精神科學結合起來了。他的社會改革方案正是他社會—國家理論的實踐設想。
雖然在國家與社會的對立中,思想的國家往往屈服于靠利益驅使的社會,而社會也由于財產的分裂而導致階級差異,有產者階級掌握國家政權,并設置種種障礙剝奪無產者獲得自由的權利,由此產生了“社會正義”的問題。但“人格化”的國家并不是束手無策的。斯泰因認為資產階級社會的核心問題在于勞動被資本控制。財富是通過勞動產生的,但勞動成果卻不歸勞動者而歸資本所有,這與勞動的本質相違背。因此必須通過社會改革建立新秩序,使勞動的本質和意義得以實現。解決19世紀的社會問題關鍵就在于建立一個工業社會,使勞動者通過勞動在一定程度上、按一定方式獲得財產,使勞動“不再是商品,而成為真正的資本,一切經濟和財產關系的基礎,物質生活和社會的內在原則”[7 ]。不過,斯泰因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產生了與馬克思主義相反的理論結果,他不主張通過社會革命而是寄希望于社會改革來實現這一目標。社會改革所依靠的既不是統治階級也不是被統治階級,而是第三種中立的社會力量即社會君主制。
其實,斯泰因非常清楚現代國家在現實社會中的遭遇,它往往會被社會中的強勢集團所掌控,即使君主制也免不了這種厄運的困擾——君主代表的是抽象的權威,實際的權力被剝奪了,只是作為一具空殼被保存下來。但是,斯泰因仍然樂觀地相信會有一種擺脫這類命運的可能性,那就是君主制必須代表純粹的國家,必須成為社會改革的領導者。斯泰因認為世襲的君主不依賴于任何社會階級,擁有人民的信任與愛,這是他與生俱來的優勢,因此只要他重新宣布自己是最高的立法者和執行機構,利用手中的權力為社會中的各個階級創造自由,特別是把對無產者的保護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自由的國家就不難實現了。
斯泰因生活的時代資產階級社會已經穩固,因此政治學所思考的對象發生了重心轉移,權力分割的法治國家思想讓位于行政思想。斯泰因的《行政學》著作正體現了他重塑國家制度與行政的理論勇氣。斯泰因的國家學說,其作用不局限于古典自由主義所限定的職責范圍,它遠遠不只是維持社會治安,而是要建立一種制度,使全體公民都有參與國家公共事務的可能性,讓他們感覺到自己是整體中的一分子,有獨立的責任意識和社會意識。國家的精神氣質應該與個人的精神生活相一致。他為政府的行政管理即所謂的“社會行政”注入了新的基礎——“生存關懷”,通過在經濟、流通領域,以及教育和培訓制度方面的行政工作,關心每個人的基本利益,保障其生存安全。國家要發展經濟,它必須是強有力的和富裕的,這樣才能促進公民福利的發展。國家更要發展教育事業,斯泰因提倡普通義務教育,讓每個孩子、每個公民不論其經濟和社會地位都能獲得受教育的機會。對所有人開放的教育資源不僅可以打通社會的流動性,擴大人們在給定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活動空間,打破階級壁壘,使無產者獲得上升的機會,而且還可以“廢除社會因勞動分工而形成的精神隔膜,全面建構人類的精神生活”[8 ]。教育是建設具有“人格思想”國家的社會實踐。當然,國家行政的真正任務是要重新確立勞動的價值和意義,通過教育把勞動階級培養成有教養的、擁有財產的社會階級,以保證自由的圓滿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說,斯泰因所理解的國家行政,與西方自由主義在解決資本主義工業化所產生的社會問題時倡導的“國家行動能力”,是有區別的,其差異就在于對國家本質的認識。
四
19世紀中期是自由資本主義凱歌行進的年代,但斯泰因卻在資本主義看似穩定的制度中預見到了工業社會無法避免的社會沖突和政治斗爭。他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意識,這為他的學術研究打開了未雨綢繆的開闊視野。
斯泰因的國家理論不是孤立的,他通過觀察社會的結構、條件和原則來研究國家,因此他的國家學說也是社會學說。他的社會—國家理論與19世紀的大多數相關理論不同,他沒有黨派觀點。他熱情地主張將人民從依附狀態中解放出來參加到整體國家中去,但卻不是自由民主的推崇者;他想建立與自然秩序相適應的政治制度,卻不是把政治詩化的浪漫派;他崇尚國家的行政權力,但卻不是國家威權主義者;他提倡社會君主制但不是王政復辟者。斯泰因的社會—國家理論重視公民福利的發展和國家的富裕充足,但這個國家又不是費希特主張建立的“封閉的商業國”,因為它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提高國家的經濟力,而在于通過國家的強大來保證全社會的自由。他的社會—國家理論也不是19世紀末歐洲所推行的簡單的“福利國家政策”,他對社會問題、社會正義的關心不僅是要解決貧富分化的社會現象,而且是要對社會結構做出質的改變。
但是,君主制還是為斯泰因的社會—國家理論添加了“保守”的色彩。雖然他不喜歡普魯士領導德國統一的小德意志道路,但他熱愛君主制。他對資產階級國家與社會斗爭的結果可以保持清醒地認識,對君主制國家的利益傾向和弊端卻視而不見。德意志帝國實行的是君主立憲制,他對君主制抱有幻想。19世紀末,這個帝國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社會保障體制,其思想淵源便來自于包括斯泰因在內的德國思想家的國家理論,認為君主制國家有責任推動經濟和社會進步,維護全體國民的利益。1890年上臺的威廉二世皇帝更是推行社會政策的“新路線”,在一定程度上拋棄了袒護資本家的階級立場,對企業中的勞資關系采取中立態度,以至于贏得了“工人皇帝”的稱號。但“新路線”并未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1918年德國君主制在一次大戰的炮聲中覆滅,乃是資產階級和社會革命力量聯合行動的結果。斯泰因所傾心的君主的“高貴的道德勇氣”,亦未能如他所愿建立起具有“人格思想”的自由國家。
事實證明,斯泰因的社會—國家理論以及他所傳承的德國思想中的整體國家觀,與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樣,只能是另一個烏托邦。現代國家不可能是黑格爾“具體自由的實現”,也不可能是斯泰因的“人格化”自由國家。正如漢娜·阿倫特所指出的,現代政治的特征就是私人利益變成公共事務,作為“整體”的國家“淪為一種更加有限、更加非個人化的行政區域”[9 ],政府的職能是向私有者提供保護。國家不可能是純粹的思想的體現者和共同利益的維護者,它不可避免地要為強勢集團所支配。
不過,斯泰因的社會—國家理論對我們仍然是有啟示意義的:第一,現代社會需要有一個體現人類整體利益的理性力量來規范和制約。第二,國家不應該只是理性的工具,它在看重效用的同時,也應當關注目的理性。國家行政的基本理念在物質性的生存關懷之外,應該具有更多的精神關懷。
參考文獻:
[1]張一兵、周嘉昕. 市民社會:資本主義發展的自我認識. 南京大學學報,2009(2).
[2][4][7]Ernst R. Huber. National staatund Verfassun-gsstaat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modernen Staatsidee. Stuttgart:W. Kohlhammer Verlag, 1965 :132 、52 、143 . [3][5]桑巴特,楊樹人譯. 德意志社會主義. 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241、239.
[6]張汝倫. 萊茵哲影.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8.
[8]Gundela Lahmer. Lorenz von Stein: Zur Konstitution des buergerlichen Bildungswesens. Frankfurt/M: Campus Verlag, 1982:131.
[9]漢娜·阿倫特. 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 文化與公共性. 北京: 三聯書店, 1998:97.
編輯 李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