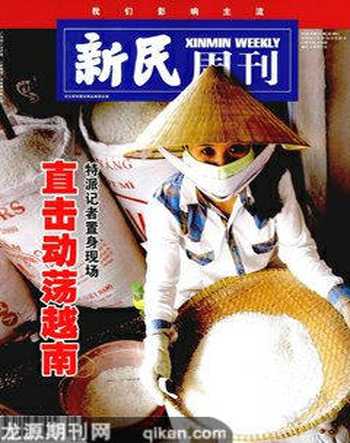木版水印:傳承108年的精湛技藝
王悅陽

“復制品”這頂“帽子”決定了水印版畫的價格只能定在中國傳統繪畫作品原作之下,這也就是為什么水印版畫始終打不開市場局面的原因之一。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有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青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云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球,陳舊而迷糊。”這是張愛玲小說名篇《金鎖記》開頭的一段描寫。細膩的文字不僅流淌出淡淡的海派情結與風雅韻味,更讓讀者記住了“朵云軒”這個名字。“朵云”是書信的雅稱,自光緒二十六年創立算起,以制作信箋、畫箋聞名于世的朵云軒至今已有108年的歷史,而其木版水印技術,便也流傳了108年。“鏤象于木,印之素紙”的傳統木版水印藝術源于中國古老的雕版印刷術,是中國古代文明和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素有中國印刷史的“活化石”之稱。受“海派文化”的滋養,一個世紀以來,朵云軒木版水印形成了用料考究、精致、秀潤的風格特征,與北京榮寶齋的木版水印形成了中國木版水印“南朵北榮”兩大流派,各領風騷。
2008年6月14日,國務院頒布了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上海朵云軒木版水印技術繼去年北京榮寶齋木版水印列入名錄后,也名列金榜,至此,傳統木版水印制作工藝的保護傳承項目終于變得完整起來。
源于傳統的精湛技藝
中國雕版印刷術“肇自隋時,行于唐世,擴于五代,精于宋人”。現藏于英國倫敦博物館的公元868年刻唐代《金剛般若經》扉頁上的《講法圖》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一幅單色版畫。到了明代萬歷、崇禎年間,雕版技術更是得到一次飛躍,隨著小說、戲曲的大量刊印,加之諸如陳老蓮、蕭云從、任渭長等明清一流畫家的參與,“饾版”和“拱花”等復雜的套版疊印工藝被廣泛采用,為今天的木版水印在技藝上奠定了深厚的基礎。朵云軒木版水印在傳承這些技藝的基礎上,為適應中國畫的筆墨語言特點,進行了長期的藝術探索,并已發展成為一門綜合了繪畫、雕刻和印刷的再創造藝術——運用刻刀、木板、宣紙、顏料、筆硯、棕耙等簡單的傳統工具,通過“勾描”、“雕版”和“水印”三道復雜的純手工工藝程序,將上至晉唐下至明清以及近現代名家作品的筆情墨韻原汁原味再現出來,而且成品能與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的材質完全一致,使木版水印產品更具“亂真”的效果。無論是人物、山水,還是花鳥等各類題材;鏡片、冊頁、立軸、手卷等眾多形式;還是工筆、沒骨、寫意等諸多技法;紙、絹、金箋等不同材料,木版水印都能神奇地再現原作神韻。
數十年來,朵云軒成功地運用木版水印技術,復制了大量精彩的書畫作品,其中,既有歷八年之功,刻版千余塊精心復制而成的晉?顧愷之《洛神賦圖卷》(絹本);也有長達三丈余、高九寸許,迄今為止木版水印復制最長的一幅手卷——明?徐渭《雜花圖卷》;更有唐?孫位《高逸圖》、唐?閻立本《步輦圖》、宋?趙佶《芙蓉錦雞圖》、明?仇英《秋原獵騎圖》、明?唐寅《玉玦仕女圖》等中國美術史上赫赫有名的經典之作……此外,齊白石、徐悲鴻、傅抱石、林風眠、張大千、黃賓虹、劉海粟、潘天壽、謝稚柳、程十發等近現代國畫大師的代表之作,也都被收入其中,令人目不暇接。
然而,千萬不能小看木版水印這門工藝,因為,每幅作品的誕生,都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心力代價的。在雕刻之前,師傅們先要根據原作的風格流派、用筆的枯濕濃淡、設色的微妙變化進行分組分版,然后用毛筆精確無誤地勾描在雁皮紙上。再把描好的線描稿反貼在梨木板上,運用各種刀具和刀法,精雕細鏤,刻出各種線條枯筆,制成“饾版”或“拱花”版。為求逼肖原作,不同大小的畫面會被分成幾十、幾百以至上千個套版,即使最簡單的作品,一花一葉,一草一木,也都需要獨立雕刻成一塊塊的饾版,才能保證與原作絲毫不差。刻板完成,便要根據原作用材、顏色及筆觸節奏,將水墨或色彩刷撣在已刻好的木版上,然后把每一幅畫的所有版子分別套印在宣紙或畫絹上,這才完成了基本工序。

木版水印字畫的制作是一個極為專業,也極富創造性的過程,不僅涉及制作人員把握原作的素養,也涉及其描繪、雕刻功底。在套色印刷時,更涉及制作人員的精湛技巧,材質、顏料、水分,甚至氣溫、濕度,稍有掌握不慎,都會導致前期勞動白費。正因為如此,一幅木版水印字畫的制作成功率相當低,以《明?胡正言十竹齋書畫譜》為例,光一套木版就耗費了幾十個專業人員前后十年的勞動,堪稱工程浩大,投入不菲。此外,一套木版的使用次數也相當有限,通常情況下,整套有效使用不過百余次。
面對市場的無奈尷尬
2006年秋季的一次拍賣會上,一幅署名“白石老人”的《荷花蜻蜓》圖引起了大家的興趣,無論從筆墨、線條還是色彩上來看,這張用筆老辣,墨韻豐富的作品堪稱齊白石晚年佳作。于是,鑒定師毫不猶豫地將此畫估價18萬-22萬元,并赫然印上了拍賣圖錄。然而,短短幾分鐘后,一個電話竟讓拍賣行大跌眼鏡。原來,這張極為精彩的《荷花蜻蜓》,竟然是上世紀50年代朵云軒用木版水印技法復制而成的,其制作成本僅有800元!
“正是這樣‘下真跡一等的高超技藝,成就了朵云軒木刻水印技術的名聲。”著名畫家,上海書畫出版社社長盧輔圣每每說起這段往事,總有著極為復雜的情感,“然而,在今天,我們也必須看到,木版水印的實用性功能已經基本消褪,只有它的文化價值、藝術價值始終凸現著。”
面對著印刷技術的不斷進步,木版水印已經不再成為復制、保存、研究古畫真跡的唯一方法,而日本東京“二玄社”的精美復制技術更令美術界嘆為觀止,甚至連著名的美術史論家、畫家謝稚柳、陳佩秋夫婦為了研究董源真跡,都不惜高價從“二玄社”買來與原作最相仿的復制品加以研究。對此,盧輔圣卻始終認為:“木版水印運用原作材料進行復制印刷,幾乎做到原汁原味,以假亂真,更不會出現現代印刷的所謂網點,絕對是現代印刷術無法做到和替代的。”拿朵云軒木版水印作品《明?胡正言十竹齋書畫譜》為例,1989年,當這套佳作送往萊比錫國際圖書藝術展覽會展出時,組委會甚至為此特設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最高獎項——國家大獎,以肯定其杰出的藝術成就。
近年來,類似于木版水印被誤認為真跡拍賣的例子不在少數,這一方面表明了技藝之精湛,但另一方面,也使朵云軒陷入了無奈與尷尬。“復制品”這頂“帽子”決定了水印版畫的價格只能定在中國傳統繪畫作品原作之下,這也就是為什么水印版畫始終打不開市場局面的原因之一。此外,高昂的人工費與偏低的市場價格始終很難協調,加之印刷周期漫長,注定木刻水印作品不能大量投放市場。根據數據顯示,若以一個人計算,制作一幅《雜花圖卷》,需勾、刻257塊版子,勾描者至少要勾勒520張刻稿,總共需花一年半左右時間;而刻版者刻這些版子,也需將近一年時間;印刷者以印一卷長卷計,需用13張宣紙組成,257塊版子,上、下版子和套版對位770余次,疊色套印、翻動紙張至少達3340次。加起來一個人勾、刻、印,至少要花費4年半時間。而所完成作品,其市場價格約在5000元左右,無論如何也不夠人工成本費用。成本和周期制約了市場規模,使得其經濟效益每況愈下。此外,從業隊伍的青黃不接,傳統技藝如何保護、傳承也是不可回避的問題。
對此,盧輔圣認為,傳承不僅僅需要保護,更在于創新和發展。木版水印在當下無法市場化的情況下,可以嘗試走一條新路,即利用這門技藝進行創作,參考西方藝術家原創版畫的辦法,使得木刻水印技術成為一種創作手段,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復制品制作的層面,同時也可提高市場價格。此外,還可以通過展覽、現場表演等方法,多渠道、多形式地進行一些宣傳與展示,深入挖掘水印木刻內在的文化內涵,使得這門具有108年歷史的傳統技藝,在今后能夠走得更遠、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