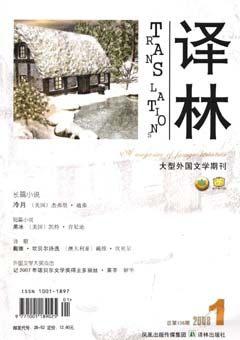成癮、娛樂(lè)和欲望:美國(guó)未來(lái)的怪誕社會(huì)
王海燕 楊仁敬
摘要:華萊士的小說(shuō)《無(wú)盡的玩笑》向讀者展示了一幅美國(guó)未來(lái)的怪誕社會(huì)的圖景。成癮、娛樂(lè)和欲望構(gòu)成了這個(gè)社會(huì)的主要特色以及這部小說(shuō)的三大主題:人們對(duì)各種東西的執(zhí)著和成癮摧毀了人的自主性,導(dǎo)致了人的依賴(lài)性,是現(xiàn)代社會(huì)種種問(wèn)題的根源;以?shī)蕵?lè)為目的的大眾文化的極度擴(kuò)張?jiān)斐闪巳藗儌€(gè)性的迷失;在美國(guó)未來(lái)極端消費(fèi)的社會(huì)中,對(duì)享樂(lè)的貪求和欲望造成了時(shí)代的悲哀。未來(lái)的美國(guó)社會(huì)就是一個(gè)無(wú)盡的玩笑。
關(guān)鍵詞:成癮 娛樂(lè) 欲望
在美國(guó)走紅的“X一代”作家群主要是指出生于20世紀(jì)四五十年代的年輕一代作家,他們大多成名于八九十年代,主要成員有威廉·伏爾曼、理查德·鮑威爾斯、大衛(wèi)·福斯特·華萊士、道格拉斯·考普蘭、凱瑟琳·克列默和尼爾·斯蒂文森。這些新崛起的作家的成就不容忽視,如伏爾曼和鮑威爾斯曾分別獲得2005年和2006年美國(guó)國(guó)家圖書(shū)獎(jiǎng)。下一位將是誰(shuí)呢?文學(xué)界和學(xué)術(shù)界許多人都看好華萊士。
華萊士堪稱(chēng)“天才作家”。第一部小說(shuō)《系統(tǒng)的笤帚》(1987)問(wèn)世時(shí),他年僅二十五歲,剛剛獲得碩士學(xué)位。小說(shuō)一出版,就廣獲好評(píng)。當(dāng)時(shí)《紐約時(shí)報(bào)》的書(shū)評(píng)將之與后現(xiàn)代派大師托馬斯·品欽的《拍賣(mài)第49批》相提并論。到目前為止,他已發(fā)表的作品還有小說(shuō)《無(wú)盡的玩笑》(1996);短篇故事集《頭發(fā)古怪的女孩》(1990)、《與丑男人的簡(jiǎn)短會(huì)面》(1999)和《遺忘:故事》(2004),論說(shuō)文集有:《探究 RAP說(shuō)唱藝人:城市的RAP與種族》(1990)(與馬克·科斯泰羅合著)、《一件我決不再做且看似好笑的事》(1997)、《起來(lái),辛巴!》(2002)、《一切及其他》(2000)和《考慮龍蝦》(2005)等。
和伏爾曼、鮑威爾斯等“X一代”作家一樣,華萊士受過(guò)良好的教育。他1962年2月21日出生于紐約州的綺色佳市,父母均為伊利諾伊州的大學(xué)教授。從青少年時(shí)起,華萊士就熱愛(ài)運(yùn)動(dòng),是不錯(cuò)的網(wǎng)球選手。后來(lái)他就讀于他父親的母校阿默斯特學(xué)院,主修哲學(xué),輔修邏輯和數(shù)學(xué),1985年以?xún)?yōu)異的成績(jī)畢業(yè),1987年獲亞利桑那州大學(xué)藝術(shù)碩士學(xué)位后,開(kāi)始萌發(fā)了寫(xiě)作的興趣。后來(lái),華萊士移居波士頓,進(jìn)入哈佛研究生院學(xué)習(xí)哲學(xué),但中途放棄。80年代末90年代初時(shí),華萊士度過(guò)了一段低潮時(shí)期,對(duì)寫(xiě)作的疑慮使他情緒低落、憂郁,他嘗試各種毒品,最后求醫(yī)治療。1993年至2002年間華萊士在伊利諾伊州立大學(xué)任英語(yǔ)副教授,2002年至今在加利福尼亞州普莫納學(xué)院任寫(xiě)作教授。
《無(wú)盡的玩笑》無(wú)疑是華萊士最為重要的著作。故事發(fā)生在2014年的美國(guó)。那時(shí)的美國(guó),科技迅猛發(fā)展,“電視電腦”(Teleputers)普及,交互電視娛樂(lè)公司掌控了美國(guó)所有的電視節(jié)目,為人們提供了無(wú)盡的娛樂(lè)和信息,人們沉浸在輕松的娛樂(lè)節(jié)目里。這些娛樂(lè)和信息將人們淹沒(méi),讓他們遠(yuǎn)離社會(huì),失去自我。同時(shí),美國(guó)也成為高度消費(fèi)和物質(zhì)化的社會(huì),廣告泛濫,一切都商品化。美國(guó)的自由女神手中舉著的不再是象征自由的火炬,而是漢堡包。美國(guó)的歷法也賣(mài)給了最高的競(jìng)標(biāo)人,因而小說(shuō)中的年代不再沿用傳統(tǒng)的歷法,而全部以某種產(chǎn)品命名,成了諸如迪潘成人內(nèi)衣年、美國(guó)哈特蘭奶制品年、普度神奇雞塊年以及歡樂(lè)之年等等。毒品泛濫、美國(guó)總統(tǒng)被暗殺、環(huán)境污染的問(wèn)題讓政府束手無(wú)策,干脆把新英格蘭地區(qū)變成一個(gè)大垃圾場(chǎng)。政府用巨型風(fēng)扇將廢料和垃圾往新英格蘭北部吹,并有意將這一地區(qū)放棄給加拿大。這樣的故事看起來(lái)像科幻小說(shuō)一樣荒誕離奇,但作品中貫穿了大量對(duì)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細(xì)節(jié)描述,使我們毫不置疑其真實(shí)性。
這部“巨著”的敘事結(jié)構(gòu)相當(dāng)復(fù)雜。小說(shuō)圍繞三條主線展開(kāi),但同時(shí)貫穿數(shù)十條輔線。其中一條敘事主線是描寫(xiě)波士頓郊區(qū)恩費(fèi)爾德網(wǎng)球?qū)W院的學(xué)生生活。這條線索主要圍繞哈爾·因肯登扎展開(kāi)。哈爾的一家是小說(shuō)的主要人物。他父親詹姆斯·因肯登扎是個(gè)恐怖的天才。他曾是天才的網(wǎng)球運(yùn)動(dòng)員,后來(lái)成為研究光學(xué)的物理學(xué)家,并嘗試導(dǎo)演電影。故事的一開(kāi)始他就以一種恐怖的方式自殺了——將頭伸進(jìn)微波爐里。他的夫人艾芙瑞是語(yǔ)言學(xué)博士,同時(shí)也是魁北克分裂分子。他們有三個(gè)兒子:足球運(yùn)動(dòng)員奧瑞;恩費(fèi)爾德網(wǎng)球?qū)W院的天才學(xué)生哈爾;身體殘疾,智力低下的馬里奧。
華萊士自己的網(wǎng)球選手的經(jīng)歷,使他能夠以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手法描述恩費(fèi)爾德網(wǎng)球?qū)W院的日常訓(xùn)練和比賽。來(lái)自美國(guó)各地的白人富裕家庭的孩子像馬戲團(tuán)的動(dòng)物一樣被訓(xùn)練、定型。為了迎合觀眾越來(lái)越高的要求和娛樂(lè)心理,訓(xùn)練十分殘酷,不少孩子身體受傷。巨大競(jìng)爭(zhēng)的壓力也損害了孩子們的心理。哈爾作為一個(gè)網(wǎng)球天才,承受了不小的壓力。同時(shí)他親眼目睹了父親死的慘狀,這些都使他備受噩夢(mèng)折磨,并嘗試以吸毒來(lái)緩解壓力和逃避現(xiàn)實(shí)。哈爾的問(wèn)題還在于從小他就缺乏生活的激情。在他看來(lái), 諸如“生活的樂(lè)趣”、“價(jià)值”等這些東西就像方程式里的變量一樣可以隨意調(diào)整、改變來(lái)滿足別人的需求,但他自己的內(nèi)心卻是空虛的,甚至無(wú)法證明自己的存在。
小說(shuō)另一條線索是描寫(xiě)一個(gè)專(zhuān)門(mén)治療成癮病患的醫(yī)院——恩里特醫(yī)院的日常生活,圍繞唐·蓋特林展開(kāi)。蓋特林原來(lái)是一個(gè)小偷,酗酒、長(zhǎng)期依賴(lài)德美羅止痛藥。在醫(yī)院期間,他接觸到了各種成癮患者,并參加嗜酒者互誡協(xié)會(huì)。通過(guò)對(duì)蓋特林和喬妮、凱特、蘭迪、布魯斯等成癮病患的描述,華萊士揭示了“成癮”這個(gè)問(wèn)題的社會(huì)性,并帶領(lǐng)讀者走進(jìn)了這些成癮病患的心理世界。
第三條線索是描寫(xiě)加拿大魁北克分裂分子的恐怖計(jì)劃。當(dāng)時(shí)美國(guó)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已經(jīng)成為北美聯(lián)盟國(guó)組織的成員(ONAN)。新英格蘭的大部分地區(qū)已變成大型的有毒廢料的垃圾場(chǎng),這些有毒廢料正向加拿大延伸。魁北克分裂分子為了獲得低毒甚至無(wú)毒的環(huán)境,決定采取恐怖行動(dòng)。而出乎意料的是他們的恐怖計(jì)劃不是炸毀或攻擊美國(guó)城市,而是找到電影《無(wú)盡的玩笑》的拷貝。《無(wú)盡的玩笑》是前衛(wèi)導(dǎo)演詹姆斯·因肯登扎的作品。任何看過(guò)這部電影的人都沉溺其中。看電影時(shí),人們會(huì)不吃不喝,對(duì)周?chē)磺惺ヅd趣,最后死于興奮。恐怖分子就是想利用這部電影讓美國(guó)人在“快樂(lè)”中墮落、毀滅。這部電影成了最有效和最恐怖的武器。恐怖分子、政府官員、間諜以及他們的朋友等卷入對(duì)這部電影的爭(zhēng)奪,人性的丑惡和政治的黑暗得到充分的揭露。
小說(shuō)的三條主線交錯(cuò)進(jìn)行,穿插數(shù)十條輔線,將眾多的人物網(wǎng)織其中。這部小說(shuō)和品欽、伏爾曼等的小說(shuō)一樣,充分體現(xiàn)了信息時(shí)代的特點(diǎn),承載了大量的信息。作品中大量的關(guān)于吸毒、戒毒、網(wǎng)球比賽、電影制作、恐怖犯罪等等的描述,涉及到廣泛的醫(yī)學(xué)、心理學(xué)、體育各方面的知識(shí)和術(shù)語(yǔ)都大大增加了閱讀的難度。但這部小說(shuō)絕不是一部讓人乏味的小說(shuō),相反,它讓人沉醉。正如《波士頓鳳凰報(bào)》的評(píng)論指出,“這是一部關(guān)于成癮的讓人上癮的小說(shuō),也是一部關(guān)于娛樂(lè)的輕松的小說(shuō),也是一部關(guān)于欲望的的很長(zhǎng)的小說(shuō)。”(注:安妮·瑪麗·唐納休:“無(wú)盡的文本:網(wǎng)球,12步驟,和恐怖主義,關(guān)于生活和笑聲的小說(shuō)”, 《波士頓鳳凰報(bào)》,1996年3月21日。)這個(gè)評(píng)論準(zhǔn)確地指出了《無(wú)盡的玩笑》這部小說(shuō)的三個(gè)主題:成癮、娛樂(lè)和欲望。
華萊士尤其對(duì)“成癮”這個(gè)主題感興趣。在《無(wú)盡的玩笑》中,“成癮”這個(gè)主題貫穿全文。小說(shuō)中,每個(gè)人物都沉溺于某種東西。哈爾沉溺于大麻,他的父親、祖父和曾祖父酗酒;奧瑞醉心于女人和性;唐·蓋特林酗酒,后又沉溺于德美羅止痛藥, 喬妮沉溺于可卡因。恩里特醫(yī)院的患者都是酒或毒品的成癮患者,結(jié)果協(xié)會(huì)的種種活動(dòng)又成為他們所依賴(lài)的無(wú)法擺脫的新癮因。小說(shuō)中的一些次要人物也沉溺于各自的愛(ài)好,如電視、網(wǎng)球等等。
華萊士從人們對(duì)酒的沉迷、對(duì)毒品的沉迷,擴(kuò)展到現(xiàn)代社會(huì)中對(duì)電視、網(wǎng)絡(luò)、電影以及對(duì)職業(yè)網(wǎng)球賽等的沉迷。他對(duì)這種當(dāng)代社會(huì)的常見(jiàn)現(xiàn)象進(jìn)行哲學(xué)思考,并將之與人的存在結(jié)合起來(lái)。他認(rèn)為成癮是一種毀滅性的享受,摧毀了人的自主性,導(dǎo)致了人的依賴(lài)性,是現(xiàn)代社會(huì)種種問(wèn)題的根源。人們愛(ài)情的失敗,后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冷漠,一直到美國(guó)的政治傲慢等都根源于人們對(duì)某種東西的執(zhí)著和成癮。小說(shuō)中華萊士將這種成癮帶給人的危害物化以及外在化。小說(shuō)中大部分人物都由于成癮而造成這樣或那樣身體上的畸形和殘疾。哈爾由于長(zhǎng)期的網(wǎng)球訓(xùn)練使手臂畸形;奧瑞的足球生涯也使他的膝蓋格外腫大。這些殘酷的訓(xùn)練都是為了迎合人們對(duì)職業(yè)網(wǎng)球和足球賽的沉溺。唐·蓋特林由于嗜食巴比妥,腦袋特大;喬妮吸毒造成臉部受傷;魁北克分裂者都是坐在輪椅上的無(wú)腿的狂熱分子。
“娛樂(lè)”主題是華萊士長(zhǎng)期關(guān)注的問(wèn)題。從后現(xiàn)代派作家開(kāi)始,嚴(yán)肅藝術(shù)和大眾文化的關(guān)系一直是人們探討的焦點(diǎn)之一。華萊士認(rèn)為以電視、電影為代表的大眾文化給人們帶來(lái)輕松的娛樂(lè),就像在一天的疲憊工作后泡個(gè)熱水澡,商業(yè)化的娛樂(lè)是人們?cè)诂F(xiàn)代社會(huì)的一種逃避方式,這種以快樂(lè)為原則的娛樂(lè)使人們的思維懶惰、思想幼稚,不愿去思索人類(lèi)的苦難、失落等深層次的問(wèn)題。電視不僅深刻地影響到人們的生活,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文化對(duì)美國(guó)文學(xué)尤其是小說(shuō)也帶來(lái)很大的影響。他不得不承認(rèn)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文化的重要性:“我認(rèn)為作家,特別是四十五或四十歲的,除非你是寫(xiě)歷史小說(shuō),否則你都不得不考慮大眾文化對(duì)美國(guó)的影響。我并不是把電視看作是我研究的對(duì)象來(lái)觀看,而是認(rèn)識(shí)到電視、廣告、流行文化、媒體、網(wǎng)絡(luò)和資訊交流都已經(jīng)成為我們環(huán)境的一部分。就像一百年前,云和樹(shù)是環(huán)境的一部分一樣。我們根本無(wú)法逃避。”但人們還沒(méi)有完全意識(shí)到潛在的危險(xiǎn)。人們不用付出任何辛勞、思考和努力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享受,而像繪畫(huà)、文學(xué)等嚴(yán)肅藝術(shù)是需要人們經(jīng)過(guò)一定的辛勞才能夠充分地享受的。華萊士指出表面的危險(xiǎn)是嚴(yán)肅文學(xué)的讀者越來(lái)越少,真正的危機(jī)在于人和社會(huì)。 他曾指出,“美國(guó)正處在一個(gè)十分悲慘的時(shí)代,這一切都與娛樂(lè)有關(guān)。”但他認(rèn)為這不是電視的錯(cuò),也不是好萊塢的錯(cuò),同樣也不是網(wǎng)絡(luò)的錯(cuò)。“錯(cuò)誤的根源在于我們自身。我們自己作出了這樣的選擇。我們選擇了更多的時(shí)間沉溺于高科技的機(jī)器,似乎視它們更重于我們的生命。”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警醒人們,這樣我們的未來(lái)才不至于那么冷酷。
當(dāng)然,在后現(xiàn)代派小說(shuō)中,對(duì)大眾文化的擴(kuò)張性的描述并非新鮮的主題,但華萊士將大眾文化與成癮主題以及后現(xiàn)代的個(gè)人身份融合在一起,從而賦予它新的含義和特征。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曾對(duì)比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人的狀態(tài),指出前者的基本狀態(tài)是疏離,對(duì)社會(huì)、對(duì)他人的疏離;而后現(xiàn)代的人們卻根本沒(méi)有自我概念,自我迷失,無(wú)從疏離。小說(shuō)中的哈爾一直試圖向自己,也向周?chē)娜俗C明他的存在,他的個(gè)人身份。他母親艾芙瑞認(rèn)為自己很了解兒子,但哈爾知道自己的內(nèi)心似乎一無(wú)所有,母親所聽(tīng)到的只不過(guò)是她自己的回聲而已。《無(wú)盡的玩笑》里所描寫(xiě)的人們似乎都是“誰(shuí)”一代。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誰(shuí),個(gè)人似乎變成了一個(gè)空洞的容器,不斷擴(kuò)張的大眾文化日益滲透其中。尋找生命的意義就成為當(dāng)代一個(gè)很重要的任務(wù)。天才導(dǎo)演詹姆斯的毀滅就在于他無(wú)法找到生命的意義。他的孩子們稱(chēng)他為“悲傷的鶴”。他的導(dǎo)演生涯就是他艱難地尋找自我的歷程,但結(jié)局是悲觀的。在訪談中,華萊士曾說(shuō),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喚醒讀者,從而意識(shí)到人們?cè)谶@個(gè)消費(fèi)社會(huì)所面臨的困境。
“欲望”這個(gè)主題在華萊士刻意營(yíng)造的極端消費(fèi)的社會(huì)中凸顯得更為深刻。在美國(guó)社會(huì)中,人們只注重自我欲望的追求和滿足,往往忽視了社會(huì)意識(shí)。這種欲望正是這個(gè)時(shí)代的悲哀。所以,盡管小說(shuō)中充滿了大量讓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和嘲諷,但在接受《沙龍》雜志的記者勞拉·米勒的采訪時(shí),華萊士坦陳,他寫(xiě)作的目的是要寫(xiě)一點(diǎn)悲傷的東西。他認(rèn)為這種悲傷的感覺(jué)和人們所處的物質(zhì)環(huán)境無(wú)關(guān),和經(jīng)濟(jì)狀況無(wú)關(guān)。這種悲傷是深層次的,是他在自己和朋友身上所看到的,是一種失落。這種悲傷是典型的美國(guó)式的,是像他這樣的受過(guò)良好教育的中產(chǎn)階級(jí)白人男性身上可以看到的悲傷。
評(píng)論家一直將華萊士的《無(wú)盡的玩笑》與托馬斯·品欽的《萬(wàn)有引力之虹》并舉,但華萊士本人并不贊同這樣的比較。他認(rèn)為,“《萬(wàn)有引力之虹》是一部復(fù)雜的小說(shuō),但它并沒(méi)有做到任何意義上的‘實(shí)驗(yàn)性。”華萊士對(duì)傳統(tǒng)的小說(shuō)的概念做了更徹底的顛覆。他顛覆了傳統(tǒng)的敘事結(jié)構(gòu),整個(gè)小說(shuō)的三條線索都沒(méi)有交代完整的結(jié)局,小說(shuō)也沒(méi)有真正意義上的高潮,因而,有評(píng)論家指出這部小說(shuō)就像是跟讀者開(kāi)的一個(gè)玩笑。華萊士也嘗試了許多技巧,《無(wú)盡的玩笑》中充斥了大量的時(shí)間、視角和行動(dòng)的突然轉(zhuǎn)換,信息的堆砌,多義的技術(shù)術(shù)語(yǔ),大量的注釋?zhuān)⑨尲幼⑨尅uU勃·威克指出,“《無(wú)盡的玩笑》是大衛(wèi)·福斯特·華萊士寫(xiě)作中一次有創(chuàng)造性的突破,也是美國(guó)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的一次突破,因?yàn)樗晒Φ貙⒃囼?yàn)性的小說(shuō)寫(xiě)作技巧與傳統(tǒng)的敘事方式結(jié)合起來(lái)。”(注:鮑勃·威克:“無(wú)盡的玩笑”,《劍橋書(shū)評(píng)》,小布朗公司,1996年。)
《無(wú)盡的玩笑》曾獲南蘭小說(shuō)獎(jiǎng)五萬(wàn)美元和麥克阿瑟基金會(huì)“天才獎(jiǎng)”二十三萬(wàn)美元,還入選美國(guó)《時(shí)代》周刊評(píng)選的1923年以來(lái)世界一百部最佳英語(yǔ)長(zhǎng)篇小說(shuō)。難怪,評(píng)論家卡庫(kù)塔尼在《紐約時(shí)報(bào)》的文章中感嘆:“這部小說(shuō)表明了華萊士不愧是他這個(gè)時(shí)代的偉大作家之一,具有寫(xiě)出任何東西的才能。他可以寫(xiě)有趣的、悲傷的;也可以寫(xiě)嚴(yán)肅的、諷刺的。既擅長(zhǎng)品欽式的宏大的史詩(shī),又熟悉尼科生·貝克式的細(xì)節(jié)描述;既能創(chuàng)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又能描寫(xiě)真實(shí)動(dòng)人的場(chǎng)景。”(注:米凱克·卡庫(kù)塔尼:“無(wú)盡的玩笑”, 《紐約時(shí)報(bào)》,1996年2月13日。)
(王海燕,廈門(mén)大學(xué)外文學(xué)院博士生,武漢理工大學(xué)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副教授 郵編:430070;楊仁敬,廈門(mén)大學(xué)外文學(xué)院博士生導(dǎo)師,教授 郵編: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