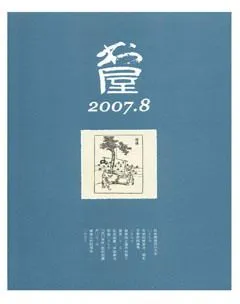大話唐僧和孫悟空
記得幾年前在學校圖書館的中文部亂翻,讀到一本錢穆老先生的演說集,其間提到《西游記》,大意是說《西游記》中的四個人物,其實就代表中國人的四種人格類型和社會現實:孫悟空本領高強但難管;唐僧身無絕技,但意志堅強,只有以唐僧的造詣、意志和地位,對孫悟空加以規范,方可成就西天取經的事業。當下恍然大悟,覺得錢穆道破了“外行管內行”這條潛規則的核心所在——本事大的人脾氣大,不由統領全局的人罩著不行。但那時對唐僧——小說中的而不是歷史上的——的佛法造詣仍是深信不疑。
最近的一次重讀《西游記》,不僅對這唐僧的所作所為愈加反感,而且對他的佛性也深表懷疑,進而相信,在小說中,孫悟空才是真正的高僧和主角,而不僅僅是唐僧的貼身保鏢。
這二人是如何入的佛門?先看唐僧。《西游記》遲至第十一回才提到唐僧,講他“自幼為僧,出娘胎,就持齋受戒;他外公是當朝一級總管殷開山;他父親陳光蕊,中狀元,官拜文淵閣大學士……查得他根源又好,德行又高,千經萬典無所不通,佛號仙音無般不會”。看上去,唐僧在取經的四人中履歷最清白,家庭出身最根正苗紅,個人成分最純潔。但反過來看,出娘胎就受戒說明唐僧只是陰差陽錯,因緣際會,因為個人的特殊經歷——“投胎落地就逢兇,未出之前臨惡黨”——做了和尚。其家世是受了迫害的唐朝高級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與俗世和政治瓜葛自是極深,其出身和道路都無從選擇。反觀孫悟空,原本就是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一開始就盡斷塵緣,哪來諸多羈絆。孫悟空的皈依,也不是因為“自幼”就被和尚收養而成了“自來紅”,而是有一天忽然起了一種存在主義的痛苦。那天,悟空正與轄下群猴開派對,喜極而悲,“忽然憂惱,墜下淚來”,原來是想到了人生的無常和輪回的恐怖,決定云游求道,“學一個長生不老,常躲過閻君之難”。這段描述出現在《西游記》開篇的第一回,一開始就表明,孫悟空求佛,完全是基于自己想要斷輪回的內心驅動。是對人生悲涼的瞬間感悟和對本心的自覺追尋,促使孫悟空放棄其“稱王稱祖”的花果山山大王這份“很有前途的職業”。
歷史上的玄奘和尚是自己前往印度取經,勿庸他議。但在小說中,取經這件事根本不是唐僧的主動追求。小說第七回中記敘如來佛祖在大雷音寶剎召集菩薩們開會,會上如來沉痛地批評了東土尚有“多殺多爭”的現象,提到自己有三藏真經,可以勸人為善。佛祖本想自己送經上門,又覺得太便宜了東土的蠢人,于是決定賣個關子,“去東土尋一個善信,交他苦歷千山,詢經萬水……到我處求取真經,永傳東土,勸化眾生……”正是在如來決策后,經由觀音親自出馬,唐僧才被指派執行這一任務,而且由唐太宗親自批準。太宗對唐僧相當滿意,尤其在他確認玄奘“學士陳光蕊之兒”的身份以后。這樣一來,在小說中取經作為一項不惜一切代價都要完成的政治任務的意義已經超過了求道的宗教意義。因此,第十二回唐僧辭別太宗時是這樣表決心的:“貧僧不才,愿效犬馬之勞,與陛下求取真經,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唐王一感動,決定和唐僧結為把兄弟,這下玄奘更是感恩戴德到不惜詛咒自己:“我這一去,定要捐軀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經,即死也不敢回國,永墮沉淪地獄”,因為“受王恩寵,不得不以盡忠以報國耳”。上路以后,唐僧每遇人問,必說“弟子乃東土大唐奉圣旨往西天拜活佛求真經者”一類話,屢屢強調“奉旨”,在第十六回的觀音院中,更徑直自稱“東土欽差”。法門寺僧人問及取經的緣由,唐僧先答以“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緊接著卻又說“愿圣王皇圖永固”。一半為佛,一半為帝。唐僧不僅對唐太宗如此,在取經途中,見了寶象國國王竟然也不住地叩頭,道“陛下,貧僧該萬死,萬死”。對比之下,孫悟空完全無視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們的權威。從名字來看,“悟空”之法名得自他真正的師父須菩提祖師,其間大有深意。悟到頭,不正是一切皆空嗎?而“三藏”則是唐太宗為送別時為玄奘御賜的,取自要取的經名,完全現實和功利。既然西天取經的政治意義更大,應當記住的是,孫悟空的師父應當是給他取了法號,教會他七十二變的須菩提祖師,他和唐僧的關系毋寧說是臨時被撮合的雇主和雇員,或者拍檔的關系。錢穆闡明的“潛規則”,也只能在這一關系下才能得到理解。試想,須菩提祖師需要動用緊箍咒來對付孫悟空嗎?
取經隊伍本身就是用行政手段脅迫、誘騙和討價還價維系的。三個徒弟外加白龍馬原本都只是為贖罪,也可稱“變相勞改”。孫悟空護送唐僧取經,就不是真仰慕其道行,只是迫不得已,因為護送唐僧是觀音賜予的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出發不久,師徒第一次因殺人而產生爭辯,悟空感到和唐僧無法合作,就撂挑子,炒了唐僧的魷魚。龍王勸悟空的理由是,不保唐僧,你自己成不了正果,悟空才勉強說“老孫還去保他便了”,可見保唐僧是手段,自我救贖是目的。唐僧為孫悟空戴緊箍一節,則極顯其詭詐荒唐。他拿出觀音給的衣帽準備讓悟空穿,悟空問,是否從東土帶來,唐僧竟順口說:“是我小時穿戴的。這帽子若戴了,不用教經就會念經,這衣服若穿了,不用演禮就會行禮。”在后來的段落中,唐僧又曾說,“我們是出家人,休打誑語”,而用如此明顯的欺騙和謊言哄騙他人,不知唐僧何以自解?第十五回孫悟空第二次想辭職不干時,向觀音投訴,說“西方路這等崎嶇,保這個凡僧,幾時去得?”“凡僧”一詞足見唐僧在悟空心中的地位,然而觀音這一次為了穩住悟空,一是許諾關鍵時刻出手相救,二是免費贈送三根救命的毫毛,才再次籠絡成功。即便在豬八戒眼里,唐僧也沒有什么權威,一旦他老豬急吼吼地要脫離隊伍,去做上門女婿時,就對那婦人聲稱“不用(和唐僧)商量。他又不是我的生身父母,干與不干,都在于我”。另一方面,唐僧也委實缺少領導風范,他最怕的就是徒弟闖禍后,“卻帶累我在此受罪”。不時卻又居功自傲,比如,以孫悟空的救命恩人自居,要求對方為自己化齋,又深具佛家本需去除的分別心,嫌豬八戒相貌丑陋,不敢帶八戒朝見寶象國國王。等到悟空救了他,要感謝了,說的卻是“奏唐王,你的功勞第一”,實在是其俗在骨。
孫悟空屢屢因為殺妖除魔被唐三藏責難,似乎后者特別宅心仁厚,或者對于暴力的使用有不同的理解。其實不然。師徒剛上路不久,遇到一只猛虎,嚇得唐僧癱軟在地,被鎮山太保救出。太保一番惡戰打死了老虎后,本已殺生,唐僧卻因為自己的性命被救而“夸贊不盡”。第二次遇虎,孫悟空當頭一棒,打得老虎腦漿迸裂,唐僧也不曾有半點憐憫,反而大聲叫好:“今日悟空不用爭持,把這虎一棒打得稀爛,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唐僧似乎更不提佛家尚有以身飼虎的故事。但是等到悟空打死了六個毛賊,唐僧突然又變得道貌岸然起來:“出家人‘掃地恐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我這出家人,寧死也決不敢行兇。”孫悟空此時所遵循的,并非不殺生的教條,而是最簡單的理性:“師父,我若不打死他,他卻要打死你呢。”對孫悟空來說,盡職地保護唐僧,揚善懲惡,比恪守不殺生的教條來得重要。從另一個角度講,殺妖除魔的過程中生與死本身也是虛空。第十八回悟空得觀音親自點撥:“悟空,菩薩妖精,總是一念,若論本來,皆屬無有。”于是,“悟空心下頓悟”。甚至可以說,孫悟空所進行的所有殺戮和暴力,其實都是他自己意念中的幻象,在這一點上,唐僧對暴力的理解仍然囿于世俗的現象世界。和悟空的明心見性相比,唐僧則著實是一個“俗眼愚心”的凡人。第二十四回,唐僧見了人參果戰戰兢兢,作者借道童清風的心理活動批評:“這和尚在那口舌場中,是非海里,弄得眼肉胎凡,不識我仙家異寶。”
唐僧心性遠未達至境,一直被現象世界困擾,很多時候甚至需要孫悟空來教育他。第三十六回中,身為領導的唐僧竟然開口抱怨“西天怎么這么難行”,擔心“魔障侵身”,卻是孫悟空開導他:“師父休得胡思亂想,只要定性存神,自然無事。”唐僧在寶林寺夜間讀經,悟空卻說:“師父差了,你自幼出家,做了和尚,小時的經文,那本不熟……如今(真)經未曾取,你念的是那卷經?”唐僧卻答道:“小時的經文恐怕生了。”二者對佛學的理解實在不同的層面上。對唐僧來說,讀經誦經最是要緊,而且必須“學而時習之”,但恰恰不能領會經的本意,而孫悟空則完全依靠直指本心,相信功到自然成的悟性。不僅如此,在第四十三回中,孫悟空還專門點出《多心經》的核心是“無眼耳鼻舌身意”,批評唐僧忘記了這句話,太“念念在意……招來六賊紛紛”。第四十七回,當唐僧又在途中問起“今宵何處安身”的時候,悟空搶白道:“師父,出家人莫說那在家人的話。”整個取經過程,對唐僧來說,其實是一個成就功名的機會,他甚至宣稱:“世間事惟名利最重。似他為利的,舍生忘死;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為名,與他能有幾何。”因此,孫悟空在第九十三回中談《心經》,又明確批評師父為只是念得,不曾解得。
唐僧在小說中的形象其實是一個儒家士大夫。道行雖然不夠高,但唐僧向來以守身如玉不近女色為人稱道,在道德上是個典范的正人君子。但恰恰是在這里,《西游記》中寫了數段極短卻堪稱心理分析經典的精彩情節,使得此人的復雜性大增。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戲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中,妖精變成美女,唐僧卻堅決認為是個好人,女菩薩。一般人總以為這是唐僧糊涂,善惡不辨,甚至善良的例證,但孫悟空卻毫不客氣地剖析道:
師父,我知道你了,你見她那等容貌,必然動了凡心。若果有此意,叫八戒伐幾棵樹來,沙僧尋些草來,我做木匠,就在這里搭個窩鋪,你與她圓房成事,我們大家散伙,卻不是件事業,何必又跋涉取甚經去!
其實,孫悟空在小說中的一個角色是作為唐僧的觀察者和研究者。他一開始就沒有認為唐僧是一個真正的高僧,一路上又屢次看到他的心驚膽顫,缺少定力,膽小怯弱,更加相信唐僧內心是個俗人,不僅在第四十三回看穿而且點出唐僧“思鄉難息”,盼著早日榮歸故里,更率先看透他有和凡人一樣的情欲。他可以容忍打死老虎,卻不能容忍打死美女,誰能說這悲憫、這善良中間沒有性心理的作用?這個“慈憫的圣僧”只能把內心泛起的一點點愛欲的漣漪,用無原則的善良和師父的威嚴包裹起來,卻又被火眼金睛的大徒弟識破。或者有人會說,孫悟空是“憑空污人清白”,但唐僧在聽了此話后的反應恰是被人說破心事后的“羞得光頭徹耳通紅”,而且孫悟空已經掣棒開打,唐僧居然還在“羞慚”,尚算面皮薄,但竟無一句辯駁,顯然是默認了悟空的指控。第五十四回,就是被女兒國國王誘惑的一節,女王來拉唐僧,唐僧先是“耳紅面赤,羞答答不敢抬頭”,一番俏語嬌聲,就立馬“戰兢兢立站不住,似醉如癡”。唐三藏的性心理,書中還有一處寫得精妙絕倫:第七十二回寫盤絲洞,唐僧自己出門去化緣,結果看見三個女子在踢氣球。作者先寫了一大段詩來詠這些“翠袖”、“金蓮”之后,輕輕著一句“三藏看得久了,只得走上橋頭……”一個癡癡的“久”字,境界全出。結果是唐三藏又被眾妖女綁架,吊在梁上,一邊忍著疼,噙著淚,一邊“那長老雖然苦惱,卻還留心看著那些女子”。審美的快感可能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肉體的痛楚(有沒有受虐的生理快感則未可知)。想那唐三藏也是一個健康的壯年男子,自幼出家,環境和信仰都不允許他接近女性,更不許產生非分之想,直到取經的路上才眼界大開,見識各路美女,但又要時時刻刻天人交戰,杜絕誘惑,“固住元陽”,以免大節不保,半世英名毀于一旦。他的背景,他的身份,他肩負的政治和宗教雙重使命都不允許他像豬八戒那樣鬧出緋聞!但他的修為,卻不足以像孫悟空那樣完全擯棄欲望,這也是一種“意淫的哀傷”罷,而他的執著,又是不是緣自被壓抑的荷爾蒙呢?
唐僧一直到小說最后都執迷不悟,境界沒有獲得真正的提升。小說第九十八回,又是孫悟空指出唐僧拜假境界、假佛像,卻不識真境界、真佛像。待到歷經周折,取了有字真經返回,石頭把《佛本行經》粘住了幾卷,唐三藏感到懊悔,孫悟空卻解道,天地不全,經粘破了乃是應不全之奧妙。最后,師徒全體功德圓滿,才由如來親自出面曝料,透露關于唐僧的內幕消息:他原是如來二徒弟金蟬子,因為不聽說法,輕慢大教,被貶下界,轉生東土。這個履歷似乎又把唐僧拉到和三個弟子連同白龍馬同等的位置上——原來他前世也是一個犯了天條的調皮鬼。但畢竟當過如來的二弟子,無論如何還是一層很硬的關系,又歷經九九八十一難的基層鍛煉,唐僧這個無論在天界還是俗世都有很不錯的背景的精英人士成佛是理所當然的。唐僧和孫悟空師徒二人在全書最后公布的諸佛名單(并不依姓氏筆劃為序)中,竟排列在觀世音之前。
孫悟空終于靠護送唐僧成了佛,了斷輪回,唐僧與孫悟空的師徒關系也就此結束。不過到最后,孫悟空也只記著趕緊把緊箍去掉,沒說一句謝恩的話,因為他心里就從沒有真正看得起唐僧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