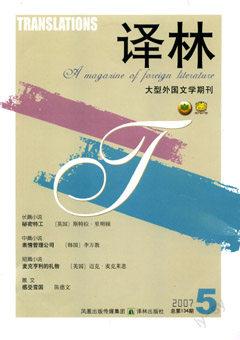論黑暗中的微光:解讀《愛的療藥》
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是當代最多產、最重要、文學成就最高的美國印第安人女作家。她的創作涉及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和兒童文學等,尤以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見長。她至今已出版10部長篇小說,其中《愛的療藥》(獿ove Medicine,1984,1993)、《甜菜女王》(玊he Beet Queen,1986)、《痕跡》(玊racks,1988)、《賓戈宮》(玊he Bingo Palace,1994)被稱為厄德里克的“北達科他四部曲”。這四部曲如果按照故事發生的時間順序排列的話,應該是《痕跡》(1912—1924)、《甜菜女王》(1932—1972)、《愛的療藥》(1934—1984)、《賓戈宮》(1981—1995)。其余6部是《燃情故事集》(玊ales of Burning Love,1996)、《羚羊妻》(玊he Antelope Wife,1998)、《小無馬地的最后報告》(玊he Last Report on the Miracles at Little No Horse,2001)、《屠宰師傅歌唱俱樂部》(玊he Master Butchers Singing Club,2003)、《四顆心靈》(獸our Souls,2004)和《著色的鼓》(玊he Painted Drum,2005)。
《愛的療藥》獲1984年美國全國書評家協會獎,該獎與美國全國圖書獎和普利策獎并列為美國三大圖書獎。厄德里克從此名聲大噪,鷹揚文壇。1985年,該小說又獲得《洛杉磯時報》小說獎。《屠宰師傅歌唱俱樂部》于2004年入圍國家圖書獎。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是她的長篇小說,其實厄德里克同時也是一個杰出的短篇小說家。《愛的療藥》由十八篇短篇小說組成,其中大多數在《愛的療藥》成書前已經單獨在文學雜志上發表過。開首篇“世上最了不起的漁夫”于 1982年獲得納爾遜·阿爾格倫短篇小說獎,次篇“圣徒瑪麗”曾發表于《大西洋月刊》,獲1985年歐·亨利短篇小說獎。她于1985年、1987年、1998年、2001年、2002年和2006年六次獲歐·亨利短篇小說獎,這在美國作家中是相當罕見的。
厄德里克與美國現代小說家福克納至少在以下四點上極為相似,軒輊難分:1.濃郁的地方特色。福克納的小說大都以他熟悉的南方為題材,創作了“約克納帕塔法”世系,而厄德里克以北達科他州齊佩瓦人居留地為背景,創作了“北達科他傳奇”;2.“約克納帕塔法”世系與“北達科他傳奇”都描述了數個家族幾代人的沉浮;3.福克納和厄德里克部分作品采用多角度敘事;4.兩位作家都曾創作過由短篇小說構成的長篇小說。
《愛的療藥》是迄今為止厄德里克的所有作品中被研究和討論得最多的一部,也是公認的文學成就最高的一部,成為美國族裔文學研究的主要文本之一。該小說初版由十四篇短篇小說構成,1993年重版時,另加入了四篇,分別是《小島》(玊he Island)、《復活》(玆esurrection)、《戰斧工廠》(玊he Tomahawk Factory)和《萊曼的運氣》(獿yman餾 Luck)。小說的特殊敘事方式受到幾乎所有評論家的關注。有的評論家認為這僅僅算得上一部短篇小說集,不能稱為長篇小說,因為它沒有聚集的中心敘述,沒有情節的發展,故事之間沒有內在的統一性;也有評論家認為,正如小說1993版的封面上所說的那樣(《愛的療藥》:一部長篇小說),這是一部由短篇小說構成的長篇小說,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長篇小說,小說的統一性主要體現在主題上,十八篇短篇小說是由“愛的療藥”這一主題連貫而成的。
在小說里,厄德里克將爐火純青的短篇小說技巧發揮得淋漓盡致。敘事的視角在不斷變化,但關注的對象不變。厄德里克借幾代人之口再現了現代和當代印第安人的毫無生氣的物質生活和苦悶的精神生活。一般讀者習慣于傳統的、線性的、中心聚焦的作品。因此,閱讀《愛的療藥》對讀者是一種挑戰,讀者必須調整閱讀姿態,參與到閱讀之中,不斷填補空白,對矛盾的說法作出自身的判斷。
《愛的療藥》以北達科他北部靠近加拿大邊境的齊佩瓦人居留地為背景。有人說,小說的背景似乎是以厄德里克所熟悉的龜山居留地(Turtle Mountain Reservation)為原型的。但研究者發現,小說里的居留地的位置在北達科他州境內,但與實際存在的地方,如法戈、威利斯頓等之間的相對關系飄忽不定,與龜山居留地的實際位置并不重疊。厄德里克似乎有意模糊虛構的印第安居留地的位置。小說里故事發生的時間跨度長達五十年(自1934年起至1984止)。十八篇短篇小說里共有二十個故事(第一篇和最后一篇各有兩個敘述者,可以分別看作兩個故事),其中十三個故事由人物敘述,七個故事由作者本人敘述。除第一篇以外小說是按時間先后安排的。小說涉及喀什帕、拉扎雷、納娜普什和莫里西四個家族。尼科特·喀什帕、伊萊·喀什帕、瑪麗·拉扎雷、露西·拉扎雷、露露·納娜普什、摩西·皮拉杰等是第一代人;尼科特和瑪麗的孩子高迪、塞爾達,露露的兒子小亨利、萊曼、蓋瑞以及瓊·莫里西等是第二代人;蓋瑞和瓊的兒子利普夏、高迪和瓊的兒子金等則是第三代人。
厄德里克的筆觸始終聚焦于齊佩瓦人居留地上的印第安人。美國政府于19世紀30年代推行居留地制度,將大批的印第安人趕出家園,安置在貧瘠的西部,這是印第安人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一場浩劫。居留地成為白人對印第安人經濟掠奪和文化入侵的前哨。在殖民者來到北美大陸以前,印第安人大都以漁獵為生,馳騁在廣袤的大地上,與自然和諧共生,沒有私有觀念。美國政府推行居留地之后,印第安人流離失所,惜別家園,來到陌生的地方。他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不能再漁獵,只能以種植為生,成為自耕農。
居留地無異于白人的“文明生活”中的一個個孤島。印第安人距“文明”越近,痛苦就越深。1887年,美國通過《道斯法案》,這一法案對印第安人更具毀滅性。《道斯法案》推行后,本來就非常狹小的居留地又一次遭到了白人的覬覦,印第安人的土地被白人騙取,生存空間進一步壓縮。印第安人在失地的同時,還被迫引入私有制,形成了部落成員的個體化和部落土地的私有化。為徹底同化印第安人,白人還專為印第安人開設全日制和寄宿制學校,灌輸白人文化,從文化上對印第安人進行斷根,使印第安人從“野蠻”歸化到“文明”,從“原始”進化到“現代”。
文化上的同化和經濟上的掠奪意欲將印第安人逼入死胡同,斬斷他們的文化之根。這標志著印第安人美夢的結束,噩夢的開始。人們無比懷念往昔。小說中最活躍的、最引人注目的是齊佩瓦女性露露。她大膽、潑辣,面對白人和部落的壓力毫不畏懼。她感慨道:“我們都搬過多少次家了?齊佩瓦人是從五大湖對岸搬到這兒來的……過去外婆常告訴我們,我們是如何被硬生生地趕到這個孤寂的角落里來的……往西搬一英尺我都不愿意。” 她與瑪麗有一幫狂熱的追隨者,主張回到白人入侵之前的野牛時代。
厄德里克描述了一幅讓人窒息的圖畫。居留地上的生活是了無生趣的,土地是貧瘠的,滿眼凋敝、蕭條和肅殺:修道院是破舊的,納娜普什的破泥屋搖搖欲墜,露露住在政府安排給她的活動安置房里,摩西·皮拉杰離群索居,一人獨居在山洞里,過著非常人的生活。由于空間狹小,精神空虛,高迪因酗酒而中毒;露露與多個男人濫交;居留地上失業率很高,艾伯丁和金走出了居留地,但前途未卜。在這一毫無生氣、以深黑為底色的畫面上很少見到光亮。
厄德里克在這已漆黑的底色上又通過描寫非正常的死亡讓黑暗深不見底,讓讀者喘不過氣來。小說是在瓊·莫里西從威利斯頓準備回到居留地開頭的。與丈夫離婚的她在酒吧中結識了白人青年安迪,酒后與安迪發生了性關系,因遭遇暴風雪而慘死在路上;尼科特在妻子瑪麗的勸說下,生吃雄火雞的心而被噎死(瑪麗認為自己吃雌火雞的心,同時讓丈夫吃雄火雞的心可以讓丈夫回到自己身邊);高迪向母親討酒不成而飲消毒水自殺;露露的兒子小亨利越戰后歸來精神錯亂,無法從血腥的戰爭回到現實,永遠擺脫不了對戰爭的回憶,為自己參加了一場“光榮”的戰爭而悔恨交加,整天對著電視機發呆,最后投河自殺;露露的丈夫老亨利慘死在鐵軌上。小說中出現過三次葬禮(瓊的、老亨利的、尼科特的)。這些陰森慘淡的畫面讓人動容。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家庭成員只有在葬禮上或者葬禮后才有機會團聚。死亡,不斷的死亡,而且是非正常的死亡,這些都讓小說充滿著讓人透不過氣來的氛圍,讓讀者不禁為印第安人的命運一掬同情之淚,為他們的未來深深擔憂。
小說中的死亡是作者獨具匠心的安排。厄德里克還借人物之口,對居留地制度、《道斯法案》、美國的司法制度、種族歧視等進行猛烈的抨擊。露露是印第安傳統文化的堅定捍衛者,她對美國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極盡嘲諷之能事。她說:“我從不讓普查員進我的家門,哪怕他們說是為印第安人好。要我說,每次他們統計出人數,也就是知道了還要除掉多少人。”尼科特被好萊塢招去做演員,讓他抱緊胸,從馬上摔下來。尼科特嘲諷道:“印第安人在電影里最多只能扮演死人的份。”為了賺錢,他脫得精光,為一個白人婦女做模特,這讓他想到“只有死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
戰斧工廠倒閉后,萊曼幡然醒悟:“他們(白人)把分文不值的土地拿給你做生意,然后再從你腳下硬生生地搶走;他們把你的孩子帶走,灌上滿嘴的英語;他們把你的兄弟送進地獄,把他榨干了再送回來。他們用酒換你的皮毛,然后再告訴你不能喝酒。”萊曼還說,白人曾經耕種過印第安人的土地,搶過印第安人的飯碗,看著鄰居受窮,自己過著優裕的生活,他們甚至從沒正眼看過那些挨餓的、迷茫的印第安人。
露露最為驕傲和自豪的兒子蓋瑞是小說中形象最豐滿的人物。他天生是個領袖,步伐輕快,充滿力量。他和一個牛仔爭論齊佩瓦人是否也是黑鬼時,朝牛仔的睪丸踹了一腳,被判了三年。艾伯丁說:“如果白人目擊者支持的話,他們是很好的目擊證人,因為他們有名字、住址、社保號和工作電話。但如果他們不幫你忙的話,就和請印第安人目擊者作證一樣,是十分可怕的。”艾伯丁在小說中充滿了對種族歧視的不滿:“對于初犯,三年偏重了,不過對于印第安人來說,還不算重。”這無疑是對美國司法制度最大的嘲諷。蓋瑞是印第安人運動的領袖,在越獄方面很有天賦。他自夸地說:“沒什么狗屁的鋼筋混凝土房子困得住齊佩瓦人。”他雖然長得高大,卻能像鰻魚一樣從監獄里逃脫。在厄德里克筆下,他是一個來無影去無蹤的英雄。他的話切中要害,直擊美國的種族歧視和種族迫害:“社會公平嗎?社會就像我們打的這場牌,兄弟。我們的命運在出生之前就決定了,就像發牌之前已經洗過牌了,而長大的過程就是一個盡量把牌打好的過程。”
這些敘述是沉重的,是從印第安人心底爆發出的聲音,描繪的是他們心中同樣黑暗的畫面。微光出現在“萊曼的運氣”這一篇,也就是倒數第二篇,已接近小說的尾聲。在反抗美國政府的印第安政策的時候,新一代的印第安人已漸漸明白如何在保持“印第安特性”(Indianness)的同時面對現實。露露的兒子萊曼是個典型的例子。戰斧工廠由于經營不善而倒閉之后,他深刻反省:“是時候了,真的是時候了。印第安人該學聰明了,該學會利用聯邦法律這個他們手里唯一的砝碼了。”他準備開發自己的項目,教齊佩瓦人怎樣正當地、彬彬有禮地從那些退休的白人手里把錢賺過來。萊曼繼承了父親尼科特賺錢的本事,認識到金錢是同化別人的關鍵:“為什么不能讓錢生錢呢?就靠人們的狂熱、企圖,還有幸運之神大賺一把吧!”萊曼計劃開賭場,碰碰運氣,還準備辦個大抽獎,中獎率高得連加拿大人都拋下家人和莊稼不管,他想象著錢像潮水一樣匯集到部落的戶頭上。萊曼已經懂得如何面對現實,通過自身努力來改變自身的命運。
小說名為“愛的療藥”,也是第十三篇短篇小說的篇名。顯然,“愛的療藥”無論是作為整個小說的篇名還是短篇小說的篇名,都是極富深意的。筆者對厄德里克的小說中“愛的療藥”這一短語出現的頻率進行了統計:在《愛的療藥》中出現過十三次,在《痕跡》中出現過兩次,在《賓戈宮》里出現過七次,在《燃情故事集》中出現過七次,在《小無馬地的最后報告》中出現過一次,在《四顆心靈》中出現過二次。在《賓戈宮》里,利普夏的情人肖尼對他說:“你有了療藥,但你得不到愛。”在“愛的療藥”這個短篇中,自認為有超能力的利普夏急于讓外公尼科特回到外婆瑪麗的身邊,想方設法制造“愛的療藥”,他想按照古老的藥方配制,但找不到藥方中所說的材料。他又突發奇想,準備去捕捉兩只黑額黑雁(因為這種鳥終生成雙成對),不成后,他又去商店買了兩只火雞,將雞心挖出,讓外婆和外公生吃。具有諷刺的意味的是,外公被生雞心噎死。這一未曾預料的后果逼著利普夏思索。一天,外公的靈魂回來看外婆,利普夏這才恍然大悟,明白愛是沒有捷徑的:“不是愛的療藥讓外公回心轉意的,外婆。是別的東西。他對您的愛超越了時空,但他走得太快,根本沒機會對您說,他愛您,他沒怪您,他明白您所做的一切。是真實的情感讓他回來的,根本不是什么魔力。”
在小說中,在有的家庭中成員之間并不存在血親關系。瑪麗收養了妹妹的小孩瓊,還收養了兒媳瓊與蓋瑞生的兒子利普夏;納娜普什收養了露露;當瓊覺得更適合與伊萊一起生活時,伊萊收養了她。瑪麗與露露原是情敵,勢不兩立,但當尼科特死后,兩人捐棄前嫌,露露的眼睛接受手術后,瑪麗幫她滴眼藥水,露露深情地說:“她像座朦朧的大山,慢慢地俯下身來,身形模糊龐大,在剛出生的嬰兒眼里,母親一定也是這樣的吧。”瑪麗的婆婆拉什貝爾對她刁蠻兇狠,兩人關系很僵,但當瑪麗分娩時,拉什貝爾非常關心,這化解了兩人之間多年的冰凍。瑪麗說:“每次見到她,我都知道她是我的母親,是我的家人,她所做的一切超越了我們之間脆弱的關系。”
小說開頭,利普夏不知自己的身世,始終無法原諒母親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將他扔進沼澤地。他奶奶告訴他,他母親當時并不是要將他淹死,而是她當時不知所措。真相浮出水面時,利普夏原諒了母親。在小說的最后一章,他開車載著母親的靈魂返回了居留地。
利普夏和外婆瑪麗重新認識什么是愛的療藥,瑪麗與露露恩恩怨怨結束了,利普夏諒解了母親,沒人要的孩子也可以投入溫暖的懷抱。通過這些,厄德里克為整幅以黑色為底色的畫卷抹上了一絲光亮:愛在心底,不能借助外力;愛的療藥只存在于寬容、諒解、訴說和傾聽;愛才是真正的療藥;愛是印第安人黑暗生活中的明燈;因為有愛,印第安人才能堅強地存活。
(張廷佺: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2005級博士研究生郵編:2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