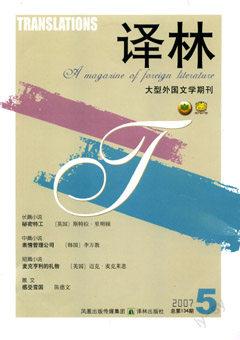感受雪國
陳德文
“穿過國境長長的隧道,就是雪國了。夜空底下變得一片白茫茫。”
這是川端康成的小說《雪國》開頭的名句。讀《雪國》,就想去雪國。作家醉心描寫的,究竟是怎樣一塊神奇的土地?有著什么樣的風景?那里生活著什么樣的人群?
常年的疑問,常年的誘惑,常年的癡迷。于是,便有了一次雪國之旅。
還記得這部小說嗎?簡練的故事,朦朧的人物,迷離的山景,飄忽的文字……《雪國》在現代日本文學史上獨樹一幟,占盡風流,惹得不同層次的文化人評說不盡。推崇者有之,貶斥者有之,不褒不貶、以平常心對待者有之。但不論采取哪一種態度,誰都無法忽視它,抹消它。在當今尚沒有任何一種獎賞能夠替代權威性的諾貝爾獎的時候,《雪國》和它的作者無疑是一個榜樣,一座豐碑,一種品牌,具有恒久的魅力。
古今中外,文學的力量是巨大的。當川端康成帶著他的《雪國》走向世界文學高峰的時候,誕生《雪國》這個藝術香馨兒的搖├骸—越后湯澤這塊自古封閉的山澗谷地,便成了人們趨之若鶩的文學的“麥加”。
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不溫不火,不及不離。欲進復退,欲言又止。蒼狗白云,鏡花水月……這就是我讀《雪國》的感覺。久而久之,縹緲的《雪國》之感漸漸沉滯下來,“固化”成“新睸”、“越后”和“湯澤”等這些實實在在的地名了。
在這種逐漸“固化”的過程中,我切實體驗了我們中國人常有的“京華何處大觀園”般的追尋和發現的快樂。當然,故事的舞臺誰都知道,盡管書中沒有涉及。不過,要想深刻地感受作品,就得到故事的舞臺上去,進入角色。帶著此種想法,我來到了越后湯澤。
初冬季節,平原上還是晚楓如火,高山里已經冰封雪裹。我走的路線和小說男主人公島村去雪國的路線正相反。川端康成首次訪問湯澤是1934年6月,走的是由南向北的路。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由水上的一手前車站,乘火車到上牧溫泉,……接著又在旅館老板的建議下,去了一趟越后湯澤。那里比水上更加偏僻。”作品開頭提到的“國境的隧道”就是群馬縣和新睸縣之間三國山脈的清水隧道。這條隧道長約10公里,始鑿于1922年,歷時九年建成。由水上穿過清水隧道進入湯澤,猶如漁人進入桃花源,眼界豁然開朗,風景也隨之一變,完全是另一個世界。尤其在冬天,四周蒼山負雪,宛若蓮花朵朵,冷、艷、奇。
我們的汽車從北方的津南町沿353國道漸漸駛入湯澤町。這里離去年“中越地震”的中心小千谷不算遠,我發現這一帶的房屋建筑很特別,房頂呈銳角形,北面窄而陡,南面闊而緩,正如《雪國》中島村所看到的:
“家家都伸出來長長的庇檐,一端由柱子支撐著,站立在馬路上。和江戶城的所謂‘店下差不多。這地方過去叫做‘雁木,雪深的時候,這庇檐下就成了通行的道路……”
書里的描寫,眼前的情景,使我想起廣州的街道,覺得很相像。不過,廣州是為了躲雨,而這里是為了防雪。自然環境的酷烈,考驗著生命的強度,激發著人類創造的智慧。幾年前連續下了幾場大雪,津南地方雪深達3.89米,出現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嚴寒天氣,我想起不久前親自到過的這處地方,才真正掂量出“雪國”這兩個字的分量,對那些豪雪擁門而毅然堅守故鄉、同自然災害英勇搏擊的民眾不由得肅然起敬。
江戶時代,生于越后的鈴木牧之(1770—1842)在《北越雪譜》一書中寫道:“凡日本國中第一深雪之地,乃越后也。古昔今人皆持此說。然越后雪深達一二丈者,唯我魚沼也。”他說的完全是實話。魚沼是產米之鄉,著名的“魚沼粳米”享譽國內外,市場價格比其他名牌大米高出一倍。魚沼米之所以美味,就是因為這里冬期長,氣溫低,雪水足。
傍晚,抵湯澤,下榻于湯澤驛附近的波斯利亞飯店。此處距當年川端康成寫《雪國》的高半旅館約有十分鐘的車程。高半旅館原由一位名叫高橋半左衛門的人創辦,至今已有八百年歷史。這是一座典型的和式溫泉旅館,位于湯澤地區最高點,溫泉水量最豐沛,常年不減。館內有一間屋子,叫“霞之間”,這里就是川端康成創作《雪國》的地方。屋內布置依舊原樣不變,一張矮桌,一把無腳背靠椅,左手一只暖爐,一只煙盤,墻上懸著字畫。湯澤還有許多同《雪國》有關的景點,如“駒子之湯”、“雪國館”、“雪國之碑”等。
江山還需文人扶,一個富于人文內涵的地方,自然會產生一種巨大的吸引力和昭示力,昔日寂靜的高原小鎮,今天成了人氣旺盛的觀光名所。近年,又開通了東京上野至新睸的上越新干線,巨蟒般的電車的呼嘯聲,震動著千年寂靜的云山野水,驅散了現代駒子們的歡聲笑語。雪夜,泡在飯店十三樓頂的“露天風呂”里,我沉下心來,望著四面黑??的山巒,想慢慢找回當年藝伎們幽怨的歌唱和三味線悲切的琴音。然而,除了眼前氤氳的水汽和耳邊呼嘯的朔風,什么也沒有得到。我的努力也像作品主人公島村一樣,最后化作了一個接一個的徒勞。
一度雪國行,勝讀十遍書。在雪國之地,讀《雪國》之書,更有一番親切的情味。我感到,用思想性和藝術性的慣用標準來評價《雪國》,則不得要領。我以為,理解《雪國》,只能憑借直接感覺。空靈,冷艷,虛幻,迷茫。主觀取代了客觀,自然淹沒了人物,影像淡化了實體,感性排除了理智。作品的美質不正潛隱于這種剪不斷理還亂、說不清道不明的晃漾著的混沌之中嗎?這,就是我對《雪國》乃至整個川端文學的認識,或者稱為評價。
川端自己說過:“島村不是我,甚至不是實際存在著的一個男人。他也許只是映射駒子的一面鏡子。”
這部小說開頭用大量文字描寫葉子映現在車窗玻璃中的幻影,真是不厭其詳,讀得我們頗有些膩味。我所厭皆作者所愛,徒嘆奈何而已。也許這就是我們和作者的差距吧。同樣,結尾關于“火場銀河”的一大段敘述,洋洋灑灑,又進一步把小說推向光怪陸離的太虛幻境,實現了作者心目中的“藝術的升華”。不過,這里沒有秦可卿引路,作為讀者的我們,只能憑借自我意識,在這座作者所精心營造的精神的伊甸園里,尋覓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