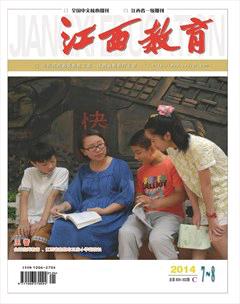一堂數(shù)學(xué)選修課的探究與思考
蔡紅
針對高中《數(shù)學(xué)》選修教材“定積分概念”第一課時中的內(nèi)容,從教學(xué)背景的分析、教學(xué)策略的選擇、教學(xué)目標的確定、教學(xué)重難點分析、教學(xué)過程的設(shè)計、教學(xué)設(shè)計特點及評價等六個方面,談?wù)勎业睦斫夂驼J識。
本課一方面讓學(xué)生獲得曲邊梯形面積的求解方法,認識“一個和式的極限”這一數(shù)學(xué)模型,同時提高學(xué)生的運算能力;另一方面,通過“割圓術(shù)”的引入以及曲邊梯形面積求法的探究過程,加強對分割思想、近似思想、極限思想的體驗,為后續(xù)定積分的概念和幾何意義的學(xué)習做好鋪墊.
通過前面對導(dǎo)數(shù)知識的學(xué)習,學(xué)生對“逼近”的數(shù)學(xué)思想有初步的認識。從學(xué)生思維特點看,很容易把導(dǎo)數(shù)的幾何意義、劉徽的“割圓術(shù)”與本節(jié)課知識聯(lián)系到一起,但是在具體求曲邊梯形面積的過程中,很難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步驟,對求第i個小曲邊梯形的面積有些困難,同時對“一個和式的極限”這一數(shù)學(xué)模型比較陌生.
筆者采用“引導(dǎo)探究式”的教學(xué)方式,在課堂教學(xué)貫徹“教師為主導(dǎo)、學(xué)生為主體,以問題為引領(lǐng),探究為主線,思維為核心”的教學(xué)思想,通過圖形和表格直觀啟迪學(xué)生的思維,注重數(shù)學(xué)思想的滲透。并從“求不規(guī)則圖形面積”這個具體問題入手,讓學(xué)生經(jīng)歷類比“割圓術(shù)”中運用的數(shù)學(xué)思想和方法的過程,觀察、分析、發(fā)現(xiàn)規(guī)律,注重培養(yǎng)學(xué)生自主探究、動手實踐、合作交流的能力,提高學(xué)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利用計算機輔助教學(xué),通過觀察幾何畫板中圖形以及Excel表格中數(shù)值的變化情況,使學(xué)生直觀感受到“逼近”的數(shù)學(xué)思想,同時鼓勵學(xué)生利用課余時間用信息技術(shù)進行探索和發(fā)現(xiàn),使信息技術(shù)真正為教學(xué)服務(wù)。
引導(dǎo)學(xué)生建立曲邊梯形與圓形的關(guān)系,引導(dǎo)學(xué)生回顧分析圓面積公式的具體推導(dǎo)過程:將圓分成很多個小扇形,當分割無限變細的時候,用相應(yīng)小三角形的邊長“近似代替”小扇形的弧長,小三角形“近似代替”小扇形,利用公式計算出每一個小三角形的面積,用小三角形的面積和“逼近”小扇形的面積和,得出此面積即圓的面積的結(jié)論。通過分析小三角形,使學(xué)生感受“以直代曲”和“逼近”的數(shù)學(xué)思想;通過類比啟發(fā)學(xué)生的思維,幫助學(xué)生找到新知識的生長點,用已知探求未知,獲得解決問題的數(shù)學(xué)思想方法。
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數(shù)學(xué)思想必須轉(zhuǎn)化成可以操作的具體方法,才能真正發(fā)揮作用,所以還有必要引導(dǎo)學(xué)生具體分析解決問題的步驟。在求曲邊梯形面積時,能否直接對曲邊梯形進行“以直代曲”?追問:如何減小誤差呢?引導(dǎo)學(xué)生初步體會“逼近”的數(shù)學(xué)思想:如果將曲邊梯形分成若干個小曲邊梯形,在每個局部小范圍內(nèi)“以直代曲”,那么就能減小誤差,而且分得越細,誤差就會越小。這樣就得到了解決問題的第一個步驟:分割。
類比圓面積公式推導(dǎo)中用小三角形面積“近似代替”小扇形面積,如何理解對每個小曲邊梯形 “近似代替”?引導(dǎo)學(xué)生以合理的方式進行“近似代替”,學(xué)生可能會提出多種“近似代替”的方案,鼓勵學(xué)生說出他們的想法,幫助他們分析每種方法,指出當分割很細的時候,每種方案的誤差都很小,從計算公式角度來看,矩形的面積公式最簡單,由此確定“近似代替”的方案。同時鼓勵感興趣的同學(xué)課下探究其他“近似代替”的方案。
在課堂上利用幾何畫板直觀演示小矩形面積和Sx逼近曲邊梯形面積S的過程,使學(xué)生從幾何角度直觀感知面積的逼近過程。隨后,請一位同學(xué)展示他所在小組課前做的Excel表格,使學(xué)生從數(shù)值上準確地看出Sx的變化趨勢。通過這種方式,使學(xué)生從數(shù)與形兩方面體會“逼近”的數(shù)學(xué)思想,認同“有限與無限的對立與統(tǒng)一”的辯證觀點,有效地突破了教學(xué)的難點,使信息技術(shù)真正為課堂服務(wù),成為提高課堂效果的有效手段。至此,得到解決問題的第四個步驟:取極限。為了進一步熟悉“一個和式的極限”這一模型,體會“以直代曲”,“逼近”的數(shù)學(xué)思想,可設(shè)計如下練習題讓學(xué)生動手操作:求由曲線y=x2與直線(x=2,y=0),所圍成的平面圖形的面積S。
回顧本課所學(xué)習的知識,讓學(xué)生通過小結(jié),反思本節(jié)課的學(xué)習過程,加深學(xué)生對求曲邊梯形面積方法的理解。師生共同提煉出本節(jié)課所學(xué)內(nèi)容的精華:一個案例、兩種數(shù)學(xué)思想、三套“以直代曲”的方案、四個解決問題的步驟。
本課采用“探究發(fā)現(xiàn)式”的教學(xué)方式,有如下突出的特點:從學(xué)生原有認知出發(fā),類比圓面積公式推導(dǎo)方法,尋找到新知識的生長點,通過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問題,結(jié)合學(xué)生的思維發(fā)展變化不斷追問,使學(xué)生對問題本質(zhì)的思考逐步深入;在確定“近似代替”方案時,設(shè)計了適合思維發(fā)散的教學(xué)環(huán)節(jié),使探究活動貫穿整節(jié)課,讓學(xué)生在思考的過程中深刻體會兩種數(shù)學(xué)思想,有效地突出了教學(xué)重點;利用幾何畫板中的圖形和Excel表格中數(shù)據(jù)展示小矩形面積和逼近曲邊梯形面積的過程,使學(xué)生從數(shù)與形兩方面直觀感受到“以直代曲”和“逼近”的數(shù)學(xué)思想,從而突破了教學(xué)難點。(作者單位:南昌大學(xué)附屬中學(xué))
責任編輯:劉 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