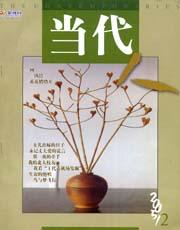一張二寸照
秋 思
1976年,縣里從各大局抽調干部下鄉組織整黨工作隊,我被分配到一個偏僻的農村中學, 中學和供銷社兩個整黨小組一個食堂,一起吃住,共有10名隊員,年齡都比較大。兩個組里 只有我一個女隊員,加上年齡最小,所以大家對我格外關照,讓我做中學工作組的材料員。 供銷社組的材料員叫劉杰,比我大兩歲,是沈陽下鄉知青,由他負責我們的伙食和后勤,平 時其他的隊員都下去辦案子,只有我和劉杰留守在家,這樣我們就熟悉起來。
當時很多知青都在復習準備參加1977年高考,我有一份固定工作,考不考都無所謂的,而 劉杰屬知青抽調的隊員,高考是他回省城和父母團聚的唯一出路。我在中學當工作隊,復習 機會得天獨厚,劉杰也就借了我的光,一有空我倆就到中學聽課。劉杰是家里的獨生子,父 母盼著他能早點回到沈陽,所以他學習很刻苦。我呢,文革前只上了初一,基礎很差,學起 來吃力,也沒信心。他就常常鼓勵我,有什么不會做的題,就讓他來給我講,每天粘在一起 ,與其他的隊員有點不同。隊員們看我倆親密的樣了,又都沒有對象,常常拿我們開玩和知 ,老隊長還偷偷喊我一邊,想給我們當月老,被我婉言謝絕。
有一天晚上,我和劉杰去中學聽輔導課,很晚才回來。冬天的晚上,天很冷,路和奶滑, 鄉村的小路沒有路燈,我和劉杰深一腳淺一腳往宿舍走著,突然一條野狗從小胡同里竄了出 來,我嚇得大叫一聲,腳底一滑,摔倒在地。劉杰扶我起來,可我腳脖子扭傷,怎么也站不 起來,疼得眼淚都流下來了。離隊部還有一程,這黑燈瞎炎的,劉杰見我不能動,就蹲在地 上,用兩只大手給我揉腳,他一動手,我就疼得大叫,后來劉杰見我真的不能走路,只好把 我背到衛生所……“太麻煩你了!”我在劉杰的背上感激萬分。“要是能這樣背你一輩子就 好了……”劉杰好像在自言自語,聲音小的像蚊子,可我聽清楚了,我的心跳加速了起來, 不知道怎么回他才好,他只是一個下鄉知青,連正式工作都沒有,我心有點打架……假裝沒 聽見,什么也沒說。
以后劉杰再沒提起什么,從那事以后,我對劉杰倒有了感覺,現在想起來可能就是初戀吧 ,可當時人們都很封建,很傳統,只是在心里有那么一點意思。工作隊的材料很多,工作計 劃,總結,案件調查,加上要復習,每天累得暈頭轉向,由于睡眠不足我有些貧血,常常心 跳頭暈,劉杰就抽出時間幫我,有時他去學校聽課回來再給我講一遍,和他在一起,我感到 很快樂很幸福。
1977年夏天,我們單位有個同事調走,人手不夠急著用人,單位請示縣里,把我中途從整 黨工作隊調回單位。
記得那是我在工作隊的最后一天。我很早就起了床,迎著初升的太陽,順著學校北面的水 渠漫步,心中有種戀戀不舍和莫名的惆悵。在回來的路上,遠遠的我已經看到劉杰,他身著 一套運動服,在鄉間的小路上跑步,他的手里還拿著一本書,看我走來,他站下了。
“這么早?”我說。
“你起的好早,你什么時候走?”劉杰問我。
“吃完早飯就離開”,我說的有點憂傷。
我和劉杰在一棵樹下站了有十多分鐘,兩個人一直沉默著,誰也不開口說話,我的心亂亂 的,不知道說什么才好。后來他和我一起到宿舍,劉杰幫我捆行李,收拾書籍,劉杰把一本 數學復習資料遞給我,“送給你吧,你需要的。”劉杰盯著我說,我眼睛有點發潮……我把 頭抬起來,希望聽到劉杰對我說點什么,可是他沒有。
早飯的時候,我和劉杰緊挨在一起,坐在一條長板凳上,“八點大家都來送你,有車送你 去車站。”劉杰叮囑著。接著他問了一句:“你還會記著這里嗎?”
“會的,隊員和學校的老師我都會記著的。”其實我很想說:“會記得你,記得和你在一 起的日子”,可我話到嘴邊,卻說出了這樣一句不疼不癢的,唉,我怎么也拿不出那份勇氣 ,只有筷子偶爾碰到碗的響聲。吃過飯,劉杰把我吃過的碗一起揀過去,幫我洗干凈,擦拭 后,放在我的包里。
一輛馬車裝上了我的物品,我和學校的領導及工作隊員們握手道別,當我的手第一次握住 劉杰的手時,我感到了劉杰的手有一種悄悄的力,傳遞給我一種特有的快感。我低著頭沒看 他,我怕自己的淚流出來,我慌亂中抽回手,匆匆跳上車。
車走了,隊員們在原地朝我揮手,而劉杰遠遠站在那,我看他的手沒有抬起來……
回城后不久,父親突然病故,由于家里缺少人手,三個姐妹中,必須留家一個照顧媽媽, 我放棄了高考,把楊會讓給兩個在鄉下當知青的妹妹,那年秋天,我就嫁了人。
兩年后,有一次我收拾東西,才發現劉杰送我的復習資料里,里面還夾著一張他的二寸照 片,照片的背面寫著:“送給親愛的人”。照片捧在心口,我想起了和劉杰一起的日子,眼 眶涌出淚水,可為時已晚,我只有把照片珍藏起來。后來有消息傳來,1977年劉杰考取了遼 大,回到了他的家鄉沈陽,畢業后留在省政府機關,我和劉杰也再沒有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