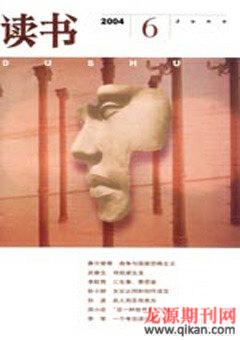文化認同和創作語言
彭小妍
讀了周質平先生在《讀書》今年二期上發表的《臺灣語文發展的歧路:是“母語化”,還是“孤島化”?》,我想從一個臺灣文學研究者的角度,探討閩南語文學在日據時代的短暫實驗,做個對照。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閩南語文學的實驗,學界一般稱為臺灣話文運動,許多當年主流的作家都曾參與。所謂臺灣話文,是與北京話文相對的。究竟只有北京話文才是白話文嗎?白話文是否能以臺灣話文寫作?臺灣話文適合寫作嗎?這些問題的提出,起因于中國文化、日本文化相繼在臺灣文壇爭取主導權,牽涉到臺灣意識的崛起、臺灣文學爭取主體性的問題。所有爭議應從臺灣的新文學運動談起。
二十年代初,一方面是受到日本“言文一致”運動的啟發,一方面是受到中國白話文運動的影響,新文學運動在臺灣如火如荼地展開。其中主要的關鍵人物是旅居北京求學的臺灣作家張我軍。雖然早期也有黃朝琴、黃呈聰等人提倡白話文,但一直是零星的呼吁,沒有立即的影響。到張我軍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下旬回臺北,擔任《臺灣民報》的主編后,才展開系統性、策略性的推廣;他左批舊文學,右打日本殖民政府,又積極推介“五四”文學,賦予臺灣新文學在政治、文化認同上的意涵。
回臺后的第二個月,張我軍就在《臺灣民報》上發表《糟糕的臺灣文學界》一文,在他的詮釋下,舊文學和新文學象征兩種階級的對立。他詬病“古典文學”代表“陳腐衰頹”,舊詩已淪為“游戲”、“器具”、“詩玩”,除了排遣酸氣以外,就是乞求日本在臺“總督大人”的“秋波”。換句話說,他點名批判的“詩伯”、“詩翁”之流,和殖民者互通聲氣,儼然形成一班“自以為儒文典雅”的階級。就張我軍而言,這批詩伯詩翁更大的罪惡是養成沽名釣譽的“惡習”,戕害了“活活潑潑的青年”。也就是說,舊詩是臺灣人自甘奴隸性格的象征,而新文學才能改造臺灣人的奴性,讓青年展現改革社會的活力和清新性格,臺灣社會才有光明。
次年一月,張我軍又進一步發表《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一文,詳細介紹胡適的“八不主義”、陳獨秀的“三大主義”等文學革命理論,更陸續轉載名噪一時的“五四”作家作品,如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淦女士(即馮沅君)的《隔絕》、冰心的《超人》、郭沫若的新詩《仰望》等。臺灣新文學運動就此展開序幕。
《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一文,除了推介五四新文學的理論和作品,更主張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影響、變遷時,“支流”就“自然而然”地隨之影響、變遷。這種說法,必須放在當時臺灣的政治、文化、社會情境中解讀。歸根究底,張我軍有這樣的主張,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分治”: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后臺灣淪為日本殖民地,大陸人與臺灣人同為漢族,卻由兩個敵對政權統治,文化上的認同問題自然不可避免。從這篇文章看來,張我軍在日本和中國之間,選擇認同中國,以對抗日本殖民統治。相對的,對日本殖民者而言,臺灣文學當然是“日本文學的一翼”;這是在臺的日本帝國大學講師島田謹二的看法。一九四一年五月,他在日人西川滿主編的《文藝臺灣》中,發表《臺灣文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文,主張相對于日本內地的文學,臺灣文學是“外地文學”:“跟內地風土、人和社會都不同的地方——那里必然會產生和內地不同特色的文學。表現其特殊性的文學名之為外地文學。”然而,就當時的臺灣知識分子而言,即使不認同日本文化,張我軍的說法,他們也并不見得全都贊成;這就是為什么不久之后,臺灣話文的論爭會展開。
從臺灣新文學運動之始,知識分子對所謂“白話文”和臺灣話文之間的關系,就各自有不同的主張。最早對這個問題提出看法的人包括黃呈聰,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發表《論普及白話文的使命》,認為臺灣話文“使用的區域太少”,而且“臺灣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背后沒有一個大勢力的文字來幫助保存我們的文字、不久便就受他方面有勢力的文字來打消我們的文字了”。他主張與其使用臺灣話文,不如研究中國白話文,如此不但把臺灣的范圍“擴大到中國的地方”,也方便到中國行事;有這樣的眼界,“就我們的臺灣雖是孤島,也有了大陸的氣概了!”一九二四年三月,《臺灣民報》繼續有兩篇持反對臺灣話作為白話文的主張。施文杞的《對于臺灣人做的白話文的我見》,認為“臺灣人做的白話文”常有文法錯誤,用了許多“啦”和泉漳的方言“鳥仔”、“狗仔”等,而且用日本語的名詞如“開催”(主辦)、“都和”(情況,方便)等。他主張應該參考中國大陸的白話文,認為以地方的方言寫作白話文會“鬧笑話”。逸民的《對在臺灣研究白話文的我見》,也認為“臺灣的方言”、“變形的臺灣方言”,做起文章來經常文言和白話不分,不但別省人看不懂,連泉漳人都看不懂。最后又批判張洪南所著的臺灣話文羅馬拼音法,認為某種程度的漢學根底加上多研究“中國國語”,白話文才能推廣。
《臺灣民報》對臺灣話文沒有既定的立場,也有許多知識分子發表文章主張應該改良臺灣話,使其適于文字書寫。著名的《臺灣通史》作者連溫卿,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和一九二五年二月連載發表《將來之臺灣語》,指出臺灣語言的流動性:“先受了宗教上用羅馬字宣傳的影響……后來受了日本教育的影響,及交通便捷的緣故,臺灣言語每說了一句話便有新名詞在。”加上臺灣住民泉、漳、客人等發音各異,新名詞的翻譯自然有別,發音未必與中國大陸相同。他認為如果要有效地表達思想,應該改良臺灣話,步驟是“第一要考究音韻學以削除假字”、“第二要一個標準的發音”、“第三要立一個文法”。張我軍本人寫作時選擇用北京話文,卻也認為北京話和臺灣話都是中國方言,都可以是白話文。一九二五年二月在《復鄭軍我書》一文中,他說道:“我們之所謂白話文乃中國之國語文,不僅僅以北京語寫作。這層是臺灣人常常要誤會的,以為白話文就是北京話,其實北京話是國語的一部分(一大部分)而已……不僅是北京話寫作的才能叫做白話文。”他認為,“如我們能造出新名詞、新字眼而能通行也可以,何必拘泥官音呢?”但是他這樣的主張,有一個前提:臺灣人的話應按照中國語來改造。同年八月他發表《新文學運動的意義》,首先借用胡適的話,說明為什么要建設白話文,然后闡釋改造臺灣語言的必要。他認為臺灣日常所用的話,多半是土話,是“沒有文字的下級話,所以沒有文學的價值”。因此他認為應該“把我們的土話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語言。我們欲依傍中國的語言來改造臺灣的土語。換句話說,我們欲把臺灣人的話統一于中國語,再換句話說,是把我們現在所用的話改成與中國語合致的……倘能如此,我們的文化就得以不與中國文化分斷,白話文學的基礎又能確立,臺灣的語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這豈不是一舉三四得的嗎?”這種主張,當然是合乎他一貫立場的。
到三十年代初,臺灣文學史上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爆發。主要是《南音》半月刊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創刊,開辟了臺灣話文討論欄,“建設臺灣話文”的議題成為論爭焦點。首先是創刊號上,署名“敬”的人士用日文片假名說明臺語的正確讀法,郭秋生則主張臺灣話文的“基礎工作”是“新字創造”。戰后被譽為“臺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在二月發表反對意見:“新字的創造,我也是認定一定程度有必要,不過總要在既成文字里尋不出‘音‘意兩可以通用的時候,不得已才創來用,若既成字里有意通而音不諧的時候,我想還是用既成字,附以旁注較易普遍……”郭秋生的回答,基本上同意賴和的看法,但是指出:“不過沒有嘗試等于是空談,可是一旦實行又不免碰著‘不妥的難關……在這基礎建設的時期,望有心人多一些協力——歌謠民歌的文字化——并進一步起來嘗試,便可以從‘不妥的荒草雜堆里發現著‘妥當的芳草出來……”
二三十年代的臺灣話文論爭不僅涉及理論,確切面對臺語有音無字的實際問題;而且當時的作家也勇于將理論付諸實踐。在文學作品中夾雜自創的臺灣話文者不在少數,例如賴和以“永過”代替“以前”,楊守愚自創“漸時”(暫時)、“即暗”(這么晚)等詞匯。但如同賴和所擔心的,由于各自有一套用語,彼此無法流通,難免產生不易普遍化的問題。像楊逵的《模范村》是日文作品,偶爾夾雜臺灣話文和北京話文詞匯,有一些是難以理解的,像“乞食伯仔”、“短褲”、“查某”、“攏不直”(沒法子過日子)、“起大厝”、“藝妲”等臺灣話文,北京話文如“電扇”、“美國”等。《田園小景》中的臺灣話文童謠,如果不加上批注,也很難看懂:
“貸切仔!貸切仔”(包租汽車)
“鹿咯馬!鹿咯馬”(老爺車)
“步兵掮銃(掮槍),乒乒乓乓,沖倒賣監粽(堿粽)!”
我們在日據時代作品中看見的臺灣話文,幾乎都是在日文或中文作品中夾雜的零星詞匯。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楊逵在日據時代曾嘗試一個故事分別完全用北京話文和臺灣話文寫作,其中實驗的企圖昭然若揭;這是罕為人知的。《死》是北京話文作品,于一九三五年四月至五月在《臺灣新民報》連載。比較起來,《貧農的變死》則是手稿,內容和《死》幾乎一樣,但卻是臺灣話文作品,在一九九八年收入《楊逵全集》第四卷之前,從未發表過。和戰后楊逵的中文作品比起來,例如《綠島家書》,《死》的文字顯得相當生澀,錯、別字很多(許多是日文漢字的寫法),也有遺漏標點之處(可能是報紙誤排)。雖然《死》主要是北京話文,里面也有部分臺灣話文和日語借詞,例如這樣的句子:“在他家中,這樣的拖磨(受苦,臺灣話文),不單是他一個人,他的老婆和兩小孩子都是總動員之下勞(日文)。”又如:“當他彎一彎進入狹小巷路(臺灣話文)之時,遇了由對面疾走來的自轉車(日文),鈴聲響得像是雷響,寬意竟也聽不見,也不曉得避開,到被自轉車碰倒在地才覺醒起來。 ”
這兩篇小說,故事的內容都描寫寬意替富豪向貧農逼債,貧農走投無路,紛紛自盡,寬意飽受良心譴責。這天聽說他前兩天才逼過債的阿達叔撞了火車,他慌張地前去探視究竟,心神不寧。雖然是不太流利的文字,描寫這樣一個小人物的心情,卻十分傳神。如果比較兩篇故事的第一段,立刻看得出來兩者北京話文和臺灣話文的差異:
雖然是再受了主人嚴重的命令到了門限外,寬意全然沒有勇氣可再去催促阿達叔了。他在頭腦中,想起阿達叔家中的窮狀,一步一步在與阿達叔的住家對反的路上,往北走了。(《死》,北京話文)
雖然是再受了頭家嚴重的命令出來到戶碇外,寬意全然沒有勇氣可再去催促阿達叔。他在頭殼中想起阿達叔家中的窮狀,一步一步在與阿達叔的厝對反的路上走向北方去。(《貧農的變死》,臺灣話文)
《貧農的變死》是楊逵打算創作的長篇小說《立志》中第一章的手稿,《立志》本來計劃共六章,只完成第一章。寫作年代不詳,應該和《死》的寫作時間很接近。在手稿上有修改的筆跡,將許多臺灣話文的部分改為北京話文,可能是賴和修改的。種種跡象顯示,楊逵蓄意實驗臺灣話文的寫作,可惜只寫完一章。而疑是賴和修改的筆跡,也讓我們意識到三十年代本土作家在使用臺灣話文創作上,意見的不一致。這份手稿的存在,等于為當時臺灣話文的辯論和實驗做了最有力的見證。
對臺灣作家而言,創作語言是實際的問題,也是建立文學主體性的關鍵。另一方面我們應該了解的是,日據時代在臺的日本人為了凸顯臺灣作為殖民地的特色,相當鼓勵文學作品中的“異國情調”,其特色是民風民俗的描寫和臺灣話文的點綴。這種現象,和二三十年代臺灣話文辯論相互對照,顯示出臺灣作家當時面臨創作環境的復雜。四十年代正當皇民化運動展開之際,除了島田謹二提出“外地文學”,也就是殖民地文學的理論,日文雜志《文藝臺灣》每期都刊登許多介紹臺灣民俗民風的文章。例如一九四○年十二月有西川滿的《赤嵌記》,重新闡釋鄭成功家族領臺的故事;張文環的《檳榔籠》,描寫作者兒時常見的女子外出時攜帶的竹編小籃子,充滿浪漫的懷舊情懷。四月號上有池田敏雄的《艋雜記》,描寫端午節粽子的來由;新垣宏一的《臺南地方民家的祛魔風俗》等。連續幾期都有黃鳳姿寫的《七爺八爺》出書廣告,贊美作者才十三歲年紀,繼《七娘媽生》之后又有描寫萬華民俗的佳作。“臺灣總督府情報部”并大力推薦,聲稱本書展現鄉土文學的價值,充分顯示出皇民化教育提升地方文化的成效。此外,《文藝臺灣》刊登的作品,不僅臺灣作家的作品經常出現臺灣話文,日本人作品亦然,例如西川滿的《赤嵌記》中,“阿母”、“沒要緊”、“愛玉”、“排骨湯”、“過房子”、“媳婦仔”、“獅陣”、“弄龍”等詞匯比比皆是,旁邊都以片假名注明臺語的發音。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經常提到由于“臺灣施行新體制”,因此秩序井然,煥然一新。按“新體制”是皇民化運動時的口號,這顯然是“以古說今”。在臺日人提倡臺灣民俗的盛事,是一九四一年七月臺灣大學人類學教授金關丈夫和池田敏雄主編的《民俗臺灣》創刊,紀錄臺灣的風俗民情、信仰慶典、諺語民謠等,一直出刊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第四十二期為止。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無論是日文或中文作品當中,臺灣話文的夾雜是殖民政府允許的。到了日本參戰后施行皇民化運動,大力推行“國語家庭”,一九三七年四月起公立學校漢文課取消,和、漢并用的報紙開始廢止漢文欄,家庭中和工作場域也標榜不用臺語,用日語。可是種種跡象顯示,總督政府卻似乎鼓勵臺灣話文所代表的民俗文化。這應該是殖民政府的一種統治技巧:一方面在日常庶民生活中實際打壓本土語言,一方面又蓄意把臺灣文化博物館化、樣板化,以精致文化的方式展現殖民政府對臺灣傳統的寬容和保護。這個現象,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二三十年代臺灣作家對臺灣話文的使用,意見是相當分歧復雜的。他們一方面認識到使用臺語創作有流通性的問題,一方面又有難舍鄉音之情;認同意識也加深了鄉土的想像。像黃呈聰,即使一九二三年明確指出使用臺灣話文創作的不實際,一九二五年一月又發表《應該著手創設臺灣特種的文化》:“凡文化是要創造、模仿、或將模仿來改造……文化若接觸異種的文化便會受刺戟感化,其理性常常要求比自己向來的文化更好的……能創造建設特種的文化始能發揮臺灣的特性,促進社會的文化向上。此種文化的建設是要大家努力。如不這樣努力,只憑著東西各種的文化所翻弄;或有傾于中國、或有傾于日本、或有傾于西洋,為二重生活或三重生活,這是無利益的。”顯示出臺灣意識和文學創作語文之間復雜吊詭的關系。
或許我們可以說,“創設臺灣特種的文化”是有臺灣意識的文字、文化工作者普遍的體認,但用臺灣語寫作,可能并非惟一或必要的途徑。就文學創作而言,最好的示范,應該是六七十年代鄉土作家的作品,例如黃春明和王禎和等。黃春明已經成為臺灣鄉土作家的代表,他的作品中常夾雜閩南語詞匯,但只出現在對話中,或只是幾個關鍵詞眼,由上下文很容易判斷這些詞匯的意思。如果黃春明選擇完全采用閩南語寫作,可能無法獲得漢語世界讀者廣泛的激賞,也就無法引起日本和西方學者翻譯的意愿。黃春明說得好:“不是說腳踩下去是爛泥就是鄉土,鄉土是心靈的故鄉。”
再說,黃呈聰所批判的“二重生活或三重生活”,從另一個角度看,何嘗不能轉化為文學藝術創作的泉源?歷來對臺灣文學有關鍵影響力的人物,大都是跨文化的人物,例如張我軍、楊逵、林海音、白先勇、王文興。當代的臺灣作家如朱天文、朱天心、張大春等,出身于眷村這樣一個特殊打造、被臺灣社會邊緣化的環境中,面對解嚴前后村內、村外的心理、政治、社會的轉變沖擊,審視來自西方、東方的文學、文學理論、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美學、人類學等話語,以大量的互文技巧(intertextuality)勾勒出混雜多重的臺灣經驗。他們一方面從事文學美學上的實驗,一方面把文學由現代派的“象牙塔”,帶入政治、社會、文化、環保批判的世俗問題中,創造了后現代意識強烈的作品。“二重生活或三重生活”已經是現代人生命的現實,其間或有認同的焦慮和不安,也未嘗不是跨越界限的契機。這就是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所指出的“邊緣狀態(a condition of marginality)”吧。許多人擔心臺灣文學被“邊緣化”,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邊緣狀態”也有積極的意義。惟有時時保持“邊緣狀態”,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才能跨越藩籬,保持批判的距離和精神,見常人所不能見,言常人所不能言。這,就是哲學藝術創新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