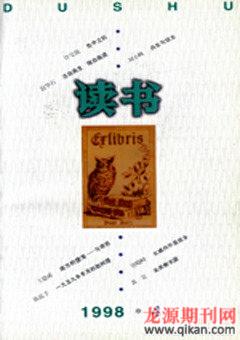危中之機
許寶強
在亞洲金融風暴中重讀布羅代爾
一九九七年底的東南亞貨幣風潮,不僅肆虐于泰國、印尼等地,而且在短短幾個月之內波及南韓、臺灣、香港、新加坡等地,極有可能導致區內為期頗長的經濟衰退。這次亞洲金融風暴,使近年甚囂塵上的“二十一世紀是亞太世紀”之說和壟斷了近十年關于東亞經濟“奇跡”的發展主義論述,受到了挑戰。
近十年關于東亞發展的論述,基本上為三種學說所主導。新古典經濟學強調東亞經濟之所以高速增長,主要是采取了自由市場和開放貿易的策略,這種學說經常拿前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與東亞地區作出比較,以此印證國家較少干預的好處。西方左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回應,除了起源于拉美,在六七十年代盛極一時的依附理論(dependencytheory)外,晚近當以“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developmentalstate)的說法最為流行。這派學說主要以南韓、日本和臺灣為例,指出這些地區“成功”的原因,除了政府大規模地直接介入經濟活動外(例如高比例的國有企業和銀行等),更由于政府運用各種以發展為主導的政策,包括低息貸款給“策略性”工業、各種鼓勵出口的措施和為企業向外借貸作擔保等,“指導”經濟發展的方向。此學說在八九十年代大行其道,它是對前一種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放任學說的一種反動。最后一種學說,就是所謂“儒家文化”。這派學說并沒有把“文化”作為問題來研究,而是把“文化因素”當成一種自有永有和同質的實體,以籠統和非歷史的“儒家文化”作為東亞經濟“奇跡”的解釋。
上述三種學說雖然各不相同,都共同接受發展主義,或某種形式的現代化主張。因此,亞洲金融危機所導致的東亞經濟神話的幻滅,對這三派學說都造成十分尷尬的局面。首先受打擊的是“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學說。隨著大企業的破產和金融危機的爆發,曾經被“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學說奉為模范的南韓,光輝不再。日本和臺灣亦處境艱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過去被說成是經濟增長妙藥靈丹的政府干預,今天被指責為金融危機的元兇——過度鼓勵信貸、政治經濟不分、官員貪污舞弊。這派學說只得由主動出擊轉為被動地答辯,把金融風暴的責任推給世界經濟的自由化進程,雖然經濟(金融)自由化往往由政府推動。新古典經濟學的處境似乎較好一點,至少它沒有將賭注全押在南韓、日本和臺灣。不過,這派學說在金融危機之下亦難以獨善其身。一方面,東亞金融風暴的一個最直接原因,正是東南亞近年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外匯管制的解除,使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市場極容易受外資投機活動左右,造就了日后爆發危機的環境;另一方面,金融危機的爆發,亦與國際投機者炒賣各類金融衍生工具有關,這些金融衍生工具,例如期匯、股指等,正是新古典經濟學派認為能以市場力量來調節金融風險的工具。不過,這次金融危機再一次印證了調節的市場的不可能性,調節工具最后亦變作炒賣對象,進一步強化金融市場的賭博性質。“文化因素”論在新的環境下也嘗試自圓其說。為什么同樣是“儒家文化”,以往能產生經濟“奇跡”,今天卻導致經濟危機?這確實是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此,有人把“儒家文化”一分為二,指出如“服從權威、重視集體利益”等“傳統”,確實對經濟發展有正面的作用;但“儒家文化”中的另一些習性,如“強調私人關系、顧存面子、處事不公開”等,對經濟金融體制,卻會起破壞的作用。這種說法雖然承認“文化”并非是完全同質的“因素”,卻仍然是非歷史的。問題是,為什么某些“文化習性”(如果存在的話)會在某些時候起著相對大的影響?另一些習性則只在別的時候起作用?缺乏歷史視野,是無法回答這些問題的。
從以上對關于東亞發展三種論述的簡單討論中,可以看到不論是自圓其說或互相攻伐,這三種學說均無法為東亞經濟的興起與衰退,提供深入的分析,反而只在不斷鞏固一種既有的發展主義或現代化理論的假設——就是認為經濟發展的“成功者”必然是有優秀的本質或運作效率,“失敗者”則本質較差這種“成王敗寇”的邏輯。這三種學說在互相引述和批評的同時,不單沒有觸動這個基本的假設,更由于它們之間的相互指涉及自我指涉,霸占了絕大部分可用作反思的場地,把另類的可能性排除掉,因而成為維護主流論述的共犯。要超越這個困局,我們得借用別的理論資源。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家布羅代爾關于資本主義的論述,正好為這次東亞金融和經濟危機,提供一個歷史的參考框架。
對于歷史的資本主義,布羅代爾提供的是一種結構主義的解讀。他認為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的發展,存在著各類時段不一的周期起落,由基欽短至三至四年的周期,到庫茲涅茨約二十年左右的周期,到康德拉捷夫約半個世紀的長波,以至布羅代爾自己提出的百年趨勢(自十三世紀至二十世紀共四次)。這些經濟周期使布氏堅信資本主義世界歷史是“一種有節奏的潮汐運動”。對布羅代爾來說,自七十年代初期開始的世界經濟收縮(東亞金融危機可以看作為這次長周期下浪的其中一個表現),可能只是進入了另一次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下浪,或百年趨勢的下降階段而已。布氏認為,在世界經濟長周期下浪所表現出來的危機,是一種結構性的危機,盡管其根本原因至今仍難以解釋。不過,布氏深信,是“經濟形勢決定相伴的過程,并制造人的歷史”,而非“過程和事件造成每個國家的特殊經濟形勢”。換句話說,國家政策(不論是否以發展為主導)或市場運作并不能左右這種結構性的經濟趨勢。決定一家企業以至一個地區或國家成功與否,往往不在于企業或政府所作的努力,亦不取決于籠統和非歷史的文化因素(事實上,在東亞興起以前,信奉新教的英、美和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城邦,以至信奉回教的阿拉伯商人,亦曾執資本主義世界的牛耳),而更取決于它們在長期的結構性趨勢中所處的位置和機遇。
根據布氏的結構性分析,東亞經濟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興起,只是世界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過程中眾多起伏中的一個環節。東亞地區的經濟在六十年代開始高速增長,正值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經濟的“黃金時段”。在冷戰時期,大量美國跨國資金流入東亞,為日后東亞成為“世界工廠”奠下基礎。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世界經濟進入另一次的長周期下浪,各地區的“失業資金”(unemployedcapital)紛紛尋找出路,經濟正在上升的東亞與拉美地區,便成為跨國資金投資的焦點。八十年代拉美債務危機以后,東亞更一枝獨秀,變作資金避難的天堂。處身在經濟長周期的下浪,需要較長期才有回報的實業投資,理所當然乏人問津,帶投機性質而回報快的行業,例如資金流動極快的地產和金融部門,反成上上之選。東亞地區近十多年的金融膨脹,以至最近投機泡沫爆破后的金融危機,均可以從這結構性的經濟趨勢中得到理解。
東亞的興起與危機并不是歷史上的特例,很可能只是資本主義世界歷史的數次重心轉移的其中之一。在十一世紀左右以歐洲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開始建立,資本主義的重心自始經歷了三次轉移。第一次轉移發生在十六世紀末,南歐較發達地區(意大利的熱那亞和威尼斯等城邦)為了擺脫一五九○年左右的經濟衰退,把經濟活動的重心轉移往歐洲北部,以享受當地較便宜的勞動力、地租和交通運輸費用,結果為以阿姆斯特丹為中心的荷蘭地區,帶來了一連串的發展機會。而資本主義的重心亦由南歐轉往歐洲北部。第二次在十八世紀下半葉,資本主義重心由荷蘭轉移往英國,其間荷蘭亦經歷了大規模的資金外流及經濟衰退的危機。二十世紀初,英國亦因資金過剩而大幅增加其在北美的投資,資本主義重心也隨之轉移至美國。資本主義重心的轉移,往往與金融膨脹和金融危機同步進行。因此在十六世紀、十八世紀、二十世紀初和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均看到資本家紛紛從實業中抽出資金,投放在高流動性的金融部門,雖然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下,其性質和規模都不同,但結果都造成金融膨脹和隨后的金融危機。
這幾次的重心轉移,是各種復雜的軍事、地緣政治、經濟、文化、技術和歷史因素影響下的結果。以十六世紀的一次轉移為例,除了上述的經濟衰退導致的資金轉移因素外,新教改革運動使歐洲北部國家獲得不同于南歐天主教地區的共同信仰,方便它們聯成一氣以對付來自南部的競爭;此外,宗教改革過程中的戰爭與紛爭,亦為新教徒商人創造了一個團結的網絡,更容易開展和擴大貿易。這些因素雖然不能以籠統和非歷史的“新教資本主義精神”概括,但顯然對荷蘭和英國的勃興起著重要的作用。
布氏雖然為資本主義的長期趨勢提供一種結構性的解讀,但與馬克思主義學說不一樣,布氏并沒有為這些周期轉移給予一種機械的邏輯解釋,相反,布氏作出的是一種歷史詮釋,也就是說,各種歷史的偶然性經常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例如蒙古帝國在十三世紀中的擴張,使意大利城邦從打通了黑海至中國和印度的陸路貿易獲得不少好處;又例如十五世紀末由于世界地理的新發現,使世界貿易重心遷移往大西洋,而位處北歐的安特衛普在鴻運高照下,在一段不短時期內成為世界經濟中心。這種歷史的視野,使布氏的論說可以保持靈活,避免僵化。
然而,不同的個人、群體、國家或地區,在處身相同的歷史周期中,獲得的機遇亦不盡相同。一方面是由于他們所置身的地緣政治位置不同,另一方面則與他們以往的財富積累差異有關。處身于經濟和政治上有利的地理位置、手握巨資和與掌權者維持良好的關系,自然較有能力把握不同的機會,獲取豐厚的回報;才會獲得資金的垂青,以供其進一步發展。用布氏的話說,就是“增長滋育了增長”。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跨國資金投向的,往往不是最貧困的地區,盡管那里的勞工、土地和資源是最便宜的。相反,資本主義中心的資金若要在中心以外尋找出路,大多數會投往經濟已有一定基礎的半邊陲地區,例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后的東亞和拉美新興工業國、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和十六世紀的歐洲北部等;非洲大陸和南亞等邊陲地區,則長年受到排拒。從另一個角度看,發達地區的資本家之所以經常獲取巨利,屢屢創造“奇跡”,很大程度上并非源于他們的文化本質,而是更與他們的“無限靈活性”(unlimitedflexibility)有關。也就是說,隨著高利潤率由一個經濟部門轉到另一個部門,由一處地方轉移至另一處地方,活躍于資本主義上層的資本家,往往能迅速反應,攫取新的發展機會。當然,這些人之所以享有這種靈活性,與他們擁有高流動性的資金,以及處身于政治和經濟上的優越社會和地理位置,有著極密切的關系。這些享受著特權利益的成功資本家,為保壟斷地位,均不想受規范約束,包括公開競爭、專業分工等市場規范,因此他們是反對市場作用于他們身上的,這恐怕也是為什么我們會在東亞地區中發現這么多“成功”而帶壟斷性質的大財團和地產商的原因。
布氏的學說除了能為我們在“新古典經濟學”、“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和“儒家資本主義”這三種發展主義論述中,對所謂東亞“奇跡”的興起和衰落,開辟一種新的理解可能性外,亦使我們能夠對發展主義進行必要的反思。主流論述對金融危機和經濟收縮的影響所作的回應,不外乎是提出各種策略,以期在短期內使東亞經濟重上快速增長的軌道。這種回應的基本假設,就是認為增長比不增長好,快速增長又比緩慢增長好。但究竟經濟增長確實對誰人好?這種以“整體”作為論述單位的發展主義假設,自然不屑深究。
布羅代爾以史學家的眼界,探討了在資本主義歷史長周期起伏的環境下,不同階層所受的影響。布氏指出,在經濟增長迅速的年代,財富得來容易,特別是對于少數特權家族來說,更是致富良機,而在資本主義的中心地區,經濟繁榮也可使普羅大眾“分得一點殘羹剩飯”,因此產生“國泰民安”的升平景象。但當經濟持續增長的效果漸漸顯現時,平民百姓的境況會變得愈來愈壞。一方面是經濟增長導致人口巨增,使勞動人口的負擔加重,加上工資的增長遠遠落后于繁榮時期高漲的物價,群眾的實際收入以至生活水平往往不升反降,貧富差距日增。相反,在經濟出現持續蕭條的時段,雖然會令上層社會“蜷縮起來,韜光養晦”,但價格的持續下降,使勞動階層的實際生活不一定會變壞。因此,布氏根據經濟史家費爾普斯·布朗和歇拉·霍普金斯的統計數據,指出在被描述為百年持續衰退,甚至是“漆黑一團”的一四三○年至一五一○年和一六三○年至一七五○年間,物質生產雖然停滯,物價雖然持續下降,但勞動人民的實際工資卻上升,消費和福利不一定比經濟繁榮時段差。
當然,布羅代爾對十五至十八世紀的歷史的觀察,并不一定完全適用于今天。事實上,隨著資本主義世界的擴張和深化,在經濟衰退期間的失業人口也會快速上升。這些失業人口由于其傳統產業(例如農牧業)在“現代化”過程中備受破壞,而難以在衰退期間回到這些傳統產業中,以自給自足的方式維持生計。不過,盡管如是,我們也不應由此便推導出一個帶普遍性的結論,認為經濟蕭條便一定導致正在增加中的失業人口生活水平下降。因為失去資本主義正式部門(formalsector)的工作,并不代表他們不能在各類非正式部門(informalsector)中覓得生計。事實上,布氏也曾指出,往往在經濟衰退的環境中,大量像小商販運、家庭勞務、以物易物等非正式經濟活動,會如雨后春筍一樣,蓬勃生長。而這個階層的生活質量,是否一定比不上在經濟繁榮、物價飛升的時期的底層勞工,似乎還未有足夠的歷史證據作出結論。
經濟增長緩慢甚至衰退,還有另外一些好處。布氏指出,經濟長周期的下浪往往會刺激文化活動蓬勃發展,例如在一八一五年后,“浪漫主義使已屆暮年的歐洲煥發青春的熱情”。此外,在經濟繁榮的年代,出于財富得來容易,因此守護既有制度的保守心態大行其道,人心不思改進,拘泥舊習。相反,在經濟危機時期,往往煥發出各種求生存活的對策,使創造力得以充分展現。再者,在經濟增長緩慢的年代,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減慢,不良的消費習慣被迫改變,這些也正好扭轉“現代化”過程帶來的種種惡果。
不管對只爭朝夕的經濟政策謀士還是當下大行其道的后現代評論家,布羅代爾帶結構主義味道:強調長時段和放眼大范圍地域的歷史敘述,顯然并不能都討好。然而,不容否認的是,布氏的長時段大范圍的歷史分析,并沒有排拒對短時段小事件的仔細探討。事實上,布氏的歷史結構分析,與別的結構主義者不一樣的地方,是其論述基本上是建立在微慎的歷史材料之上,而其立論亦不是以演繹邏輯為依歸,相反只是常常以反問的方式,點出問題的所在,因此容許多種詮釋的空間。不過,布氏的歷史分析只提供一種理解當代問題的視角,并不能取代對具體的情況、具體的群體,作出具體的分析。若要詳細了解經濟周期趨勢對個別群體、國家或區域起著怎么樣的影響,不論在以往還是今天,細致的歷史分析還是不可避免的。
對于那些強調只爭朝夕的評論,布氏借批評凱恩斯那一句常被人引用的俏皮話:“在長時段中,我們都是死人”來回應,他認為,凱恩斯這句話“既平常又荒唐。因為我們同時在短時間中和長時間中生活,我所說的語言,我從事的職業,我的信仰,我周圍的各色人等,都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這一切先我而存在,等我死后也還將存在。”對長時段和大范圍地域進行結構性的探討,若分析得法,還是有值得參考學習的地方。
(布羅代爾:《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三卷本),三聯書店一九九六年版,87.20元;《資本主義的動力》,三聯書店,一九九七年版,5.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