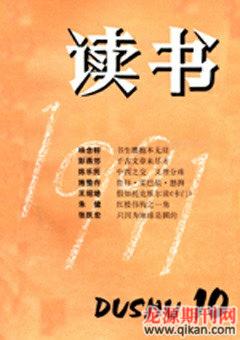歷史研究的公正
朱 曉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厄恩斯特·邁爾寫的《生物學思想的發展》,有一個精辟的見解:科學發展的最重要方面是科學家頭腦里思想的發展。他寫的這本書著重介紹了生物科學家頭腦思想的發展,雖然具有生物科學的專業性,但是也為其他科學工作者帶來閱讀的興趣:因為各門科學的科學與“頭腦思想的發展”往往有共同之處。讀了《生物學思想的發展》,接觸過生物學的人可以梳理一下自己頭腦中生物學發展的線索,而不曾接觸過生物學的人可以因他這本書拓寬眼界,因為正如邁爾說的:“研究一個領域的歷史是理解這個領域的概念的最好途徑”。更重要的是,不論你對生物學的興趣有多少,都可以從作者的筆觸中欣賞到歷史研究中最可貴的公正。
作者關于生物學歷史上一些事例的思考,對讀者極有啟發。
例如,他談到“許多傳統的科學史(及其標準教科書)被神話和假造的傳聞逸事包裹了起來。”帶著這個觀點分析達爾文偉大發現的契機,不難看出:“人們一直重復是貝格爾(Beagle)號上的經歷使達爾文成了博物學家這種神話,但這種說法與事實不符。達爾文一八三一年參加貝格爾號航行之前,已經成了一名非常有經驗的博物學家……他具備的知識令人驚嘆,不僅關于昆蟲……而且關于哺乳類、鳥類、爬行類、兩棲類、海洋無脊椎動物、化石哺乳類和植物都具有廣博的知識。”的確,參加貝格爾號航行在達爾文一生中具有決定意義,但在此前后,自然科學的發展為論證生物進化規律提供了極多的新材料,正是在前人思想材料積累的基礎上,達爾文建立了進化論。如果沒有他,歷史也會把這付擔子交給別人的,與達爾文一起發表進化論的華萊士就可能是這種人,盡管他的理論很不成熟。
這一類神話不難在科學史的其他地方找到。比如牛頓是由于看到蘋果樹上的蘋果掉下來而想到萬有引力的;瓦特因為兒時看到祖母用水壺燒開水,最終發明蒸汽機,等等等等。其實在牛頓之前,有哥白尼、伽利略、第谷,尤其是約翰·刻卜勒,為萬有引力論的完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瓦特之前,由于生產的需要,熱機的研究已經興起,有了法國工程師卡諾的蒸汽機工作原理,瓦特的貢獻是大大改進了蒸汽機的設計。這種編造科學史神話和傳聞逸事的所謂歷史,錯誤在于以個人經歷的偶然性去掩蓋思想發展的歷史必然性。正如恩格斯論述的那樣:“在每一科學部門中都有一定的材料,這些材料是從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維中獨立形成的,并且在這些世代相繼的人們的頭腦中經過了自己的獨立的發展道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501頁)“任何新的學說……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56頁)
邁爾指出:“正如在生物學史中所極為經常發生的那樣,相互對立的理論沒有一個在最后流行起來,相反是折衷的融合。”這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見解。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很多人在探索怎樣從一個簡單的細胞發展成為復雜的有機體。關于有機體的個體發生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論。預成論者認為卵中存在某種預先形成的東西,作用在于使卵轉變為成體,更為極端的是,干脆設想卵里含有同一種類的一切未來世代的預成“小體”或微型;而漸成論者認為,是一個全然不定型的卵逐漸分化,形成成體的器官。現在的胚胎學就可以證明,兩者都包含正確的因素——漸成論者闡明了初始階段的卵基本上沒有分化,預成論者肯定了卵的發育受某種預先存在的東西(即現在認識到的遺傳程序)控制。即使在生物學史上,也不容易找到完美的例子去印證林妹妹“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妙人妙語。作者很有見地地指出:“如果以為任何一個時代總是由一種思想基調亦即說明框架或思想體系所決定,又由一種新的而且常常又全然不同的概念框架或思想體系所取代,則是錯誤的。”
邁爾以為:“在傳統上,學者中有一種傾向,就是以一種如果不是誹謗性的也意味著貶低的語言提到他們對手的研究……因為歷史學家是從外邊來看待這些表述,很可能沒有認識到這類聲明純粹是從心理工具,是貶低對手以抬高自己的地位。”人們都看到,這有兩種情形,一是如同他說的:“只要有科學爭論,失敗的一方的觀點后來幾乎毫不例外地被勝利的一方曲解了。”很明顯,這是受到“輝格派”科學史觀的影響,這種科學史觀是用科學家對于現代已經確定的科學解釋貢獻的大小來評價科學家。就是偉大的達爾文也難免是這樣,他曾明確地否認從拉馬克的書中獲得過任何益處,“那是十足的垃圾……我從中沒有得到任何事實和觀點。”事實上,拉馬克因其理論面受的冤枉幾乎把他的成就全部抹殺掉了——獲得性遺傳的概念從古到十九世紀廣泛為人們接受,拉馬克只是簡單地用它為進化理論服務。拉馬克理論中的進化與意志的作用無關,誤會部分在于錯將“besoin”(需要)譯成“wan”(想要),而不是譯成“need”(需要)。
另外一種情形更讓人遺憾:甚至未見得成功的理論借助政治強權來打擊有可能成功的對手。比如倡導了小麥春化法的李森科,憑仗當時的寵信,無情打擊了蘇聯的其他生物學派,尤其遺傳學派,使原來居世界領先地位的蘇聯遺傳學一撅不振,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這件事又表明,政治意識形態對于生物科學的興趣常常要比對于物理科學的興趣大得多。
關于意識形態之爭,邁爾提到了“無產階級科學史”以及他自己的看法:
“近些年來,馬克思主義的編年史家特別闡述了以下論點:社會意識形態影響科學家的思想,但是一直到現在,科學史在實踐中完全忽視了社會背景環境。他們認為,結果就是,現在的科學史是資產階級的科學史,這種科學史和無產階級科學史是完全不同的。他們說,所需要的是以‘激進的,歷史來取代現有的科學史。這種要求就最終回到了馬克思關于統治的思想不能和統治階級分開的主張。因此,無產階級科學史是完全不同于資產階級科學史的。”
“然而,存在著以無產階級方法寫作的科學史,這個論題是和以下三組事實相沖突的。首先,人民大眾并沒有建立起一種和現在掌握著科學的階級的科學理論不相同的科學理論。如果要說有什么區別的話,那就是,當科學家放棄了一種思想之后,‘普通人還常常堅持它。其次,在科學家中存在,著大量的社會流動,每一批新的科學家中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來自于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階級。第三,就決定叛逆性的新思想產生的因素來說,在某個社會階級中的出生早晚要比是哪個社會階級的成員重要得多。以上這些事實與那種社會經濟環境對于特定的新科學思想和概念的產生具有支配性影響的論點是相沖突的。雖然,主張這種觀點的人負有證明這種觀點的義務,然而到現在為止,他們并沒有提供出任何具體的證據。”
仔細思考一下邁爾反駁無產階級科學史的三個論據,不難看出,邁爾自己也沒有超越階級分析的圈子——他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講話。這一態度似乎有悖于他在其他地方表現出來的公正。任何一個歷史學家,不論他屬于哪個陣營,總會有人來指責他因階級局限導致的不公正。其實,由自然科學并不具有階級性這一特點所規定,人們在研究反映自然科學發展的科學史的時候,并沒有必要僅僅限于階級的影響這一方面。
事實上,歷史人物本身除階級屬性以外,還有諸如氣質、心理等等對歷史發展來說是偶然的東西,對這些避而不談,就不免會有意無意地犯不顧史實的錯誤。馬克思說過:“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末世界歷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納入總的發展過程中,并且為其他偶然性所補償。但是,發展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開始就站在運動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這樣一種‘偶然情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393頁)
在具有必然性的思想發展方面,中國歷史的軌跡與西方的也大不一樣。一方面,西方有近四百年的科學穩步發展,這對人們的世界觀有深遠影響,而中國人少有自由學術思想的浪漫,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只是曇花一現;另一方面,西方人經歷了黑暗的中世紀,而中國人從未經歷過宗教強權的箝制。對中國思想影響最深遠的是“存天理滅人欲”的心性理學。西方學者很容易把中國的這種儒家傳統與他們理解的倫理學認同起來,也許基于這種理解,邁爾教授在為中譯本所寫的前言中表達了他真誠的愿望:“在我看來似乎進化的思維……較之笛卡兒——牛頓的物理主義傳統更接近于中國文明的傳統。倘若如此(只有進一步研究才能證實這一假設的正確與否),那么,進化生物學的基本哲學觀念也許會導致某些古老的、傳統的中國文明恢復活力……它也許有助于東西方文化的整合。”但愿邁爾意指的“某些古老的、傳統的中國文明”不是那扼住中國人喉嚨的“存天理滅人欲”。
有一點要肯定,中國應該有自己的歷史學家,公正地總結中國的科學思想史,乃至思想史,以填補傳統歷史學及科學史學上的某些空白。
(《生物學思想的發展》,〔美〕厄恩斯特·邁爾著,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