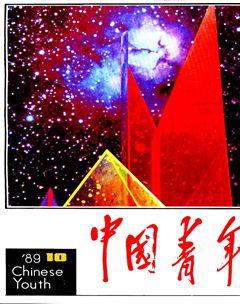她在尋找那顆星?
假如她不是這樣出奇的苗條、出奇的秀麗,她的命運也許會像大多數(shù)普通姑娘一樣,即使沒有太多幸福可言,至少也不會痛苦至此。
多年前的小李彤是個讓人愛死不償命的兵娃子,15歲,劉海齊眉,裹上大軍裝,新鮮得活像一支才發(fā)的竹筍。幾年后見到她時,我詫異地發(fā)現(xiàn)她幾年前還無比茂密的頭發(fā)已稀疏,“搞什么名堂小李彤?”我以我的方式開始了談話,“你丈夫硬是把你虐待成這樣?餓你飯啦?”
她沒有馬上回答。我知道下一步我得等她哭一陣。她曾經(jīng)也愛哭,請不準假也會小哭一陣。記得她哭得最痛的一次是聽說要送她去住院,當時她被查出有慢性闌尾炎,不動手術(shù)危險。她住了20多天醫(yī)院,被王副司令認成了干女兒。那之后,小李彤生活中第一個變化就是星期天有地方去了。王副司令和藹精干,是個一貫獲得人們好印象的首長。我在15歲那年也被他拍著腦袋寵過10來分鐘,那是一次演出謝幕后。“星期天到我家來玩!”我當時心里溫暖過,但相信首長不是認真說的,也就沒有認真做反應(yīng)。不久,小李彤開始坐小車來往,起初小車停得離我們駐地較遠,后來大家看慣了,它也就停到了院門口。有時看見一位富態(tài)的婦人樓著她,大家知道那是王副司令的夫人,是軍區(qū)門診部的醫(yī)生。大約兩三年后,小李彤從干女兒變成了未過門的兒媳婦。首長的兒子王雋,人長得挺拔俊逸,當時是某大學外語系學生。與他戀愛關(guān)系一確立,小李彤便改行學通訊去了。再后來,聽說她嫁進了首長的小樓。
“我被他們趕出來了。”李彤哭一會靜下來說。我不太吃驚,因為傳說她新婚半年的丈夫突然提出離婚,還說副司令的女兒在飯桌上對她開了罵,動了武,對此我不全信,好歹也是80年代的將軍門族。直到小李彤捋起袖子讓我看傷,我才大開眼界地想,原來發(fā)生在窮街陋巷里的事也會在豪門發(fā)生。
李彤說她也完全不明白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她一向都順著王雋和他全家。他們說跳舞沒出息,她就改行;他們說上學有前途,她就進了學校;他們說該結(jié)婚了,她就在21歲那年快快活活地出了嫁。結(jié)婚前夕,王雋從學院畢業(yè),學院決定分配他去西藏,他告訴李彤,叫她放心,說,就是已將他分到了西藏他也不會去,只要家里一句話,想進軍區(qū)機關(guān)哪個部就進哪個部。李彤對這些除了感到權(quán)力的威懾之外,只是陪笑幾聲。
“結(jié)婚半年,王雋沒有表示過對你不滿嗎?”
“沒有啊。”李彤說,“他早上還用自行車送我去上班,晚上忽然講到離婚,我以為他說笑話,沒理他。我們談戀愛時他給我寫過幾百封信,每個寒暑假他都跟我一起過,一天都不離開我……”她猶豫片刻:“就是有時我倆單獨關(guān)在房里,他半開玩笑地說起誰誰漂亮,誰誰眼神會勾魂。還說我雖然長得不錯,到交際場合根本拿不出手,沒那個魅力派頭。我想我是般人家出身,他又不是結(jié)婚前不知道。后來他媽媽也半真半假地對我說,她兒子找我找虧了,沒半點圖頭。他們這樣搞得我特別緊張,越想討他們喜歡,關(guān)系就越處得受罪一樣。但沒想到全家都會對我突然翻臉,那天我跟王雋頂了兩句嘴,引出他母親一通大罵,接著他姐姐闖上來叫我滾,還一邊用手拖我,我一掙扎就被她打,最后還是保姆上去抱住她,叫著不能打人,我才沒被打得更慘……”
我打斷她問道:“這時王副司令在哪?”她說他不在場,并滿懷希望地說若在場就好了。她就那么帶著傷帶著淚跑出了首長院。第二天想去拿軍帽上班,門口警衛(wèi)擋住說:“你不準進。”有兩個過路婦女說她們認識李彤,警衛(wèi)說我們曉得她是誰,但里頭打了招呼,以后不準她進了。“我當時硬是用背抵住墻,才沒讓自己倒下去。”李彤說。
接下去的許多天,李彤僅是躺在集體宿舍流淚,淚水漚爛了她的眼臉。這期間不斷有人來與她談話,無論好聽的難聽的,意思只有一個,就是讓她明智些。不管她怎樣堅持,王雋最終會成功地和她離婚的。
一直在期期艾艾訴說的李彤,忽然凄厲了一句:“那他為什么不喜歡我了呢?……他為什么不喜歡我了呢?!”
“你看你看,”我說,“你錯就錯在這里!……你為什么總想著要他,讓他們來喜歡你呢?!你是活人,活人都應(yīng)主動地去生活!不是物件,只有被動地擺在那里,任人家喜歡或不喜歡!……”我的手在空中亂掄,掄得李彤眼睛一眨一眨的。這時我才覺得自己發(fā)了毛病,沖這個膽小乖順的女孩吼什么。“你為什么不直接去找王雋的領(lǐng)導談?wù)劊俊?/p>
“我找過。不過你曉得,他跟他的上級還不知誰領(lǐng)導誰呢!我們正在談,王雋進來說你不要理她,那位上級就乖乖地不理我了。屋里就剩我和王雋,我差不多跪下求他,我說我15歲你家就看上我了,是看著我長大的我有什么不好,以后可以改,為什么要對我這樣呢?他沒講一句話,直到他單方面的離婚起訴書遞到我手上,讓我簽字。他仍沒有在上面寫出一條像樣的理由。你想想,我要真簽了,還有什么活頭?我真的好想好想去死啊。”我認真聽著,以至她離去后我一想到她誠心誠意以求一死的聲調(diào)還會心驚肉跳。
李彤找我的目的,是想請我?guī)退话眩瑢懳恼陆o任何一個可以為她伸張正義的地方。文章很快寫出來了,半個月后,我收到某法律雜志的退稿箋,說是這并不屬于法律范疇,而屬于道德范疇。我立即投奔另一家與此沾邊的刊物,不料又被拒絕說:只要有打人行為,完全可以算法律范疇。那么我的稿又像只球似的被打回到前者界內(nèi)。然而被告知:被打傷要有證據(jù),比如疤痂什么的,最好現(xiàn)打現(xiàn)告。我趕緊找到李彤,一看,傷處已消失。最終我找到了婦聯(lián),她們愿意干涉此事,但她們提出首先要與李彤本人談?wù)劇_@個不難,我想。
卻是一連許多天,我沒找到李彤。在我替婦聯(lián)為李彤向上級寫申訴信期間,聽人說李彤幾番去請求有關(guān)部門,讓他們允許她見見自己的公公。她想結(jié)婚前這位老首長曾給她許多安慰和溫暖,最初是他對她非常的憐愛,才導致以后一切的發(fā)生。但保衛(wèi)干事對她說:“首長沒時間,不能見你。”
我一邊寫那封信邊牽掛著李彤的健康,以及她的情緒。讓我最擔心的一點是,像她這樣老實本分的女孩,會在這樣的打擊下精神崩潰,她說不定會瘋的,等我將信寫完,寄出,卻忽然聽到一個消息,說是分居后的李彤目前正被另一位首長的兒子追求。想起來了,那是個大塊頭小伙子,常在人們上班時看見他睡眼惺忪地開始晨跑。
終于給李彤打通了電話,沒容她說什么我就將這邊的一系列戰(zhàn)績報給她:“婦聯(lián)準備支持你把官司打到底!你現(xiàn)在馬上出來,我在大門口等著你,然后我?guī)闳D聯(lián)!”
老遠看見李彤走過來,換了便裝,一身花的連衣裙,身材雖瘦,胸脯卻撐得滿滿的,膚色又那么水靈。一時間,我為她的健康和情緒懸了許久的心輕輕地擱下了。在我為她安排向婦聯(lián)陳述時的前后秩序時。她顯得心不在焉。“別怕,你說不定會贏!”我說。
她忽然對我笑起來,說:“哎呀,我一點都不想去了!我現(xiàn)在想開了,離就離嘛,我又不是七老八十!”
我一聽高興了,這姑娘養(yǎng)傷養(yǎng)病,養(yǎng)出志氣來了。
“我真正是想開了—去找一個比王雋還帥的,比他爸爸官兒還大的唄!”李彤認真地對我說。
調(diào)到北京后,幾回搬動舊稿子都看見我為李彤寫的那封信,我也不懂何故我留下它。似乎我超然地、淡泊地、甚至游戲地寫了那么多東西,唯有它是我干的一件正經(jīng)事。巧極了,當這天我又翻出它來時,有人叩門,竟是李彤。我們已有四五年沒見了,甚至連有關(guān)她的消息都不再有人告訴我。她說她到北京出差。她頭發(fā)更少了,臉上涂了一層挺厚的粉。東拉西扯一會兒,我問起她的婚姻,她說她有一個女兒了,是王雋的。王雋有一陣又喜歡她起來,說是“轉(zhuǎn)來轉(zhuǎn)去覺著你還是挺漂亮的”。于是他把她帶回家,她心一軟也就讓他帶回家,兩人瞞著父母一塊兒住了幾天,但從她懷孕到孩子出生,他就始終不出現(xiàn)了。
“我現(xiàn)在在學外語。”她說,笑了一下,脂粉下有了不少細皺紋,也還有她往日的老實巴交。“他們講,法國人和美國人都很喜歡中國女孩子。哎呀,我現(xiàn)在真正是想開了。”
我拿出我那胡扯的勁頭,對她說想開了就好。我有什么好自責的呢?我只是不由自主在為她祝福也為她擔憂,但愿她不再誤入歧途而能找到那個真正屬于自己的星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