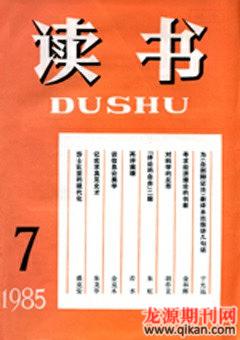談武俠小說和偵探小說
東方望
武俠小說和偵探小說屬于通俗小說,同流行歌曲一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過“通俗”和“流行”都是說明其讀者之廣;也許從所謂“接受美學”的觀點來看,這是不可忽視的;若作為社會文化的一種表現,這也還是不妨試作粗略考察的吧?
不算清朝的,只作為現代的東西,不管那些《七俠五義》、《七劍十三俠》以及《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之類,只從五四運動前幾年算起。我略略回憶一下,值得提出而確實流行過的,“武俠”類可舉出陸士諤、不肖生(向愷然)、還珠樓主(李壽民)以及香港的梁羽生。金庸的,內地見不到,可不算。至于《荒江女俠》雖拍過電影,也可不提,那是沒有特色一閃而過的。“偵探”類有寫福爾摩斯和亞森羅頻的,近年才譯出的克里斯蒂和松本清張的。還有些某某偵探案之類算不上流行,連亞森羅頻的名聲也比不上福爾摩斯。這個英國偵探的案子先譯成文言,后改譯為白話,解放后又有新譯本,最近還加上電視連續劇,真是至今不衰。此外還有一些反間諜小說。
一排名次就可看出這兩類小說雖都流行,卻有一點大不相同:“武俠”是國貨而“偵探”是舶來品。解放后出版過“反特”小說,也是從蘇聯譯過來的。自己創作的始終打不響。“武俠”卻象中國的武術一樣“獨步全球”。現在的電視劇《霍元甲》、《陳真》,出于香港,不大地道,也還是國貨。
這是怎么回事?我們的“公案”為什么不能發展成為偵探小說?這個問題先讓大家考慮吧。
一提到武俠小說,為什么我立刻想到這幾個作者?可以查看一下。
陸士諤是上海的中醫,寫小說并不是他的專業,但他可以作為那一時期的同類作者的代表。他的小說題目我記不起來,內容特點卻很明白。一是正當民國初年,他突出了滿漢矛盾,著重寫雍正時期的劍俠。雍正奪嫡,組織“血滴子”暗殺集團;由文字獄而全家被害的呂晚村的女兒呂四娘成為刺殺雍正的劍俠。二是他宣傳了內功和所謂武當派。傳說確有其人的甘鳳池(《儒林外史》的鳳四老爹)屈居雍正八俠之末,而“不見經傳”的虛構人物卻高居前列,顯然是為了便于對內功作神奇的描寫。這兩個特點不但風行一時,而且到梁羽生的《武當一劍》、《七劍下天山》還寫明末清初和內功劍法。因此我不能不提起開這個頭的陸士諤。
向愷然曾去日本,早年署名“不肖生”寫過《留東外史》,書不好卻出了名。以后他寫起武俠小說,大出風頭。《江湖奇俠傳》中的一部分故事演成電影《火燒紅蓮寺》,成為一種典型。另一部《近代俠義英雄傳》宣傳了霍元甲。這兩部都是一集又一集,沒有寫完。這也開了寫不完的連續小說之風。他寫的和前人有所不同。一是他是湖南人,把湘西的“辰州符”寫得神乎其神,不僅是“祝由十三科”的巫術,而且加上了神怪的成分。二是他本人和精武體育會有關系,懂武術,內功外功都寫的偏于內功,寫了霍元甲時期的真實加虛構的英雄俠客。他寫的不是滿漢的種族矛盾而是提到對外的國家矛盾了。這一點在近來的香港電視劇中還可見到。此外,他的文筆和構思也超過前人。他寫的放木排的辰州“排客”和人斗法,吳大屠夫訪師學藝,羅某為師報仇,“窯師傅兩斗鳳陽女”等故事很能吸引那時的好奇的青少年。解放初報載他進了湖南文史館,還在講精武體育會。
“平江不肖生”擱筆多年,張恨水占了通俗小說的頭把交椅,但不寫武俠。抗戰結束后出現了署名“還珠樓主”的李壽民,轟動一時。他的《蜀山劍俠傳》寫了五十多集還未完,在上海曾編成連臺戲上演。他沒有繼承不肖生的武術宣傳,而發展了不肖生的神怪故事。他寫的“蜀山劍俠”,開頭并無足奇,幾回以后忽然出現“綠袍怪”,從此愈出愈奇,編造了幻波池和峨嵋“開府”的大故事,再套進小情節。他同時寫幾部永遠“未完”的長篇小說,《青城十九俠》、《長眉真人傳》等。除人物繁多和情節離奇之外,他也有不同于前人的特點。一是他是四川人,延伸了不肖生的湘西巫術而大寫西南少數民族巫術。二是他把“法術”現代化了。什么“空谷傳聲”,分明是無線電話。所寫的法寶仿佛原子彈爆炸。他的有些希奇想象物可以看出是在二次大戰以前想象不出的。“劍”已經不是“一道白光”了,脫離了荊軻、聶隱娘等的傳統。他寫的兩派斗爭也明顯不是傳統的世襲宗派斗爭,有了現代的影子。解放初他還出了一本小說,寫西南民族。在序中說,他聽了領導文化的同志對他談話,有所覺悟,作了自我批評。以后他便銷聲匿跡了。
“武俠”在大陸絕跡以后,在香港仍連綿不斷。梁羽生參加了一九八五年的作協代表大會,寫“武俠”的作家也得到承認了。從我所見到的他的幾本小說看來,他繼承了以前的一些特點而抹去了“神怪”色彩,改寫成“神奇”。他注意了小說作法,企圖加一些“藝術性”。他繼續發揮內功勝過外功的近代傳統觀點。他的小說也有改為電影的,和流行的武打片中硬碰硬的“功夫”有所不同。他想突破傳統的為消遣娛樂而寫的束縛,但仍未能解脫出來。
從以上的約略考察可以看出,這些小說和古代的俠客描寫貌似而神非,明顯是隨社會文化推移而有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從古到今對于武術有兩種想法:一是武打,以力和術取勝;一是超出武打,以內功不戰而勝,甚至由神奇到神怪。古時雖有“妙手空空兒”的故事,但到現代才大發展。這是一種趨向,也是我國的一個獨特傳統,講究以柔克剛,以弱敵強,以內勝外,仿佛是精神力量超過物質力量,和外國的擊劍不同。目前電影和電視中表現的是硬碰硬,不是小說中的軟碰硬了。是不是又要有變化?還是退了回去?
中國的“武俠”和外國的不同。歐洲有過中世紀騎士(唐吉訶德所摹仿的),印度有過剎帝利(武士),日本也有過武士。中國始終沒有形成這樣的穩定的社會階層或集團。從司馬遷寫《游俠列傳》以后就不見有史家再寫,只唐代傳奇中還有一點。社會上沒有職業性的武士,卻有打斗的宗派和幫伙。文人、武官、盜賊、乞丐、和尚、道士、尼姑、婦女、工、農、商、莊主以至貴族、皇帝(雍正)都可以參加在內,作為俠客。專業的只有受雇于統治者或豪門的打手、保鏢,那也往往出身于綠林而為俠客所鄙視。黃天霸畢竟不如竇二墩。特別的是俠女,自唐代以來有過不少,最為人所喜愛而流傳。《聊齋》中也寫《俠女》。《十三妹》編成戲曲。這好象是外國沒有的。可以說“武俠”在中國是獨樹一幟的。外國的“行俠仗義”不同,若有類似的便會受到歡迎。例如司各特的書,林琴南(紓)譯為《撒克遜劫后英雄略》而流行。大仲馬的書伍光建也譯為《俠隱記》,后來又叫《三劍客》,其實是《三個火槍手》。中國人歷來心目中的英雄和外國的不同,總帶些俠客之風。從前拜倫的詩為青年人讀英文時所愛好,恐怕也是因為他有點俠氣。不少人喜歡他的武裝肖像。奇怪的是,為什么這一特點現代只存在于通俗小說之中?為什么現在武打片中只見宗派少見俠義呢?就過去的小說而論,寫打架和打仗的似乎無論西方或東方都沒有超過中國的,正象《孫子》巍然為世界戰略書最高峰一樣。怎么現在不行了呢?青少年從這些既不“俠”又不“武”的“武俠”能學到什么呢?
偵探小說僅靠進口,不能自己制造,那就更加奇怪。法國人編造亞森羅頻也抵制不住福爾摩斯,這不是一國情況。但各國畢竟有自己的同類型小說。蘇聯自有其反間諜小說。日本人更發展出獨具一格的推理小說,現在又出現所謂“企業懸念小說”。英、美也自有其犯罪小說,克里斯蒂的封閉式推理風靡世界。為什么中國出不來呢?翻譯的偵探小說有人看,可見不是銷的問題而是產的問題。也許是我們的罪案較少,難以取材;也許可以試比一比審案的不同。外國這些小說中主要寫靠求證和推理去偵破罪案,著重的不是判案。中國自從漢、唐的酷吏直到清末《老殘游記》寫的“清官”,都是判案靠刑具和口供。包公也不過是先做點私訪,判案時照舊。所謂“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和“請君入甕”就是古代的傳統。好象是歐洲重過程,中國重結果。有證,有供詞,即作判斷,無須推理、考核。中國哲學思想史中邏輯也自有一套,歐洲式或印度式的《墨辯》、“名家”、“因明”并不發展。流傳的是判斷式。判斷充滿了經史子集,很少追究“為什么”,著重“是什么”。印度傳來的神秘主義的《金剛經》還要再三問“何以故(那是由于什么原因)?”然而“天命之謂性”,“道可道,非常道”,“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這一類都是不講道理,不查證據,說是什么,就是什么。“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口供畫押就算定案,何必費事傷腦筋去查核證據推索理由?是不是這個思想習慣傳統壓在身上,以致五四運動以來幾十年還沒有徹底決裂,竟影響到偵探小說不發達?
我國第一部文學總集《詩經》的編者(掛名孔仲尼)很高明。他的詩歌分類是“風、小雅、大雅、頌”,從民間到廟堂。這一直貫到五四運動。“騷”可以說是“楚風”。第二部總集《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掛名主編)就分類繁瑣了,但還收了《奏彈劉整》,其中有口語供詞。第三部總集《玉臺新詠》(梁、陳徐陵奉命編)似只一類,歷來被認為格調低下,壞在那篇序文,但它還收了《孔雀東南飛》和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不壞的詩。文學作品可以有高低、優劣之分,但一個類型出現了,流行了,就很難用一紙命令或一場輿論取消它。不屑道者未必不屑一看。流行的“武俠、偵探”之類作品不高,不優,也許是能寫的人不寫,不能寫的人要寫;也許是寫的人不了解所寫的,或則所寫的不是心里所要寫的。為什么編電視劇還要乞靈于《水滸》、《西游記》、《包公案》呢?那不是古代的通俗小說嗎?為什么宣揚“舊道德”和“人情味”的日本電視連續劇能在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受到觀眾歡迎呢?是不是可以作為問題提出來,請大家思考一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