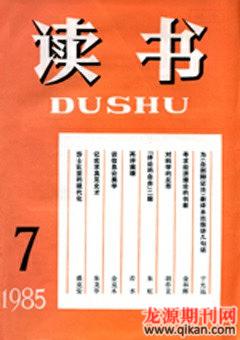重讀湯因比《歷史研究》(節錄本)
謝遐齡
各門社會科學中,歷史學是最基礎的學科。不但國家領導人必須具備敏銳的歷史感,就是學者們,若想讓自己在專業研究上有功于本國和人類的發展,也必須有歷史感,必須懂歷史,尤其是懂世界歷史。一些西方大國,連情報部門的首腦都由學術造詣高深的世界歷史學家擔任,使得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在作出戰略決策時,往往表現出深遠的眼光。
不容否認,在我們的基本觀念中缺少了重要的一環:中國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這個問題亟待研究。我國的改革和四化建設亟需歷史學家的建議。應當改變長久以來忽視世界歷史學的傾向。而要研究世界歷史,讀一讀當代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著的《歷史研究》,無疑是有益的。
按西方標準,湯因比這部著作可歸入歷史哲學類,盡管他的學說意在提示西方世界的領袖們,在決策和領導時應遵循怎樣的原則,才能防止西方文明衰落,同狄爾泰、克羅齊等人的歷史哲學相去甚遠。按中國標準,湯因比的理論屬于哲學。《歷史研究》雖然夠不上劃入經類,也應入子類,很難入史類的。中國哲學強調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這一點上來看,湯因比的路數頗合于中國哲學,他的書,我們讀來會感到很有興味的。一個半世紀以前,中國被西方的炮艦逼迫著加入了世界,這使我們觀察世界的眼光,混雜了屈辱、憤怒、恐懼等色彩,我們失去了昔日固有的泱泱大國之風。今天,中國正在崛起,我們應當采取一種新的眼光,觀察國際社會的歷史運動。在這方面,湯因比的書會給我們提供一些啟發,何況,他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還把世界的和平、繁榮的希望寄于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湯因比生當維多利亞盛世,在他接受希臘文化教育之后,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很自然地,他由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聯想到公元前四三一年雅典-伯羅奔尼撒大戰爆發。后者標志古代希臘文明開始衰落,那么,前者是否標志西方文明開始衰落?他進一步提問道:既然每個文明都可能死亡,那么,西方文明是否必然死亡?
湯因比的思想先驅斯賓格勒,在其所著《西方的沒落》中,主張文明象生物一樣,要經歷生、長、老、死四個階段;因而,對任何一個文明,死亡都是必不可免的。這種觀點未免悲觀得沒有道理,其病根是科學主義,即把自然科學的方法照搬到屬于理性、意志領域的文明歷史中。科學主義忽視人在創造歷史上的主動作用,會導致宿命論。
相反,任何一種取積極態度的歷史理論,都應強調人的主動性,或曰主觀能動性,或曰主體性。這種態度,按中國典籍中的說法,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十二年前,我第一次讀《歷史研究》節錄本時,衷心感佩的,還不是湯因比極為淵博精深的知識,也不是他駕馭材料的非凡才能,而是書中到處閃爍著的自強不息的精神。他強調人的創造性和自由,指出文明不是注定要死亡的,一切取決于人自己的努力。這些,不正是振興中華所特別需要提倡的嗎?
湯因比的自強不息態度,集中表現在他的理論對精神因素的強調上。
在兩個基本論點上,他與斯賓格勒是一致的。其一是:作為歷史研究對象,可以從自身說明問題的最小單位,是社會,或稱文明,而不是獨立的區域性國家。英國只可算區域性國家,整個西歐才是一個文明的空間范圍。
第二個基本論點是,一切所謂文明類型的社會的歷史,在哲學意義上都是平行的和具有同時代性的。“公元后的一九一四年和公元前的四三一年,在哲學上是屬于同時代的兩個時期。”(《歷史研究》(節錄本)中譯本,下冊,第428頁)這兩個年代的同時代性,在于它們各標志一個文明開始衰落。
這個基本論點(也可稱為基本假設)在方法論上十分重要。湯因比要診斷西方文明的命運并開出藥方,須認定歷史中有法則可循。新康德主義巴登學派主張歷史中無法則可言,是假設歷史事實為一次性的,自然現象才有重復性,因而自然科學是制定法則的學科,歷史學是描述特征的學科。要得出歷史有法則的結論,須假設兩點:一,文明多元論,即有足夠數量的文明;二,這些文明有平行性,即有相當于自然現象的重復性(或齊一性)。湯因比把六千余年的人類文明史劃為二十一個或二十六個文明。“二十幾”這個數字對制定法則說來,是遠遠不夠的。原始社會有六百五十幾個,這個數字剛夠制定法則。因此,他自己承認,整個《歷史研究》的探索帶有冒險性。平行性的意義是,一切文明的發展,都可用“起源、生長、衰落、解體、死亡”五階段模式描述和解釋。
在第三個基本問題——文明起源問題上,他便同斯賓格勒分道揚鑣了。他鼓吹英國經驗論,反對斯賓格勒的德國先驗論。有趣的是,本來屬于科學主義的經驗論,到了湯因比手里,由于他把少數天才的精神生活看作中心因素,成了反對科學主義的有力武器。相反,在文明起源、死亡等問題上,斯賓格勒尋求自然規律式的確定性,忘記了由于人有主動性因而人類事務有不可預測性、不確定性,在墮入科學主義的同時,不得不伸手向神秘主義求援。
文明的起源有兩類情況,一是從原始社會進到文明社會(這時是第一代文明),一是從正在解體的文明中誕生出新的文明(第二代或第三代文明)。由此,對文明起源的性質可得出一個公式:從靜止狀態轉入活動狀態,或由靜到動。
在這一過渡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物質因素還是精神因素?湯因比的回答是:精神因素。
為數眾多的原始社會,為什么只有很少數過渡到文明社會,絕大多數卻沒有發明農業、冶煉術等,從而打破靜止狀態,進入活動狀態?這只有到精神方面找原因才說得通。文明是精神創造出來的。作為物質因素的生產工具,應當算文明的組成部分,也是精神創造的。“人是制造工具的動物”,工具是人制造的。要造出,先須想出,想在做之前;制造工藝,也須想出。想是創造的關鍵環節。
只要把原因歸結到精神方面,那么,精神上領先的必定是少數人。其實,不討論富有創造性的人物是否在總人口中占極小比例,也可以肯定,創造的實際過程,總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率先想出,其他人隨后在行動上跟上。倡導、制定新政策的,不總是少數幾個人嗎?湯因比把在文明發展中精神上領先的少數人稱為創造性天才,把大多數人跟隨少數人的行為稱為模仿。
精神因素包含兩個方面,除了創造性,還有自由。談到自由,中國人往往理解為縱情肆欲,于是一面是得志便猖狂,另一面是視之如洪水猛獸。因為自由概念來自西方,所以談論自由的那些西方哲學派別常受牽累。實際上,在西方,社會自由不但講權利同時還講義務,而且,哲學中的意志自由,恰恰要求克制情欲、遵守道德義務。人是自由的,并不意味人的行為任憑自己的情欲和物質利益所左右。恰正相反,人的自由意味他擔負著沉重的社會責任,要求他審慎地作出選擇,使自己的行為合乎道德法則。
創造性和自由選擇二者說明了文明發展的不可預測性。這是科學主義的滑鐵盧。按自然規律可以預測,任何一個原始社會,都應當有創造性人物存在,時不時地閃現出幾點創造的火花。按自然規律卻無法解釋,為何不是所有的火花都燃起燎原大火。自然規律止步之處,便是意志自由生效之處。天才的精神創造,須通過人們的模仿,才能使社會由靜入動。天才得不到模仿,其代價便是付出自身的生命。對少數天才說來,面對創造出來的各種方案,須作選擇;對多數人說來,也存在著模仿與否的選擇問題。對文明的起源,多數人的態度起著決定性作用:原始社會同文明社會的根本區別,就在于模仿的方向不同。在原始社會里,模仿的對象是老一輩,包括已經死去的祖宗,他們的觀點和主張極有權威,并通過活著的長輩支配著整個社會,傳統習慣占據統治地位,天才遭到扼殺。而在生長中的文明社會里,模仿的對象是富有創造精神的開拓型人物,傳統習慣的堡壘被沖開了,社會生機盎然地前進著。
湯因比如此強調人的精神因素對文明發展的作用,是同他的歷史學家兼國務活動家的身分相合的。而且,在創造性和自由二者中,他注重后者,其意味更為深長。歷史學家的眼光不同于哲學家的眼光。歷史學家不僅要鑒定一種思潮的性質,更要從思潮及其嬗遞中窺出文明在生長抑或在衰落、解體的消息。如果說,盧梭、康德貶抑科學、知性而主張感情或意志的優越地位,表征西方文明在生長;羅素指斥盧梭為極權主義張目,攻擊馬克思“人類中心論”,表征西方文明衰落;那么,湯因比的學說上承盧梭、康德的反科學主義態度,卻不說明西方文明的生長,僅說明湯因比在力圖把西方文明從衰落扭轉到生長的道路上來。論不合時,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是他的悲劇之所在。
就世界論中國
湯因比的體系中有許多新奇的思想,其最著者,也許是一反常識,不把統一國家看作文明生長的現象,反而看作文明解體的象征。其實,他的論點自有合理之處。通常人們衡量一個人是否興旺,看的是他的財產與權勢,不看他的德行的光輝和創造性煥發出來的魅力。類似地,通常人們衡量一個社會是否興旺,看的也是它的威勢。夷平各種不同思想被贊揚為“文治”,建立統一國家、對外軍事擴張被稱頌為“武功”。但是,一個人的財勢不能令人生敬生愛,徒令人生畏而已。而一個人若不令人生敬生愛,是不可能白手起家,變得有財有勢的。一個國家要有實力,同樣必須經過創業。考慮創業,就要研究文明的生長問題;選取文明為研究對象(這是湯因比的第一個基本論點),就必定得出相應的結論。
用湯因比的理論觀察中國歷史,會給我們許多啟發。在湯因比看來,中國歷史可劃分為三個文明:商代文明,古代中國文明(約公元前十一世紀到公元五世紀:商朝末年——魏晉時期),遠東文明主體部分(公元五世紀——二十世紀,遠東文明還有日本—朝鮮分支)。古代中國文明開始衰落的標志是公元前六三二年晉楚城濮之戰,而秦、漢帝國是這個文明解體過程中建立的統一國家。十六國時期,是蠻族軍事入侵的混亂時期。公元二世紀從貴霜傳入的大乘佛教,和東漢末年張陵創立的道教,則是內部無產者創立的高級宗教。大乘佛教是遠東社會的蛹體。隋至盛唐時期是遠東文明主體生長到頂峰,安史之亂時開始衰落,五代至南宋屬于解體階段的混亂時期,元帝國、清帝國是解體階段的統一國家,明清時期這個文明在解體過程中進入僵化狀態。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教,被看作解體中的遠東文明主體的內部無產者在外來靈感的刺激下創造的宗教。
近代,西方國家侵入中國,被看作西方文明同遠東文明主體在空間上的接觸。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是西方文明對中國社會的挑戰。一七九三年馬戛爾尼勛爵使節團到達北京,要求建立英中外交關系,中國社會的應戰是乾隆皇帝的拒絕。一八四○年爆發的中英鴉片戰爭,是對同一個挑戰的新應戰。以后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是對這力度越來越強的同一個挑戰的各次應戰,都是失敗的。無論勝敗,在一系列應戰過程中,中國社會在逐步被西方文明同化為后者的內部無產者。
與古代中國文明解體時入侵的是蠻族軍事集團不同,近代中國社會遇到的是一個文明社會。不能說這個文明比中國的文明高級。這兩個文明同屬第三代文明,它們各是古代希臘文明、古代中國文明(均屬第二代文明)的子體文明,無高下之分。只是,處于僵化狀態的、解體過程中的中國,碰上了正在生長中的西方文明,當然敵不過后者。
如果同意上述分析,那么可以得出許多重要結論。過去,中國就是天下,盡管也談治亂興衰,并依之判定身處的時代狀況,以決定應取的方針,但終究是就中國論中國。過去,中國雖然同古代印度文明等接觸過,畢竟只限于宗教、貿易等,與近代以來同西方文明全面接觸相比,不可同日而語。現在,中國已不是天下。可是,我們往往仍然就中國論世界,還不能就世界論中國。不認清中國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將很難在世界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如果西方文明已經開始衰落,甚至進入解體階段——目前處于建立統一國家之前的混亂時期,那么,現在的中西文明之間的關系,同一七九三年、一八四○年已大不相同了。作為西方文明的一個可能的新成員、作為一個獨立的區域性民族國家,中國社會至今遠遠沒有完全西方化,也許不可能徹底西方化。西方文明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大機器工業帶來的異化。而從古代中國文明以來形成的文化傳統,對治療使西方社會陷入無以自拔困境的異化,可能是一帖良藥。中國也許能在工業化的進程中創造出一條新路,保持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從而引領西方文明繼續生長;或者,中國以天下大一統的傳統儒道思想,擔任解體中的西方文明的引導,建立統一國家,從而保證世界的和平與繁榮——這是湯因比晚年的希望。
中國也確實表現出了巨大的創造性。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便體現了這種創造性。在由于極左思潮的肆虐而經歷過一段時間的沉寂之后,這種創造性現在又重新活躍了起來。一九七二年,湯因比在論到中國時,雖然已寄希望于中國,但對前景仍感到把握不定。他寫道:“西方文明的浪潮洶涌襲來之后,中國人卻在痛苦中趨于分裂。‘西化乎?‘俄化乎?‘本位乎?中國人在西方文明的挑戰下,尚未表現出有力的創造性應戰。”今天,我們可以確定地說,中華民族已經走上了一條創造性的道路,既不“西化”,又不“俄化”,也不“本位”。創造性表現為不拘成格、試探前進。什么時候認為很有把握、有成套經驗可以應付一切,這時往往就是衰落的開始。什么時候認為沒有把握、沒有辦法,這時倒往往是一派生機勃勃的興旺景象。湯因比在談到哺乳動物戰勝爬行動物,成為地球的主人時,同意赫爾德的論點,主張原因不在物質方面,而在心理方面。“這種心理上的防衛之所以有力,是因為它的精神在實質上是處于一種毫無防護的狀態”。哺乳動物的血是熱的,因而感覺敏銳,“它不但能解決一項問題,而且能解決許多問題,因為其中沒有一項是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中冊,第109—110頁)。這不是很有啟發性嗎?中華民族的創造性在今天的集中表現,是鄧小平同志標揭出“實事求是”的大旗,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它得到了舉國上下的熱烈擁護。中國的前景是光明的,并有可能為世界歷史帶來新的轉機。西方歷史學家重視中國改革的進展情況,其原因恐怕即在于此。我們自己也有必要認識改革的世界歷史意義。也許,我們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為人類創造出一個新的文明——“第四代”文明。
湯因比的知識分子理論,也有參考價值。他把知識分子定義為一個起著“變壓器”作用的社會階層,它產生于兩個文明在空間上接觸時處于守勢的那個社會中,任務是改變本社會人們的生活方式,使其適應處于攻勢的外來文明的節奏。第一批知識分子是海陸軍官(洋務運動時期的北洋艦隊),接著是外交家,然后是商人(廣州的行商),最后才是知識分子最為特有的形式——教師、文官、律師。在任何情況下,只要出現了知識分子,就證明有兩個文明發生了空間上的接觸,而且其中一個正在被另一個吸收為內部無產者(中冊,第190—191頁)。按湯因比的學說,把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同古代中國的“士”相提并論的流行觀點,是錯誤的。古代中國的“士”,并不是兩個文明接觸的產物。如果同古代中國相比較,現代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可以劃入“士、農、工、商”中的“士”,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要劃入“工”。古代中國的科學家、發明家、技術人員社會地位一般較低,由此可以得到解釋。而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厄運,是中國社會抵制西方文明同化作用的表現。他們地位的改善,則是中華民族創造性再度活躍的征象。
新文明的誕生與全社會的精神變革
對湯因比的責難,無過于斥他為“神學家”、“宗教家”了。
這是不公允的。不錯,在《歷史研究》中,隨處可以讀到湯因比鼓吹宗教重要性的言論。不僅如此,在他的基本理論構架中,宗教還占據極重要的位置。他先是把教會(誕生于第二代文明的解體過程中)看作第三代文明的蛹體,而后,他更把教會看作高一級的社會品種。按這種看法,人類發展的最后目的和歸宿,是綜合現存四大高級宗教(基督教、大乘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的全教會社會,而曾經存在過的各文明社會,只不過是走向這個全教會社會的手段和階段。
對于湯因比的這一觀點,我們是難于茍同的,然而,據以論證他是神學家或宗教家,似乎證據還嫌薄弱。他自己聲明過,“我不知道究竟有沒有上帝”,“我并不是一個信教者,……我不能符合基督教的信條”(《湯因比論湯因比》)。事實上,他只不過是一個認為宗教在人類歷史中起著巨大作用的歷史學家和哲學家,連做個普通教徒都不大夠格,更談不上當神學家了。
我們不贊同他以宗教為軸心和歸宿的歷史觀;作為中國人,在自幼長大的環境中,從未有過湯因比所感受過的那種宗教氣氛,很難對宗教有否積極作用有切身的體驗。盡管如此,他的歷史觀中的合理成分,還是可以看到的。
首先,他強調宗教的地位,是為了反對科學主義,克服異化。他上承盧梭的學說,主張宗教以感情為基礎;并承襲康德的學說,主張知性的語言不能充分表達靈魂的見解。盧梭認識到近代科學向西方社會提出了異常重要的道德問題,清醒地看到,科學未曾、也無力解決道德問題。康德受到盧梭的啟發,轉變了自己早期的科學主義立場,開始重視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問題。康德認識到,在他所處的文化背景和社會條件下,要遏制科學主義,只有依靠宗教。要重視人,就應當把實踐理性的位置擺得高于理論理性,這就是說,在道德和科學的沖突中,天平應當擺向道德一邊。上述原則在西方社會中的具體化,就是假設上帝存在。
湯因比完全繼承了康德的這套主張。也許,由于是后來者,他看得更為清楚一些:既然西方文明是基督教文明,要擺脫上帝去另尋一個假設,終究是一件耗力無功的事業。由于他所處的時代比起盧梭、康德的時代,西方社會的異化更為嚴重,他反對科學主義的言論,雖然不象尼采那樣尖刻,激烈程度卻相差不遠。例如,“人對于非人類自然界的支配力向前進展一英里,還比不上他對于處理自己、處理同胞、處理神的能力向上提高一英寸那樣重要。”(下冊,第122頁)
基督教是兩個因素的綜合,即猶太教的人本主義同希臘哲學的科學主義的綜合。中世紀神學、經院哲學的全部爭論,都是這兩個因素的相互沖突。這沖突經過近代,一直延伸到現代。對上帝的強調一般屬于人本主義潮流。當然,這只是粗略的說法,實際情況是極為復雜的。湯因比道破了上帝的真面目,他說:“‘神的法則顯示一個人的理性和意志所追求的單純不變的目標。”神的法則就是人的自由(下冊,第320頁、第365頁)。這就是說,他用“神的法則”體現全人類的共同理想。追求神就是追求人類社會的完善狀態。“神的王國”是自由王國的宗教形式。比起康德把追求神理解為追求個人道德上的完善,湯因比顯然要高明些。
其次,他強調宗教的作用,是為了有利于人在處理一切事務時保持謙卑態度,因為這種態度是文明生長的根本條件。謙卑是自強不息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所說的謙虛謹慎,一驕傲就要犯錯誤,是這一真理的又一種說法。中國古訓“小心翼翼”、“戰戰兢兢”,說的是同一個真理。就連當代科學主義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羅素,也強調謙卑,并懂得維持一種信仰是使人們謙卑的條件。羅素既討厭上帝這種假設,也不喜歡真理這個概念,但是,為了訓導人們謙卑,不得不二中擇一時,只得挑出真理概念供信仰之用。由此可見,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學派,都要強調保持謙虛,那是做成任何事業最為根本的前提。而驕傲則往往導致獨斷論,導致社會和思想的退化與僵化。湯因比是歷史學家,眼界比羅素廣闊,比較的面要寬廣得多。兩人相比,羅素多少顯得有些感情用事,湯因比的說服力要強得多。
湯因比主張教會是新文明的蛹體,出于他認為,新文明的誕生、生長,以一個社會的精神變革為前提。哲學是解體文明中的少數統治者創造的,依哲學的本性,只是少數人的事業。宗教與哲學相反,它是內部無產者創造的,依其本性,對因文明解體感到深重痛苦的大多數人有強大的吸引力。因此,只有一個宗教運動才可能完成新文明誕生所需要的遍及整個社會的精神變革。大乘佛教前身是一種哲學,當它發展成宗教并傳入中國之后,從中誕生了遠東文明。湯因比的這些看法,如果我們不過于偏執狹隘,是值得深長思之的。魯迅先生棄醫學文,是他看到中國人的病根不在肉體而在靈魂。要締造新的中華文明,首先需要全民族的精神變革,實現國民性的改造。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人民革命運動使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已經有了極大的改變,從而為人類創造了嶄新的經驗。但是,看來還不能說這一變革已基本完成。如何從根本上改變國民性,如何使社會中那些特立獨行、富于創造性的開拓型人才得以順利出土,并發揮他們的社會作用,已成為今天的一個急迫課題。這是我們應當下大功夫研究、解決的。
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的基本立場是馬克思主義的,對湯因比理論中的許多東西,我們不能接受。與此同時,應當承認,湯因比提出的許多問題,不能因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就一律棄之如敝屣。
湯因比本人是富有創造性的,也勇于承認錯誤。他在晚年承認,以希臘模式衡量所有二十六個文明犯了簡單化的錯誤,而這是《歷史研究》的基本論點之一。他提出,除了希臘模式之外,還有猶太模式、中國模式。這等于說,《歷史研究》中關于中國興衰的評論,須作調整。黑格爾把中國文明貶為處于長不大的童年時代,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承認中國的獨立地位和獨特價值,已經高明得多。到晚年,由于對中國哲學有了較深入的研究,較深地體會了中國文化的精髓,他的見解更高明了。在他的理論中,中國文明的地位更高了。他認識到,在中國,人文精神超過宗教觀念。他從大乘佛教未能逐出儒、道思想這一事實,推翻了“統一教會創造第三代文明”同樣適用于中國的論點。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我們自己也應從中引出教訓,對我們的傳統文化,不可妄自菲薄。在現今,要深刻了解自己,必要條件之一是深刻了解西方文化;同樣,要深刻了解西方,必須深刻了解自己。在現今的條件下,作為中國人,無論是研究中國問題,還是研究西方問題,實質上都是比較研究。自覺地進行比較研究會使我們深入得更快一些。湯因比思想開明、積極。這個睿智的頭腦奉獻給中華民族的,我們不應拒絕接受。
(《歷史研究》,〔英〕A·J·湯因比著,〔英〕D·C·索麥維爾節錄,曹未風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冊,一九五九年八月第一版,2.05元,中冊,一九六二年三月第一版,2.65元,下冊,一九六四年三月第一版,2.7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