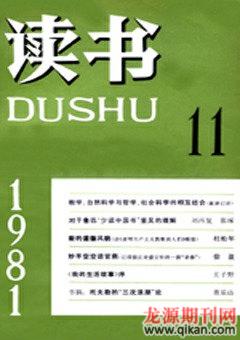是詩?是畫?
凌 宇
是詩?是畫?詩畫里有的東西它有,詩畫里沒有的東西它也有。它不是一曲戰歌,卻非軟性音樂;它真是一幅水彩,卻不失于纖弱,秀麗其衣,健美其質。汪曾祺的《大淖記事》,充溢著一種獨特的藝術魅力。
《大淖記事》寫的是一個愛情故事。但它不是一般的愛情悲劇,沒有一把淚,一滴血;也不是一般的愛情喜劇,三分幽默,七分笑料。它不落俗套,立意新奇。故事不能說不悲慘,但使人沒有重壓之感;描寫的風俗決不是美玉無瑕,讀了卻讓人神清氣爽。
故事的主線是巧云與十一子的奇特遭遇。它是悲劇,又不是悲劇。我們同情人物的命運,也憎惡那些邪惡勢力。但我們不能說同情,你要的“純潔”、“貞操”與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不可同日而語。從表象上看,大淖也真有幾分“風氣不好”,但骨子里卻充溢著美和力。真象蓮花,雖身出污泥,卻神骨不染。愛,錢買不到,強力搶不到。愛是心心相印,是靈魂的吸引。她們說不出這番道理,卻真正領悟了人生愛情的真諦。那些流氓、強盜,那些仗勢欺人的惡棍,當然該殺該剮。他們對女性的侮辱,是十足的野獸行為。巧云被人強行破了身,她痛恨那些惡棍,失悔“沒有把自己交給了十一子!”但過去的不能挽回,未來的全靠自己。有什么理由要悲不欲生,要跳水,要自殺,要為那些惡棍殉身?執著地追求生,追求愛,追求自己的權利,這才合理。巧云就看破了人生的這一層老殼。她不要救世主,也不要人來憐憫,她自己救自己。在巧云的行為面前,封建主義的貞操觀,豈不黯然失色?
人是環境的產物。巧云的行為植根于大淖的特殊社會環境。婚娶不用媒人,對所愛的人情愿在經濟上“倒貼”。因為愛情不是施恩的謝禮。這里的風氣與街里相比,哪里更好?確實“難說”。大淖的風俗和人物的行為當然不全是金子。金子混在砂子里,一切都還是一種混沌狀態。巧云被劉號長強行破了身,媳婦們只罵一聲“這個該死的!”巧云對自己愛情的執著追求,也不是意識到自己奴隸地位的自覺反抗。那是環境造成的,人物的行為擺不脫環境的制約。
礦砂并不就是金子。金子卻在礦砂里。《大淖記事》不是人物帶出環境,而是從背景中推出故事。它象剝筍。不,在剝之前,先是連根帶泥都掘起來。然后再一層層剝下去,最后才見到那透明純凈的筍心。在這浪淘沙式的選擇里,作者找到了對待生活應有的態度。
作者的情感傾注在人物的命運里。他沒有為她們流悲天憫人的淚。他知道這反倒會褻瀆了她們。向著未來執著的追求,使作品神骨健美。它沒有抽象的道德說教,卻把你的靈魂吸引了過去。在這充滿帶有幾分野性的生命活力的美面前,你得到了從那些聽厭了的道德說教里,從那些哀哀戚戚的悲歌里永遠得不到的精神和道德的熏陶。是作者說服了你?是作品中人物的品格說服了你?這都有。因為作者的心貼到了這些可親可愛的人物身上,我們提不出異議。
這些人物,這種生活形態,在現實中,也許特別稀少,那臨近大淖的街里就沒有。但正因為稀少,才顯得特別可貴。這些特殊的生活形態和地方風俗,是哪個時代或哪些文化傳統的產物,誰也沒法說清。但它確實有,不僅過去有,現在又何嘗沒有?不信,你去生活里尋找,只要你肯。即使真找不到,又有什么關系?關鍵在于作品處理得合理不合理。《大淖記事》在人物與人物、人物與環境的關系上,我們找不出大的毛病。
《大淖記事》給人的教益,主要不在它的題材本身。作者不是誘惑讀者去獵取特異的世態風俗,也不只是讓人陶醉于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透過題材的表皮,我們獲得了一種啟示:應該如何面對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它觸及到一個雖不是永恒,卻決不是一個短時期就消逝的問題。《大淖記事》里的故事早成過去了。它所涉及的問題卻仍在困擾著現代人的心。作者從一種特殊的生活形態里,看到了某種閃亮的東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看法對不對?許多人會這樣發問。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這個問題也許得不到統一的結論。但我敢說,《大淖記事》對生活矛盾的回答,不是悲泣,不是絕望,它具有一種向上的自信,一種健康的力。這種對生活的態度,也許逾越了題材本身的范圍,散射到生活的各個領域,適用于面對現實世界的一切矛盾。
這種向上的自信和健康的力從作品描寫的生活里透射出來。但作品在風格上,卻不以粗獷見長,秀麗才是它的本色。剛健的靈魂裝在秀美的軀殼里。外柔內剛,剛柔相濟,是《大淖記事》的獨特格調。
通篇是風俗畫的連綴。作者對社會風俗的熟悉、了解,寫來如探囊取物,不見任何杜撰的痕跡。娓娓敘來,如數家珍。三教九流,人情世態,觀察得細致入微,毫發畢現。保安隊捕匪過街,錫匠們唱“香火戲”與挑擔游行、頂香請愿,媳婦們在大淖里洗澡……,使人應接不暇。作者寫風俗,并非全般實錄,他有選擇。雖不是美化,卻是詩化了。作者從民風民俗里,別具只眼地提取出“詩”來。一切都那么情趣濃郁,詩意盎然。
有詩必有情。《大淖記事》調子輕快,但不輕佻。在現代文學中,我們也見過類似的題材,類似的寫法。但那些作品大都帶有一種感傷。《大淖記事》洗去了這種感傷。感傷并非一定不好。那時的作者,身處那個時代,沒法不感傷。黑暗的壓力太重,他們看不到足以使人自信的東西。翻閱解放前的雜志,偶而見到作者四十年代的一篇舊作,題為《囚犯》。同樣是寫士兵押送囚犯的情形。雖然作者也看到囚犯身上“有一種美,一種吸力”,但字里行間卻透出對人生命運的迷惘和感傷。也許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站在今天看昨天,蘊藏在生活中的內在的力凸現出來了。這是站在今天審視過去生活的好處。也許,作家在審美過程中,真得有這么一點距離?
這種秀麗的格調,取決于作者詩人的眼力,也取決于作者運用語言的功力。讀作者的小說,你會為他的文字的魔力所傾倒。句子短峭,很樸實,象在水里洗過,新鮮、純凈,“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每句拆開來看,實在很平常,沒有華美詞藻的堆砌,也沒有格言的鍛煉。但合起來,卻神氣全出。一句句向前推移,意象一層層蕩漾開去,構成形象鮮明神氣凸現的意境。
舊衣服,新托肩,顏色不一樣,這幾乎成了大淖婦女特有的服飾。一二十個姑娘媳婦,挑著一擔擔紫紅的荸薺,碧綠的菱角,雪白的連枝藕,走成一長串,風擺柳似的嚓嚓地走過,好看得很!
敘述樸實,卻有聲有色。越過文字的表皮,你沒有聽到生活的內在節奏,感到人物身上生命的活力?
小說不是沒有缺點。將大淖的風氣與街里那些沒有愛情自由的封建婚姻形態相比,優劣自無需評說。但大淖的風氣里畢竟羼雜著渣滓。違背生活真實,人為地加以凈化,固然不必;要求作者生硬地加以議論,于藝術也屬無益。但作者的態度終究太過客觀,這可能使一些鑒別力不高的讀者,良莠不分。個別細節描寫,如巧云對劉號長勉為其難,也損害到作品的審美價值。藝術對結構的要求,是布局的勻稱。《大淖記事》從環境中推出故事,這無可厚非。但作品對大淖風俗鋪述過多,進入情節較慢,前后篇幅的安排,使人略有失重之感。盡管如此,《大淖記事》仍是一篇優秀之作,從近幾個月來作者連續發表的幾篇小說看,作者在有意發展自己的獨特風格。雖然有對前代作家的借鑒與繼承,卻也有自己鮮明的個性和獨創。在不斷嘗試與探索中,作者一定會寫出更好的作品來,我們這樣期望著。
一九八一年四月,于北京大學
(《大淖記事》,《北京文學》一九八一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