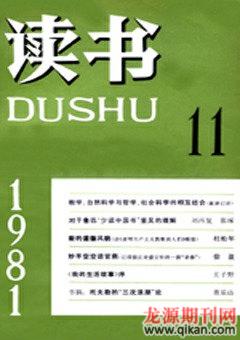泣不成聲的絕叫——《窮人》
胡從經
魯迅在《<豎琴>前記》中曾論及俄羅斯文學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形成了“為人生”的主流,列舉了近代俄國文學四大家的姓氏,認為他們是“為被壓迫者而呼號的作家”,其中即有陀思妥夫斯基(現通譯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筆者),雖然他們“離無產者文學本來還很遠”,但卻也道出了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叫喚,呻吟,困窮,酸辛”乃至“掙扎”。
由于對近代以至“五四”前后一段時期的翻譯文學史涉獵甚淺,未能考證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最初引進中國的具體時間;但魯迅曾指出最先“陸續翻譯他們(即指陀氏等。——筆者)的一些作品”的是上海的文學研究會,這大概與史實不會相悖太遠。現查文學研究會的機關刊物《小說月報》,其十三卷一期(一九二二年一月)即辟有“陀斯妥以夫斯基研究”專欄,刊發有沈雁冰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小航的《陀思妥以夫斯基傳略》、郎損的《陀斯妥以夫斯基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等,同時還披露了陀氏小影、手跡。在此之前,《小說月報》十二卷還編印過“俄國文學專號”的增刊,其“論文”部分有沈雁冰的《近代俄國文學家三十人合傳》,其中即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略;其“譯叢”部分則有陳大悲譯的陀氏短篇《賊》。文學研究會的另一機關刊物《文學周報》(《時事新報》副刊)第十九期(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也特辟了“陀氏百年紀念專號”,第二十期(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三十二期至三十五期(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都有關于陀氏的文章、資料。以上就是“五四”時期關于陀氏介紹的概況。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作品的中譯單行本,則是由魯迅主持的未名社翻譯出版的。陀氏作品第一種中譯本即他的成名作——書簡體小說《窮人》,韋叢蕪譯,經魯迅校閱并編入《未名叢刊》,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初版,印數一千五百冊。譯稿由韋叢蕪于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完成,翌年春即送交魯迅先生審閱。(查《魯迅日記》,韋與魯迅交往的最早日期為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該日記有:“得霽野信并蓼南文稿。”蓼南即韋叢蕪,文稿疑即《窮人》譯稿)魯迅后據原白光的日譯本予以校訂。
《魯迅日記》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條記有:“往東亞公司買《支那童話集》、……《賭博者》,……各一本,共泉十元二角。”《賭博者》即為上述原白光譯《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五卷,其中除《賭博者》(湖風版洪靈菲中譯本題作《賭徒》——筆者)外尚附有《窮人》,此即為魯迅據之以校改譯稿的日譯本。檢索《魯迅日記》,可見二五年至二六年間魯迅、韋叢蕪信札往來頻仍,并時相過從,惜這些函件大多散佚,已無從查考其內容,其中極可能涉及《窮人》譯稿推敲事。現存魯迅書簡中唯一論及《窮人》譯稿的,僅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致韋素園箋,其中說到:“昨看見張鳳舉,他說Dosto-jewski的《窮人》,不如譯作‘可憐人之確切。未知原文中是否也含‘窮與‘可憐二義。倘也與英文一樣,則似乎可改,請與霽野一商,改定為荷。”譯本的題名也商榷再三,可見魯迅先生在培育文學青年時一絲不茍的認真、負責態度。
《魯迅日記》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條記有:“上午寄素園信并《窮人》小引。”魯迅在《小引》中說:“中國的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將近十年了,他的姓已經聽得耳熟,但作品的譯本卻未見。……這回叢蕪才將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紹介到中國來,我覺得似乎很彌補了些缺憾。”魯迅還根據《陀思妥夫斯基文學著作集》(《Dostoievskys litterarsche Sch-riften》)、梅列士柯夫斯基:《陀思妥夫斯基與托爾斯泰》(Meresch-kovskys:《DostoievskyundTol-stoy》)以及
這里,我想說些題外的話,即二三十年代時,中國一些勇于變革、敢于身殉的先進知識分子,也就是一些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前驅者,亦同魯迅一樣,一度熱衷于陀氏的紹介。例如“左聯五烈士”之一的李偉森就曾編譯過,《朵思退夫斯基——朵思退夫斯基夫人之日記及回想錄》(北新書局,一九二八年六月初版),洪靈菲翻譯了陀氏的《地下室手記》(湖風書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版)和《賭徒》(湖風書局,一九三三年三月初版)。我想,他們之所以選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有關著作及作品,當然是因為陀氏對黑暗社會暴露得深刻、對貧苦民眾同情得真切吧,也因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人民在蔣介石“法治”之下的際遇,與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俄國人民在沙皇尼古拉二世“勛政”下的命運并無二致,故而借助陀氏犀利的筆鋒來揭露獨夫的專制與暴虐。而另一方面,他們對于陀氏作品中所宣揚的“陰暗哲學”,亦即高爾基曾指出的“悲觀主義、神秘主義”,“聽天由命,順從一切,寬恕一切”的“無為思想”(高爾基語),也當然是不以為然的。魯迅晚年為日本三笠書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而作的《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對于陀氏的思想與創作有了更深刻的剖析,針對“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從——對于橫逆之來的真正的忍從”,認為正是俄國沙皇專制統治下的病態產物,進而指出陀晚年熱衷于宣傳正教的“神”——基督,和中國孔教崇奉的“禮”一樣,都是麻痹人民斗志的精神鴉片。魯迅極為透辟地揭示,要揚棄對于惡勢力的“百分之百的忍從”,而代之以“虛偽”。這種有特定涵義的“虛偽”,是被壓迫者漸次覺醒、起而抗爭的前奏,作為一種斗爭手段是必需和必要的,“因為壓迫者指為被壓迫者的不德之一的這虛偽,對于同類,是惡,而對于壓迫者,卻是道德的”。這當然早已超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從”的“說教”,而昭示了陀氏所不敢正視的“被壓迫者對壓迫者,不是奴隸,就是敵人,決不能成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這一樸素的真理。
至于《窮人》,魯迅在《小引》中關于它的問世及影響也有所記敘:“《窮人》是作于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發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為大家的作品;格里戈洛維奇和涅克拉梭夫為之狂喜,培林斯基曾給他公正的褒辭。”并且還以驚嘆的口吻寫道:“而作者其時只有二十四歲,卻尤是驚人的事。天才的心誠然是博大的。”以上評介,可以說是全般揄揚,無一微辭。但十年之后在論及《窮人》時卻如此說道:“一讀他二十四歲時所作《窮人》,就已經吃驚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且介亭雜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雖無貶抑,卻已存疑。魯迅對陀氏認識的深化,還散見于他晚年寫的文章以及所編輯與支持的刊物。例如在一九三四年七月所寫的文章中曾說:“壁上還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畫像。對于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殘酷到了冷靜的文章。”(《且介亭雜文·憶韋素園君》)在魯迅所贊助,莊啟東、陳君冶編輯的《春光》上,則譯載了盧那察爾斯基的《妥斯退夫斯基論》(云林譯,刊該刊一卷二號,一九三四年四月),其中對于作為藝術家與思想家的陀氏作了精到的評析,闡揚了他的偉大與不凡,也揭示了他“極端惡魔主義”的重負,指出“妥斯退夫斯基的精神的源流,就是一面避免著頑強的獨裁制,一面與這河床(按指宗教——筆者)合流著。”但陀氏思想中有一條主線是不能忽視的,即他始終滿懷憂戚與希冀矚目祖國的未來,他的愛國赤誠是毋庸置疑的。最后,盧那察爾斯基寫道:“俄國現在是多難的,但是正在向光榮的道路前進。它的背后,站立著祝福他前進的偉大的預言者們的姿影。而這些預言者之中,最有魅力的最美麗的姿影恐怕就是妥斯退夫斯基吧。”象以上這篇試圖以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剖析陀氏的作家論,可能是第一次介紹到中國來。
《<窮人>小引》曾先刊發于《語絲》周刊第八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而《窮人》印本亦于同月下旬出版。(《魯迅日記》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條記有:“午后托廣平往北新書局取《語絲》,往未名社取《窮人》。”)
《窮人》作為陀氏作品第一個中譯本問世,倒也裝飾得綽約淡雅,封面素潔、樸直、沉郁,與書的內容卻也吻合無間。以藍灰色厚紙為底紋的書面上,上方印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走筆龍蛇似的簽名式;右側配置一小方陀氏版畫肖像,署名“FV”,系法國畫家跋樂頓所作,刀法粗疏而傳神,于一片昏暗中浮現著陀氏愁蹙的苦臉,似乎在向我們敘說那令人揪心與寒顫的故事;左側書名則由魯迅手書近隸體的“窮人”兩字,蒼勁瘦削,給人以形銷骨立之感,書名下綴有“韋叢蕪譯”一行小字。裝訂款式即為《未名叢刊》統一的道林紙印毛邊裝,經過半個多世紀仍悅目而柔韌,不愧為魯迅親手擘劃的中國現代出版物中的精品。扉頁亦為《未名叢刊》的統一格式,方框內僅注明叢刊、作品、作者、譯者之名,雖無任何花飾卻醒目而美觀。扉頁后印有一幀陀氏抱膝而坐的照片,端重、愁苦、冷峻的神色一如他作品的風格,下端則署有陀氏的花體簽名式。魯迅撰《小引》置于卷首地位,緊銜其后的即為譯本所據原本之一——美國現代叢書社《現代叢書》版的英譯本《引言》,ThomasSeltzer所撰,其中也概述了陀氏的生平與創作,其中引述了別林斯基在讀完《窮人》原稿時驚呼:“一位新果戈理出現了!”并興奮地對陀氏說道:“告訴我,青年,你理會你這里所寫的一切是如何地真實么?你真正捉住這一切可怕的真理么?不!在你這大年紀是不可能的。你深入事物的本質了。真理顯示于你如同顯示于一個藝術家似的。這是天賦的。護持這種天才,忠誠地對它,你將成為一個大著作家。”可惜這段話的出處我未能查到。
讀畢《窮人》,那“暮年是這么孤寂,而又不安于孤寂”的“可憐的老人”,所發出的裂人肺腑的“不成聲的絕叫”,如此強烈地震撼人心,竟然在耳際回蕩經日,似乎不絕于耳,其迫人的感染力當然要歸功于原著,但也不能忽略了譯筆的忠實、流暢。譯者當時不過是一個二十余歲的文學青年,譯述態度是謙恭而嚴謹的,他所據以翻譯的主要底本是英國女翻譯家康斯坦斯·迦內特(Constance Garnett)的英譯本,又參考了美國《現代叢書》(《Modern Library》)的英譯本;譯稿先經其兄韋素園以原文本校訂,復又經魯迅先生據日本翻譯家原白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本加以校核,“以定從違”。三種文本的反復校改,譯文的忠實與練達,當然無可疑慮了。
《彷徨》初版本(北新書局,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版權頁后刊有《未名叢刊》廣告,其中關于《窮人》寫道:“俄國陀斯妥夫斯基作,韋叢蕪譯。這是作者的第一部,也是即刻使他成為大家的書簡體小說,人生的困苦與悅樂,崇高和卑下,以及留戀和決絕,都從一個少女和老人的通信中寫出。譯者對比了數種譯本,并由韋素園用原文校定,這才印行,其正確可想。魯迅序。并有作者畫像一幅,并用其手書及法人跋樂頓畫像作封面。”這則“廣告”是關于《窮人》的最凝練的評介,很可能是魯迅先生手擬的;其中未提及自己據日譯本校定,正由于先生的謙遜,此亦可作系魯迅親撰的旁證。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更可見魯迅先生對《窮人》所傾注的心力,而這滲透著魯迅血汗的譯本,也更應該得到后人的珍視,不要因為譯者后來的蛻變而連同擯棄如敝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