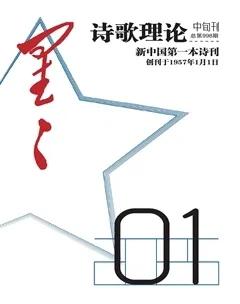詩歌,本是大眾的事業
詩歌由大眾寫、大眾讀,詩歌也寫大眾,由大眾傳播、傳頌直到今天。從《詩經》開始,詩歌就是與大眾共一腔樂愁的事業。《魏風·碩鼠》描寫的是兩個階級的矛盾,《周南·關雎》描寫的是男女情事。而以人間風物常事為內容和風格的《風》《雅》《頌》中的《風》,不僅數量最多,而且藝術成就最高,也最為后人樂道。唐詩記錄了一個由廟堂到民間的細碎而又完整清晰的大唐風貌,宋詞刻畫了兩宋國家到個體情感與生命的“清明上河圖”。
如果我們稍稍回到事實與常識,就會發現藝術、文學的流變規律一直延續著這樣的路徑:從廣大的民間出發,帶著生命的荒莽生猛之氣,觀察自由、鮮活、日常的時代,雖然初時有些殘缺不全,但隨著藝術規律的完整,逐步走向成熟,最后成為精致、雅趣、高蹈的經典而為小眾群體所欣賞自娛,最終因小眾的封閉而消亡,接著再開始新的輪回,循環往復。流變規律顯示,內容和形式最與時代大眾相近的時段,就是文學最繁榮的時段。
回到當下詩歌現場中來。
我一直認為,2014年是中國當代詩歌的一個分水嶺。無論今天的詩人如何眾多,無論現場如何熱鬧,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詩歌的熱度、詩集的銷量從這一年開始一分為二,由此出現疲軟、下滑,甚至無人問津的現象。在這一年之后,有高銷量、被市場廣泛認可的詩人,只是非常有限的幾位。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極其復雜,有互聯網的沖擊,也有生活的奔突不暇,更多的,恐怕還是詩歌自身的因素所致。作為一名長期的詩歌文本閱讀者,從個人體驗來說,有兩個最主要的問題無法回避,那就是詩歌的同質與離場。
曾有一位詩友經常把詩歌群里的作品發過來,讓我做評判。我現在越來越難以分辨它們的優劣高低,甚至無法分辨這是誰的作品,因為在用詞、斷句、意象、節奏、手法、內容等方面,幾無區別。如果沒有作者的名字在作品前面,我有時真以為就是同一個人的作品。擴而充之,如果我們把某一期詩歌刊物的作者名字全都隱藏起來,其閱讀感受也區別不到哪里去。為什么多數年齡、文學修養、知識儲備、生活與命運都相去云泥的詩歌作者,創作出的大部分作品類似得無法分辨呢?答案復雜又簡單,那就是流水線生產的時代,個性是危險的。個性常被視為異類,它非常難以被接受,更沒有誰愿意去冒險。因為大家都穿同樣的衣服,邁同樣的步子,把車往同一條路上開,往往是安全的。而文學創作最需要的恰恰是林子邊上的那棵樹。
詩歌無關世道人心、無關社會現實已是一個巨大的悲哀。這個悲哀不獨是詩歌創作,其實也包括其他方方面面。我們從當下汗牛充棟的詩歌作品里好像讀到了許多,又仿佛什么也沒有。這些詩作像輕風吹過這個世界,什么也沒有留下,什么痕跡也沒有。沉重的生活壓力,巨大的現實矛盾,支離破碎的個人情感,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撕裂……我們無法改變這些,只有小情小緒,風花雪月,自說自話地安撫自己的內心。詩歌的時代內容與生活印跡淡得不能再淡,詩歌與當下仿佛兩個平行的宇宙,永不相交。
中國一直是詩歌的國度。因為詩文記錄了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輪廓與細節,記錄了眾生的悲歡離合,后人有幸得以由這些詩文了解我們是誰?從哪里來?從而知道自己將向何處去。我們讀別人的詩作,其實也是在讀自己的內心,尋找與遙遠古人對話的通道。中國人認識歷史、感受遙遠的時間風塵,常常從詩文開始。不是每個人都能接觸到史料,也不是每個人都對專業的歷史研究有興趣。而所謂的歷史內容,有些也是存疑的,唯有從當時現實出發、從生活現場出發的文學與藝術作品,作偽成分最少也最難,反而可信。
為了引入本次的主題新大眾文藝,我雜亂地梳理了這么多,雖然有些判斷不一定是準確的,可能充滿了片面性、主觀性,但它們的確是造成當下詩歌困境的原因之一。下面以我的詩作為例,再試作分析。
我的詩歌作品大致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在報刊發表,一部分結集作為詩集出版。當然,這些詩作從內容到手法也并無明顯的不同,有很大一部分是重疊的、共型的,既用于發表也用于出書,但我還是有意識地讓它們有所不同。用于發表的詩作,盡可能寫得溫暖一些,珠圓玉潤一些;用于結集出版的詩作,會保持銳度和粗糲性。這是因為期刊的閱讀人群與詩集的閱讀人群頗有差異,但也有交叉重合。另外,刊物的審稿與詩集的審稿定位有所不同,前者要求時效性和話題、語境等,后者要求作品個性化強一些。畢竟出版一部詩集對出版社來說是有成本的,要想獲得市場收益就得有賣點,或者說能獲得市場長效性。當然,報刊發表的詩歌和詩集結集的詩歌誰優誰劣,我也不好判斷,因為詩無達詁。我發現,在報刊發表的作品因發表時間、發表刊物不同,因而內容相對可以同質化,比如一年寫五十首類似的詩歌作品,分別在不同的報刊發表,很少有人會將這些作品進行集中比對,即使同質化,卻因不在同一報刊同時發表,就可以無視,而把它們結集在同一部詩集里,讀者便會感覺到作品的雷同,造成閱讀疲勞,從這個層面上講,詩集中的詩歌作品的差異化要求更強。
這些年我一直在做兩件事:一是應讀者朋友要求,從不同的售書平臺把自己的作品集買回來,簽名并寫上寄語發給全國各地的讀者朋友;二是給一些詩歌作者改稿。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一個現象,就是購買我詩集的人和讓我改稿的人并不是同一批人,前者更純粹,而后者更功利。購買詩集的人大多是純粹的詩歌愛好者,并沒有當詩人的夢想,而讓我改稿的人,其出發點就是發表詩作,想做詩人。這些想做詩人的人購買的多是詩歌刊物,目的是從中找方法,尋風向。讓我覺得特別幸運的是,這兩個群體的讀者都在讀我的詩作。
話題再次回到出發地,新大眾文藝時代詩歌如何“出圈”,如何打破讀者群體間的壁壘,如何引領審美和趣味,這似乎是個無解的問題,就像交響曲再也無法回到貝多芬時代一樣。可還是有一些事可做。首先要做的是,找到不同群體間對閱讀需求的共性,用詩作觸動他們內心最深處的靈魂部分;其次,詩歌創作不是自說自話,而是讓詩歌回到現實,回到生活和人心現場,回到人民當中;最后,詩歌創作不僅要回望來路,還要關照人類未來,這大概也是詩歌的共性所在。當許多年后回首當下,人們也可以從詩歌中看見我們這個時代的細節與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