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的跨文化要義
〔摘要〕 文學文本中詞語的雜糅性以及理論話語的多重性從根本上決定了文學研究的跨文化屬性,這一特征對于理解不同的文化傳統并在互為語境的方式中呈現自身文化特質均具有重要價值。以詞語轉換和批評話語為著眼點分析文學研究的跨文化本質,同時強調文學研究應充分考慮文學文本的語言要素、批評術語的理論淵源以及研究者本人的文化立場,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學研究在人文學術知識生產中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 文學研究;跨文化;雜糅;話語;知識生產
〔中圖分類號〕I0-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 - 4769 (2025) 01 - 0205 - 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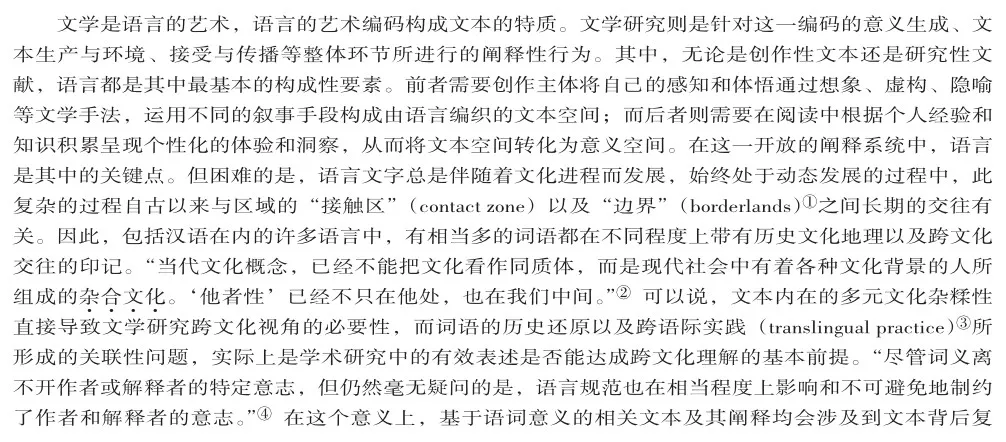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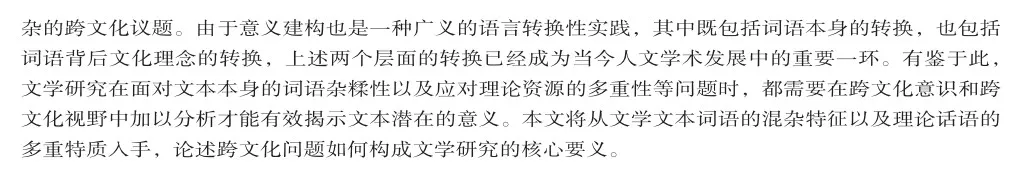
一、詞語的混雜性與跨文化轉換
語言的歷史發生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過程,其中語文學(philology)對于理解語言和文化之間的關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該詞的希臘語“philologia”本義是指“對文獻的熱愛”(love of literature);拉丁文的“philologia”指“對學識的熱愛”(love of learning),亦即“學問”(scholarship),是對確定文獻版本和意義進行的研究。① 由于語言學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了系統的分支,在總體上涵蓋了語言的歷史發展與變化,即歷時語言學(diachronic linguistics),以及在某一時間段內對語言狀態的研究,即共時語言學(synchronic linguistics)等,因此,早期的語文學已劃歸到語言學領域。由于語文學奠定了人文學術傳統中詞語、言說、意義三位一體的重要基礎,因此也是學術史和人文學術實踐中難以繞開的基本領域。“語文學有兩個主要分支,相對于‘詞語’與‘言說’的使用,一者是說什么,一者是以何語言說”。②語文學的這兩個分支對于文學研究而言有著重要意義,這是因為文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涉及言意關系,其中,由語詞的定義及其意義指涉范圍所構成的關鍵性術語,在文學研究中總是對某一學術議題的闡發起到支撐性作用。因此,文學研究必須依據語言的命名功能,并通過語言與經驗、認知和慣例的相關性來解讀文本,在跨文化語境中考察詞語的多義性以及詞語之間的可通約性,從而較為全面地理解意義生成。
然而,當代語言,包括文學研究中的特定術語,大多具有混雜性,許多關鍵詞語多是對源自不同語言表述的音譯、意譯或編譯的結果,且長期經由各自母語經驗的實踐,形成了語義的特定指涉范圍。加之這個趨勢在近代隨著不同群體交往以及媒介傳播的便捷性而加快,因此,詞語的定義、內涵、擴展性實踐及其在不同語言間的轉換等,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決定著文學研究的基礎性邏輯和學理性前提,即“如此認定文字概念超越并包含語言概念,當然以語言和文字的確切定義為前提。”③ 其實,語詞的雜糅特征是文化發展階段中歷史性融合的必然結果。例如在中國學術文化史的進程中,佛經的譯介就產生了巨大而持續的影響,“在中國,佛經的翻譯自后漢至宋代,歷一千二三百年,這樣歷久不衰的翻譯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④ 佛經譯介不僅需要進行語言之間的有效轉換,而且還涉及語言背后不同的信仰理念和表述方式,加之歷史地理的隔斷等客觀條件限制,其難度可以想象。因此,譯經工作既要依靠譯者與一些接觸區了解相關語言的人物的合作,也需經過常年修行的高僧對譯文進行多年的打磨。荷蘭學者許理和(Erik Zürcher)曾對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以及復雜的譯經過程做出過說明:
在許多年內竺佛念是其中的佼佼者。這位僧人來自涼州,世代居住在邊遠地區,因而借助于其游歷,他通曉了梵語和幾種中亞語言。……實際上那個時代所有的譯經都出自他的譯筆,而外國僧人的作用僅僅是背出或寫出佛經原文。……道安在譯場中的角色是“譯主”和導師。他請外國僧人復述他們能“出”的佛經,然后與他的合作者探討翻譯問題,否決一些明顯的翻譯錯誤,并在譯文“筆受”之后進行文字潤色,為之作序。⑤
佛經的譯介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廣泛影響,僅在文學方面,佛教理念、故事結構以及相關詞匯等,不僅影響到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唐代變文,并且“使中國文學語法結構和遣詞用句方法也發生了某些變化。漢語中的反切四聲的確立,就是佛經影響的結果。”① 佛經的引介也促使中國學術文化進入了某種融合式的發展進程中,使異域的文化要素轉化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傳入中國,當魏晉玄談極盛之時。道家之言,以虛無為主,佛氏之說,則寂滅為歸;出世之旨,同超乎人格,故能含融深義,浸入人心”。②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從歐洲來華的一些學術型傳教士(the scholarly missionaries)③的譯介活動也值得追溯。他們早期的譯介工作都與中國學人的合作分不開。例如: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與徐光啟“在一年時間里每日上午工作”,合作翻譯《幾何原本》(Elements of Geometry),前六卷于1607年出版④,這一重要的合作開啟了以翻譯轉換為知識擴展的方式。后來陸續進入中國的傳教士的翻譯活動也大致延續了這一傳統,其中英國人理雅各(James Legge)在翻譯《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的過程中就主要得益于與王韜的合作。
在隨后的翻譯準備中,王韜的貢獻更大。尤其是《中國經典》的第4卷《詩經》(于1871年首版)、第5卷《春秋》和《左傳》(1872年首版),還有1885年首次面世的《禮記》。在這些卷中,經常可以看到王韜的注釋。另外,應理雅各的要求,他曾廣集各家評注,對那些冷僻著作中的評注尤為注意,以免為外國學者忽略。⑤
歐洲學人的譯介工作以及與中國學人多種形式的合作,不僅為知識的跨界與借鑒提供了文獻基礎,而且也引發了不同區域知性經驗的蔓延。
語言轉換形成的雜糅特征不僅僅體現在語言形式上,而且還隱含在文學書寫的主旨、策略以及思想觀念上。時至20世紀后半期興起的后殖民文學中,此現象十分典型。其中,雜糅指的是“在殖民化帶來的接觸區中被創造出的新的跨文化形式”⑥,這些形式是不同文化碰撞、交融的必然結果,也由此帶來詞語的借鑒、其內涵的改變以及相關的語言實踐。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殖民文學中,語言的雜糅特征并非指向由跨界引發的知識擴展,而是作為書寫手段來表達相關的文化政治訴求。在外國文學對于流散經歷和后殖民經驗的書寫中,最為突出的就是語言的策略性使用。出于受眾和出版等多種復雜因素的現實考量,很多后殖民書寫仍然使用了殖民者的語言,即使如此,書寫者對所使用的帝國語言也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改造,如創造出了以語符轉換和方言音譯為主要特征的“克里奧連續體”(creole continuum)⑦等,這一現象早已受到學界關注。“這些策略使作家獲得了世界范圍的讀者,生產出文化差異和文化挪用的術語,宣稱自己盡管使用‘英語’但卻有所不同。后殖民作家如此促進了英語文學的轉型,摧毀了將文學經典固化為西方精英話語的意識形態假設。”⑧ 因此,語言策略成為后殖民書寫中的決定性特征,以表達書寫主體所屬文化對殖民文化的應對方式和政治態度。
非裔美國文學是植根于殖民歷史但又在北美新大陸得以發展的文學類別,雖然大部分非裔文學表達的都是人物在美國的生活經歷,但其語言的雜糅特征及其鮮明的書寫政治是該類別文學的核心特質。小亨利·路易斯·蓋茨(Henry Louis Gates, Jr.)在分析19世紀非洲裔美國作家書寫的文本時,發現了非裔社區的語言特質以及非洲和北美洲雙重文化傳統的交織關系,并從中剝離出非裔美國人的歷史境遇和文化身份特征。① 小休斯頓·A. 貝克(Houston A. Baker, Jr.)則從布魯斯音樂入手,論述了非洲裔美國文學如何利用獨特的方言傳統形成黑人美學以表達意識形態訴求。② 蓋茨和貝克的研究揭示出非洲裔群體在北美與其他文化傳統接觸之后,如何發展出了獨特的文學表達方式,在語言形式和思想主旨的雙重維度上凸顯出非裔美國文學與非洲文化傳統的因緣關系,以及對于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持續反思和批判。對于這樣一種書寫,采用現成的文學理論并不能有效呈現文本的特色,因此,蓋茨和貝克均采用了文學知識考古的做法,從文本的語言特性出發揭示出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歷史、文學與文化傳統之間的復雜聯系,使非裔美國文學理論(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Theory)成為學界公認的分支領域。
由此可見,文學的生成本身涉及復雜的跨文化語境。在不同人類群體的長期接觸和交融過程中,言說形式及其意義生產早已帶有深刻的跨文化印記,使文學成為“語言的綜合”:“文學是把文本中各種要素和成分都組合在一種錯綜復雜的關系中的語言。”③ 因此,語言本身的跨文化屬性以及由此產生的語言的多義性是把握文本形式與意義的關鍵。
二、話語的多重性與跨文化批評
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與文化傳統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的關系,前者通過鮮活的人和事呈現人們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世界,以一種融入及共情的方式影響人們的價值觀念;后者通過分析闡釋,以意義的指向作用于人們的思考方式,并同時帶來對文化傳統的新解釋。因此,“文學作品的解釋對文化傳統的形成是極為重要的。”④ 從文化史的發展軌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此種關系。進入早期現代時期(the early modern)⑤以來,人們主要依據文本內容和自身的理解進行批評實踐,從而使闡釋行為具有人文主義的精神,也使文學研究作為現代知識學的分支開始顯現。實際上,此實踐方式與西方古典學中的箋注、校勘以及考辨等傳統研究有關,因為這一古老的傳統在客觀上形成了對教義式解釋的某種質疑。時至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還在詩學理論及文學批評的發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們在神學家面前為詩所作的辯護,導致了一些有趣原則的確立。為古代詩人們所作的注釋,尤其是其導論,包含了一些相關的反思”。⑥ 這些有關文學研究新的原則、方法和觀念也帶動了對文學歷史性作用的思考。可以說,當代文學研究中的理論言說所內在的質疑和反思特質,都可以追溯到這一學術文化發展脈絡中的一些重要節點。
顯然,古典學在學術史的發展中占據了重要地位,這是因為人們在將文學批評實踐納入到整體的新觀念和知識形態的同時,需要在梳理史實之間的聯系中不斷透視遠古與現代之間的有機聯系。于是,古典學成為重要的歷史坐標,“這使得現代人不僅可以理解自己的世界,也能掉轉這些智識工具的矛頭,將它們用于過去,從而比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更好地理解他們的世界。”⑦ 文學研究在繼續發揚古典學傳統的同時,也借鑒了同樣久遠的闡釋學理念,將詩性知識的定位建立在文本闡釋的基礎之上,這一點在浪漫主義時期顯得尤為突出。“在浪漫主義時期,當文學在某種程度上開始在部分讀者那里替代宗教的作用,且意義的重要性以及理解的難度均有所加大之時,闡釋就成為了必要。”⑧ 隨著拉丁語的支配性地位在歐洲書寫、教育以及學術文化中的逐漸消解①,人們開始挖掘自身的文本傳統并通過語言強化民族文化認同,其中包括對于經典文獻采納自身語言進行的重譯和闡釋工作,此趨勢在18世紀之后達到高潮。“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知識分子在界定民族特性時,養成了一種極強的意識,凸顯語言在其中的重要地位。”② 當代文學研究中一些基于民族文化的思想陳述均與這一文學現代性運動密切相關。
從上述簡要回顧可以看到,文學研究本身的發展是一個與社會文化發展基本同步、同時將不同文學文化傳統加以融合并使其不斷更新的過程。不同文化區域在各自歷史發展的階段一般會有文化的側重點,在面臨不同文化資源的時候,也會出現選擇性變化。此變化在近代以來主要體現在由翻譯為主的譯介實踐過渡到知識再生產為主,亦即將不同區域的文本和理論資源納入到研究對象中進行闡釋性實踐,實施某種融會貫通,并形成了文學與文學研究的某些特征:其一,不同文化區域的書寫文本,尤其是獲得世界性文學獎項的作品,往往被及時翻譯成其他語言出版,形成了跨區域、跨文化的共時傳播現象;其二,文學理論本身在上世紀的快速發展所導致的大量譯介成果,也使得基于自身語言的理論言說更為多樣,形成了話語生產與研究視角的多樣性,以及對跨學科方法論的普遍認同。
文學研究的對象除了大量的跨區域、跨文化文本之外,源自不同理論家的話語表述不僅構成了文學研究的跨文化性,而且其理論表述本身也同時構成了解讀的難度。可以看到,語言始終是難以繞開的中心議題:
困難點依然是理論的語言。大多數理論家都是法國人,而我們是通過翻譯解讀的,有時是相當笨拙的翻譯。由于法語是羅曼語族,其許多詞匯直接源自拉丁文,而在我們簡潔和熟知的日常用語盎格魯-撒克遜詞匯中,往往沒有對應的表達。因此,譯自法文學術的英文文本常常包含了大量較長的拉丁語匯,由此構成英文讀者的難點來源。③
自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批評理論的興盛充分彰顯出話語形態的豐富性。作為語言學的通用術語,話語(discourse)的內涵與外延有其特別的優勢,這是因為話語可以在不同分支領域中通過語境形成話語組合。“從廣義建構角度來看,話語理論(discourse theory)從三個知識傳統中獲取了洞見和支撐:闡釋學,社會建構和人種學,以及左翼政治力量的分析性研究。”④ 話語理論的動態發展促進了文學批評的更迭式發展,無論是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還是族裔、性別以及后殖民批評等文學批評實踐,其顯見的范式均是以文本的語言為切入點,以理論話語為支撐點來揭示語言背后的文化政治權力及其知識體系傾向。
值得注意的是,文學書寫的對象即便是在同一文化區域,也都會涉及到差異性的階層和族群,受制于其中的權力與經濟結構,以及文化、種族、性別等觀念形態的支配。所以,這一文化產品雖然是由個人化書寫所構成,但個體書寫行為并不能脫離當時的文本環境,也不能脫離書寫者的生活世界和認知前提。對于研究者而言也是如此,因為“沒有人曾經設計出什么方法可以把學者與其生活的環境分開,把他與他(有意或無意)卷入的階級、信仰體系和社會地位分開,因為他生來注定要成為社會的一員。這一切會理所當然地繼續對他所從事的學術研究產生影響”。⑤ 換言之,文本是由靜態的語言編碼組合而成的動態結構,在此多重意義的開放系統中,文學研究并不僅僅是對詞語的考察、轉換以及建立某種話語單位,而是針對文本編碼的隱喻及修辭功能與觀點呈現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繼而通過社會文化語境的有效考察,依據語言或話語單位呈現思想性陳述。因此,對于這樣一個由語言構成的復雜文本世界進行研究,其對應的是特定的書寫語言與歷史階段中文化語言之間的關系,這也是文學研究作為知識生產的核心要素。“知識在于語言與語言的關系;在于恢復詞與物的巨大的統一的平面;在于讓一切東西講話。這就是說,在一個所有標記的層面之上,使次等的評論話語產生。知識的本義并不是注視①或證明;知識的本義是闡釋。”② 因此,每一個新的理論話語的產生,都是諸多學人在該領域長期耕耘的結果,其中包括對源自不同文化區域的理論缺陷進行的質疑,并明確自身術語的理論指涉。所以,當代重要的工具書往往圍繞理論、人物和術語三個交織的層面展開,以便使人們更為清晰地把握論證結構和話語單位之間的支撐點。《當代文學理論百科全書:方法、學者與術語》(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Lit erary Theory: Approaches, Scholars, Terms)這本權威工具書在標題上就直接說明了三者的關系。③ 自21世紀以來,人們可以看到有關文學研究的理論范疇、議題、術語以及研究范式等,不僅獲得了大量的翻譯和闡發性介紹,而且經由現代漢語的再生產,形成了某種衍生且逐漸固化的話語形態或通識性語匯。這些話語形態和移植而來的議題在持續的再生產批評實踐中,形成特定的指涉功能和覆蓋范圍,并由此成為學界的某種認知和再闡釋的前提。
中國文化在與其他文化的交流過程中,古代文論以其獨特的語言表達方式被西方學界所認識,形成文化間的互識與互鑒,只不過在理論術語的翻譯上,譯者多采用了漢字音譯的形式,這不僅由于理論語言很難實現跨文化通約,而且還可以凸顯中國文學和中國文論的異質性。④ 例如權威工具書《霍普金斯文學理論和批評指南》(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Criticism)中就包括了“中國理論與批評”(Chinese Theory and Criticism)這一詞條,涵蓋中國詩論、小說與戲劇等分論題,其中多處涉及中國理論術語之處均采用了音譯的方式。⑤ 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其研究中國文論的著作中,專門列出了以音譯形式出現的中國古代文論中的理論術語,將其作為附錄進行集中定義和解釋,包括“ch‘i”(氣)“ching”(情)“hsing”(興)“pi”(比)“tz‘u”(辭)等,以呈現詞語的歷史發展軌跡。⑥ 在文化全面交融形成的多重資源條件下,閱讀主體更需要在跨文化的語境中理解關鍵詞語的確切語義,以透視不同理論言說的內在邏輯,并在此基礎上與原有的知識結構形成鏈接。因此,在重新審視文學研究的基本原理時,詞語的跨文化轉換以及話語形成的復雜性均是值得特別重視的問題。
由此可見,文學批評中的跨文化問題早已成為其內嵌的話語特質和文學思想的生產機制。除此文學批評本身的內在發展邏輯之外,文學研究者所處的歷史文化語境也會不可避免地被帶入到批評實踐中,再一次擴展了文學闡釋的跨文化維度。由于重要的作家往往能夠“最有創造性地協商所屬文化情境的張力和可能性”⑦,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解讀和文學批評就是對某一文化傳統的深度體驗,在此過程中,處于另一文化語境中的閱讀主體和批評主體與文學文本之間形成文化接觸地帶,激發審美體驗和意義闡釋。“一部文學作品的每一種解讀——無論這種解讀是多么無意識——都會受到我們自己文化價值和文化預設的影響。”⑧ 閱讀者的個人經驗和認知前見決定了其勢必會將不同歷史階段中的書寫納入到某種觀念之中加以定位,并在互為語境的文化變遷中看到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復雜關系,解析出各個具體的環境何以構成了觀察和了解世界的方式,亦即“在描寫所謂的‘外國’文化這個‘確定他者’的過程中,構建了‘本國’文化的思想意識。所以,對‘自我’的定義是與‘他者’文化的特性相關聯的。”① 閱讀者原有的文化意識對其閱讀過程產生的制約作用直接導致了外國文學研究的跨文化屬性,也會帶來文化身份的相對性建構。這一點正是“世界文學”② 概念在近年再次受到學界關注的歷史動因,因為不僅文學書寫之間有著跨時空和跨文化的聯系,而且文學文本的歷史價值也只有將其放置在跨文化的維度中才能更好地加以理解和認識。
結語
文學研究的跨文化問題涉及互為結構的兩個方面,即由詞語的雜糅性帶來的書寫文本本身的跨文化屬性,以及由理論話語的多重性導致的跨文化批評視角,二者均通達文化之間的互識與互鑒。明晰這一要義的意義在于:第一,由于書寫文本具有跨文化屬性,文學閱讀因此是一種涉及跨文化理解的個體行為和社會實踐,這要求在閱讀過程中對于文本中部分詞語的歷史淵源保持敏感,不能強行將之納入閱讀者所屬的語言傳統中加以理解。第二,由于文學批評話語也具有理論資源的多元性,因此在文學研究中使用批評術語時要對其哲學、歷史和文化背景保持關切,切忌將同一詞語在不同理論話語體系中盲目加以延展使用,避免可能由此造成的理解上的偏差。第三,由于文學文本的構成性要素往往會在跨時間、跨地域的不同文學傳統中被繼承、改造和發展,因此,闡釋文學文本時還要關注這些要素的跨文化流變,這樣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學書寫策略及其隱喻,并在更廣闊的世界文學譜系中理解文本的意義和價值。概言之,文學閱讀與文學研究均涉及到文化間的理解,亦即對書寫、接受、傳播等環節中的問題進行揭示并對相關經驗做出解釋,因此,在跨文化視野中多線索地考量文本內外環境和文化傳統等基礎性工作依然不可或缺。在復雜的歷史語境下,研究者需要始終清醒地意識到文學研究的跨文化要義,因為“觀點在不同文化力量的交織中才至關重要”③,以此才能充分理解文學研究在人文學術知識生產中的重要作用。
① 參見范發迪:《知識帝國:清代在華的英國博物學家》,袁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頁。該譯本將“borderlands”譯為“邊境地區”,但實際上,不同文化之間的接觸不一定僅僅發生在邊境地區,而是人群相遇的流動邊界。
② 方維規:《“世界文學”推原》,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22年,第117頁。強調部分為原文所有。
③ 有關“跨語際實踐”的表述,參見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宋偉杰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頁。
④ 赫施:《解釋的有效性》,王才勇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第37頁。
① David B. Guralnik, ed.,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American Language, Cleveland: William Collings Publishing,INC., 1978, p. 1069.
② 約翰·埃德溫·桑茲:《西方古典學術史》第1卷,張治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3—54頁。
③ 雅克·德里達:《論文字學》,汪堂家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第10頁。
④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語言文字》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第69頁。
⑤ 許理和:《佛教征服中國:佛教在中國中古早期的傳播與適應》,李四龍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7—288頁。
①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文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第11頁。
② 林尹:《中國學術思想大綱》,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89頁。
③ 有關“學術型傳教士”的命名,參見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New Haven, CT: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p. 1。
④ Jonathan D. Spence,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New York: Viking, 1983, p. 152.
⑤ 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雷頤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57頁。
⑥ Bill Ashcroft, et al., Post-Colonial Studies: The Key Concepts,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108. 黑體部分為原文所有。
⑦ 有關“克里奧連續體”的更多討論,參見Bill Ashcroft, et al.,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 nial Literatures,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43-46。有關后殖民文學中使用的轉喻、典故、挪用、注解等其他語言策略,參見Bill Ashcroft, et al.,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2nd ed., pp. 50-76。
⑧ Bill Ashcroft, et al.,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2nd ed., p. 76.
① 參見Henry Louis Gates, Jr., The Signifying Monkey: A Theor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以及Henry Louis Gates, Jr., ed., Black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84。
② 參見Houston A. Baker, Jr., Blues, Ideology, and Afro?American Literature: A Vernacular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以及Houston A. Baker, Jr., Afro?American Poetics: Revisions of Harlem and the Black Aesthetic, Madison,WI: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③ 喬納森·卡勒:《當代學術入門:文學理論》,李平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1頁。
④ P. D. 卻爾:《解釋:文學批評的哲學》,吳啟之等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第1頁。
⑤ “早期現代”的分類方式是20世紀西方學界所提倡的,以避免歷史截然分段所帶來的弊端并強調過渡期的重要性。參見G. R. Potter, planned, Denys Hay,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1. The Renaissance 1493-15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⑥ 查爾斯·B. 施密特等:《劍橋文藝復興哲學史》,徐衛翔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34頁。
⑦ 內維里·莫利:《古典學為什么重要》,曾毅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8頁。
⑧ Paul H. Fry,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0.
① 有關歐洲拉丁文的歷史,參見弗朗索瓦·瓦克:《拉丁文帝國》,陳綺文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
② 帕特里克·J. 格里:《中世紀早期的語言與權力》,劉林海譯,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第21頁。
③ Peter Barry, 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3rd e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7.
④ Michael Groden, et al., eds.,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Criticism, 2nd ed.,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11.
⑤ 愛德華·W. 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13頁。
① 原譯文如此。
② 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莫偉民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第55頁。
③ 參見Irena R. Makaryk, et al., eds., 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pproaches, Scholars, Terms,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3。
④ 費維廉(Craig Fisk)主張,“正是中國文學的異質性,即‘他者性’,使之變得更有趣”。Craig Fisk, “The Alter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its Critical Contexts,”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2, no. 1, 1980, p. 87. 張隆溪教授也主張,“語言上的差異很有可能被夸大,以彰顯極度不同的思維方式。”Zhang Longxi, “What is Wen and Why Is It Made So Terribly Strange?” College English, vol. 23, no. 1, 1996, p. 15.
⑤ 參見Michael Groden, et al., eds.,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Criticism, 2nd ed., pp. 188-204。中譯本見邁克爾·格羅登等主編:《霍普金斯文學理論和批評指南》,王逢振等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299—322頁。
⑥ 參見Stephen Owe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583-595。
⑦ David Damrosch, 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9, p. 107.
⑧ Terry Eagleton, How to Read Literatur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83.
① 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楊淑華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第76頁。
② 學界普遍將“世界文學”概念的提出歸功于歌德,但在過去三十年間,西方學界出版了眾多在該概念指引下編輯的文集和理論著作,對其進行了重新解釋和應用。在大衛·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看來,“世界文學”的概念“包括了所有流通到其起源文化之外的文學作品,無論是以翻譯的形式還是以原來的語言”。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
③ Adam K. Webb, Beyond the Global Culture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xv.
(責任編輯:潘純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