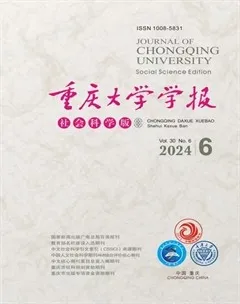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新型城鎮化的改革紅利與機制完善





Doi: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4.10.001
歡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劉偉.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新型城鎮化的改革紅利與機制完善——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6):12-25.Doi: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4.10.001.
Citation Format: LIU Wei. The reform dividend and mechanism improve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tudy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4(6):12-25.Doi: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4.10.001.
摘要:城市化是工業化的重要支撐,也是現代化的重要支撐。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背景下,“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發展理念正給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帶來一場深刻變革。制度創新—體制創新—實踐創新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核心精神要義,根本目的是通過改革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聚焦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的全面性、系統性、集成性改革需要,面對當前社會經濟發展條件和客觀環境的深刻變化,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視閾下深入探討新型城鎮化亟待解決的區域經濟平衡、公共產品均衡性、城鄉治理融合性和城鄉互動關系雙向型等突出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系統論證新型城鎮化背后發展邏輯和實施路徑調整的必要性、合理性。以新型城鎮化為載體的“二次城市化”從要素流動、公共服務、社會結構、制度潛能等方面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強化改革動能,擴展改革空間。新型城鎮化的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場體制機制的重塑與再造,頂層邏輯由激勵式的城鎮化轉變為包容性的城鎮化,對可能出現的城市運營和公共產品成本負擔增大、城鄉人口遷移市民化不充分、中小城市和縣城綜合承載能力弱化、產城一體化不融洽、不完全等風險與挑戰進行分析研判、風險防范和對策應對,通過集成化的系統改革在公共產品、城鄉互通、權益保障、國際競爭、區域經濟均衡等領域取得新突破。這對于下一階段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促進城鄉公共資源的高效利用,推進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有助于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化、現代化建設提供理論指導、模式借鑒和政策指引。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二次城市化”;新型城鎮化;城鄉融合;改革紅利
中圖分類號:D60;F2992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8-5831(2024)06-0012-14
導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城鎮化會議中指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1]。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提高城市規劃、建設、治理水平”[2]。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以下簡稱《決定》)明確要求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要健全推進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3]。城市化、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三大支撐,當前我國正處于由資源、要素、人口驅動的“初次城市化”向以科技創新、營商和人居環境、人才驅動的“二次城市化”轉型的關鍵階段,在城市化高階形態下亟需適度地進行社會主義城市發展的理論創新和政策調整。面對當前城市化的二次轉型期,以新型城鎮化為載體的“高階城市化”發展邏輯和實施路徑應該進行怎樣的調整?如何利用新型城鎮化的進程牽引力激發城市化的新質生產力,進一步挖掘人口、消費、生產、市場增量等紅利潛力?需要深化中國特色城市化理論研究,系統分析中國城市化發展的趨勢、動力與現實挑戰,提出未來城市化發展的優化策略。同時,也要審視和汲取“初次城市化”的經驗與教訓,對下一階段城市化中的風險與挑戰作出前瞻性研判。這有助于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高質量發展,提升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統性、結構性、整體性效能,也可以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化提供政策借鑒和模式經驗。
一、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市化發展模式
(一)城市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承載依托
城市化與工業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兩大引擎,城市化是在工業化的推動之下,由農業向工業轉型,農業人口向城市聚集的歷史進程中自然形成的,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塞薩繆爾·P·亨廷頓認為城市化是衡量現代化的尺度,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4]。英國城市地理學家Peter Hall認為城市化是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推手,城市化與現代化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互依賴和推動作用[5]。城市化不僅是現代化進程的推動力,而且是現代化的核心內容。城市作為經濟、創新和文化的聚集地,聚集了人才、技術、信息和資本等生產要素,推動了地區社會經濟活動的高水平發展。文貫中指出城市化既是城市化率提高的過程,又是城市不斷現代化的過程,“城市化的現代化過程是無止境的”[6]。孫建平指出“沒有城市化的支撐與融合,就沒有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7]。城市化的推進不僅提高了現代化水平,而且進一步強化了現代化的發展形態與社會秩序,形成了一種脫離鄉村的文明形式。總之,城市化與現代化之間是互為依托的支撐關系,它們之間相互促進、相互滋養,形成了國家現代化的彼此依靠。
城市化作為一個集合概念,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在科技進步、生產力發展、社會結構演變和社會文明進步等方面發揮出主導和引擎作用。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就曾提出21世紀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兩件事情:一件是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第二件是中國的城市化[8]。中國的城市發展史也是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史,現代中國由“鄉村中國”走向“城市中國”的轉型,離不開城市化的支撐與推動。城市化是當代中國改革與發展中無法回避的關鍵詞,在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中成為我國擴大內需、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生產方式的戰略重點和重要依托。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現代化和城市化是一種發展中國家創立的全新類型。新中國75年的城市化歷程不僅是一場政治經濟體制變革、國土空間結構變革和生產要素增長貢獻變革,而且是一種社會發展形態的變革。在中國改革開放后,城市化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推動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快速發展、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提升人民生活品質以及增強國家綜合實力等方面。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不僅促進了經濟的增長,還加速了社會結構和文化的轉變。中國的城市化不僅刷新了人類對城市化和現代化關系的認知,也刷新了城市化對于國家崛起重要作用的新定位,讓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模式得到了國際社會和學界的廣泛關注。
(二)中西方城市化模式的特征性差異
城市化不僅是推動現代化的有力工具,而且是現代化建立的基礎,各國的城市化進程呈現出很強的階段性和異質性。從發展動因和發展模式分析,中西方城市化模式有著本質的區別。大衛·哈維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化的本質是資本的城市化,城市的發展是資本生產與繁殖的結果,而不是人的全面發展”[9]。資本主義城市化體現的是高度集中和高度分散的“雙重地域結構效應”,造成的是懸殊的貧富差距和尖銳的階級對立。這種“雙重地域結構效應”不僅體現在資本主義內部,也對全世界發展中國家和人民造成空間剝削。資本空間生產的逐利性和無序性,也在部分國家和地區引發“過度城市化”“失序城市化”“對立城市化”的風險。而中國的城市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城市建立和發展的核心目標是公有制經濟基礎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整體生產力的提升。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在城市化中保持適當的制度彈性和利益平衡,這也是中國在現代化和城市化的疊加進程中保持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秩序穩定有序的關鍵。在城市發展順序上,西方國家的城市化是“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遵循時間順序發展,彼此之間是遞進式的流程關系;中國的城市化是“并聯式”,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互為依托,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疊加發展[10]。劉士林于2013年率先提出了“中國式城市化”這一概念,他認為,中國式城市化模式有一些不易覺察、僅僅屬于自身的深層規律和特殊原則,形成了獨特的發展中國家城市化模式“中國方案”[11]。從特征性上分析,中國的城市化是一種內生型城市化,最顯著的特征是城市土地所有權的國有制和使用權的市場化,生產要素流動是從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雙向結合。陳明星等認為,中國的新型城鎮化逐步實現從“人口城鎮化”到“人的城鎮化”的轉變[12]。李力行指出,近 20 年中國城市化的變革可以概括為“一高一低”{“一高”指的是土地城市化速度高于人口城市化速度,“一低”指的是中國戶籍人口城市化率比較低。},本質上是一場“粗放型”的城市化生長歷程[13]。由于客觀環境和條件的限制,上一階段的中國城市化進程也出現“不完全城市化”“不充分城市化”和“粗放型城市化”等不足之處。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城市化理論的重構與創新是一種不同于西方的新方案,形成一條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二、中國式現代化新型城鎮化的新變化與新趨勢
(一)當前中國新型城鎮化呈現出的新特征
中國當前迎來的新一輪城市化浪潮也引起了國內外社會和學者的廣泛關注。2012年黨的十八大首次提出“新型城鎮化”這一概念,它是在中國快速城市化和工業化背景下,結合城市化面臨的新形勢和新挑戰提出的。新型城鎮化也被稱為“再城市化”或“再城鎮化”,主要特點是小城鎮的承載能力提升,區域內城市結構性優化與大城市綜合治理。國內學界對新型城鎮化的定義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將新型城鎮化水平定義為城鎮戶籍人口占城鎮人口的比重,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第二種認為新型城鎮化是指城市向都市的轉型,城市群和都市圈成為主要形態;第三種是將新型城鎮化理解為“城市化2.0版本”,是一種“二階城市化”。國家發改委發布的《2019年二次城市化建設重點任務》指出城市化進程將由第一次城市化的“整體快速發展擴張”,進入到“分化發展、集約精細化發展”階段。國家“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城市化”的提法部分代替了“城鎮化”一詞,并更加強調發展壯大城市群和都市圈。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這些論斷均體現對城市化發展理念的修正。
當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正處于全球資本空間生產流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發展任務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眾多時空交織的空間變革之中,既有西方國家城市化中的共性特征,也體現著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性特征[8]。具體體現在:第一,城市化發展步入減速穩定階段。美國地理學家 Northam認為城市化階段可分為“起步—加速—成熟”三個階段,曲線呈倒“S”型[14]。福卡智庫的《福卡分析》指出中國城市化已經進入中高速平穩推進的后半段,呈現出人口流動由中心集聚向多點擴散轉變、空間結構由分散性中小城鎮向區域性城市群轉換、城市功能由產城分離向產城人融合轉型的過渡性特征。第二,城市發展動能出現結構性調整。如表1所示,當前,中國的城市化進入精細化、集約化、低碳化發展階段,目標導向出現明顯的調整。政府競爭是中國城市高速發展的重要推力,城市生產和發展動機由資本主導轉變為人本主導,制度創新在中國城市經濟高速發展中具有決定性作用,全球分工的調整是中國城市崛起的重要力量,而非農產業的集聚是中國城市高速發展的關鍵支撐。第三,城市發展出現差異性分化加劇趨勢。當前,中國的城市化在區域空間分布上存在著較大的離散度,在城市化的過程中“飽和”與“不足”并存。城鄉融合和城市群極化吸附雙向疊加,人口流向“從鄉到城”和“從城到城”雙向疊加,城市新興和城市衰退并存。當前,城市發展進程分化,城市生命周期顯現,城市治理方式轉變為構建跨單位城市化治理體系,共同推進城市發展綜合質量提升。
(二)中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邏輯
上個階段的城市化是政府主導型,體現的是一種建構理性秩序(Constructivist order),城市化的制度剛性強,導致了人在城市化中的被指令、被規劃成分大;而新型城鎮化是一種進化理性秩序(Spontaneous order)或者自生自發形態的城市化、上下互動的城鎮化,更多強調市場機制的發揮,人在城市化中具備獨立的選擇能力和生存環境適應能力。“新型城鎮化”是中國城市化進入新階段后面對提質換擋的新要求產生的,將“以人為本”為發展指導,以統籌兼顧為實施原則,以體制創新為發展保障,以新型工業化為發展動力,以城鄉融合發展為主要形態,以提升城市綜合承載力為改革目標,以全面提升城鎮化質量和水平為核心目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聚焦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的體制、機制、制度改革,核心目的是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逐步發揮系統性、累積性、集成性的改革紅利,推動中國社會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新型城鎮化是黨中央面對中國城市化發展實際提出的改革方向,發展邏輯是在城市發展中樹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理念,把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作為城市化的動力,“注重‘個體人’的生存、發展和參與機會等權利的平等享有”[16],著力提升人居城市品質和持續化發展能力;現實邏輯是吸取西方國家“初次城市化”的教訓并結合新形勢下城市運行的新特征,城市發展由擴張型轉變為集約型;運行邏輯是提升城市生產資源利用效率,提升城市運營管護水平,提高城市的綜合承載能力;形式邏輯是增強城市發展的包容性、平等性和均衡性,形成凝聚共同價值觀的新國家空間。
具體體現在:第一,城市發展理念的置換更新。經濟改革解決的是供給問題,社會改革解決的是需求和分配問題。城鎮化發展理念的變革實際上是國家整體價值的提升,是國家整體進步的表現。如圖1所示,當前中國城市化的支撐條件發生轉變,新型城鎮化發展模式由粗放型到集約型,由激進式到漸進式,由指令性到包容性轉變,逐步改變了以往倚重城市擴張、城市基建、城市資源的消耗性發展模式,過渡到產業科技創新、城市規劃協同、城市品質提升、城市宜居改善等軟實力發展,實現各類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等資源和要素的高效優化配置,核心的目的就是人民群眾享受到城市化發展的改革紅利,讓人民切實享受到改革帶來的社會福祉。
第二,城市發展動力機制轉變。如圖2所示,城市化進程中各驅動要素的地位和能效是不斷變化的,在上一階段城市化中,資源、勞動力、土地、交通、資本依次作為主導因素對城市的空間生產起到了主導性作用。新型城鎮化要實現“二次城市化”的能動轉換,將城市驅動的發展動能由資源消耗轉變為改革效能。在下半程迫切需要通過城市新質生產力的培育,擺脫房地產依賴,著重提升技術創新、營商環境與人力資源的紅利催化效應,提高城市綜合承載力。
第三,城鄉資源要素的雙向流動。當前城鄉融合的不完全、不充分、不協調問題仍舊十分突出。例如: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程度較低,中小城市的產業承載能力不夠,特大城市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較低,部分城市安全韌性存在短板弱項等。《決定》強調構建產業升級、人口集聚、城鎮發展良性互動機制,從體制改革、資源互通、空間融通、發展保障等系統綜合推進,破除要素流通不暢的體制化障礙。
第四,提升城市發展質量和生活品質。目前,我國城鎮化發展目標已由前期的規模增量建設轉為存量提質改造和增量結構調整并重[17],由貪大求全轉變為注重城市獨特風格,由外延擴張式發展轉為內涵集約式發展。新型城鎮化在經濟新常態下,逐漸降低城市建設和運行成本,注重城市營商環境和人居環境提升,注重保留獨特的中國城市文化風貌,增強城市的發展韌性和可持續性。
三、中國式現代化新型城鎮化面臨的現實挑戰與突破方向
中國式現代化目標清晰,動力強勁,進展穩健,但是面臨復雜的國際環境和時代變化,尤其是面對國際競爭程度加劇,國內經濟面臨提質增效壓力增大,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深水區之后,前期城市化中的各類風險源、風險點相互交織、相互催化,在快速城市化前期所積累的大量社會問題在后期正集中顯露。如果不進行及時的防范和疏導,就會疊加傳導、遞進加深、使局部化的風險演變為體系化的風險。因而,下一階段迫切需要消化“初次城市化”后期衍生的城市問題,對后階段城市化治理可能出現社會福利板結、就業下滑、資源分配不公和管理模式錯位等城市社會問題,進行前瞻性思考和對策預防。
(一)影響和制約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突出挑戰
第一,城市公共產品和運行成本負擔加重的財政風險。“應對重大風險挑戰”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的六個必然要求之一。上一階段城市化經歷了大規模、快速、大范圍的基礎設施投資,城市公共事業的經濟效益顯著,但是社會效益、環境效益未充分展現,導致城市運行的可持續性遭到滯緩。隨著資源消耗和經濟環境的變化,前期過度依靠土地資源換取資本投入的一次性置換模式不可持續,過分倚重城市基建來拉動城市經濟發展動能的驅動方式不可持續。導致城鄉生產要素雙向流動出現平等性差異,部分大城市的環境承載能力達到極限,“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中心城區出現產業空心化,城市建設用地粗放低效等問題。一方面,隨著房地產市場的逐漸回冷,房地產市場的稅收紅利逐漸減少,但是前階段城市公共服務的運營管護成本逐漸增大,城市財政的補貼總額隨之增加,城市透支型基建引發財政風險,導致部分地方政府出現債務危機。另一方面,隨著城市擴張的收縮,現在的城市逐漸擺脫了工業型城市的發展定勢,更希望滿足多元化的發展需求,這就需要提供城市遷移人口更高質量的公共產品,例如教育、醫療、養老、生態環境等,對公共事業的資金需求增大,城市的公共財政負擔與日俱增。
第二,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后的市民化程度低。《決定》中明確提出要“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這是基于我國城市化的不完全、不充分現狀,城市治理能力現代化對城市治理和城市服務提出更高要求的現實。經過近40年的高速城市化,城市戶籍人口總量和比重快速提升,但常住城市人口和戶籍城市人口之間存在較大差距。如表2所示,截至2023年末,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18.5%,涉及人口數量2.5億多,其中絕大多數是農村流動人口[18]。以前通過城鄉戶籍屬性差異壓縮城市發展成本的模式已經與現實發展不適應、不匹配,由此衍生出階層結構變化、利益訴求多樣化、人口流動波動化等社會問題。由于戶籍管理制度,戶籍屬性中的公共產品和權益差異不僅在城鄉之間,還包括城市與城市之間造成多元利益沖突,并且隨著區域發展水平的差異,這種戶籍制度衍生出的差距將會增大增多。一方面,戶籍制度改革及其配套政策措施尚未全面落實,一些外來人口流入大城市落戶門檻高、普通勞動者落戶困難,體制性障礙造成城市移民難以享受城市平等性公共服務;另一方面,城鎮落戶困難和不愿落戶及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同時存在。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供給總體不足,難以全面覆蓋到所有城市常住居民,很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戶口“性價比”不高、農民落戶意愿不強,“不敢想”和“不太想”共同制約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共同導致市民化進程滯后。
第三,部分城市制造業萎縮造成居民充分性就業壓力增大。《決定》指出,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工業化、城鎮化與現代化的適應性、匹配性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更是民生問題。張鴻雁認為城市化水平超過50%以后,社會將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將會出現新的社會轉型、發展模式和新的社會問題[19]。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不相適應就會形成產生眾多經濟社會問題的底層性原因,如果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將會延緩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入城市,工業化將面臨就業人口缺乏、消費市場萎縮的局面,也會阻礙城市公共事業的發展和產業升級換代,導致城市的經濟輻射效應、帶動效應不顯著。如果工業化進程滯后于城市化,城市化缺乏足夠的工業產業支撐,就會陷入拉美國家的“過度城市化”困局,主要是失業人口增加,經濟收入水平較低,社會治安惡化,城市產業“空心化”,陷入“現代化陷阱”。反觀西方國家“過度城市化”不僅沒有形成國家發展的現代化,反而造成了高度城市化軀殼下的“虛假繁榮”,制造業萎縮引發城鄉失業風險。當前,我國經濟處于從工業化逐漸進入后工業化的階段,要警惕部分城市出現的制造業萎縮和過度城市化傾向,會導致公共財政收入減少和失業率增大風險。
第四,小城市和縣城產業集聚和人口承載能力不足。《決定》將“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列為改革的一項關鍵任務。滿足區域經濟的最佳生產效益,對不同類型的城市進行產業協作分工是必要的,也是市場經濟作用下生產要素自然外溢的必然結果。袁夢、楊華指出當前城市化下縣域空間風險聚集,農民城鎮化壓力增加,呈現不穩定特征[20]。中小城市和縣城是連接城鄉的重要樞紐,是率先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載體,但目前人口、產業等要素向大中城市特別是大城市集中的趨勢依然明顯,中小城市和縣城吸引力還不強,產業基礎薄弱、抗風險能力差,產業發展、要素投入、人口集聚面臨更大困難。關鍵原因是一些中小城市和縣城資源投入有限,政策效力較低,對產業和人口的承載能力不足,缺乏基礎的產業人口支撐,僅剩的生產要素資源反而被大城市進行虹吸,陷入資源枯竭、增長乏力的境地。同時,在大中小城市橫際交換關系上,生產要素資源沒有形成高效合理的空間優化配置,超大特大城市對周邊的輻射帶動作用發揮不夠,城市群之間沒有形成高質量的供給體系,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效應有待進一步提升、分工協作水平有待進一步優化等問題較為突出。
(二)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目標和突破方向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在城市化下半程,要在就業住房、職住平衡、產城融合、社會融入、區域經濟均衡度等領域取得新的突破,有效解決當前的“不充分城市化”和“不完全城市化”現象,消解城鄉空間壁壘,提升共同富裕水平,推進城市化高質量發展。
第一,完善城市空間格局合理分布。首先,進一步發揮城市群(帶)的牽引力,積極推進都市圈同城化的政策配套與銜接,形成由“行政空間”向“事實空間”的發展與治理思路轉變,降低行政壁壘,增強市場功能。《決定》強調要建立都市圈同城化發展體制機制。實現城市群同城化發展,關鍵要解決城市間利益分配問題,推進城市共建、共治、共享、共富,切實提高城市群高端要素集聚的空間供給質量。其次,要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縣城綜合承載能力的試點,重點提升產業集群、基礎教育醫療、公共事業配套設施、交通路網完善等民生保障工程,形成結構合理、產業協同、職住平衡、配套完善的城鎮化空間格局,形成以縣城為樞紐、以重點城鎮為節點的縣域經濟體系。再次,優化特大城市空間結構和布局,統籌空間、規模、產業三大結構,總體布局增設一批中小城市,使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成為吸納區域流動人口和資本的重要載體。最后,要規劃、引導、激勵特大城市與中小城市聯動協調發展,培育形成一批輻射帶動力強的現代化城市群,“通過中心城市集聚效應的外溢,帶動中小城市相關產業鏈的形成”[21],推動優勢地區優質資源要素加快外溢,釋放動能、減少虹吸,進一步發揮大城市對縣城、城鎮、鄉村的輻射帶動效應。
第二,合理推動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對于城市化率較低、工業化發展不充分、人口規模較大的人口大省,應該在省內積極培育、壯大產業類型聚集的中小型城市,將其作為省域內部人口流動就業安置的重點。通過統籌新型城鎮化戰略和新型工業化疊加發展,降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人口跨省大范圍遷移,平衡省際的就業人口波動。一方面,實施新一輪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行動,進一步提高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質量,完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配套政策,健全進城落戶村民的權益維護政策。以進城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為重點、兼顧城市間流動人口,著力解決好農業轉移人口最關心的穩定就業、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會保險等問題,著重“彌合城鄉在資源機會層面的不合理差距”[22]。另一方面,更加尊重人口遷移規律和趨勢,降低限制人口遷移的各類制度約束,以中心城市為引領,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以都市圈建設為突破口,對中小城市分類施策,完善與時俱進的人口流動政策和定居配套服務。
第三,提升區域城市的國際競爭水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23]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是引領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排頭兵,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支點,是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主要平臺。要更好地實施城市群、都市圈協同發展戰略,在切實解決好規模無序擴張、功能過度集中、人口過度集聚、城市病凸顯等突出問題的同時,要進一步發揮好特大型城市在國內市場發展、國際市場競爭中的帶動和輻射作用,勇于參與國際產業鏈的分工與競爭,推進“城市群發揮正集聚效應”[24]。要充分發揮特大城市科技資源豐富、科技創新能力強的優勢,突出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進一步增強特大城市科技創新、產業創新、培育未來產業、發展新質生產力等核心功能和核心競爭力。
第四,形成穩定健康的社會公共價值。《決定》強調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中國特色的城市化是一個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是對中國社會傳統價值取向、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變革。城市與鄉村不僅是戶籍屬性的差異,也有著更深層的價值觀點的差異。當前,城市公共工程正由規模化增量建設轉變為存量化的更新、改造與管護,城市化方針由外延式的擴張型轉變為內涵式的集約型,主要的出發點就是降低社會面的利益沖突,減少城鄉居民的價值觀分歧,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價值觀的實現。但是,目前戶籍制度所衍生出的教育公平、醫療文化、社會保險、公共服務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依舊十分突出,社會公共價值的凝聚還亟待提升。迫切需要進行行政體系化的重塑,在法治層面構建平等包容的人居屬性,城鄉之間、階層之間、地區之間的權益平等,享受公平的發展權利;在經濟發展層面,優化收入分配政策,實現均衡性、普惠化的階層關系,加快共同富裕建設步伐;在文化層面,形成一種各階層在同一空間內思想凝聚、觀念包容、權利均衡的發展環境,形成健康穩定的公共價值秩序。
四、進一步釋放新型城鎮化的改革紅利與制度潛能
當前,隨著客觀環境的深刻變化,傳統城鎮化紅利正在逐漸減弱,亟須培育城市接續發展動能[25],挖掘和釋放新的城市化紅利。2024年7月國務院發布《深入實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劃》,明確提出要進一步充分釋放新型城鎮化蘊藏的巨大內需潛力,持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進一步明晰了新型城鎮化的改革方向。
(一)進一步挖掘和釋放新型城鎮化的改革紅利
第一,體制機制變革的改革紅利。堅持系統觀念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要求。目前,針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靠局域化、臨時化、突擊性的改革已經難以奏效,必須從機制性、結構性、長效性的框架內進行體制機制改革。如圖3所示,客觀現實的變化要求既要對城市化模式作出必要的改革,釋放體制機制的改革潛能,也要在改革中挖掘改革紅利,保持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動能。陸銘認為在城市化下半程需要通過釋放新的制度潛能提升勞動力、資金和土地等硬件資源配置效率[26]。在部分中大規模的城鎮,放權改革面臨瓶頸、城鎮化潛力釋放受到制約、“小馬拉大車”問題突出。浙江省龍港市錨定“大部制、扁平化、低成本、高效率”改革方向,通過“撤鎮設市”降低行政運行成本,施行“市管社區”穿透式直接管理,在縣域基層治理方式上作出創新探索,不僅提升資源利用效率,也利用體制變革激發了治理效能的提升,促進城鄉融合發展。通過改革紅利的持續釋放,龍港市的城市建設、城市規模、城市功能和城市能級達到較高水平,形成了結構性轉化效益,承擔起為國家新型城鎮化改革探路的使命。
第二,新興產業的投資紅利。《決定》要求“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當前中國正在歷經一場人口紅利“拐點”,人口教育質量的提升不僅可以提供更為優質的勞動力,也可以增加市場需求總量,助力規模性投資。從投資角度分析,城鎮化率每提高1%,可以拉動投資需求超過1萬億元。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為66.16%,整體上還有一定的提升空間。新型城鎮化可以進一步加大對傳統基建和新基建的投資力度,促進房地產、建筑、交通、電力、通信、新能源等關聯行業發展,推進公共服務設施提標擴面,產生新的產業催化效應,并由此產生大量固定投資,充分釋放投資需求潛力和創新創造潛力。城市更新和產業結構優化也將創造巨大的投資需求,可以進一步擴大和更新公共產品的供給規模和質量,還可以帶動環保建材、文旅康養、教育醫療、旅游地產、數字經濟等行業的發展,助力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
第三,新興消費的市場紅利。由于城鄉之間的公務服務和社會保障的差異性,導致鄉村居民移民城市之后,消費市場出現“城鄉搖擺”的特殊局面,例如:社會保險、公共醫療、子女教育等重點領域引發城鄉之間的體制化沖突,不僅損傷了農村轉移勞動力享受平等的城市服務,也降低了轉移人口的消費需求。從消費角度看,城鎮化率每提高1%,每年新增2 000多億元的消費需求。城鎮人口和中等收入群體快速增長,成為促進消費的重要人群,新型城鎮化將推動我國轉向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增長。通過優化消費環境,創新消費場景,適應個性化、差異化、品質化消費需求,持續提高公共產品數量、規模與服務質量,推動生產模式和消費水平升級。市民化比例的提升,有助于擴大國內市場的消費需求,改善消費市場的供需結構,促進消費和投資實現良性循環。
第四,科技創新的人才紅利。根據“諾瑟姆曲線”以及國際經驗,當城鎮化率進入60%~70%區間時,城鎮化的主要動力將從數量驅動型轉向結構分化型。關成華指出當前我國正處于由資源要素驅動的一次城市化向以創新、人才驅動的“二次城市化”邁進的關鍵階段[27]。創新型人才是城市發展的催化劑。世界知名的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都因為人才紅利實現高質量發展。近年來,在特大城市周邊部分科技型產業鏈的中下游、產業集群的邊緣環節已開始出現人才科技的“外溢效應”,部分城市甚至出現科技創新人才資源向城郊地帶的“流失”,既帶動了人才資源的流動,也牽引生產要素的流動。李力行指出要繼續挖掘中國城市化的潛力,促進人口紅利的第二次釋放,將城市集聚效應充分發揮出來[13]。下一步要催化中心城市的人才、資本、技術、知識、信息等高質化要素的集聚與溢出效應,應積極推動中心城市、城郊地帶、毗鄰地區的產業移植,發揮出人才紅利的最大效益。
(二)進一步完善與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體制機制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最突出的體現就是人口分布在城鄉空間劇烈變化,體現在農業和工商業的人口流動。推動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與現代化的協調發展,僅靠單一的經濟或者社會改革方案是遠遠不夠的,必須統籌協調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生態環境、財稅消費等各個領域。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引,開創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需要利用政策的不同領域的相互配套、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的彼此結合、宏觀政策與微觀政策的相互融合、一貫性和靈活性的相互結合共同合力推動。
第一,實現“人—產業—城市”的融合發展。推進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改革需要推動新型工業化與新型城鎮化協調發展,要正確處理好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關系,構建產城融合、進程協調、規劃協同的良性互動機制。優化城市內部和城市之間的空間布局,建立多維度的城市發展目標,改變粗放式的城市化擴張模式,不再以城市的等級、人口、經濟總量規模作為城市發展目標,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新一輪城市化要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著力將縣城作為城鄉融合發展的核心,引導沿海產業向內陸轉移,適當加大制造業的比重,擴大和保持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就業水平,更好滿足農民就近就業定居的需求。同時,通過建設特色小鎮、都市農業、田園綜合體等項目,促進鄉村產業升級和形態優化,激活城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還要推動優質教育、文化服務、醫療資源向鄉村延伸,縮小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差距,利用市場機制引導城鄉要素的自由流動,形成城鄉互動、優勢互補的發展態勢。
第二,推進城市的集約化、低碳化和可持續發展。新型城鎮化要堅持以人為本、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推動城市化發展路徑由“量”向“質”切換。在新型城鎮化建設道路上,應調整土地供應結構,提升土地整治力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益。通過土地資源儲備和整治規劃進行土地資源的精準調節,優化城鄉工商業土地利用,加快發展建設用地二級市場,推動土地混合開發利用、用途合理轉換,盤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29]。同時,一方面深化城市建設、運營、治理體制改革,不僅要重視城市公共工程的建設成本,也要充分考慮維護、管護成本,對城市特大型公共工程根據常住人口波動實際進行動態規劃調整,實現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另一方面,改變傳統高投資、快節奏、高負債、大而全的城市發展路徑。逐漸收縮城市擴張和改建工程,注重城市更新和管護,更加注重保持城市獨有的文化風貌和社會景觀,鼓勵城市設置因地制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不斷提升城市業態、功能、品質。
第三,穩定和提高城市經濟的制造業比重。城市化與工業化是現代化的一體兩面,工業化為城市化提供了動能,城市化為工業化提供了勢能,兩者共生共存成為經濟增長、技術進步、推動社會保障的加速器。城市化不是“去工業化”,反而工業化應該成為城市化的支撐,要高度重視制造業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重要作用。城市化的發展應該與國家(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相適應并且符合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規律,部分城市應該及早及快地糾偏過早的“去工業化”政策傾向,大力推進“再工業化”進程。在加快發展高端服務業的同時,提高城市經濟的制造業比重,保持充分就業比例,防止出現城市區域“制造業空心化”。同時,對于人口規模較大、產業支撐較好的地區要積極保持一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守住制造業比重“紅線”。對于不具有區位和產業優勢的一般縣城可借助自身比較優勢與大城市合作,通過“飛地經濟”“地瓜經濟”等模式為本地農業轉移人口和返鄉農民工提供就業崗位。特大型城市、城市群在新一輪全球產業鏈重構和布局中,要保住核心競爭力,從而保證產業鏈安全,進一步發揮產業經濟的輻射效應,有效提高區域經濟綜合承載能力。
第四,加快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決定》提出“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體系”。劉耀彬指出城鄉統籌的設計形成了和諧共生的社會關系和人地和諧的空間關系,工業化和城鎮化過去是一對矛盾體,現在成為一個融合體[28]。遷移人口的市民化不是簡單的戶籍屬性市民化,而是發展權益的市民化。對于人口流入的大城市,要積極構建青年友好型、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優化戶籍管理政策,優化人口和經濟的空間結構,增強遷移人口內生發展動力,提升遷移人口的城市歸屬感。對于不在中心城市輻射范圍但自身產業基礎較好的“節點縣城”應注重產業和公共服務補短板強弱項,加強與周邊區縣協作,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探索“小都市區”發展模式[30],增強其經濟造血能力,提升公共財政收入水平,形成次級市民化吸附規模,幫助減輕大城市人口壓力。對于城鄉流動性人口,要深化居住證配套性服務,增強居住地的資源配套供給規模,重點保障子女教育、醫療保險、住房保障、社會救助等無差異化公共服務,讓城市流動人口平等地享受城市發展紅利和改革紅利。
第五,提升科技創新的增值潛力。《決定》提出“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科技是最關鍵的生產要素,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是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關鍵,而新型城鎮化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和經濟環境。曾智洪認為下一階段的城市化從排斥性演進向包容性發展—包容性創新轉變,提升城市生產效益,促進市場資源整合[31]。以改革創新為動力,促進生產要素聚集,形成增長創新驅動力。要更加注重提高城市創新能力,聚焦中長期技術突破和產業化發展方向,前瞻布局未來產業,應重視科技創新與市場化應用的結合,不斷優化資源配置。要積極搶灘布局行業新賽道,尋求符合自身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的城市工業差異化發展路徑。要推進招商引資體制機制創新,不斷優化營商環境,建立“投行思維”推進資本招商,專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與新一代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一批“專精特新企業”。同時,確保發展進程中的開放性、安全性和可持續性,提升產業技術水平和價值鏈競爭力。
結語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科學謀劃和系統部署,提出增強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明確要求。實現新型城鎮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命題,也是中國經濟爬坡過坎的重要動力。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型城鎮化是超大規模和超常規速度下的高質量城市化,是人人享有城市化發展改革紅利的城市化,是保持經濟發展活力和社會安定秩序相統一的城市化。在進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階段之后,部分西方媒體開始出現唱衰中國城市化的言論,散播“中國城市化引擎正在熄火”,“中國城市化紅利消耗殆盡”,“中國的土地財政走入死胡同”等不實言論,目的就是唱衰中國的改革動力和改革環境。對照城市化國際指標,當前我國的城市化已經進入“下半場”。相較于城市化初期,現在人口對比基數變大,增速逐漸放緩,改革的難度變大,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城市化已經失去動力,經濟發展的強大韌性和巨大潛力沒有改變,反而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中可以繼續深化改革,消除體制性束縛,進一步擴大發展空間和釋放改革紅利。
“治理”“公平”“安全”“質量”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核心精神要義,是未來一個時期我國改革深入推進的目標指引。當前,我國的城市化進入提質增效的新階段,新一輪城市化的風險和機遇并存,需要審視部分西方國家在城市化中引發的問題和教訓,作出必要的風險預警和評估,系統推進用學科系統交叉的多維化視角去分析中國當代城市化的新趨勢、新變化、新問題。這有助于提高對社會主義城市化的運行機制、問題成因和發展趨向的認知,有助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城市化理論與實踐的創新與發展,有助于提升當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理論生長力,豐富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理論體系,還可以有力回擊中國城市化潛力殆盡、城市化紅利結束、中國陷入“中等收入困境”等唱衰中國的錯誤論調,為經濟社會健康發展提供政策支撐和輿論支持;既驗證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的正義性和科學性,也落腳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方案之中。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EB/OL].(2014-04-03)[2024-08-15].中央政府門戶網站,http:∥www.gov.cn.
[2]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2.
[3]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22.
[4] 高力克.中西文明與現代化:亨廷頓的啟示[J].浙江社會科學,2022(1):12-23,156-157.
[5] 楊貴慶.21世紀:中國的城市世紀:對Peter Hall爵士關于中國城市化和中歐城市發展比較的采訪及其思考[J].城市規劃匯刊,2004(6):3-6.
[6] 文貫中.吾民無地:城市化、土地制度與戶籍制度的內在邏輯[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23.
[7] 孫建平.中國式現代化為中國式城市化指明方向[EB/OL].(2022-11-23)[2024-08-20].文匯報, https:∥www.whb.cn/commonDetail/497176.
[8] 劉偉.中國式現代化視閾下城市化模式的“中國道路”:“資本邏輯” 到“人本邏輯” 空間重塑[J].新疆社會科學,2023(6):43-53.
[9] 大衛·哈維.資本的城市化:資本主義城市化的歷史與理論研究[M].董慧,譯.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7:20.
[10] 于安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之“全面”論析[J].蘭州學刊,2023(5):5-14.
[11] 劉士林.關于中國式城市化的若干問題與啟蒙思考[J].江蘇社會科學,2013(5):129-133.
[12] 陳明星,葉超,陸大道,等.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理論內涵的認知與建構[J].地理學報,2019(4): 633-647.
[13] 李力行.中國的城市化還能走多遠〖DK〗?[EB/OL].[2024-08-27].http:∥nsd.pku.edu.cn/sylm/gd/534990.htm.
[14] 李國平,譚玉剛.中國城市化特征、區域差異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社會科學輯刊,2011(2):106-110.
[15] 孫立行.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的科學內涵[EB/OL].[2024-08-15].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219/c1001-23890085.html.
[16] 汪彬.中國式現代化引領的新型城鎮化:邏輯、內涵與路徑[J].江西社會科學,2024(6):55-63.
[17] 孟凡君.以產興城以城促產 新型城鎮化潛力巨大[N].中國工業報,2024-08-19(01).
[18] 丁茂戰.把握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重點任務[N].經濟日報,2024-09-12(10).
[19] 張鴻雁.中國城市化理論的反思與重構[J].城市問題,2010(12):2-8.
[20] 袁夢,楊華.農民縣域城鎮化的實踐邏輯與社會風險[J].城市問題,2022(7):24-32.
[21] 劉秉鐮,高子茗.城市群空間結構視角下中國式城鎮化的內涵、機制與路徑[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4):11-22.
[22] 范根平.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城鄉融合發展的理與路[J].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4):27-36.
[23] 習近平.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J].求是,2019(24):1-3.
[24] 洪晗,肖金成,陳蕊.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的新型城鎮化:概念辨析、現實困境和突破路徑[J].區域經濟評論,2024(2):38-49.
[25] 周毅仁,李智.更好發揮新型城鎮化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支撐作用[J].行政管理改革,2024(4):4-14.
[26] 陸銘.從人口紅利到人口空間再配置紅利[EB/OL].[2024-08-08].未來城市實驗,https:∥36kr.com/p/2896915678435972.
[27] 關成華.中國城市化進程新特征[J].人民論壇,2023(2):62-65.
[28] 劉耀彬.中國新型城市化包容性發展的道路與政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90.
[29] 劉國中.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N].人民日報,2024-08-01(06).
[30] 張蔚文.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N].光明網-理論頻道,2022-05-10.
[31] 曾智洪.中國新型城鎮化包容性制度創新體系研究[J].城市發展研究,2017(5):1-7.
The reform dividend and mechanism improve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in"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tudy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LIU Weia,b
(a. Institute of Marxist Studies; b. Zhejiang Province “Eight-Eight Strategy”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stitute,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Hangzhou 311121, P. R. China)
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s and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concept of people-centered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s bringing about a profound chang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ystem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are the cor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the fundamental aim of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at are more compatible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reform.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focused on the need for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and integrated refor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faced with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condition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objective environment, it explored in depth the outstanding institutional problems such as the balance of regional economy, the balance of public products, the fusion of urban and rural governance, and the bi-directional urban-rural interaction. It also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s the necessity and reasonableness of the development logic behind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The second urbanization with new urbanization as the carrier will further release the dividends of reform, strengthen the kinetic energy of reform and expand the space for reform in terms of factor flow, public service, social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potential.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of new urbanization is a reshaping and re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and the top-level logic has been changed from incentive-based urbanization to inclusive urbanization, so as to analyze and judge, prevent and respond to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that may arise from the increased burden of the costs of urban operation and public products, the insufficiency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relocation and citizenship, the weakening of the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d counties, and the lack of harmon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urbanization. Through integrated systematic reform, new breakthroughs can be made in areas such as public goods, urban-rural connectivity, rights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balance. Thi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next stage of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for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efficient use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resources, and advanc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will also help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model reference and policy guidelines for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econdary urbanization; new urbaniz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reform dividend(責任編輯"傅旭東)
基金項目:2024年度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常規課題“中國式現代化城鄉融合發展的機制優化與效力提升——解碼共同富裕‘浙江經驗’ ”(24CCG31);2024年余杭區社會科學研究課題重點項目“提升鄉村運營能力促進余杭區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實現路徑研究”(Yhsk24Z01);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歷程與經驗研究”(23amp;ZD031)
作者簡介:劉偉,中共浙江省委黨校(浙江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講師,博士,浙江省“八八戰略” 創新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浙江省委黨校基地研究員,Email: 85094530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