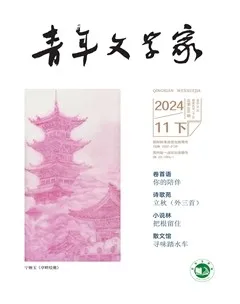論《萬壽寺》的后現代敘事策略
王小波的《萬壽寺》作為一個后現代文本,體現了多種后現代敘事策略,不再像傳統文學那樣完整地敘述故事,結構雜亂無章,情節被拆解甚至顛覆,藝術手法也取得了突破。元小說的表現手法顛覆了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其互文性的大量運用,削弱了現實主義文本一貫主張的價值與意義,加之碎片化的情節拼貼與無序的結構布局,徹底顛覆了人們習以為常的敘事模式,展現了一種全新的文學審美。作者刻意拆解、顛覆作品中的各種成分,使得作品沒有中心,將一切內容都放置在同一平面上。其敘事特征可作如下具體分析。
一、互文性
法國結構主義評論家克里斯蒂娃指出“互文性”就是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編。從許多后現代主義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互文性的手法常常顛覆和解構傳統文本中的人物、故事,從而起到批判的作用。除此外,文學作品中的互文性也包括引用、指涉自己的作品,構成內文本性。比如復制、戲仿等表現手段,在《萬壽寺》中均有體現。
(一)對作品的復制與改寫
作為后現代主義小說,《萬壽寺》不是以現實生活為基礎,而是對現有文本進行加工、仿寫,從而變成一個新文本。
首先,《萬壽寺》對袁郊所作的《甘澤謠》中的《紅線傳》進行了改寫。王小波在文中也提到:“我寫到的這個故事可以在古書里查到。有一本書叫作《甘澤謠》,里面有一個人物叫作薛嵩,還有一個人叫作紅線。”作者直接表明借鑒了其他小說,但細讀文本后會發現,《萬壽寺》的內容要比《紅線傳》復雜得多。《紅線傳》中薛嵩與紅線二人為主仆關系,且以女俠紅線為中心展開故事,講述了紅線為節度使薛嵩排憂解難的故事;而《萬壽寺》只是借用了“薛嵩”和“紅線”兩個人物的名稱,故事情節則大相徑庭。
其次,《萬壽寺》借鑒了莫迪亞諾《暗店街》“遺忘—尋找”這個主題。小說開篇就提到莫迪亞諾在《暗店街》里寫到的:“我的過去一片朦朧……”王小波和莫迪亞諾都注意到了“記憶”的重要性,但同一主題,兩位作者卻講述了不同的故事。《萬壽寺》中的王二用了一個多星期便找回了自己的記憶,然而他更想逃避現實,向往著自己筆下的詩意世界;《暗店街》中居伊·羅朗一生都在尋找自己的身份,雖苦覓無果,但仍然堅持。《萬壽寺》在這個主題之上,對唐傳奇故事進行改寫,巧妙地結合了中西小說的表現元素。通過許多細節暗示,能夠看出作者復制、模仿其他作品的行為。
對作品的復制與改寫還體現在文本中敘述人對手稿的改動。文中寫道:“既然已經確知這稿子是我寫的,我也不必對作者客氣—可以徑直改寫。”被改寫的文本《紅線傳》和《暗店街》相較于敘述人看到的手稿本是獨立存在的,但被復制后,就成了手稿的一個組成部分,文本間構成層層復制的關系。《萬壽寺》中還存在著故事情節的反復重現、人物之間的互相指涉,如“薛嵩就是我”,“塔里的姑娘”就是白衣女人的化身等。這進一步促使作品內部形成豐富的互文性。
(二)戲仿
戲仿是對小說文本的再次虛構或再創造,它扭曲、夸大小說原作,模糊原作本身的真實意義,是對原文的異化和戲謔。前面已經提到了《萬壽寺》對《紅線傳》與《暗店街》的借鑒,而這里要談的是戲仿在《萬壽寺》中的應用。
《萬壽寺》主要以唐傳奇故事《紅線傳》為戲仿對象。紅線在原唐傳奇故事中是武功高強的女俠,為主人薛嵩保駕護航。原故事中僅簡略地提到紅線為薛嵩的婢女,是為了報恩而留,沒有描寫她與薛嵩的日常;而王小波利用很大的篇幅來改寫紅線的形象。首先,紅線的身份變成了薛嵩的侍妾,二人的關系由奴仆的報恩轉為更為復雜的情感糾葛。其次,紅線與薛嵩成長環境差異很大。紅線是在山上的苗女,潑辣且不懂禮數;而薛嵩來自中原,一心想讓她學習漢族的禮節,確立二人“小奴家”與“大老爺”的對立關系。薛嵩雖認為二人有地位上的尊卑之分,但紅線卻不這么認為,如薛嵩被刺客砍傷后,撒氣到紅線身上,罵她是苗子,紅線則“從地下撿起刀來,對準薛嵩劈面砍去道:好哇!要和我們開仗了!老娘就是要謀殺你這狗屁親夫!”薛嵩對紅線的教化,紅線雖表面接受,內心卻十分鄙夷,產生了強烈的諷刺意味。紅線敢愛敢恨,打破傳統禮教的束縛,是一個有著渴望女性獨立精神的形象。這樣的紅線是對《紅線傳》中刻畫的“女俠”形象的反叛。
二、顛覆傳統線性敘事方式
和傳統小說不同,后現代主義作品的敘事不再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萬壽寺》文本缺乏因果邏輯,原本的線性時間敘事走向碎片化和平面化,語言上也是相互顛覆、互相拆解。像是許多意識流的片段組成,情節往往跟隨作者的心情發展。
(一)情節碎片化
零散化、碎片化敘述常見于后現代主義文本中。這類文本敘事通常缺少中心、不講邏輯,不交代前因后果,故事的情節時斷時續。這不僅是為了強調碎片感,而且讓作者有自由和空間在故事中插入其他小片段。
《萬壽寺》中,不管是敘述人的現實生活,還是手稿中的虛構世界,情節之間聯系并不密切。作者會隨意地在敘述人的現實生活與手稿里來回穿梭,上一段還在敘述自己與表弟聚餐,下一段又開始了“薛嵩決定要搶紅線為妻”;剛剛還在現實中“吐槽”考古系的主任,突然又走進自己的故事中去塔樓里營救姑娘。段落間仿佛各種碎片隨意拼湊在一起,缺乏過渡所需的情節基礎和內在邏輯聯系。但有時作者會用敘述者的口吻來引導讀者,故事里的事就是敘述者自身的事,比如王二與薛嵩的經歷有多處一致的地方。盡管這些情節碎片不能還原為一個整體,但它們并不是孤立的、毫無聯系的。讀者需要像偵探一樣抓住文本的細枝末節,將隱藏在其中的線索串聯起來,不然就容易被碎片化的情節繞得云里霧里。
除了情節與情節之間的跳躍外,小說還會毫無征兆地結束故事,“我隱約感到這個故事開頭拖沓、線索紛亂,很難說出它隱喻著些什么。這個故事就這樣放在這里吧”。作者不管故事情節是否敘述完整,直接結束敘述。虛幻與現實的交疊的表述方式,使得傳統故事敘述被分割,有意地讓小說像思維或說話一樣流動著,不在乎人物性格和故事情節是否完整,讓讀者感覺到閱讀過程中的震蕩和跳躍,同時也給予讀者足夠的想象空間。
(二)平面化敘述
將線性時間轉化為平面空間的敘事方式是后現代主義小說敘事的突出特征。將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發生的事放置在同一平面上,能使故事具有多種可能性,消解了歷史感。
《萬壽寺》以王二與白衣女人、薛嵩與紅線為兩個不同時空的線索展開描寫。作者在古今兩個時空中來回穿梭,交叉敘述。現實生活中的“我”在萬壽寺工作,而手稿中的“我”又穿越到唐朝化作薛嵩、化作紅線去體驗他們的人生。敘述人根據古人的生存境遇還會引申出來與現代人生存境遇之間的類比,將不同時間、不同場合發生的事和經歷的感受羅列在一起,在同一空間平面展開討論。薛嵩與紅線在打造囚車時,二人意見不同,有很多想法。這時作者跳出來說“他們做事的方式有點亂糟糟,就像我這個故事”。文本中,作者經常會在寫手稿里主人公的某一行為、心理時,聯想到現實人相似的行為和心理,轉而描寫現實中“我”的境遇。這樣跨時空的手法打破傳統的敘事模式,使整個文本的框架變得平面,在同一層次上展開敘述。
在讀《萬壽寺》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其情節具有開放性,每個情節都經過多次的重構。手稿先描寫一個確定性的情節,但讀下去會發現故事情節并沒有繼續發展,而是會被敘述人的想象打斷。例如,“我”在講述虛構世界中發生的故事時,戛然而止,對所講之事發表自己的見解;或者敘述人在同一層面上建構出另一種可能的情節,如“薛嵩被刺”這一情節在文章中重復出現,作者常常發揮想象,給故事另一種可能性:“有關薛嵩被刺的經過,還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這個刺客還有可能是個亮麗的女人……”“這刺客也可能是個男的……”這就使原本線性的發展情節發生間斷,在同一平面發散開來。這樣的做法看似是在堆砌情節材料,卻能顯示出一種獨特的敘述張力。
三、元小說
《萬壽寺》之所以有趣,就在于故事情節之間的轉換與改寫,作者將自身的內心世界與外在世界相連,采用“元敘述”的方式,創作了書中有書、撲朔迷離的后現代敘事作品。
(一)自我指涉
后現代小說敘述主體會強調“自我”的存在,在文本中會津津樂道自己的創造過程。除此外,在后現代敘事中,敘述主體的身份和權力也受到了質疑。一方面,敘述者總是介入故事,使自己成為故事中的一個人物;另一方面,敘述者的敘述常常受到質疑和批評。
《萬壽寺》中,作者借序言以及文中王二之口,多次表明小說的創作靈感,展示自己的創作過程。我們會經常看到“有一件必須說明的事”“還有一件需要補充的事”等這樣的句子,作者向讀者暴露自己的敘述痕跡,讓讀者清楚地看到“我”是怎樣敘述故事的,同時也展示了作品自身的虛構性。
在《萬壽寺》中,敘事視角展現出多維特性,敘述者既能以全知全能的視角縱覽全局,又能融入故事,化身其中一員,采用第一人稱的口吻親歷敘述:“秋天的下午,我在塔里等待薛嵩……”“我穿著白色的內衣……如你所知,我是那個來幫忙的表弟。”敘述人由王二變成塔里的姑娘,又變成表弟,從任一位置移到另一個位置,讀者跟著敘述者感受不同的場景,故事也因不同人的視角而不斷豐滿,也能夠感受到作者想要和讀者溝通的強烈愿望。
《萬壽寺》也體現了作者與小說敘述者之間的交流。敘述者“我”常常跳出來懷疑自己:“我覺得自己對過去的手稿已經心領神會……只有一點不明白:我為什么要寫下這個故事?”這種小說,會讓讀者覺得不是在讀,而是在聽敘述者講故事,過程當中還會有互動問答。甚至當作者的敘述與小說敘述者的不相符時,作者還會受到書中主人公這樣的指責:“我是這樣的嗎?”“你瞎說什么呀!”如果事先讀者對作者的寫作風格和后現代主義手法并不了解,按照一般規律閱讀,就會感到困惑。但也正是這樣才會促使讀者思考,直到發現文本的深層含義。
(二)融合現實與歷史、虛構與事實
《萬壽寺》的故事中夾雜著兩條線索、兩個時空交錯敘事,打破了小說的時序性。但其中包含著敘述者對一些事物相同的體驗,也正因為感覺的共鳴,從而縮短了歷史與現實的距離。閱讀《萬壽寺》,文中時不時會蹦出讓讀者出乎意料的描述,如士兵臉上露出的“蒙娜麗莎似的微笑”,到時間就會提醒“請撒尿”的智能夜壺,以及紅線隨口而出的“Anyway”等,這種穿越時空,將歷史與現實相融合的實驗性語言,給讀者以無限的樂趣。將這種現代情緒帶到唐傳奇的故事中,一方面產生了一種陌生化的效果,令讀者產生新奇的閱讀感,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作者天馬行空的想象力。
《萬壽寺》是虛構中的虛構:現實中,萬壽寺是一個令人感到壓抑的庸俗世界,而想象中的鳳凰寨和長安城是一個充滿詩意的虛構世界。敘述者“我”在現實與虛構中有著截然相反的兩種處世態度。前者是玩世不恭的,后者是積極且富于創造的。二者造成的反差也正是表達了作者追求個性、渴望自由的精神追求。無論是碎片化的情節、時空交錯的敘事,還是實驗性語言的運用,作者都是力圖展現作品本身的虛構性。但虛構中又帶有真實色彩,無論是在文中略帶嘲諷地映射現實社會,還是敘述者口中的“詩意的世界”,都體現了作者內心的真實情感。
《萬壽寺》作為王小波探求小說無限可能性的一部作品,將敘事藝術展現得淋漓盡致。小說的創作手法是隨意的,經常導致故事情節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對同一情節的描寫出現多種可能性,使得確定的理解變得不確定。而且,小說突破了傳統小說時空的限制,沒有傳統小說一貫的“開頭”“高潮”“結尾”等正常的邏輯過程,展現出的是較缺乏邏輯、時序混亂、段落跳躍、句與句之間相互矛盾的敘事手法。這種強調自我意識、打破傳統的后現代敘事策略,突出了作者的精神世界—自由。這是小說《萬壽寺》的意義所在,更是王小波一直以來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