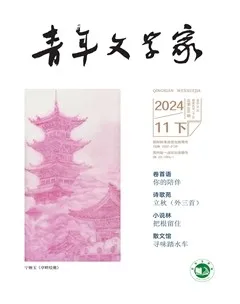生活世界中的本真探尋
作為2013年的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與“當(dāng)代契訶夫”,艾麗絲·門羅的小說備受中外學(xué)者關(guān)注,尤其是她的敘事藝術(shù)、女性思想和日常書寫,如沃爾特·R·馬丁的《艾麗絲·門羅—悖論與平行》,貝弗利·J·拉斯波里奇的《兩性之舞:艾麗絲·門羅小說中的藝術(shù)與性別》,以及丁林棚的《門羅小說中的日常生活和加拿大民族性》。的確,艾麗絲·門羅善于結(jié)合自己的經(jīng)歷,細(xì)致書寫平凡女子的成長(zhǎng)與細(xì)碎生活,并將作品中的主要時(shí)間和地點(diǎn)設(shè)為二十世紀(jì)四五十年代的加拿大小鎮(zhèn)。然而,我們還應(yīng)關(guān)注到,她是要在生活中借助女性視角來思考每個(gè)人的自我覺醒、依循自我的存在方式,以及自我與日常生活之間的矛盾等本真話題。正如凱瑟琳·謝爾德里克·羅斯在《艾麗絲·門羅:雙重生活》中所言,艾麗絲·門羅的作品之所以聞名于世,是因?yàn)樗哉嬲\(chéng)的私人情感和深切的同情進(jìn)行創(chuàng)作,為平凡生活賦予魔力,讓讀者在真摯的敘述中發(fā)現(xiàn)女性內(nèi)心最深處的自我,如《逃離》中的主人公卡拉在逃離一成不變的原生家庭時(shí),留下“我總渴盼一種更為本真的生活,我知曉你難以理解這一切”的字條。
本真(Eigentlichkeit)由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shí)間》中明確提出,是指人是其所是,與非本真(Uneigentlichkeit)相對(duì)。研究艾麗絲·門羅作品中日常與本真關(guān)系是為了探究艾麗絲·門羅作品的真正問題域,理解艾麗絲·門羅思想的內(nèi)核,也是為了研究艾麗絲·門羅寫作的文學(xué)史意義和當(dāng)代存在價(jià)值。
一、生活世界對(duì)本真的催發(fā)
西方傳統(tǒng)作家多書寫偉岸英雄的崇高事跡以及宮殿與戰(zhàn)場(chǎng)的場(chǎng)景,直至資產(chǎn)階級(jí)興盛的18世紀(jì),“‘世俗社會(huì)’的元素進(jìn)入了藝術(shù)和哲學(xué)”(亨利·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小人物”的出現(xiàn)成為西方文學(xué)史中的重要事件。以艾略特、喬伊斯、貝克特等人為代表的現(xiàn)代主義作家棄置了典型人物、環(huán)境與特征的塑造,開始描摹日常生活的凌亂、荒蕪與瑣碎,但他們大多對(duì)日常存在持批判態(tài)度,并寄希望古希臘式或牧歌式那樣的有意義的生活。換言之,他們并非與傳統(tǒng)作家一般,而是用一種更具意義、精神與秩序的高貴生活,來輕視日常存在。從這個(gè)意義上來說,艾麗絲·門羅的日常書寫有特別的意義。她的眾多小說發(fā)生于極其普通的小鎮(zhèn)、家庭中,也在切菜、除草和照顧孩子等日常雜事中逃離、返回與打轉(zhuǎn)。可以說,她并不期許一個(gè)遙不可及的彼岸世界或超越世俗的精神世界,而是認(rèn)可與承受日常的生活世界,也在這一世界中深入思考現(xiàn)代人的存在。她知曉人們?yōu)槿粘I钏В矔r(shí)時(shí)刻刻置身于其中,從中獲取所需的房屋、食物、知識(shí)、經(jīng)驗(yàn)與各種關(guān)系,在其中交流、學(xué)習(xí)、勞作并度過自己的一生。日常構(gòu)成人生的源泉、場(chǎng)域與內(nèi)容。所謂的高尚世界與活動(dòng)不能與日常生活分開,而要在日常生活中發(fā)生。日常生活是人類生產(chǎn)所需要的一切事物的總和。海德格爾亦曾強(qiáng)調(diào)“此在分析在最初恰恰不應(yīng)從某種差別相入手,而要從日常生存的平均狀態(tài)或無差別相入手。正因?yàn)槿粘I鏄?gòu)成了此在最切近的生存方式”(《存在與時(shí)間》)。
艾麗絲·門羅筆下的人物在父母的呵斥、夫妻間的陌生以及周邊人的評(píng)頭論足中,依然認(rèn)真地生活著。然而,這并不表示他們是行尸走肉或人云亦云地度過自己的人生,而是在與他人、器物的打交道中,逐步地萌發(fā)自我意識(shí)并產(chǎn)生探尋自己人生的祈盼。《好女人的愛情》中伊內(nèi)德的父母對(duì)她的護(hù)理工作充滿偏見:對(duì)男人身體了如指掌必將致使男人偏頗地看待護(hù)理女孩,毀棄她成為好女人的可能,“護(hù)理工作會(huì)讓女人變得粗俗”,護(hù)理應(yīng)該等待婚后才可著手去嘗試。她卻不愿聽從父母的安排,而是出于對(duì)護(hù)理工作的熱衷,投身于照顧病人的事宜中。在該小說中,艾麗絲·門羅筆下的角色甚至意識(shí)到,他人的意見與命令有時(shí)會(huì)產(chǎn)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尤其是當(dāng)這些意見與命令與個(gè)人意愿相違背時(shí)。在被父母勸說不要嫁給農(nóng)夫之后,伊內(nèi)德以“這些都是瘋狂的想法”表示拒絕,并選擇了農(nóng)夫魯佩特作為自己的丈夫。即便后來得知魯佩特是殺人犯,她也堅(jiān)守自己的選擇,沒有離開他。
弗洛伊德曾指出,人們因?yàn)槲窇指赣H的權(quán)威,往往會(huì)抑制自己的期望和欲望,采用一個(gè)社會(huì)性自我來生存。然而,艾麗絲·門羅的敘事卻表明,他人的反對(duì)與威嚴(yán)有時(shí)反而可能成為個(gè)人探尋自我及追求自我生活方式的催化劑。在某種程度上,為了達(dá)至與實(shí)現(xiàn)本真,人也需要與許多常見相背離,尤其是女性。“一般意義的‘婦女’承擔(dān)著全部日常生活的重負(fù);她們受到日常生活的約束遠(yuǎn)遠(yuǎn)大于‘男人’。”(亨利·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幸福過了頭》中的索菲亞在數(shù)學(xué)領(lǐng)域具有天賦與興趣,獲取數(shù)學(xué)界最高獎(jiǎng)項(xiàng)勃丁獎(jiǎng),得到眾人的贊許,在明亮高雅的房屋中發(fā)表了演講。然而,她的工作請(qǐng)求卻被無情拒絕,那些人甚至認(rèn)為雇用一只受過訓(xùn)練的黑猩猩更劃算,她也不被大科學(xué)家的太太們所理解,只被視作一只通曉多種語(yǔ)言的鸚鵡,或者某些天才兒童。只不過種種的不解、質(zhì)疑與阻撓,對(duì)于有著強(qiáng)烈自我意識(shí)的索菲亞來說,都只會(huì)進(jìn)一步激發(fā)她的反抗精神,使她更加堅(jiān)定地捍衛(wèi)自我,抗?fàn)幉还K嘣谇诿恪⑴εc不屈中成為世界上的第一位數(shù)學(xué)女博士、第一位女教授與第一位科學(xué)院女院士。《伊達(dá)公主》中的母親同樣表現(xiàn)出“怪異”,她決然地背離家庭主婦這一傳統(tǒng)身份—“家庭主婦沉浸在日常生活中,被日常生活淹沒;她從來都逃不出日常生活,除非她待在非現(xiàn)實(shí)的世界里”(亨利·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而趨向社會(huì)婦女。該母親執(zhí)著地參加有知識(shí)素養(yǎng)的聚會(huì),厭惡低俗娛樂的社交,敢于拋頭露面,在報(bào)刊上刊發(fā)文章議論教育、宗教與地方治理等問題,開車前往各處售賣百科全書。誠(chéng)然,她的行為給她和她的女兒帶來了親戚和鄰居的閑言碎語(yǔ),甚至是尷尬與羞辱,但這絲毫沒有動(dòng)搖她投身社會(huì)事務(wù)的決心和行動(dòng)。自幼年起,她就在哥哥的虐待、母親的去世以及父親粗暴干涉她求學(xué)決定的過程中,逐漸培養(yǎng)和堅(jiān)定了自己的意識(shí)。年僅8歲的她就穿著男孩的鞋走遍鄉(xiāng)間,發(fā)放《圣經(jīng)》,保持對(duì)世界的興趣,后來她也毅然違抗父親的意志而離家前往學(xué)校。“母親沒有放棄任何事情。我們知道,母親的目標(biāo),雖然有時(shí)會(huì)有一點(diǎn)兒模糊,或者轉(zhuǎn)移,她仍然保持著更年輕的自我,奮發(fā)而充滿希望。”該母親這一系列與世俗常見唱反調(diào)的“怪異”行為,身體力行地實(shí)踐著海德格爾的本真觀點(diǎn),當(dāng)一個(gè)人放棄其所不是,就會(huì)成為其所是,這必然伴隨著自我本質(zhì)的頓悟前的長(zhǎng)時(shí)間的精神壓抑與拉扯,以及為了維持個(gè)人本真而反抗充滿權(quán)威與意志的生活世界的強(qiáng)大勇氣。
二、生活世界對(duì)本真的環(huán)伺與壓制
艾麗絲·門羅也清晰地認(rèn)識(shí)到并非所有人都如伊內(nèi)德、索菲亞與“母親”般,秉有強(qiáng)烈的自我意識(shí)并敢于抵制和行動(dòng),大多數(shù)人在他人的持久影響與周邊的非議中,放棄自我而用他人構(gòu)成自身。海德格爾早已指出與他人共存這一存在本質(zhì),致使人們?cè)诂F(xiàn)實(shí)中難以實(shí)現(xiàn)本真,人們不僅時(shí)時(shí)被他人侵?jǐn)_,還要接受普遍常識(shí)或共同觀念以消除自己與他人的差別,來與他人交談、共事與生活。德里克·阿特里奇也提出當(dāng)個(gè)人的精神世界采用了普遍的既定模式,那么人的主觀自我就會(huì)因?yàn)槔鄯e效應(yīng)的影響而發(fā)生改變,甚至有可能就是由他者創(chuàng)造。《烏德勒支的寧?kù)o》中有兩位出生在朱比利小鎮(zhèn)的普通女孩—海倫與麥迪。海倫不畏流言蜚語(yǔ),勇于走出小鎮(zhèn)和母親的陰影;而麥迪則遵循姨媽們的觀點(diǎn),認(rèn)為有責(zé)任感的兒女應(yīng)為身患重病的父母放棄一切,因此在大學(xué)畢業(yè)后選擇留在家鄉(xiāng)照顧母親。數(shù)十年照顧脾氣極差的母親與最后放任母親病情惡化的經(jīng)歷,既導(dǎo)致麥迪無法擁有自己的人生,也造成她在其母去世后仍舊活在陰影中,難以尋到屬于自己的道路。她始終為親戚們的流言與內(nèi)心的羞愧所折磨。
亨利·列斐伏爾曾指出,日常生活的整體化特性促使每項(xiàng)人類活動(dòng),在形成確定的社會(huì)實(shí)踐形式后,都必須轉(zhuǎn)化為普遍適用的模式。而且,他人或日常生活的影響、侵入,并非強(qiáng)行或一次性的,而是不間斷的、溫和的,假以普遍和正義之名。正如親人們用家人身份和責(zé)任勸誡麥迪,小鎮(zhèn)上的人以風(fēng)俗規(guī)勸她。接受過大學(xué)教育的她曾用現(xiàn)代精神病學(xué)反駁過姨媽們的傳統(tǒng)觀念,但其潛意識(shí)又顯然認(rèn)可或無力反駁陳舊思想。概言之,他人的認(rèn)可、更好的共同存在、日常生活的整體性促使各種傳統(tǒng)觀念、禮儀風(fēng)俗與道德責(zé)任像蛛網(wǎng)一般,纏繞著人,浸入人的意識(shí),壓制與摧毀本真的嘗試與存在。《辦公室》中的“我”是一個(gè)家庭婦女,也是位作家。相對(duì)于男人可以將工作帶回家中,在屋子中專門布置一個(gè)空間滿足他的工作需要,且不指望他來接電話、尋找東西、看護(hù)孩子,女人則在家中必須忙于照看孩子、烹飪食物等,也不可有專屬自己的獨(dú)立空間:
想想吧,要是一個(gè)媽媽關(guān)上了房門,而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她就在門后頭。為什么孩子們都會(huì)覺得這樣對(duì)待他們太粗暴?一個(gè)女人,坐在那里,看著空氣,看著一片鄉(xiāng)村的田野,但她的丈夫并不在這片田野中,她的孩子也不在,人們就會(huì)覺得這是違反人類天性的。所以,房子對(duì)女人的意義和男人不一樣。她不是走進(jìn)屋子,使用屋子,然后又走出屋子的那個(gè)人。她自己就是這房子本身,絕無分離的可能性。
為此,“我”提出需要一間單獨(dú)辦公室的想法,但丈夫只表露出冷淡默許,孩子們則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懷疑與漠不關(guān)心。而在“我”滿懷期待并租下一間充滿男性氣息的辦公室后,房東卻反復(fù)質(zhì)詢、防備與多次試探“我”這位女性租客的動(dòng)機(jī),使“我”不堪其擾。房東始終認(rèn)為“這可不是一個(gè)正常人的表現(xiàn)。要是沒什么要躲躲藏藏的話,用不著這樣。更別說一個(gè)年輕女人,說自己有丈夫有孩子,卻跑得遠(yuǎn)遠(yuǎn)的,把自己的時(shí)間花在咔嗒咔嗒的打字上”。最后,“我”不得不搬離向往的“辦公室”。在日常生活中,“文化不允許女人承認(rèn)和滿足她們對(duì)成長(zhǎng)和實(shí)現(xiàn)自己作為人的潛能的基本需要”(貝蒂·弗里丹《女性的困惑》),文化不留痕跡地建構(gòu)、調(diào)節(jié)和控制著公共話語(yǔ)體系。即使女性能夠在處理日常瑣事之余走出家庭,她們依然難以在社會(huì)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中獲得平等的對(duì)待。脫離男性支持和肯定的女性自我建構(gòu)往往只是空中樓閣,難以實(shí)現(xiàn)。“婦女這個(gè)術(shù)語(yǔ)似乎暗示了一種異化……這個(gè)異化壓制了婦女,阻礙了她們實(shí)現(xiàn)她們自己,把她們置于從屬地位,降低她們的身份,把她們與真正的她們分割開來,把她們與男性對(duì)立起來。這個(gè)異化是什么?這種異化的力量是愛,或母親,或日常生活中的家務(wù)事?”(亨利·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
《男孩與女孩》揭示了女性如何因種種細(xì)微的觀點(diǎn)、責(zé)任以及社會(huì)的默認(rèn)態(tài)度而受到區(qū)別對(duì)待和束縛。在家里,作為一個(gè)女孩的“我”要為父親送水、除草與堆雜草,為母親剝桃子皮、切洋蔥,做著沒完沒了的活兒,但仍得不到父母的認(rèn)可。而弟弟只需玩耍,從不承擔(dān)任何家務(wù)。推銷員也只說“我”是個(gè)小姑娘罷了。而來家中小住的同為女性的奶奶也只會(huì)對(duì)“我”提出各種苛刻的束縛人自由與天性的舉止要求,以普遍化的慣習(xí)規(guī)訓(xùn)“我”成為社會(huì)認(rèn)可的好女孩。“慣習(xí)構(gòu)建了一種社會(huì)化的主體性,既是身份的標(biāo)志,也是區(qū)隔和禁錮自我的囹圄,它就這樣悄然無聲地融入了日常生活中,具有超強(qiáng)的穩(wěn)定性與自我生產(chǎn)性。”(周怡《艾麗絲·門羅:其人·其作·其思》)“我”終于發(fā)覺:
女孩這個(gè)詞,原本對(duì)我來說是無害的,沒有什么負(fù)擔(dān),和孩子差不多,現(xiàn)在看來,根本不是這么回事兒。女孩并非我當(dāng)初所想象的,不過是我的身份而已,而是我不得不變成的一個(gè)角色。它是一個(gè)定義,總是與強(qiáng)調(diào)、責(zé)備以及失望聯(lián)系在一起。它對(duì)我來說,還是一個(gè)笑話。
日常生活的慣習(xí)和風(fēng)俗筑籬限定了女孩的自我成長(zhǎng),“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是傳統(tǒng)的習(xí)俗和男權(quán)社會(huì)的需要造就了女人”(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其中,他者的話語(yǔ)與他者所施加的力量是不可分離的。就如“女孩”這一詞環(huán)伺著“我”,界定著“我”的身份,將“我”與弱者、文靜、缺陷緊密關(guān)聯(lián),立于弟弟對(duì)面。為此,艾麗絲·門羅也堅(jiān)持認(rèn)為本真在生活世界的環(huán)伺中不乏一種拒絕的嘗試或決然的舉動(dòng)。《辦公室》中的“我”疲于家庭瑣事外出,尋找屬于自己的辦公室。海倫深知“媽媽”這個(gè)詞能夠動(dòng)搖她完整身份與狂妄青春期經(jīng)歷所構(gòu)筑的自我認(rèn)知,這種微妙而有力的沖擊讓她擔(dān)心自己的本真會(huì)被侵蝕,因此,她選擇不參加母親的葬禮。《男孩與女孩》中的“我”在父親槍殺老馬弗洛拉時(shí),用放走老馬的舉動(dòng)第一次反叛父親的決定。老馬最終逃跑失敗,被捕槍殺,盡管“女孩”這個(gè)“天生的性別劣勢(shì)”讓“我”輕易地得到父親的赦免,但也讓“我”在權(quán)威的寬恕中不自覺掩蓋本真,調(diào)整了成為“女孩”的鏡像自我。是以,艾麗絲·門羅的故事揭示了日常生活中現(xiàn)代主體性所面臨的危機(jī),描繪了處于壓迫之下的人們強(qiáng)烈的本真追求與潛在的存在無意義感,以及這兩者與現(xiàn)代社會(huì)文明之間緊張的關(guān)系。
三、本真在生活世界的淡化與融入
人們?cè)诿鎸?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時(shí)只有堅(jiān)決反抗與妥協(xié)放棄這兩條道路嗎?艾麗絲·門羅顯然不這樣認(rèn)為,她發(fā)現(xiàn)不少人與《逃離》中的卡拉相似,先是決定逃離,再付諸行動(dòng),但最終又回歸了家庭。卡拉的舉動(dòng)既失敗又成功,既妥協(xié)又有抵抗,而本真思想也在她的日常生活中淡化但又融入,這也構(gòu)成艾麗絲·門羅的第三條道路。“門羅要求我們思考幸福,同時(shí)拒絕讓我們對(duì)個(gè)人生活中哪種組織原則更可取做出堅(jiān)定的判斷。”(卡羅爾·L·貝蘭《艾麗絲的幸福追求研究》)艾麗絲·門羅認(rèn)識(shí)到人逃離一種日常生活,又終歸要回到另一個(gè)生活世界,還要在其中吃喝、工作、交往,應(yīng)對(duì)新的風(fēng)俗、禮儀與道德,甚而為貧窮、物質(zhì)或拜金主義所困的人只是不停地工作,活著即是他們的生活,為一種必然性所束縛。日常生活的瑣碎也常常耗盡人們的精力、時(shí)間、需求、欲望與自我追尋。鮮少有如《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包法利夫人》中的愛瑪一般,有著充足的金錢、時(shí)間與可能,全身心地探尋獨(dú)立、理想的生活。
作為家庭婦女的卡拉明顯不具備這些,尤其是她已然從原生家庭中叛離出來,只是為了與現(xiàn)在丈夫結(jié)合。所以,她在第二次逃離后又回到無聊壓抑的家庭,意識(shí)到日常生活的強(qiáng)大與人的無力,安娜、娜拉、愛瑪?shù)热说膽騽』e動(dòng)畢竟罕見,死亡更不是普通人可以承擔(dān)的。事實(shí)上,一般的堅(jiān)決逃離都必須忍受失敗、被人指責(zé)的風(fēng)險(xiǎn),承擔(dān)獨(dú)自應(yīng)付一切的責(zé)任,承受不顧一切的心理重負(fù)與危險(xiǎn),而且極有可能從一個(gè)失敗的婚姻跳入另一個(gè)失敗的婚姻,用一個(gè)破碎的身份換取另一個(gè)破碎的身份。卡拉對(duì)原生家庭的叛離既未給她帶來幸福,也未能給予她獨(dú)立與本真,倒是遭到丈夫的輕視,也沒被丈夫視作一個(gè)完整的人。前一次逃離的失敗,也會(huì)誘使卡拉在潛意識(shí)中懷疑與否定自己,加重逃離的恐懼,驅(qū)使她將就著接受現(xiàn)實(shí)。卡拉的逃離失敗也是普通人不可承擔(dān)這一切的表征。為此,許多人是在“模糊狀態(tài)下生活。只要問題沒有立即顯露,或者只是預(yù)備提出這些問題,人們可以忽視那些問題”(亨利·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
但卡拉在回歸后,也感到“對(duì)于埋在心里的那個(gè)刺痛她已經(jīng)能夠習(xí)慣了。現(xiàn)在再也不是劇痛了—事實(shí)上,再也不讓她感到驚異了”。最終,卡拉經(jīng)歷一段重復(fù)、多步驟的過程,在這個(gè)過程中,卡拉嘗試了一種男性化的對(duì)自由的自主追求,但失敗了;被提供了一種女性化的善意選擇支持,但遭到拒絕;并最終期待一種含混的未來的到來。面對(duì)家庭和社會(huì)持續(xù)的平行壓力,女性無法像傳統(tǒng)男性那樣輕易擺脫,然而正是因?yàn)橐淮闻央x帶來的情感宣泄,也因?yàn)樘与x使她可以與日常生活達(dá)成和解。所以即便失敗,逃離仍舊具有重要價(jià)值,回歸也不應(yīng)該被理解為一種失敗,或者可以被理解為菲歐娜·托蘭所比擬的“英雄開始了一次遠(yuǎn)征并凱旋的敘事模式”(《離開與回歸:艾麗絲·門羅〈逃離〉中的沮喪離別與女性探索》)。它是一個(gè)出口,使人物可以在無法承受時(shí)暫時(shí)躲避,也是一個(gè)本真期盼,可以從這遙望、探尋與感受本真。至少她在那一刻,靈魂是自由的。簡(jiǎn)言之,這短暫的休憩與自由,滿足了人物的自我之需,又使之可以容忍與勇敢繼續(xù)日常生活。在這一點(diǎn)上,同樣符合海勒的觀察:“許多女性的人生追求都有一個(gè)相仿的特征,那就是一次受挫或不可能的旅程,一種對(duì)限制的猛然覺醒以及與社會(huì)對(duì)女性鈍性和固化的期望的和解。”(海勒,達(dá)娜·A:《探索浪漫的女性化:激進(jìn)的背離》)
在《沃克兄弟的放牛娃》中,艾麗絲·門羅書寫了一位父親的精神的短暫出逃。作者先用極多筆墨敘述出一個(gè)溫馨的四口之家:父親幽默風(fēng)趣,給孩子們講著故事,逗妻子開心并努力掙錢;母親精心裝扮與布置著房子;孩子們嬉笑玩樂著。但這看似溫馨的家庭因?yàn)槠飘a(chǎn)而面臨種種危機(jī)。母親不舍破產(chǎn)前的體面生活,而依然精心打扮自己與女兒,追求精致的生活。父親則成為推銷員,不得不放下尊嚴(yán)取悅別人,甚至當(dāng)著子女的面被潑尿卻仍要坦然應(yīng)對(duì)。困頓與喪失體面的父親只有在與“前任”諾拉的交流中恢復(fù)他的神采,兩人分離之后,女兒“感覺到爸爸的生命從車?yán)镲w了回去”。父親與諾拉之前因?yàn)樽诮绦叛龆珠_,如今的他們相遇但并無逾矩之舉,父親看望諾拉也不是為了生理的原因或出軌的歡娛,而是為了短暫地從操勞和失卻自我的窘境中脫離出來,在昔日的愛戀與溫情中獲得暫時(shí)的自由和愉悅。而作者選擇年幼的女兒作為父親情感出軌的觀察者,顯然是對(duì)父親的“逃離”不加以批判,而是視之為一種平常的生活狀態(tài)。作者在故事的最初提到休倫湖的長(zhǎng)久存在,在故事的最后再次提到休倫湖的永存,表明壯闊深沉的日常生活可以包容偶爾的精神出逃。艾麗絲·門羅后期的作品《多莉》也表達(dá)出相仿的觀念。83歲的詩(shī)人富蘭克林與71歲的教師“我”原本過著和諧平靜的生活,這一生活由于富蘭克林年輕時(shí)的戀人多莉的突然出現(xiàn)而被打破。富蘭克林和多莉是因?yàn)閼?zhàn)爭(zhēng)而分開,但富蘭克林在婚后仍舊迷戀多莉,時(shí)常為她寫詩(shī)。他們兩人在意外相逢后分外歡喜,一起準(zhǔn)備早餐,一起出門修理汽車,一起歡聲笑語(yǔ)。作品中饒有趣味的是“我”的感受變化,“我”起初對(duì)他們的行動(dòng)很是不滿,決定出門散心,其后又反省起自己年輕時(shí)的偷情舉動(dòng),對(duì)當(dāng)年偷情的男方妻子產(chǎn)生愧疚感,最后又回至家中與丈夫和好如初,撕毀要與丈夫分離的信件。《多莉》以婚姻和日常生活的模糊性消解了相逢和偷情的不道德,也以這些不道德的舉止為他們保留一定的自由空間。肩負(fù)著家庭的責(zé)任、承擔(dān)撫養(yǎng)孩子的義務(wù)、遵循道德禮俗并與個(gè)人生活需求相調(diào)和,人們往往順應(yīng)日常生活的節(jié)奏,勇敢地履行各自的責(zé)任。然而,作為具有自我意識(shí)的個(gè)體,他們內(nèi)心深處卻懷揣著對(duì)自由的強(qiáng)烈渴望,期盼能真正活出自我,體驗(yàn)無拘無束的人生狀態(tài)。在日常與本真之間的背離中,短暫的逃離便成為重要的緩沖劑,滿足本真之需又不讓人完全拋棄對(duì)日常的承受,使本真與日常的矛盾得以緩解。艾麗絲·門羅堅(jiān)持嘗試探索這種日常生活中短暫的自由和幸福的必要性,即使它看起來暗藏危機(jī)或終將失敗。“但是在這種逃離中,甚至是受挫的探索,都充滿了它的力量,這是一種有限但重要的能力,用以支撐向往未來旅程的勇氣。”(菲歐娜·托蘭《離開與回歸:艾麗絲·門羅〈逃離〉中的沮喪離別與女性探索》)
艾麗絲·門羅以細(xì)致入微的筆觸,描繪了身邊再尋常不過的小鎮(zhèn)日常生活,展現(xiàn)了小鎮(zhèn)中男人與女人、父母與子女、鄰里之間復(fù)雜而又微妙的關(guān)系,以及相關(guān)的風(fēng)俗道德與常識(shí)。她通過對(duì)日常生活經(jīng)驗(yàn)的細(xì)微記錄,試圖化解生活矛盾和精神束縛,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深化了對(duì)主體性本質(zhì)的認(rèn)識(shí)。“她筆下的人物(希望也是她的讀者)沒有在日常社會(huì)習(xí)俗、憂郁或恐懼中尋求庇護(hù),而是發(fā)現(xiàn)自己在思考人類創(chuàng)造性的生存本質(zhì),盡管存在種種困難。”(安德魯·希斯科克《“渴望人類氣候”:艾麗絲·門羅的〈我年輕時(shí)的朋友〉和失落的文化》)本真與日常之間的關(guān)系構(gòu)成艾麗絲·門羅小說的內(nèi)核。她也通過眾多小說人物及其命運(yùn),展現(xiàn)了三種關(guān)系及三條出路,每一種都至關(guān)重要,都隱含著一種挑戰(zhàn)以及必須承擔(dān)的命運(yùn)責(zé)任。但從她對(duì)小鎮(zhèn)及其生活不厭其煩的描繪來看,她更傾向于第三種關(guān)系與出路:既與日常生活保持矛盾與抵制,又能在短暫的逃離后與之達(dá)成和解。在漫長(zhǎng)且廣闊的日常生活中,她筆下的人物保持著平凡與隱忍,同時(shí)又不忘時(shí)時(shí)懷有自我期盼,并在關(guān)鍵時(shí)刻偶爾堅(jiān)持自我的人生道路。這雖然和流行文化及過往眾多文學(xué)作品中的結(jié)局存在差異,卻展現(xiàn)出獨(dú)特的轉(zhuǎn)折。
從克爾凱郭爾、尼采、海德格爾與薩特等人的激進(jìn)思想來看,艾麗絲·門羅的本真觀點(diǎn)無疑不夠正確或偏于保守。但對(duì)于大多數(shù)像艾麗絲·門羅筆下的一般活在生活世界中,也長(zhǎng)久被日常環(huán)繞的平凡人來說,艾麗絲·門羅的本真思想?yún)s有更為實(shí)際的意義,而且對(duì)日常與本真關(guān)系的研討,也具有啟迪作用。在漫長(zhǎng)的歲月中,即便是短暫逃離日常生活的瞬間所帶來的幸福感,也足以喚醒我們內(nèi)心深處強(qiáng)烈的“為自己而活”的情感。這種情感激勵(lì)我們?cè)诮舆B不斷的生活挑戰(zhàn)和沖突中不斷地更新世界和自我,從而過上更加有意義的生活。
本文系湖南理工學(xué)院研究生科研創(chuàng)新項(xiàng)目“門羅作品中本真與日常關(guān)系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YCX2023A14)的研究成果;2023年湖南省社科基金項(xiàng)目“國(guó)內(nèi)存在主義文學(xué)學(xué)術(shù)史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23JD041)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