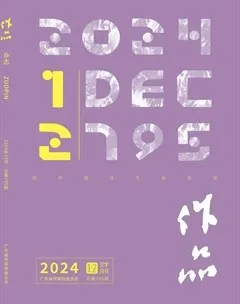虛浮的概念
在翻閱完廣奈的這幾篇小說之后,我立即找了后續的幾期關于廣奈小說的評論文章。讀到那篇《用廣奈體小說回贈廣奈》時,我會心一笑。先澄清一下,評論中將這種寫作手法歸于“碎片式”敘事手法,不太嚴謹。“碎片式”寫作手法的核心,是將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切成碎片后,用增加探索成本的空間障礙打亂敘事的時間線。這是一種在探索解密游戲中非常普遍的敘事技巧。在另一篇評論文章中,作者本身是個電子游戲愛好者,他強調廣奈小說中的“致幻性”,對于這種小說風格的接受度就比另外兩位要高得多。
其實這種“致幻性”小說,我最初是在二十年前抽屜寫的《比愛更喧囂》里接觸到的,那是在青春文學最繁榮的時期;緊隨而來的網絡文學發展初期,也有像冥靈這樣的作家在奇幻作品里選擇這種風格。總體來說,與很多人面對這樣的文字還頗感新鮮不同,我卻覺得這樣的風格讓人頗有懷念之味。
但真要說起來,廣奈的文字比起上個“世代”的作家,更有些當下的風味。當今的國內網絡游戲世界構成中,廣泛而普遍地使用這種寫作手法——將通俗的東西用讀者(絕大概率)覺得陌生的詞匯替代,構造一種新的“概念”。為什么是新的概念而不是替換的概念呢?因為這樣的替換是非原物的。這樣的替換手法在早期的奇幻文學里其實還不顯,因為奇幻文學抓住的是神話與歷史文學的延長線。這樣災難性替換的開端更多地體現在“科幻”題材里。因為科學詞匯天生就具有精英化的性質,最方便地適用于營造陌生感的條件。(順帶一提,當今短視頻信息流推廣中,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這種“陌生”感取得聽眾的信任。)在“泛科幻”題材作品里,扭曲科學定義下的某物概念成為普遍現象。當“光錐”“原石”“坍塌”這樣的詞匯,被包裹在精心包裝的所謂“世界觀”中,作者賦予它們新的定義后,它們原本科學上的定義將不復存在。這是我讀到廣奈的《彈射》,看到里面不嚴謹地利用曲線、線段、質量、坍塌等數學與物理學概念之后想到的,大概嚴謹了之后,它可能會是一篇科幻小說。
而說到廣奈的《我們如此熱愛飛躍》與《“石頭剪刀布”虛構史》的時候,我不禁要感慨,“誰家的游戲文案把設定稿搬出來了”。這大概更能體現我上文說的“當下的風味”——文章在用編史的手法構造世界的風貌、構造游戲的規則(當然這其中包含我上文提到的大量的替代式新概念)。這樣的敘事是絕對性濃縮的,而不是展開的。它在行文中必定抹去了世俗的情緒和傳統敘事——我從不掩飾自己對這些“老掉牙”東西的偏愛,但是也不愛看到它們是這一切浮華概念包裹的世界之內展露的本核。但是精雕玉琢的場景建模終歸只能提供有限的場景敘事,作為主角的玩家如果不踏進來,一切意義都不復存在。
所以在我看到《恐龍拼圖》的時候,我以為終于要有一些值得撫慰閱讀情緒的“老掉牙”的東西的時候,文章卻在回憶錄式樣的時間線(Timeline)里又重走了“概念化”的老路。在文章中,“他”的消亡與恐龍的復活是必然的,在敘事上,“他”的消亡與“概念”的浮起也是必然。或許要說,“他”在整個過程中經歷了坎坷、困境,也是有血有肉的。但是很可惜,恐龍與拼裝的“概念”奪舍了“他”的生命力,在文本之內與文本之外。
說了那么多,其實我沒有那么大的惡意,我只是覺得,在面對這樣的文字的時候,“小說”這一概念無法完全地包容它。它毫無疑問是文學創作,但是當以“小說”的概念去看待,這顯得有些奇怪。當下的文學作品追求一種新意的時候,最激進的保守派也無非像我這樣將它們作為點裝天空的氣球,它浮于空中之美,用近乎密碼的含蓄文字包含著一段等待發掘的“黑幕”。然而當它作為主菜被端上桌時,與當今很多網絡游戲敘事選擇的一樣,“概念”奪舍了全部,吸引了眼球,人們在賦予詞匯以新的意義中狂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