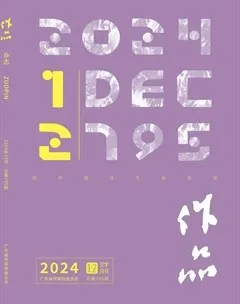時間的幻術
《時間的形態》有一個簡單的人物結構:消失的父親以及作為敘事者的“我”。父親在一個夏日突然消失,“我”從此以后都在尋找父親的蹤影。在尋找的路上,我創造出“想象·回歸論”,并因此邂逅了各色人物,也經歷了是否仍然通過想象等待父親回歸的疑問。小說結尾,“我”最終超越時間的限制,在沿著河邊觀看父親曾經看過的風景的同時,在想象中與父親相遇。《時間的形態》的核心議題是時間問題。廣奈將時間置于書名之中,作為小說一條牽引人物與事件的主線。事實上,從小說開端父親在普萊塞河畔消失的那個夏日開始,時間將小說中的敘述者“我”(萊昂納德)和消失的父親、失眠的女人、丟失小貓的婦人、失去記憶的男人引入回憶洪流之中。在小說中,主人公“我”萊昂納德只是投影的幕布,時間才是小說真正的主人公,不同的時間在小說中像一個個容器,在對記憶的追溯中流露出作者對于情感的篤定。
在小說中,“我”的敘述首先具有一種時間上的線性——但不止一條線,也不一定是連續不斷的線,而是線條的結束。它既是父親消失后“我”獨自守候在小屋內,翻閱逝者的故事,構想出前所未有的追蹤方式;也是“我”給小狗萊昂納德講述的愛情故事,“我”與夢中的戀人相互交換對戒;更是“我”潛入水底拿出藍寶石戒指后,重回年少時光,父親對于我無微不至的叮囑……“我”所擁有的時間,大多是模糊的、前后跳躍和交叉的時間,那些時間更多的與某個事物緊密相連,例如對父親的記憶發生在小屋布滿灰塵的家具上,夢中對白裙女人的愛戀與藍寶石戒指相連,衰老時期和小狗的緣分與人名萊昂納德相連……這也使得小說中的時間,實際上往往是過去經驗的證明,它蘊含著某種推動萬物發生變化的力量。
正如在小說中,時間推動“我”日復一日等待父親歸來,但同時它也使得我創造出“想象·回歸論”,最終成為萊比錫城最忠實也最鍥而不舍的追尋者。時間見證了“我”與父親的相互陪伴,見證了“我”如何運用“想象·回歸論”幫助他人找尋回遺失的事物。包括在“我”敘述的最后一次找尋中,忘卻姓名的“我”見到了尋找死去愛人的白裙女人,她被回憶折磨得幾近癡狂,但在我的勸說下,她最終放棄了尋找萊昂納德的舉動,并將那枚象征著感情的藍寶石戒指投擲進河流之中。這是小說中的隱藏情節,即在時間中,所有人都無可避免地成長、衰老,乃至最終死亡。人生命的終結固然是一個厄運的開始,但讓消失的事物從此消失,或許便是最好的選擇。因為消失自有它本身的目的,這也是生命的應有之義。
此外,廣奈從特定空間、場景中看出時間的能力,近于巴赫金所說的“時空體”。父親離開后,偏僻小屋中放在工具盒里涂滿潤滑油的釘子、頂部積灰的電視機、墻上早已過期的掛歷以及破舊的榔頭昭示著“我”獨自一人的處境。當廣奈從塵封的舊物中看出時間流動致使“我”淪落于無聲的煎熬中時,他無疑是敏銳的,甚至是深刻的。那種黯淡壓抑的時間經驗,與偏僻小屋作為回憶之所的空間屬性,本有可能結成富有意味的時空體。但廣奈似乎決意要舍棄浮露在外的細枝末節,而直抵生存狀態的內在真實。小說中的“空間”書寫在小說后半段往往被廣奈有意弱化,其“時間”書寫則趨于具象化。正如小說結尾“我”與過去的自己在河邊相遇,不同年齡階段的、不同版本的自我于此合二為一,這使得時間就此掙脫束縛,從而呈現為柏格森意義上的無盡“綿延”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