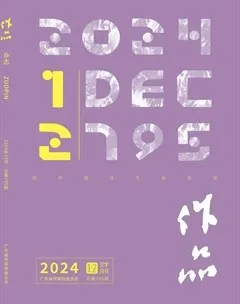卡珊德拉的預言(外一篇)
南瓜燈博士就是南瓜燈先生。
美國作家查理德耶茨的短篇小說集《十一種孤獨》里面的小說《南瓜燈博士》,主人公是一個從鄉下去城里念書的性格孤僻的小男孩。
南羽很喜歡這個美國作家,他買了查理德耶茨的所有著作。當時他受困于二十多平方米的公租房,為了把《革命之路》也一齊買上,他花光了自己的生活費。大蔥拌豆腐,真是一窮二白了,甚至沒有想接下來的日子該怎么過。
呵,不就是一個月面條嗎?一個月后又是好漢。閱讀查理德耶茨就像和老朋友在一個寧靜的音樂酒吧相聚,聽著民謠《安河橋》,微醺恰好能夠袒露胸懷,說些后悔的事。
《安河橋》?是那個前奏一響狗都會流眼淚的《安河橋》?南羽打開網易云,很快找到了它,強烈的欲望迫使他又為自己的情緒投入了十幾塊錢。
真是鐵打的會員,流水的錢。為一首歌開個會員值不值得?
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時的沖動總是迫在眉睫。
話說回來,《安河橋》治好了他的失眠。戴上耳機,他可以在極度孤寂的聲音中聽到自己的回音,如同靈魂出竅一般,到了另外一個世界。擺脫了疲憊、麻木的軀體,在真空中生活,那里不存在病變。
南羽愛上民謠與他愛上查理德耶茨幾乎是同時的,藝術說到底都是殊途同歸。
南瓜燈先生起初是南羽的網名。由于他立志做一個出色的作家,因此成了他的筆名,筆名公開亮相是在一本著名的文學雜志上,內容是陽光大道上席地而睡的貨車司機。他每天下班回宿舍都經過陽光大道,其實那并不是陽光大道,那是工業大道,一條只有大貨車經過并且沒有路燈照亮的寬闊的瀝青路,周圍是一人高的蘆葦和不知名野草,月光鋒利,十分幽深而昏暗。
雨又來了。
他更加堅信一件事:不管科學多么發達,都無法征服自然。是的,科學無法預測天災。這場雨對他來說莫過于一場災難,他出門從不習慣帶什么東西,包括傘。
雨水很快占領了鄉賢文化公園以及那里的亭子和亭子里的棕褐色長凳。黑云壓城城欲摧,這不是不可能。雨下得南羽心情有些煩躁,他的心事太多了。
碰碰車攤主以為用繩子沿著路燈的分布把廣場中心區域圍起來就是他的天下了。的確,綠色顯眼的繩子為他的生意提供了固定的場所,其他人都繞道而行,仿佛廣場真的就是他的一樣。
南羽不樂意這樣的行為,因為廣場是所有來這里的人所有,他不應該圈起來。他不說話,在亭子里往鄉賢文化公園的牌坊望去,攤主正慌亂地把碰碰車推到牌坊下面。那是一條三層翹檐式牌坊,面向北位于永順路的一側,面對寬闊的永順路顯得極其狹窄。攤主獨自撐著傘,沒有離開一步,連一個和他打招呼的人都沒有。
南羽看過天氣預報,天氣預報說晴天會持續到下午四點鐘,四點鐘那一刻他正坐在一家咖啡館喝著咖啡,強烈的感官刺激讓他想到一塊水豆腐餿了,不可思議的是他放進了冰箱,中途他去參加了一次約會,便忘了吃。
一塊餿了的水豆腐。它足夠堅強了,持續三四天持續被人忘記,拿出來的時候浸泡豆腐的水體變得有些渾濁,隱隱發綠。咖啡異常苦澀,直到舌根才有了一些甘甜。太陽照耀在重疊的云層上閃閃發亮,此刻云層低得出奇,正緩慢地朝著咖啡館移動,南羽坐在四樓,從落地窗中能窺視到城市和在這里翱翔的鳥兒。
砰砰砰……撞死一兩只后,鳥兒們在落地窗前不知所措地用翅膀拍著,它們想撲進來。并沒有什么誘惑性因素,它們單純地想進來。這里有什么好?
全是無事可做,消遣時間的客人。南羽有時候也想讓它們進來吧,風餐露宿不完全都是好的,但是他無能為力。
今天篤定不會下雨了,除非勃南大森林會移動。
他為了讓少有的閑暇時間更有興致,決定起身出去散步。沿著圭江走,河堤多樹木,疏影錯落有致。偶爾涼風帶來快意,他把這種不確定看作是一種反叛,和突如其來的暴雨別無二致,說不上來其他的。
南羽想一直走下去,如果不出意外的話,直到夜幕降臨,圭江北上的盡頭會多一個男人的背影。
天變比翻書還快。云層疊得越走越厚,遮住了太陽,愁云慘淡,雨就嘩啦啦下了。南羽腦子里還是那片勃南大森林,《麥克白》中的橋段已在他腦子里消失殆盡,怎么也回憶不起來。
女巫為麥克白提供了三次預言,因此麥克白殺了國王鄧肯、班柯,女巫還告訴麥克白永遠不會被打敗,除非有一天樹林向高山移動。
那么森林移動了嗎?
麥克白要殺的還有麥克德夫。王子馬爾康最后回來了,麥克德夫也在其中。森林怎么會移動?王子馬爾康帶領軍隊砍下整片森林作為掩護,草木皆兵是嗎?
他已經來不及思考更多了。他開始往回跑,并在途中掃了輛共享單車,到達了鄉賢文化公園的亭子。到達公園前,雨不是最大的時候。雨滴在他白色長袖襯衣上劃過長長一段,沿著布料的紋理發散開,并沒有濕透,反倒像長滿了羽毛。
他感受到雨滴的溫度,這個溫度正好,吹一吹就干了。
那次約會壞掉了一塊豆腐。南羽本想做芥菜豆腐蛤蜊湯,一定要放白胡椒和姜絲。
至于那次約會,沒什么特別。南羽在一處網咖度過了整個晚上。其實他早就知道鑰匙會掉,準時赴約讓他感到有些緊張和壓力,本該擁有一次愉悅的心情。
他有輕度的強迫癥,每次強迫癥犯的時候總會帶著一些疏漏。他站起來抖了抖襯衣,用手按住不停跳動的左眼皮。
回想起來,他總埋怨左眼皮在那天跳了一整天。但是他無能為力。
在九月見面
終于他們又見面了,南羽和他的女朋友語鶯,在北流步行街的一家餐廳。
北流步行街是北流最熱鬧的商業街之一。維多利亞時代的仿古路燈和門店燈牌把夜空點飾得恰如其分,黑鐵的燈座和精致的雕刻讓這個夜晚分外典雅。
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他們開口說話。
浪漫永不落幕。
許個愿吧。語鶯虔誠地雙手合十,緊閉雙眼。睫毛的影子照映在墻上,纖長、卷翹,墻上是一幅壁畫,綠色的青蛙。
干杯!
干杯!
在語鶯的生日晚餐過后,南羽決心在這里住上一陣子,他回絕了一些遠在幾百公里外的工作。如果遇到輾轉反側的失眠夜簡直一點辦法都沒有。
別在晚上做決定。
為什么?
晚上只適合做夢。
晚上只適合見你。
但愿吧。
他們心不在焉地笑了。共處對于剛結束異地戀的情侶來講是多么難得。不過世事難料,就像語鶯畢業就到了北流,而南羽花了兩年。如果在生活中事事都如人所愿,又有什么深刻呢?
南羽比語鶯高兩屆,南羽大四,語鶯大二。一定是上天給他的恩賜,他很慶幸。年輕人們把校服被婚紗代替看作是一種幸福的儀式,相當神圣的儀式。
可是一紙憑證從來不是那么輕飄飄的,結婚也不像婚紗的裙角隨風飄搖。不管怎么說,付諸行動比承諾更重要。
他一時間辭掉了兩份工作,一份是在一家國有企業做文字秘書,一份是高中教師。
南羽收拾好行李,上了火車,黑色行李箱容量太小,除了一些衣物和日常用品外,再也裝不下一點東西。分期付款的空調和熱水器還不完全屬于他自己,在宿舍頂樓只有源于九月的溫熱是完全屬于他,且不由他選擇。
上了火車。出發前,別意喚醒了他對使用多年的行李箱的愛意,因此他買了新的行李箱提手進行更換,黑色的噴漆足夠讓一個生命重煥生機。
那是夏天余熱蔓延的九月,人們稱它為“秋老虎”,一只充滿野性的猛虎是多么貼切、生動。
四百多公里后,他進入了玉林地界。各地的文旅宣傳工作做得很詳細也很及時,短信送達手機時發出陣陣振動,他的心跳也是如此。
他鼻子尖兒酸酸的,但僅僅是鼻子尖兒。終于與語鶯又見面了。
此后的一年里,他還在忙于考試的時候,總有許多人替他惋惜,比如提前到來的雨季。
沒什么后悔的,人總要有些缺憾才算完美。他大學沒掛過科,年輕時也沒有做過什么出格的事,他曾經以為那是最好的結局,可結果恰恰相反。他畢業兩年后回到北流時,才意識到這一點,其間并不是一切順利。
缺憾和完美是個永恒的辯證命題,永遠無法談到一塊去。就像愛與被愛,很多時候不能畫等號。等號不適用這個世界,南羽用絕對來形容它,沒有一件絕對的事。
所以他接受了一切缺憾。
步行街的石板路沒有想象中的平坦,電車駛過它會發出清脆的砰砰聲。
就像世界上沒有一處沒有一點瑕疵的街道一樣。他對語鶯說。
他說的話語鶯也許沒聽進去,但是墻上的影子記錄下來了。南羽與這家店逐漸熟悉起來,只要一有時間他就會帶著語鶯來到這里。
這家店主要是賣蛙的,是煮熟的蛙,當然還有其他的許多美食,酸辣小皮蛋、去骨雞爪和爽口魚皮。兩人餐一次一百五十八,要比桂林貴得多,不然怎么說各有各的不同呢?
我還是第一次來這里。
吃過蛙嗎?
沒有。這是第一次,說實話我還沒做好準備。
這里的紫蘇蛙最好吃。
真好吃。
南羽愛上吃蛙了,就在這家店。
什么時候開張的?
不清楚,我沒在這里吃過。
看樣子有幾年了,我為什么沒發現?
現在的店面都特別注重形象,隨時都在更新,很難看得出來它的年齡。
那倒是。
我真決定在這里住下來了。
別在晚上做決定。
我說真的,以這杯酒為證。他倒滿滿一杯啤酒,一飲而盡。
你嘴角漏了一滴。語鶯說。
沒關系,再來一杯。他果然再來了一杯,一滴不漏地喝下了。
你不是不喜歡喝酒嗎?
現在我心里有棵火苗,一不小心就會蔓延成火災。
與他工作時完全不同,他和你說過他不喜歡喝酒。
所以需要澆滅嗎?呵呵。好了,沒問題,如果你能找到安穩的工作的話。
南羽頓時有些語塞。他咽了咽口水。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他們就這樣度過了一次美好的晚宴。當晚他們去了銀行附近的一家酒店,因為還不滿足住在一起的條件,他們還沒有住處,除了自己的家。
那時語鶯剛畢業不久便到北流的一家銀行上班,她打算搬進職工宿舍。但是今晚還不行。職工宿舍是一棟老樓,它為銀行服役了近三十年。原來沒有生命的樓房也會衰老,這就對了,一切都有使用周期,只不過它缺少一張說明書和在墻體噴上保質期限。
確實夠亂的。墻體光滑的石膏偶爾脫落一塊,老式綠色防盜門開關時稍微用力就會哐哐響,屋子里堆滿了雜物,灰塵覆蓋厚厚一層,蜘蛛網見證了這里的冷熱。
南羽時常看見壁虎。語鶯說壁虎是益蟲,它會吃蚊子和水蟻。
下雨前夕你就知道了。她說,成群的水蟻在窗外聚集,它們會想方設法從窗戶的縫隙中鉆進來。
飛蛾撲火,你見過嗎?
見過。
那沒什么說的,一樣的原理。
晚餐過后,他們還不想回家,往陵寧路的一頭走去。北流就像一個球,無論走哪條路都會走到家。
九月晴天居多,仿佛秋老虎治愈了所有眼淚。
責編:胡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