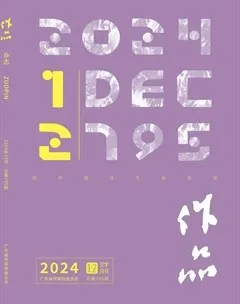阿拉爾(小小說)
阿拉爾,我初次遇見你,是躺在水底的淤泥,被你擺動尾鰭揚動的渾濁驚醒。你模糊的身影并不真切,也許你棲身在那晚悄悄游過的硬骨魚群之中。我期盼你再次出現,即使我無話可說。我被孤獨的水草包圍,終日凝望水面上方的光影變化,這顆星球最早的數學活動被我用來計算對你的思念。也許你又來過?我和我的同伴都在缺乏意象的夢中聆聽過似真似幻的低鳴。
夸張的時間,一條河遺忘了它曾經是海。當我被無數同類困在灘涂,我看見渾黑的你長出帶蹼的四肢,拖著濕滑的身軀爬過我,爬進了岸邊的草叢。你在我肌膚上留下很快被曬干的水跡,也在心中留下無法磨滅的印跡。阿拉爾,我還想見你,這大概是我以寂靜和寂寞的形式存在的意義。下一次,你會變成螺旋狀的菊石,還是覆滿甲殼的節肢動物?
我依然是我,只是河流漸漸干涸,草叢河泥的遺址中冒芽,星星點點的花朵在我朦朧的意識中留下不同溫度的印記,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這可以稱為“顏色”,可有些事情我又為何懂得更早?也許這般的等待,自我尚未意識或早已忘卻的遙遠世代就已開始了。阿拉爾,唯有你是我感知時間的活坐標,當我看見你長出茂密的淡黃色毛發、三角形的吻部,當我看見你叼著一只柔軟的灰色小動物穿過灌木,當我第二次向你遠去的山谷凝望,那里已長出了高大的森林,但最高的那棵樹也夠不著它們背后恍如浮于天際的高山。
阿拉爾,原來世界那么大,你又會在哪里呢?最溫柔的風也聽不懂我的請求。你在草叢和樹葉數百次、數千次由綠變黃,又由黃變綠的歲月變遷之中,也只是偶然途經并造成我的夢境的悸動。你有時是小鳥,有時是螳螂,有時只是踩住我,遮過我的一大團黑影,我看不清,但聞到獸類的氣味,是牛、羊還是老虎?你不會捕獲我,甚至不會注意我。某次,我從草叢間隙瞥見你是一朵紫色的小花,綻放在不遠處的山坡上。我很驚喜,因為能與你日夜相伴,卻又擔心坡頂那塊搖搖欲墜的巖石隨時會滾落下來。我恨不得像風那樣說話,像動物那樣行走、奔跑,就像燕子闖進春天那樣跑向你。但不記得何時的一場雷雨過后,你又離去了。
阿拉爾,有時多想哪怕有一片經游天地的云朵向我提起,你變成了一棵杉樹,我就至少可以再睡上很長一段時間。變成猴子也好,你也許就會比其他飛禽走獸更親近我些,或許也會傷害我。我情愿你傷害我,這樣你就會稍微記得我,哪怕只是從飛出到落地的剎那。不久之后,我看到一些比猴子更大的生物遠遠走過,隱約感覺不安。我很少做夢,但那天之后經常夢見光怪陸離的場景:發光的石頭山、沒有眼睛的螞蟻、翅膀龐大的白鸛……許多許多,你也在其中。阿拉爾,我從未如此害怕,我的夢成了現實,我看到你完全陌生的形象出現在那片長滿樹莓的灌木旁,你用兩只腳行走,用另外兩只腳摘果;你把獸皮裹在身上,披一頭棕黑色的長毛;你似乎無意中往我這邊望了一眼,在和煦的陽光下,我仿佛從你眼中窺見一個無限小,無限大的宇宙。我知道,我們的過去就藏在你的眼中,而你一定能使我想起。
我在你眼中,夢中,遙遠的異鄉。阿拉爾,當你注視我的剎那,我仿佛第一次也看到自己。我期待你走來,但你只是將樹莓都裝進兜里就離去了。不知過了多久,你又來摘樹莓,頭上的長毛卻白了,仿佛你的靈魂,你的上半身,也宛如一根積滿黃昏的枝條彎折下來。我想你拾起我。
你離開后,一場大雪將我淹沒。我在黑暗中失眠,想象再次與你重逢的場景。雪漸漸融去,地上躺著許許多多的大猴子。那年春天的溪水泛著淺淺的紅色。
阿拉爾,你終于變成了人,這顆星球上最孤獨的物種。只有人才會注視身邊與他們同樣孤獨的事物,阿拉爾,終于有一天,你會變成穿著漂亮衣服的小女孩,牽著爸爸媽媽的手來到這片亙古的野地游玩。你喜歡蝴蝶,喜歡鮮花,喜歡五顏六色的美好事物;你與忠誠乖巧的金毛犬在草地奔跑、追逐。我能聽見你清脆的笑聲、叫喊聲。阿拉爾,有時你離我很近,只要再往右走兩步你就會注意到,或者踩到我。阿拉爾,也許你依然沒有想起我們在廣闊無垠的宇宙中結伴而行的漫長歲月,但只要你發現我,注視我,將我捧在手心,就一定能想起你我宛如星辰的無窮往事,一定能將這場穿越亙古的捉迷藏視為眨眼間的游戲。
一定有某個瞬間,你無心中低頭一瞥,恰好與被草叢遮掩的我對視。阿拉爾,你認出我了嗎?你為何停住腳步,像凝視天上的星星那樣凝視我?阿拉爾,你聽不見你的父母正在遠處喊你嗎?你就這樣蹲下來,向我伸出手。我緊張地注視著你手指的尖端,不敢移開視線。阿拉爾,你就要觸碰到我了,只要再一寸,我們就能再度相認,再度朝著不復醒轉的來日飛去。阿拉爾,即便距上次離別已過去不知多少個紀元,我們也要重新開始,重新相愛。
一聲尖銳的骨哨——
當我從萬古未有的驚顫中回神,你已經不見了。
仍是在晴朗的春天,仍是在爛漫的野地,我周圍卻只剩下沉默。從這時起,我又不得不從第一天開始想念你。阿拉爾,你以萬物的姿態不斷途經我,卻總是錯過。阿拉爾,你知道嗎?直到你明天,下一個春天,或許是數百萬年后才能再度發現并觸碰我的時候——
我才不再是一顆永恒的石頭。
責編:胡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