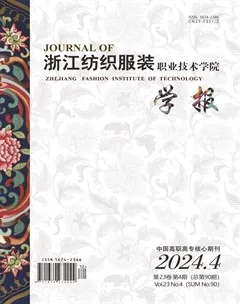技藝中視覺呈現:劍河苗族紅繡服飾“母花”數紗繡針法研究












摘 要:劍河苗族紅繡服飾紋樣的視覺呈現是隱性的“母花”數紗繡針法外顯的結果。“母花”是劍河苗族紅繡女性進行服飾紋樣裝飾時所使用的針法模仿范本,其針法有別于一般的針法,有著雙重的技藝呈現內容:一為“母花”本體的紋樣和針法;二為運用“母花”紋樣衍生出的服飾紋樣和針法。本文以田野調研為基礎,對劍河苗族紅繡服飾“母花”數紗繡針法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解讀,探討了紅繡服飾紋樣產生視覺差異的成因,總結出劍河苗族紅繡女性以運用和傳承“母花”紋樣為手段,在技藝的視覺呈現中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構和集體記憶的延續。
關鍵詞:劍河苗族;紅繡;母花紋樣;服飾紋樣;數紗繡針法
中圖分類號:TS935.1" " " " " " "文獻標志碼:A" " " " " " " 文章編號:1674-2346(2024)04-0001-09
Visual Presentation in Technique: A Study of \"MuHua\" Yarn-Counting
Embroidery Stitches of Jianhe Miao Red Embroidered Attire
CAO Hanjuan" " ZHOU Me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The visual presentation of Jianhe Miao red embroidered attire pattern is the explicit result of the hidden \"Muhua\" yarn counting embroidery stitch.The \"Muhua\" is a model for stitch imitation used by Jianhe Miao red embroidery women for the decoration of clothing patterns.Its stitch is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stitches and has two technical contents:one is the pattern and stitch of the \"Muhua\" itself and the other is the use of \"Muhua\" pattern derived from the clothing pattern and stitch.Based on field research,the article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Muhua\" embroidery needlework of Jianhe Miao red embroidery costumes,discusses the causes of visual differences in red embroidery costumes,and concludes that Jianhe Miao red embroidery women use and pass on the \"Muhua\" pattern as a means to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identity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visual presentation of their skills.
Key words: Jianhe Miao;red embroidery;Muhua;clothing patterns;yarn-counting embroidery stitch
貴州黔東南劍河苗族紅繡①服飾“母花”(Muhua)是當地苗族女性進行服飾紋樣裝飾時“可供模仿之花樣子”[1]。劍河苗族紅繡服飾在眾多的苗族服飾支系中以其獨特的紋樣裝飾構建起區別于他族的身份標識,究其原因,這與紅繡服飾紋樣成紋的技術動因――運行“母花”數紗繡針法直接相關。紅繡“母花”紋樣以固態物的形式存儲了本民族本支系的母體文化,在一代代劍河苗族紅繡女性輸出“母花”針法的過程中延續了本族共享的集體記憶和自我身份的建構。然而,由于“母花”數紗繡針法為片段化經驗而少有人去梳理,從技藝的角度探析“母花”紋樣差異的成因,學術界尚未有深入的研究。本文通過田野考察、實踐研習對大量“母花”紋樣針法的軌跡(繡線線路)進行梳理、提取、復原,嘗試厘清紅繡服飾“母花”針法與紅繡服飾紋樣 之間的關系,對不同針法的紋樣視覺呈現進行多維度的梳理,并對“母花”背后所蘊含的文化屬性進行分析。
1" " 劍河苗族紅繡服飾“母花”數紗繡針法――“母花”紋樣及針法
1.1" " “母花”數紗繡針法之“母花”紋樣
海德格爾(Martinheidegger)認為:“技術的本質不是手段,是一種解蔽方式”[2]。“解蔽”可以理解為讓技術成為顯現的過程,劍河苗族紅繡服飾“母花”針法的技術物――紋樣,即針法技術的顯現。紅繡服飾“母花”紋樣結構清晰,明暗相間,由浮起的繡線(正紋)和下沉的無繡線空槽(負紋)這兩部分構成,繡者以應用“母花”的經驗為內容,從心理到材料上將負紋的一道道空槽填充完形。“母花”紋樣結構外形多為不完整形,其外形是根據它所對應的紅繡服飾紋樣最小完整構成單元紋樣而來,如服飾紋樣最小構成單元紋樣為對稱形,“母花”即取其半個單元(圖1),如為非對稱形就取一個單元(圖2),進而根據紋樣擴展的方向排布此半個或一個單元紋樣,從而構成“母花”紋樣的整體外形。
本文從劍河紅繡服飾“母花”紋樣的構成線跡(兩針孔之間的繡線)外形特征出發,通過分析“母花”數紗繡針法紋樣的線跡組織、紋理形態、紋樣造型等特征,將“母花”紋樣分為3種類型:(1)非等線型“母花”紋樣;(2)等長線型“母花”紋樣;(3)等交線型“母花”紋樣。
1.1.1" " 非等線型“母花”紋樣――雙面直線“物”的呈現
劍河苗族紅繡服飾非等線型“母花”紋樣由約0.1厘米至2.5厘米之間不等長的線跡構成(圖3a),紋樣正面和反面都是水平“一”形線跡(圖3a),繡面平順,輪廓多呈規則的矩形。這種“母花”紋樣以“浮線”面為反面(圖3b、3e),以“空槽”面為正面(圖3c、3f),結構多為對稱性菱形“線面”結構,并以菱形為中心向外擴展圖案(圖3a、3d),紋樣形式以復合式為主,由多個紋樣組合而成,主要有花鳥類和幾何自然類,其中花類構成紋樣有手指花紋、菱形花紋、樹枝紋、楓樹紋等;鳥類構成紋樣有天鵝紋、鴿子紋、鳥紋等紋樣。幾何類構成紋樣有萬壽紋、鉤紋、梳紋等;自然類構成紋樣有風車紋、田埂紋、水波紋等。此外,也有這兩類復合型紋樣內的構成紋樣交叉組合的方式。(圖3)
1.1.2" " 等長線型“母花”紋樣――單面直線“物”的呈現
劍河苗族紅繡服飾等長線型“母花”紋樣由約0.1厘米至0.3厘米之間的長度相等的線跡構成,紋樣正面是水平“一”形直線線跡,反面“/”斜線線跡(圖4a),繡面紋樣立體感強,輪廓為不規則形。此種紋樣結構為菱形“線框”式結構,以菱形框為中心向二方或四方擴展紋樣構成要素。紋樣造型樣式有兩種:一為光邊菱形樣式(圖4b),即菱形線框為直線形式要素的樣式,其紋樣有田字紋、蝦弓紋、十字紋等;二為鉤齒菱形樣式(圖4c、4d),即菱形線框上排列有鉤形或齒形造型要素,其紋樣有回形紋、鉤形紋、萬壽紋、勾連紋等。
1.1.3" " 等交線型“母花”紋樣――交叉斜線“物”的呈現
劍河苗族紅繡服飾“母花”等交線型紋樣由約0.2厘米至0.3厘米之間長度相等線跡構成,紋樣正面為“x”形線跡,反面呈“一”或“1”形線跡,反面紋樣不成紋型(圖5a至5d)。
此種紋樣繡面呈網狀浮起,立體感強,輪廓為不規則形,是前兩種“母花”紋樣的輔助紋樣。由于等交線型“母花”紋樣在服飾中面積較小,劍河苗族紅繡女性一般通過疊加多層“十字”的方法來增強紋樣的裝飾性,其紋樣以二方連續紋樣為主(圖5e),有回紋、杉樹紋、勾連紋等,也有獨立紋樣(圖5f),如騎馬紋、萬壽紋、蝴蝶紋等。
1.2" " “母花”數紗繡針法之“母花”針法
1.2.1" " “母花”數紗繡針法分類
劍河苗族紅繡服飾“母花”數紗繡,是一種以經緯交織的平紋布為底,用棉線有規律地在布紋孔眼戳納成各種花紋的刺繡工藝,其核心操作是“數紗”和“挑紗”。目前與紅繡“母花”針法相關的定義有“直線繡”“反面直線繡” ,對數紗繡基礎工序、組織結構進行了外觀的描述用以解釋紅繡“母花”的針法,還不能清晰地表達正反面針法連接的操作特點。如相同形狀的數紗繡紋樣,在不同的正反面繡線軌跡里,其針法全然不同。因此本文根據紋樣正反面線跡特征、構成邏輯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結合傳統的針法分類將紅繡“母花”針法分為雙直針、單直針、十字針3類基礎針法,并在此基礎上,利用譜系分類法對3種針法的衍生針法進行進一步的挖掘、整理、提取、還原、歸類,總結出一套“母花”的針法體系。(圖6)
圖6中劍河苗族紅繡服飾“母花”數紗繡針法根據譜系分類法分為如下4個層級:
第一層:“母花”總針法層(A層),為紋樣針法總層;第二層:“母花”屬性針法層(B層),是不同特征的針法類別層,由雙直針、單直針、十字針3類基礎針法構成;第三層:“母花”功能針法層(C層),是塑造出不同紋樣形態的針法層,有連接針、分界針、廓線針、裝飾針4種。其一,連接針。這是動因針法,其技藝要訣是“連接”動作,連接針又可分為兩種:一是“直路連接針”,即同一維度行針線跡的連接,也就是順沿常規基礎針法的連接;二是“換路連接針”,指在切換路徑時銜接另一方向或區域里的行針,如在運針換行、拐彎、跨線和跨區等重要構形軌跡上實現關鍵連接的針法;其二,分界針是對內部紋樣要素進行劃分和區分的針法;其三,廓線針是塑造紋樣內部要素輪廓形態的針法,在跨紗數量、行針角度、排列數量和質感上有所區分的針法;其四,裝飾針是服飾紋樣物的針法,在紋樣的特定位置通過疊加繡線、點綴顏色等方式來豐富紋樣層次的裝飾性針法。第四層:“母花”針法層(D層),是以上針法層具體實現紋樣的針法單位層。
1.2.2" " “母花”數紗繡針法之“母花”針法
劍河苗族紅繡服飾“母花”數紗繡針法外顯過程也是紋樣的“繡線”動態連接的過程,如仔細觀察“母花”紋樣就會發現其紋樣是由一條持續連接完整的繡線構成,這條繡線(紋樣)“含有視覺圖案內容的敘事性與視覺圖案造型的樣式化,還兼有工藝制作啟迪性。[3]”要將工藝制作的啟迪信息轉化為可操作的針法,需要紅繡女性從紋樣固態物上“數紗”提取出紋樣造型所需的針法軌跡(繡線連接的路線),并按照此針法軌跡逐步地臨摹“連接”繡線從而實現紋樣的外顯。通過在劍河紅繡地區的多次田野考察和實踐研習,本文得出運用“母花”數紗繡的3個重要步驟:
第一步,用“眼”觀看“母花”(表1中1-1),即從觀察“母花”中獲得紋樣繡線所在“母花”布孔的位置,同時結合手指,點對點數出一粒紋樣繡線的兩個布孔點之間的紗線數;第二步,用“腦”分析“母花”,將通過手指數紗獲得的多個點對點連接而成的繡線軌跡在腦中激活成動態的“針法運行”信息(表1中1-2);第三步,用“手”輸出“母花”紋樣。將腦中獲得的針法信息在服飾繡布上手動輸出,轉化成紅繡“母花”紋樣或服飾紋樣(表1中1-3)。如此,通過“眼、腦、手”感覺器官和肢體的不斷重復感知,將在“母花”中所提取的針法技藝知識內化于“心”,如莫里斯(Maurice Merleau-Ponty)所言“當我實現身體的功能,我是走向世界的身體,我才能理解有生命的身體的功能”[4],身體感知對外部世界具有決定性意義。由此,本文在實踐研習“母花”針法的基礎上,以內化隱含在“母花”繡線軌跡里的針法為依據解析雙直針針法、單直針針法和十字針針法。
(1)雙直針針法――非等線型“母花”紋樣
雙直針針法,是非等線型“母花”紋樣的針法。行針時將繡布的反面朝上,正面行“一”形針,反面行“一”形針,完成的紋樣正反兩面成正負(此有彼無)的關系。如圖7a所示,從1起針,自下而上戳紗進入到繡布正面,從2落針[5],從正面自上而下戳出正面進入到繡布反面,并落一線跡在正面,如此重復連到6,完成一排“一”形線跡。雙直針針法成紋分為3個基礎步驟:第一步,重復行“一”形針,完成第一排a點至b點的“一”形線跡(圖7b);第二步,行“換路連接針”。如圖7c所示,運針時,針線從b點出,c點入,從原本水平“一”形針切換方向行“1”形針,為下一排的“一”形線跡打通線路;第三步,行第二排“一”形針,完成上下兩排平行線跡的連接。如此,重復以上3個步驟可實現非等線型“母花”紋樣的外顯。
(2)單直針針法――等長線型“母花”紋樣
單直針針法,是等長線型“母花”紋樣的針法。行針時也是將布的反面朝上刺繡,正面行“一”形針,反面行“/”形針,正面再行“一”形針,連續3針形成一個“Z”字形的針法(圖7d)。單直針針法成紋分為3個步驟:第一步,重復行“Z”形針,形成一個由數個等線“一 ”形斜向錯位排列而出的斜線“線柱”(圖7e);第二步,行“換路連接針”針。從一個“線柱”到另一個不同方向“線柱”之間的連接針法,如圖7f中的bc連接線通過切換行針方向,打通了不同方向的“線柱”運行的軌跡;第三步,行“Z”形針。重復操作以上3個步驟可實現等長線型“母花”紋樣成型。
(3)十字針針法――等交線型“母花”紋樣
十字針針法,是等交線型“母花”紋樣的針法。運針時將布的正面朝上刺繡,兩粒斜線線跡架成“€住斃蔚惱敕ǎ械ナ趾投資至街殖晌普敕ǎㄍ?g)。第一種,單十字針,即一次連續3針完成一個完整的十字的針法。如圖7h(右)中從1至4構成正面一個交叉“€住斃危疵妗?”形。第二種,二階十字針,即分兩個階段來完成十字的交叉。第一階段,首先完成兩個“半十字”;第二階段,從圖7h(左邊)5至8完成反方向的另外兩個“半十字”,從而構成兩個“€住斃巍8菟櫛蒲南嘸7較潁岷稀盎宦妨誘搿笨墑迪值冉幌咝湍富ㄎ蒲?
2" " 劍河苗族紅繡服飾“母花”數紗繡針法――服飾紋樣及針法
2.1" " “母花”數紗繡針法之服飾紋樣
“母花”紋樣的生成和應用,無論是從形式上還是技藝上都是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這種帶有流動性和轉化性的技藝特征是反映該族群極具地方特色的技術現象和文化現象。[6]運用紅繡服飾“母花”的服飾紋樣保留了原有“母花”的繡線軌跡(針法)、組織結構、排列秩序等特征,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擴展、填充、完形和裝飾等工序。由于“母花”紋樣和服飾紋樣功能屬性的不同,其紋樣傳達的文化內容也有所區別,母花是用于指導女性繡出紋樣的一種數紗工具即針法摹本,其核心傳達的內容是紋樣和針法信息;服飾紋樣具有公共性質,是一種用于對外展示和識別身份的象征物,是建構女性身份認同和延續集體記憶的符號載體,在材料、顏色、結構、尺寸等方面與“母花”紋樣都有所不同。總的來說,無論是“母花”紋樣還是服飾紋樣都來自對“母花”數紗繡針法信息的應用和傳遞。
2.1.1" " 非等線“華麗型”服飾紋樣――雙直針針法的外顯
非等線“華麗型”服飾紋樣保留了非等線型“母花”紋樣的基本特征,材料從單色棉線到彩色絲線,結構從不完整到完整,紋樣從扁平(有空槽)到飽滿(無空槽)。在運用“母花”雙直針針法的基礎上,紋樣線跡平順,結合紅色為主的絲線材料呈現出一種隆重而華麗的服飾紋樣視覺效果。此種紋樣布局在盛裝上衣的前肩胸、袖肘、后肩、后背以及盛裝大圍腰的下半部分;便裝冬衣上的前肩和袖肘以及夏衣的后肩部位。從表2中紋樣布局的實物圖可知,非等線“華麗型”服飾紋樣是盛裝服飾的主體紋樣,也是紅繡服飾紋樣中布局面積最大、視覺效果最強烈的一種紋樣類型。
2.1.2nbsp; " 等長線“雅致型”服飾紋樣――單直針針法的外顯
劍河苗族紅繡等長線“雅致型”服飾紋樣同樣從單色棉線到彩色絲線,結構從不完整到完整,紋樣從有空槽的正負形到無空槽的飽滿厚重的紋樣形態。在運用“母花”單直針針法的基礎上,等長線服飾紋樣呈現出秩序強烈、大方雅致的風格。此外,由于紋樣的短線結構,不易勾絲耐磨的特性,紅繡女性將其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從此類紋樣在服飾中的布局部位來看,其多分布在便裝主裝飾和盛裝輔裝飾部位,如便裝冬衣后背、頭帕底邊、小圍腰下端以及盛裝衣擺等服飾部位(表3)。從等長線“母花”紋樣布局位置可知,此種紋樣是當地女性使用頻率最高的一種紋樣類型,如春夏秋冬四季圍腰以及春夏秋三季頭帕上都布局有等長線型“母花”紋樣。劍河苗族紅繡女性自覺地遵守著本族本支系的紋樣裝飾布局和呈現規范的規定,并以這種本族特有的服飾紋樣視覺符號來傳達女性間的身份認同和集體情感的表達以及自我的經驗表述。
2.1.3" " 等交線“素雅型”服飾紋樣――十字針針法的外顯
等交線“素雅型”服飾紋樣保留了等交線型“母花”紋樣的顏色、材質,在運用“母花”十字針針法的基礎上延展了紋樣尺寸,加厚了針法線跡,形成了一種肌理凸出的紋樣效果。與前兩種紋樣有所不同,等交線型“母花”紋樣是一種輔助裝飾紋樣,其布局呈現有一定的規則:一為“點綴式”,這是在盛裝頭帕作小面積三角形區域的呈現方式;二為“邊框式”,這是在便裝頭帕、小圍腰、兒童帽檐的外圍以邊框的呈現方式;三為“衣緣條式”,此方式在盛裝上衣袖口、前衣擺、后衣擺位置以及夏衣的袖口和下擺以細長條狀呈現的方式。雖然等交線型“母花”紋樣面積較小,由于其強烈的肌理質感,因此應用范圍較廣,在紅繡服飾紋樣中起到了強化紋樣整體裝飾性的作用。(表4)
2.2" " “母花”數紗繡針法之服飾針法
劍河苗族紅繡服飾紋樣是“母花”紋樣針法的另一個階段。運用紅繡服飾“母花”的服飾紋樣針法是在不完整形“母花”紋樣的基礎上進行填充、裝飾等一系列的具有完形和美化功能的針法。本文以紅繡便裝冬衣袖肘上的非等線“華麗型”紋樣――“天鵝與花”復合紋樣在雙直針針法中的呈現為例,通過分階段分步驟的方式提取“天鵝與花”紋樣的技藝要訣,并將其轉化為可視化圖像信息,揭示其從紅繡服飾“母花”轉化為紅繡服飾紋樣的技術動因。“天鵝與花”紋樣在針法中的呈現過程包括:構造“母花”紋樣框架、填充“母花”紋樣、裝飾“母花”紋樣3個階段,其具體流程和針法操作如下:
第一階段,臨摹“母花”,繡制框架,擴展尺寸。首先,在刺繡服飾紋樣前,準備好雙直針針法的“天鵝紋”紋樣“母花”布本,開始行針。第一步,連接“一”形針,從A點到B點落針完成第一排線跡(圖8a)后,右手捏住繡布的左側順時針將繡布紋樣旋轉180度,準備繡下一排。第二步,行“換行針連接”針。連接換行拐角針B至C,實現平行的兩行跨行②至③(圖8b)。操作時,“母花”紋樣的“換行針連接”為拉一斜線線跡,而服飾紋樣的“換行針連接”是留0.3至0.5的松度(圖8c右)線跡,以便橫向調整“平服”[7]繡線的松緊度。第三步,重復連接,完成框架(圖8d)。從C點向右運針至D點再連到h點,完成第二排平行線,如此重復以上動作直至完成對“母花”紋樣的復制、翻轉、擴增。
第二階段,脫離“母花”,填充框架,完善繡面。在繡制好的紋樣框架內,填充無繡線的空槽區域。操作時,從反面繡制,并參照反面有繡線的紋樣部分,將反面紋樣從正面繞一圈包住,從而填充出正面無繡線區域的紋樣(圖8e)。填充框架空槽分為同色包繡填充和異色包繡填充兩個步驟:第一步,同色包繡填充(圖8f)。從反面取紋樣外形,用同色線(紅)包繡,此時紋樣反面兩層繡線,正面一層繡線;第二步,異色包繡填充(圖8g)。從反面取需要裝飾的紋樣位置,用異色線(粉)包繡。如圖8h中“天鵝”單元部分包繡粉色,具體操作時,當包完一個粉色“天鵝”單元后,需要行“線框橋針”:從一個“天鵝”單元繡制區域跨度到另一個“天鵝”單元繡制區域的連接針法,一般從兩頭往中間包繡,繡完一豎排后再包繡另一排“天鵝”單元紋樣。
第三階段,升級“母花”,點綴繡面,豐富層次。在填充完紋樣整體繡面之后,進而對紋樣繡面進行針法裝飾的一系列步驟:第一步,選取紋樣的中心位置進行多層包繡點綴,如圖8i中對花心的裝飾包繡,其完成的紋樣中心繡線分為正兩層,反兩層,共四層;第二步,對紋樣外框的裝飾,多采用異色線填繡,如圖8j用粉色繡線繡出的鋸齒紋樣;第三步,裝飾十字針,豐富繡面肌理層次。運針時先拉一排平行斜線(圖8k),再返回拉第二排斜線(圖8l),從而完成一排“X”形花紋裝飾。如此,完成了冬衣袖肘“天鵝與花”復合紋樣的裝飾外顯。
3" " 結" " 語
劍河苗族紅繡服飾“母花”數紗繡針法技術物――紋樣為紅繡服飾紋樣的視覺呈現提供了“詳盡”的針法信息,紅繡女性通過“數紗”就可將構成“母花”紋樣的每一粒線跡的針法提取而出,再以動態繡線的“連接”將針法轉化成服飾紋樣,這是一般的刺繡紋樣所不具備的功能。“母花”數紗繡所呈“母花”本體紋樣和針法以及服飾的紋樣和針法之特有形式,成為劍河苗族紅繡女性共同維系的服飾裝飾符號象征,劍河苗族紅繡女性以應用“母花”紋樣為手段,在技藝的視覺呈現中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構和集體記憶的延續。
注釋
①“紅繡”是劍河地區的苗族女性用紅色線材織造、刺繡技藝以及紅色織錦和繡品的統稱,在當地苗語稱“紅繡”為“miu xie”,也意指“紅色苗裝”。
本文的紅繡“母花”紋樣及紅繡服飾紋樣的樣本主要來自劍河縣的暗拱村、六府村、南高村、巫亮村、巫泥村、南腳村等地。
目前學術界對劍河紅繡母花數紗繡針法及其歸類還未達成共識,與本文“雙直針”針法相似的有“直線繡”的定義:“平紋布的表面朝上,根據圖案紋樣調整線跡的長短,繡至最左邊后將線剪斷,再回到右邊重復運針。”不同的是,筆者看到的紅繡“雙直針”為平紋布的表面朝下,繡至最左邊不剪斷反面連接下一排線。與“單直針”相似針法有“反面直線繡”,定義:“將布的反面朝上開始的刺繡,繡出的紋樣,反面線跡較短,而正面線跡較長。”如將“單直針”針法定義為反面直線繡,但實際上針法的反面是斜線,很容易與“雙直針”針法混淆,這是兩種差別較大的針法。“直線繡”和“反面直線繡”的定義參見鳥丸知子《一針一線:貴州苗族服飾手工藝探秘》,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11年,第59至60頁。
參考文獻
[1]周夢,曹寒娟,李煒彥.貴州苗族服飾“母花”的界定與文化屬性研究[J].裝飾,2023(03):100.
[2]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M].孫周興,譯.北京:生活€范潦閫沸輪櫚輳?005:10.
[3]賈京生,賈煜洲.苗族服飾圖案與母花本的文化解讀[J].貴州民族研究,2019,40(12):100-105.
[4]莫里斯€訪仿鍊放擁?知覺現象學[M].姜志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109.
[5]沈壽.雪宧繡譜圖說[M].張謇,整理.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51.
[6]譚曉寧,徐東升.施洞苗族母花紋樣的生成與轉化研究[M].裝飾,2023(09):21.
[7]廖力耕.中國民族傳統刺繡針譜[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