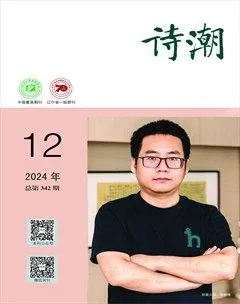詩學隨筆二題

詩是對“自然”驚奇,詩是深感“日常”
之神秘
在讀湖北詩人李漢超作品時,遇其中一首《柿子樹》,深感有趣:
我停止了看書
去看柿子樹
樹上結滿了柿子
黃的,尚未熟透
我似乎發現了這棵柿子樹
的秘密:它只結柿子
而不結其他的果子
十多年過去了
每年結出的都是柿子
當我確認這個秘密時
樹上所有的柿子
像打開開關的小燈籠
一下子都亮了
柿子樹自然只結柿子,不會接別的果子,但是,我們問過這是為什么嗎?大哲學家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曾言:“真正令人感到神秘的不是世界怎樣存在,而是世界盡然存在。”世界竟然如此存在!這本身就是一個“秘密”!誰能對這樣的“秘密”發問?那些對此“秘密”發問的人有福了!在中國文化中,我們很少對“自然”發問,因為“自然而然”、自然本就如此,何必發問?《道德經》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是什么?本來應該深究的一個無比重要的問題,卻因一句“道法自然”而終結了。“自然”的背后又是什么?英國的牛頓(Isaac Newton,1643—1727)竟然思想蘋果為什么會掉到地上而不是飛到天上,牛頓正是這樣被這個發問祝福的人。美國萊特兄弟(Wilbur Wright,1867—1912;Orville Wright,1871—1948)從鳥的飛行得到啟發而發明飛機,人們將作為機械的飛機視為人類偉大的發明而驚奇,但卻從未對鳥在天空飛行而驚奇。
在將“自然”仍然視為被造物(“自然”不是Creator,而是Creation)的文化中,就有人會對自然之存在而驚奇。故在我們的文化語境中,詩人李漢超在這里驚嘆“世界竟然如此存在!”我真的很意外也很欣慰,因為這是人的智慧的一個開端,他可能由此會去探尋超越人世的更大的存在——世界為什么竟然如此?如此奇妙的世界,其背后是因為有更大的智慧存在嗎?無論如何,我看到了因來到這個開端,詩人的心靈之燈似乎突然明亮了:那些柿子如同“打開開關的小燈籠”,這種修辭是一種移情:其實是“我”的心亮了,故“我”面前的物也是亮的。
這首詩的意趣關乎存在的秘密,看得出詩人日常對一些重大問題的思考,故此詩讀起來平常,但細細思量,非常讓人震撼。詩人深諳寫作上的舉重若輕之道。我也想起另一位在四川的詩人野川的詩作。他的詩中,亦有對“自然”的驚奇——詩作《坐成一棵翠綠的桑樹》里邊,即是這種關于“我”之存在的驚奇:“整個夏天,高處的蟬/都在嘶鳴,像在喊我/我故意不應答,是想看看/世間是否還有另一個我/從暗處,大大方方走出來/把蟬殼摘下,勛章一樣/掛在胸前,然后在地埂上/坐成一棵翠綠的桑樹”。
無數人寫日常生活,但以我有限的視野,我只在野川這里讀到了日常生活的“神秘”性,哪怕是在小區遛狗,他都能體會到這種“神秘”:
仿佛在調整與神秘的距離
太陽未落下,月亮已升起
天空蔚藍,亙古的對話
是朵朵白云。在小區
我一邊看天,一邊遛狗
兩只:一黃一白,乖巧萌人
它們停停走走,走走停停
仿佛在調整與神秘的距離
這種“神秘”,首先來自人本身,當我們專注自身的存在,你可能會意識這是一個“謎”,像現代詩人穆旦(1939—1945)所說的“藍天下,為永遠的謎蠱惑著的/是我們二十歲的緊閉的肉體”(《春》,1942年),可惜我們太多人年紀輕輕就輕忽了人自身存在的偉大與神秘,自我降格為蠕蟲般的存在。大哲學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也曾言:“對于無窮而言,人就是虛無,對于虛無而言,人就是全體,他是無和全之間的一個中項,他距離理解這兩個極端都是無窮至遠,事物的歸宿以及它們的起源對他來說,都無可逾越地隱藏在一個無從滲透的神秘里面,他所由之而得出的那種虛無以及他所被吞沒于其中的那種無限,這二者都是同等的無法窺測的。”很可惜,我們大多數人,既自愿地被虛無所擄,又倦怠于探尋那個作為真正信仰對象的“無限”。對于帕斯卡來說,人極容易被此“虛無”吞沒,故人脆弱如“蘆葦”;但人會思想,人是“思想的蘆葦”,人也有“偉大”之處;但“偉大”之人,若不認識“無限”,就會“驕傲”。
野川詩的形而上品質,正來自于他與“虛無”和“無限”的糾纏。他寫日常生活,使日常生活有了非同尋常的“神秘”性。這種“神秘”不是關乎鬼魔、精靈,而是關乎“虛無”與“無限”,正因為后者,我們的生活有可能是——“……那種循環/簡單,迷人,又深不可測”:
窗 外
我家窗外有兩棵樹
我辦公室窗外有三棵樹
無聊的時候
我做加法,做減法
偶爾也做乘法
只有寫詩的時候
我做除法,不是三除以二
而是二除以三
我喜歡那種循環
簡單,迷人,又深不可測
現代詩人卞之琳(1910—2000)名作《距離的組織》(1935年)似乎是一種“元詩”,意在告訴我們寫詩的根本技法:詩意的來源關乎詞語、意象與所指之間的“距離”——距離過近,則詩意平常、無趣;距離過遠,則詩意晦澀、讀者無從把握。我讀野川的組詩《仿佛在調整與神秘的距離》,也有一種“元詩”之感覺,作者似乎在提醒我們,當代詩的形而上品質,關乎“人”與“神秘”的“距離”——當我們對此“距離”一無所知,我們筆下的“生活”則如蠕蟲之存活無異,寫作很難有真正的詩意;而當我們僭越了“無限”的位置,自己定義何為“人”,自己宣告此“神秘”的特征,那種詩歌看起來非常關切人的精神狀況,也抒寫苦難云云,事實上是“蘆葦”的“驕傲”,是關于生命與世界的妄語。一首詩的境界之好壞,與這種“人”與“神秘”之間的“距離”息息相關。
詩,不是傳達哲理而是遞交感覺
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2014)說他的《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是“我認為我最好的作品”。能好過《百年孤獨》?帶著這種疑問我讀了這本小說,但這個小說把我讀笑了。這是啥呀?就這?這個小說簡單說來其實就倆字:等待。一個年邁的上校苦苦等待政府曾經承諾的養老金,“一等就是十五年”,盼望有人給他來信,然而,始終沒有。
對于渴望故事和情節的小說讀者,這個作品一定讓你很失落,你不解馬爾克斯如此贊譽此作到底何意。但幾次翻閱之后,我還是覺得這個小說有非常動人之處,那就是他沒有給我們稱之為小說硬核的東西,卻給我們一個軟性的、彌散的生活氛圍:等待。等待是需要“耐性”的,而這個“耐性”,恰恰是我們對付生活的要訣,正如在漫長的雨季里、在一堆雞毛蒜皮之中無盡等待的上校的感嘆:“生活就是這么回事兒……生活是人們發明出來的再美妙不過的東西了。”
我認為這句話是此作的文眼。對很多人而言,“生活”無意義,人們需要“發明”一種意義來將生活進行下去。就像搖滾樂隊《五條人》的代表作《阿珍愛上了阿強》中那句歌詞:“雖然說人生并沒有什么意義/但是愛情確實讓生活更加美麗”。在這里,“生活”的一點點意義附著在“愛情”上面。而對于上校來說,“生活”的意義其實就在于“等待”,那個即將要到來的信件其實是他為生活預設的,那封信到底有沒有,他實在沒有把握,但因為那封始終沒有來的信,他的“生活”最終成立了(他“發明”一種靠著“耐性”認真“等待”的“生活”)。

這當然是個悲劇,但太多小說以故事和情節或者人物的悲慘命運來講述這種悲劇了,而馬爾克斯,卻以漫長的篇幅在傳遞一種“感覺”:在讓人厭煩的天氣中,在日常生活的令人窒息的氣味和場景中,一個人在無盡“等待”。這叫小說?我不敢說這叫好的小說,但我想說,這才是好的文學,文學不是傳達一個可以清晰把握的、引人入勝的故事的語言活動,文學是借著語言和敘述來傳遞作者對生活的感覺的藝術行為。這種文學是“詩”意的。
反觀詩歌。詩歌本來應該是傳遞作者的感覺(在現在的維度上)、想象(在未來的維度上)與記憶(在過去的維度上)的,整體上他試圖傳達一種涵括前述三者的“經驗”。這種經驗在作者這里,是整體性的(非分析性的),是難以言說的,正是這種難以言說,詩歌寫作派上了用場。詩借著對感覺和記憶的描述、思維和語言在想象上的展開,呈現了一種生命經驗的“具體性”,這種具體性不是一句兩句話可以說清楚的。很多人,常常說他不懂詩歌,其實不是他不懂,而是他不明白詩歌之“懂”異于散文之“懂”。詩歌之“懂”不是我讀了一首詩就將這首詩翻譯出來:它說了什么、它結構如何——這是散文之“懂”。對于一首詩的懂,我們最重要的不是說出其“硬核”的東西,而是整體性地體會其中的感覺與經驗。對于一首詩,最好的“懂”,是感嘆:它寫得真好,但我說不出……
但是我們的詩歌教育以及很多讀者、作者對詩歌的認識方式恰恰是散文式的、小說式的。我們把“詩意”簡化為“哲理”。孩子們評價一首詩時,最愛說:這是一首哲理詩。但是,哲理用哲學的話語不是更好嗎?為什么要用詩呢?我們給孩子們的古詩,通常附上白話文的翻譯。葉維廉先生(1937年生)曾痛批這種對待詩歌的方式,比如我們遇到“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出自五代翁宏的《春殘》),馬上你就能看到譯文:“人在落花紛揚中幽幽獨立,燕子在微風細雨中雙雙翱飛。”這里的詩句和后面的譯文能等同嗎?前者是詩,是一種整體性的人生感覺、生命經驗(孤獨感)的傳遞,不是后面那種散文化的語言陳述的狀態能夠等同的。
在我看來,“詩”/“文學性”,其實首先是言語活動所體現出的一種別樣的意趣、意味。從作者來說,他是主動的,他希望能夠表達出一個真實的、更內在的自我,為此他會運用與日常交際語言不同的說話方式;而從接受角度,作者所呈現的語言活動之特別,會讓讀者在“異樣”的接受中去意識另外的內容,通常是獲得關于人、關于生活或生命的某些新的感知。當然,這種感知不是概念推演、在嚴密的邏輯性敘述中的哲學化的“具體”,而是蘊藉在文學性的“具體”之中。這種“具體”由對情緒、感覺、經驗、想象和記憶的敘述構成。這樣的“具體”敘述其目的是作者所體會到的存在,能在最大程度上被某些讀者“具體”感知。如同俄國形式主義理論家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ij,1893—1984)所言:“正是為了恢復對生活的體驗,感覺到事物的存在,為了使石頭成其為石頭,才存在所謂的藝術。”藝術的目的(也是“詩”之目的),首先不是讓人思慮“石頭”意味著什么,而是讓“石頭”作為“石頭”本身被人感知。這塊“石頭”,在馬爾克斯的小說里,就是我們也在遭受的“生活”。
我們閱讀許多外國小說,讀著讀著會很煩躁,因為進入故事和情節太緩慢了,怎么那么多的場景敘述和心理、感覺的吐露。其實,這種小說在我看來,才很好地“對應”了我們的“生活”,它們真實地傳達了“生活”給人的那種無盡的、覆蓋性的、命運般的“感覺”。這種小說在我看來,恰恰是“詩”的。而我們的詩,絕不能寫成有“硬核”的哲理性在里邊的東西。
之所以說“遞交”,意思是詩所言說的“感覺”,從作者到讀者,始終是整體性的,如同一個物的傳遞,傳遞(寫作與闡釋)行為完成了,但“物”始終是“物”。當然,這是理想的閱讀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