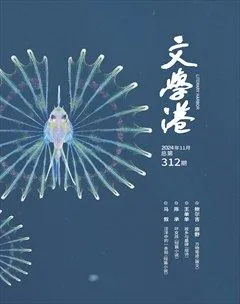訪(fǎng)談:真正的詩(shī)人是一種宿命
朱夏楠:王老師好。你是在怎樣的契機(jī)下,和詩(shī)歌結(jié)緣的?
王單單:應(yīng)該是二十年前了,青春期的心靈密語(yǔ)促使我孤獨(dú)地爬上詩(shī)歌的天梯,我在那里徘徊許久,最終被無(wú)形之手拖進(jìn)詩(shī)歌的大殿,接受一個(gè)個(gè)語(yǔ)詞的揀選與認(rèn)領(lǐng)。我總是近乎偏執(zhí)地認(rèn)為,真正的詩(shī)人是一種宿命,從他呱呱墜地開(kāi)始,生命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在為“詩(shī)”作準(zhǔn)備,而“寫(xiě)下”,只是詩(shī)在語(yǔ)言中現(xiàn)形。
朱夏楠:很多人都遭遇了青春期的迷茫與掙扎,不斷地找尋著出路。雖然是無(wú)形之手使然,但想必也是個(gè)人的主動(dòng)選擇吧?你是如何做出這個(gè)選擇的呢?
王單單:畢業(yè)之后,我飄蕩了一年,一無(wú)所獲。迫不得已,只能回老家參加特崗教師招聘考編。那是2006年秋天,我只身來(lái)到鎮(zhèn)雄西部一所偏僻頹敗的鄉(xiāng)村中學(xué)教書(shū),在那里我舉目無(wú)親,第一次陷入沉重的孤獨(dú)與失落,加之鄉(xiāng)村生活的單調(diào),這一切將我逼向漫無(wú)邊際的閱讀中。還是詩(shī)歌,它讓我的閱讀逐漸有了朝向,像離岸久遠(yuǎn)的孤島,成為迷霧漫漫的大海上最先向我伸過(guò)來(lái)的半截歸途。相較于學(xué)生時(shí)代的淺嘗輒止,在這個(gè)鄉(xiāng)村,我開(kāi)始癡迷于詩(shī)歌的閱讀與寫(xiě)作,甚至到了無(wú)藥可救的程度,似乎在里面觸摸到了另一個(gè)我,他埋得很深,但已經(jīng)被我死死攥住,我要將他從無(wú)盡的深淵中拽出來(lái),我要和他滴血認(rèn)親,使其歸位于我的心靈。
朱夏楠:第一次正式發(fā)表作品是什么時(shí)候,還記得當(dāng)時(shí)的情形嗎?
王單單:算了一下,我大約寫(xiě)了九年才正式在刊物上發(fā)表詩(shī)歌,雖然長(zhǎng)期默默無(wú)聞,但一直樂(lè)在其中,我尤其珍視這段時(shí)光,閱讀與寫(xiě)作帶來(lái)的愉悅是如此純粹。我第一次正式發(fā)表詩(shī)歌,是在2012年《詩(shī)刊》第5期下半月“詩(shī)歌新元素”欄目,天才少年詩(shī)人王薌遠(yuǎn)是本期頭條詩(shī)人,無(wú)比遺憾,他已去了另外一個(gè)世界,我在這里懷念他。藍(lán)野老師是我的責(zé)任編輯,幾年后我去《詩(shī)刊》見(jiàn)習(xí),和他在一個(gè)辦公室待了兩年,緣分真是奇妙無(wú)窮!更有意思的是,這組稿子原本是當(dāng)時(shí)《人民文學(xué)》編輯朱零老師約去的,他在博客上讀到我的詩(shī)歌,便向我約稿,百感交集啊,我一次性給了他三十多首。但刊物版面有限,發(fā)不了這么多,于是他分了一半給藍(lán)野老師,遂成我的“首次正式發(fā)表”。感謝這些師友,感謝寫(xiě)作道路上所有給予我溫暖的人!
朱夏楠:可以簡(jiǎn)單說(shuō)下你的成長(zhǎng)環(huán)境嗎?這個(gè)環(huán)境對(duì)你日后的創(chuàng)作,有什么鮮明的影響嗎?
王單單:十多年前,我寫(xiě)過(guò)一首題為《滇黔邊村》的詩(shī)歌,從中可以了解到我的成長(zhǎng)環(huán)境,選段錄于此:
滇黔交界處,村落緊挨
泡桐掩映中,桃花三兩樹(shù)
據(jù)載古有縣官,至此議地
后人遂以此為名,曰:官抵坎
祖父恐被壯丁,出川走黔
終日惶惶,東躲西藏
攜妻帶子,落戶(hù)云南
露宿大路丫口,寄居廟坪老街
塵埃落定于斯,傳宗接代
香火有五,我父排三
鄰舍出資,我父出力
背土筑墻,割草蓋房
兩省互鄰,雞犬相聞
有玉米、麥子、土豆、高粱煙葉等
跨界種植,一日勞作汗滴兩省
余幼時(shí)頑劣,于滇黔中間小道上
一尿經(jīng)云貴,往來(lái)四五趟
有時(shí)砍倒云南的樹(shù),又在
貴州的房頂上生根發(fā)芽
……
90年代后期,官抵坎
有女嫁人,有兒遠(yuǎn)行
剩下老弱病殘留守空村
闊別十六年,夢(mèng)回官抵坎
曾經(jīng)滇黔交界上的小道
我從云南找到貴州
又從貴州找到云南
都找不到我少時(shí)留下的尿斑
我總覺(jué)得,每一個(gè)身陷困厄,在生活中掙扎的身影,都來(lái)自我們村,都是我的父老鄉(xiāng)親。我的寫(xiě)作無(wú)法回避那一張張欲哭無(wú)淚的臉,那一個(gè)個(gè)驚惶未定的眼神,那一條條窘迫不安而又卑微如塵的生命……
朱夏楠:有沒(méi)有參加哪些詩(shī)歌社團(tuán)?對(duì)你的創(chuàng)作有影響嗎?
王單單:我沒(méi)有主動(dòng)加入什么詩(shī)歌社團(tuán),影響更無(wú)從談起。歷史上詩(shī)歌“興觀(guān)群怨”中的“群”,從沒(méi)像自媒體時(shí)代這么興旺發(fā)達(dá),有時(shí)朋友邀約進(jìn)群,我也只是“端坐其中,沉默不語(yǔ)”。
朱夏楠:對(duì)你詩(shī)歌創(chuàng)作影響最大的詩(shī)人有哪些?
王單單:這個(gè)問(wèn)題曾被多次問(wèn)起,以往我會(huì)列出諸如杜甫、布羅茨基等古今中外的大詩(shī)人,以此虛立“詩(shī)設(shè)”,側(cè)證我的詩(shī)歌“來(lái)處”,后來(lái)一想,此舉何其淺薄。一個(gè)成熟的詩(shī)人,其詩(shī)歌觀(guān)念和美學(xué)養(yǎng)成錯(cuò)綜復(fù)雜,絕非單一通道所能抵達(dá)。平日里我閱讀大量詩(shī)人的作品,從中獲得抒情的慰藉或敘述的啟示,這些詩(shī)人影響了我,與此同時(shí),同樣的慰藉與啟示也會(huì)發(fā)生在別的詩(shī)人身上。于我而言,這種“影響”是淺層次的,真正能將我的寫(xiě)作與眾多詩(shī)人區(qū)別開(kāi)來(lái)的,必然是生命之初最早注入身體的愛(ài)與悲憫,是我在這人世間使出渾身解數(shù)也無(wú)法避開(kāi)的奔波與勞頓,是平凡人生里那些肉眼可見(jiàn)的掙扎與人性深處的光輝,是那些被命運(yùn)之手反復(fù)捏造與戲弄的無(wú)名之輩。“我”才是對(duì)我詩(shī)歌影響最大的詩(shī)人。
朱夏楠:你迄今為止最為滿(mǎn)意的作品,是哪一部?可以大概做個(gè)介紹嗎?
王單單:慚愧,我至今尚無(wú)最滿(mǎn)意的作品集。第一部詩(shī)集《山岡詩(shī)稿》收集了早期作品,雖有沉郁粗糲之風(fēng),但也不乏稚幼之作;第二部詩(shī)集《春山空》,在寫(xiě)作技法和藝術(shù)風(fēng)格上做過(guò)一些探索和拓展,但這種嘗試并非全是成功的;第三部詩(shī)集《花鹿坪手記》是對(duì)自我寫(xiě)作能力和表達(dá)技巧的一次顛覆和挑戰(zhàn),我希望跳出情感與情緒的推動(dòng),在現(xiàn)代詩(shī)中回到“指物作詩(shī)”的傳統(tǒng),更多追求一種精神速寫(xiě),如此一來(lái),也有部分作品難免失之于單薄。等我老了,封筆之前我想出一本自選集,那應(yīng)該才會(huì)接近我最滿(mǎn)意的作品。
朱夏楠:詩(shī)歌在你生活中占據(jù)了怎樣的地位?
王單單:忽然想起故鄉(xiāng)那些年邁的農(nóng)夫,無(wú)論房屋多么凋敝、簡(jiǎn)陋,他們都會(huì)在里面找出一個(gè)隱秘的地方,有可能是床鋪或枕頭下、柜子里、墻縫間、梁木上、瓦楞下,用于存放身份證、地契、貸款憑據(jù)、泛黃的信件、舊照、孩子們的出生證、亡父的半寸照等,這些在外人看來(lái)無(wú)用的東西,對(duì)他們卻是無(wú)比珍貴,是絕對(duì)不能丟失的,他們活得卑微、毫不起眼,唯有這些物件才能證明他們的存在,是生命的另一種賦形。我的詩(shī)就像農(nóng)夫們潦草人生里那“隱秘的地方”,我在里面珍藏著各種各樣的“我”,他們被時(shí)間擊敗了,退出命運(yùn)和生活的前線(xiàn),去那里療養(yǎng)、復(fù)原,成為個(gè)人史的一部分,等待更多共情的人到來(lái),一起復(fù)述從前的故事,重溫心靈震顫的瞬間。
朱夏楠:對(duì)自己的創(chuàng)作,你有怎樣的期許?
王單單:沒(méi)有期許。就讓我在詩(shī)里一條道走到黑吧,走到月落烏啼,走到星垂大荒,走到天邊光芒乍現(xiàn),走到四周孤峰突起,走到走投無(wú)路,走到絕處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