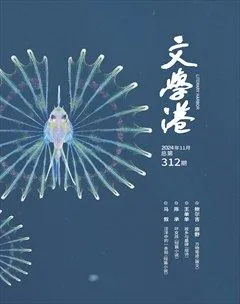汪洋中的一條船(短篇小說)
一
漂在公海上的是一艘無號無牌的加裝了原機(jī)四倍半動力的大馬力柴油機(jī)白卵鐵殼機(jī)動漁船,這船比一般漁船的速度快了三倍多,就是馬力強(qiáng)大的漁政船也遠(yuǎn)遠(yuǎn)追不上它。白天光來到這條船上已經(jīng)一個半月。到這條船上不是他自己來的,而是被綁架到了這條船上。
那天,白天光與幾個朋友一起租了一條休閑漁船出海打魚休假,漁船先是在海灣里拖網(wǎng),拖了一網(wǎng),拉上一看,除了少得可憐的一點點小魚蝦,幾乎就是一張完全的空網(wǎng)。朋友說,我們把船開得遠(yuǎn)一些,也更深一些的海上去,那里必定會有魚可打。這個建議得到了大家的熱烈響應(yīng),就這樣這條漁船在再加兩千元錢的前提下開往外海打魚。漁船開到了很遠(yuǎn)的海面上,放下了長長的拖網(wǎng),待魚網(wǎng)再被拉上來時,收獲讓大家高興得忘乎所以。所有人,包括船老大,都到船尾甲板上圍著打上來的那網(wǎng)魚蝦轉(zhuǎn)。只有白天光不喜歡湊熱鬧,坐在船艙里沒動。就在這時,休閑漁船邊上來了一條快艇,快艇靠上休閑漁船,迅速爬上來四個人,二話沒說用膠帶蒙眼架走了白天光,放到快艇上迅速駛離了休閑漁船。等休閑漁船上的朋友發(fā)現(xiàn)白天光不見了時,快艇已經(jīng)開到了公海的海面上了。摘下遮眼布,白天光已經(jīng)在一條白卵船上了。白卵船上的人讓白天光撥通了朋友的電話,剛說,我被海盜綁架了,現(xiàn)在他們的船上。隨即就被強(qiáng)制掐斷了電話。接著,白卵船上一個叫陳阿姨的男人,用這個電話給白天光的朋友再打次去電話,交代對方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須得在兩個小時內(nèi)打入人民幣二十萬元到一指定賬號,如果報警的話將毫不留情地將白天光撕票。從通電話,轉(zhuǎn)賬入戶,確認(rèn)到賬,又確認(rèn)被轉(zhuǎn)出,再到確認(rèn)取款機(jī)取出完畢,再到拔出電話卡扔到海里,這個過程連貫dc39b811ff4772da4162de0b8f39e92a7f0aa6c85ab0e0f1bf52d6414c999728、流暢、順利,兩小時里完成了全流程。這時,白天光知道自己已經(jīng)徹底失去了價值,白卵船上的人完全可以用任何一種方式處置他。白天光想,白卵船上的人極有可能隨手一抬,就把他扔進(jìn)大海里喂魚了,但是白卵船上的人并沒有對他作出處置。
頭半個月,白天光只是被一直綁著看著,這期間,白天光一直希望能夠有漁政船或緝私艇緝查這艘船,但是到了最后,白天光看不到任何能夠逃得掉的希望,有兩回倒是有漁政船想追上白天光所在的這條船檢查,卻很快被這條白卵船甩得遠(yuǎn)遠(yuǎn)的。
半個月的時間太長太長了,關(guān)在船艙里,不知外面的任何情形,只有船體隨波浪的起伏,有時風(fēng)浪大了,起伏幅度大,心一下一下地隨著船體的起伏被拋到浪尖又跌到谷底,反復(fù)不停地交替上下,使白天光絕望,并且連絕望也那么枯燥,每天都是或看著無邊無際的大海,或看著巨大得無法形容的天空。白天光越來越絕望了,根本就沒有任何希望,任何可能被發(fā)現(xiàn)、被救援。最后是一張眼看到大海就發(fā)瘋一樣地嚎叫、大哭。
哭個鳥啊,你哭又有什么用?想死也不可能,但是,這半個月來你應(yīng)該很明白了,任何人都不可能解救你回去。船長王大餅說。
除了絕望,白天光在這半個月里還受盡了羞辱,開始時他每被他們羞辱總是無地自容,痛苦不堪。七八天之后,白天光雖然已經(jīng)能扛住所有的羞辱了,但是徹徹底底的絕望還是擊垮了他。當(dāng)情緒重新安定下來時,他開始與他們同流合污了。他坐在船上,不再因為加入他們而感到愧疚。他不再想其他任何事。活著是唯一的。在此刻,除了生命、肉體、活著,其他與我又有什么相干呢,他想。就這樣,白天光完全融入了白卵船的群體之中。
晚上,王大餅請白天光喝酒。酒是高度燒酒,很烈。白天光猛喝了一口,喉嚨嗆得厲害。但是酒在船上是好東西,這一頓酒,把白天光因絕望帶來的壞情緒全給抹平了。主要是白天光不再想事了,突然11b0ea3285c8e0d8a0948f210353615e85fb3b99fa91b700587d6ca05ab83d9d變得單純了。王大餅說,我知道,你與我們是完全不同的人,我們是海盜,你是讀書人,是知識分子,但是在這船上,知識有屁用!白天光說,是的,我知道,在這白卵船上,你們每一個人都比我強(qiáng),所以我現(xiàn)在沒有怨言,既然到了這船上,就天隨人意了。王大餅說,那也不能白養(yǎng)活你,你得對我們有用,才能在這船上活下去。白天光說,這我知道。
王大餅說,你知道了嗎?不,其實你并不知道。
白天光說,白卵船上,你是一錘定音的人,也許我是真不知道。
王大餅說,船上的人不一定給你活,也可能包括我,但是你一定要想辦法自己活下來。
聽了王大餅這話,白天光怔了好長時間。
二
白卵船上連白天光一共八個人,另七個是:王大餅、陳阿姨、陳小六、王阿根、王不能、王大能、林根本。每人都配有槍支,四支左輪手槍,三支AK47自動步槍。
除了船長王大餅外,大副林根本是一個航海專家,白卵船在洋面的任何一個點上他都能迅速地定位出經(jīng)緯方位,并能從雷達(dá)上判斷出周邊的船只情況,及時地避開漁政船與邊防巡邏艇。白天光看出林根本與其他人不一樣。全船人也只有林根本愿意與白天光說話。林根本持有一把AK47自動步槍,他在白天光面前表演過一次槍械全拆裝過程,從槍械的完全分解到重新組裝完畢到射出第一顆子彈,只用了不到兩分鐘時間。林根本的槍械分解組裝動作,敏捷、鏗鏘、連貫、流暢、精湛。在這整個過程中,他緊抿著嘴唇,面頰上兩塊咬合肌來回滑動,雙眸發(fā)亮、敏銳、狠惡。
林根本說,你上了賊船,就不可能再有退路了,你只有安心,也必須安心在船上,才是唯一的活法。
白天光說,你當(dāng)初也是被他們綁到船上的吧?
林根本說,你不要問這個,問這個沒有意義,做好眼下的事最重要。
眼下要做好的是什么事?
眼下重要的事是丟掉一切多余的想法,做一個狠毒冷血的人,不要有任何婆婆媽媽的想法。
白天光最想了解的人除了眼前的林根本外,還有一個就是船長王大餅。白天光問林根本,王大餅是船上的靈魂人物吧?但看得出他是一個沒有知識的人。
林根本說,你是小瞧王大餅了,他完全與我不一樣,沒有什么書本知識,但他在海上的做事風(fēng)格與方法,都是你我永遠(yuǎn)可望不可及的。
林根本又說,船上的人都是沿海各縣的人,陳小六是三門人,王大能、王不能是玉環(huán)人,陳阿姨是臨海人,王大餅是平陽鰲江人,王阿根與我是福建連江人。
白天光說,想不到就這么幾個人卻來自這么多不同的縣,他們也不想著回家去看看嗎?
林根本說,干這事能回家嗎?一回家就等于親自把自己送到局子里去,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所以就要把對家對陸上的一切思念與瓜葛,都徹底地忍了。
白天光說,說實話,就是蹲局子也比在海上這漫無邊際地漂著強(qiáng)啊。
林根本說,我剛到船上時也是這么想的,但再過些日子后,你就不會這么想了。
白天光說,也許吧。
白天光林根本兩人正這樣漫無邊際地說著時,王大餅過來,說,別閑扯那些沒用的。
林根本說,那哪些是有用的?
王大餅說,有用的不是說出來的,得是干出來的!
林根本說,你是行動派,我與你不一樣,我還是得想,得說。
王大餅說,鳥!看你這鳥書生樣!
林根本說,我槍也玩得不錯。
王大餅說,這個好,真功夫。
王大餅離開后,林根本冷漠地說,其實船上個個狠毒得很,要不是供給充分,在船上什么事都會發(fā)生。
白天光聽到林根本這話,怔了一下,不再說什么。心想,這林根本,并不是自己原先判斷的那樣一個人,其實是一個不可測的人,與王大餅不一樣,在這樣的船上,知識有時更可怕。突然之間,白天光原本與林根本在交談中建立起來的那一點信任,剎那間蕩然無存。
白天光想,白卵船上個個都是鬼魅,個個都是活在算計與被算計之間。
三
三天后,白卵船泊在公海的一個島嶼旁,島嶼沒有碼頭,只有一窄條的沙灘可供從接駁快艇下來的人登陸。雖然不遠(yuǎn)處有個簡易碼頭,但只有等漲潮后船只才能靠得上。白卵船上八個人上島后到了一處不錯的住所。王大餅說,大家在這待三天,三天里,不要給我惹出什么事。
林根本對白天光說,這島嶼雖然是有所屬國的,但從沒有政府方面的人來這島上管理過,基本相當(dāng)于無國籍島嶼。島上流通美元與人民幣,你是遇上好運氣了,我們一年到這島上也就來那么兩三回,你才來就上島了。
路上,還遇到幾個不明國籍的老外。白天光很快就明白了,這是一個專供海盜及不明身份者落腳的島嶼。
王大能與王不能兩兄弟轉(zhuǎn)眼就不見了。林根本說,他倆一上島就找女人去了,對他倆來說女人比命重要。
這時,陳小六過來,說,我比他倆更喜歡女人,但是我不會在這里找。
白天光問,為什么?
陳小六說,我喜歡女人,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命。
白天光說,知道了。
陳小六說,知道什么!你保好自己的命最重要,說不定什么時候自己這條小命沒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白天光已經(jīng)不再像一開始聽到王大餅他們說這話時吃驚了。白天光說,知道了,我要先保好自己的命。
林根本說,看來你是多少已經(jīng)有點明白了,這對你,包括對大伙,是好事。
過了一會,其他人包括林根本、王大餅,消失在白天光的視野中了。轉(zhuǎn)過一座房子,到了住宿的地方,白天光發(fā)現(xiàn)只剩下了自己一人。這些人都去哪了呢?是找女人去了嗎?不一定,像林根本、王大餅是不會一上島行李都還沒放下就像王不能與王大能一樣去找女人的。畢竟陳小六說過與女人比自己的命更重要的話,這話應(yīng)該也適用于林根本與王大餅這樣的頭目人物。
晚上,王大餅組了一個酒局。除了王大能與王不能外,其余六人都在,參加酒局的還有另外一條船上的兩個人,一個叫張龍飛,一個叫日新日。一個臺灣花蓮人,一個馬來西亞人,兩人的海盜歷史比王大餅他們都要長。他們的船上共十二人,船上的人都冷血無比。雖然大多時候都是只劫財物,不奪人命,但遇到強(qiáng)烈反抗的,則會殺人不眨眼!張龍飛說,你的哥們王大能王不能,撬了我哥們的女人了。王大餅說,這島上的女人能打記號嗎,今天你的女人,明天他的女人,再明天又是另外人的女人了。張龍飛說,雖然是這樣,但在我哥們還沒放棄以前,那就是撬墻角!王大餅說,島上女人少,她們來這樣的地方,為的是什么,難道會為狗屁愛情與狗屁男人嗎?她們就是沖著錢來的,王大能王不能的錢不花到這些女人身上還真是沒地方花。
日新日說,王大餅說的是,這島是什么地方,海盜窩,女人算什么。王大餅說,話又說回來,搞到錢了,就是女人最讓人神往了,他娘的女人啊,弄不好真的是男人間拉仇恨的種子。再喝的時候,突然王大餅有種不祥的預(yù)感,王大能王不能該不會有事了吧。一想到這,王大餅心里不安起來,也就沒心思喝酒了。
張龍飛看出了王大餅心不在焉,說,王大餅,叫我們來喝酒,你自己卻心不在焉。
王大餅實話實說,我是感覺王大能王不能可能會出事。
王不能王不能還是出事了,王大餅的預(yù)感一點都沒錯。
王不能被打成輕傷,王大能被打斷了腿。
王大餅問白天光,你是讀書人,心里想得細(xì),你說,這事怎么辦?
白天光說,你去找張龍飛,這個事最好能夠講和,不然事情會越鬧越麻煩。
王大餅吼了白天光一聲,你個軟蛋!這是什么餿主意!這事要是你這樣處理,我王大餅還怎么在兄弟中間混!
白天光想不到王大餅發(fā)這么大的火。難道他問自己不就是想商量主意嗎?
王大餅說,不管王大能王不能他倆做事多么不地道,但是只要是我的兄弟,就不能讓外人欺負(fù)了。
王大餅帶著白卵船上的一船人,到對方那里,二話不說,開槍打斷了打傷王大能王不能那人的腿,也算是以牙還牙了。王大餅對張龍飛說,你是我的兄弟,但王大能王不能更是我的兄弟,雖然撬了你家兄弟的女人,但能撬走女人是自己的本事,而暗算傷了我兄弟,我不能不管!
張龍飛與王大餅比,氣勢上就差了一截,凡這事,只要先發(fā)制人,豁出命去,不怕死,更狠毒,就沒有不怕的。
張龍飛說,這事就這么過去了吧,也無須說什么道理與理由,江湖事,還是不說清為好。
張龍飛顯然是一個久經(jīng)江湖的人,雖然做海盜的歷史比王大餅早,但是既遇上這樣的拼命三郎,就只能委屈一下,這也是為自己更長遠(yuǎn)的大局考慮。
白天光覺得,張龍飛雖然強(qiáng)悍比不上王大餅,但他是一個比王大餅想得更多的人。在這樣的時刻,想得多的不一定好,強(qiáng)中還有強(qiáng)中手,在這樣的情況下更合適的應(yīng)該是像王大餅這樣的人。
王大餅對王大能王不能兄弟說,島上本身女人就少,所以玩女人就是玩本錢,你倆是不夠玩這本錢的,知道嗎?
王不能說,平時提著腦袋做事,這時我就是想痛痛快快玩一回。
林根本說,島上不明身份的人太多,這樣玩只會是哪天老命丟了都不知道。
王不能說,我們的身份不也一樣嘛,一條船也是白卵船。
林根本說,這倒也是。
四
王大餅吩咐陳阿姨、陳小六負(fù)責(zé)采購,把補(bǔ)給都裝上船。
陳阿姨說,早裝上船了,供給都買足了,供給船上沒有的東西也都備齊了。
公海上賣供給的供給船往往供不應(yīng)求,所以每次上島時負(fù)責(zé)采購的陳阿姨都會把供給買足買夠。因為白卵船不載貨不捕魚,所以就有足夠的載重空間來裝供給,包括加艙的淡水。這樣白卵船一次裝夠的供給至少可以滿足一個月的船上生活需求。有時碰上供給船貨源充足,或者從別的貨船或漁船上搶到供給,那么補(bǔ)充的供給又可及時延長船上生活需求的時間。只是淡水容量不足,因此就會常常向其他漁船買多余的淡水加艙。
白天光參與的第一次海盜行動是離島五天后的夜里。
白卵船重新進(jìn)入海域后,那種枯燥、無聊、焦慮重又爬上了白天光的身體與心里。白天光發(fā)現(xiàn)林根本的心理狀態(tài)與自己差不多,但又感覺林根本是城府比自己深得多的人,包括船上的其他六個人,都沒有林根本的城府深。重新進(jìn)入海域后,林根本的話就明顯地少了,也不像一個月前白天光剛到白卵船時的光景。也許那時林根本對白天光而言是一個老資格的成員,又是比較重要的成員,因此對話時有一種優(yōu)越感,這樣的關(guān)系下林根本說出的道理與教訓(xùn)也就相對的多了些。現(xiàn)在的林根本是回到了原先的狀態(tài),仿佛白天光根本就不存在于這條白卵船上。
王大餅則完全不一樣。回到海上后王大餅的情緒最好,也許王大餅本就是靠豪情義氣及本色干海盜的人,只要是個不怕拼命的狠角色就行了,而且這樣的人更有著一種向心力,在這個群體,簡單、義氣、狠、能拼命,就適合當(dāng)老大,計謀什么的一般都是由副手來操心。
王大餅拉王不能陳阿姨陳小六玩撲克,玩梭哈。王大餅的牌局不是斗地主,而是梭哈。梭哈簡單、快捷、無牌技,直來直去,偶爾運用一點心理戰(zhàn),隨時看對方的面色、表情,分辨出到底是虛張聲勢還是真實牌況,來決定押注的增加或放棄。王大餅喜歡這樣的打牌法,但他從不善于使用表情及聲音來制造梭哈迷局,因此總是輸?shù)臅r候居多。
白天光來觀戰(zhàn)時,王大餅手上的牌勢并不佳,但是他憑威嚇與大膽險勝了一局。下一局,王不能與陳阿姨、陳小六很快識破了王大餅善于虛張聲勢的特點,讓王大餅賠了三千多塊錢。也許開始一局是三人讓著王大餅。白天光看出王不能等三人也不是第一次被王大餅叫來玩梭哈。玩梭哈是白卵船上唯一的娛樂消遣。
王阿根是有一只耳朵全聾的人,聽講話時總要側(cè)著頭,因此王大餅在玩牌時不會叫上他。其實白天光也比較提防王阿根,聾人脾氣倔,心也會狠,也特別敏感,常常自尊會被放大,扭曲,但王阿根比常人都要專注,因此,一般情況下王大餅讓王阿根做白卵船上把握方向盤的操舵手。只有在非常情況下,才由王大餅親自操舵。而洋面情況與雷達(dá)觀察,由大副林根本負(fù)責(zé)。
王大餅他們梭哈牌局進(jìn)行到差不多第五局時,林根本從駕駛臺下來,說,我們船的左后方有一條大船正往西北方向駛?cè)ィ烙嬍且粭l貨輪。
王大餅接過林根本的望遠(yuǎn)鏡,看到了一艘懸掛馬來西亞國旗的貨輪從遠(yuǎn)處駛來。打劫這么一條大貨輪當(dāng)然是一項集膽量、冒險與技術(shù)活的海上綜合行動。備梯、備索、挎槍、放艇,靠上去。這些打劫的前奏行為都是容易的。難的是把繩梯掛上高高的貨輪右舷,然后無障礙地爬上去,并搶奪錢財物資。爬掛梯是最危險的,有時船員只要拿一棍子守住掛梯上頭,等爬掛梯的人一露頭,只要狠狠的一悶棍子就能直接把人打回海里。
王大餅掛梯成功,白天光與其余的人一起爬上貨輪。爬船之前白天光猶豫了一下,就這一下的猶豫,被王大餅狠狠地扇了個耳光。這一耳光是白天光有生以來第一次被人打耳光,王大餅這一耳光打得白天光瞬間成了一個白癡,頭腦一片空白,自然而然地跟著王大餅爬上了貨輪。幸運的是貨輪上的人并沒有發(fā)現(xiàn)爬船行動,因為這一帶公海上的海盜密度相當(dāng)?shù)停埠苌俾牭接写庥龊1I洗劫,因此通過這一海域的船只大多沒有什么戒備。而且即使遭遇了海盜,也不像索馬里海盜扣船扣人要千萬贖金,像王大餅他們這一類的海盜也只是搜索些財物帶走。當(dāng)貨輪上船員看到船舷上突然冒出來全副武裝的王大餅他們時,頓時傻了,面對手提AK47的海盜,終于明白過來傳說中的海盜登上了自己的貨輪。林根本說:Don't move,or I'll riddle you with bullets!(不許動,亂動的話就開槍把你全身打出窟窿!)林根本的三腳貓英語就這句說得最流暢。這句已足夠有震懾力!林根本手提AK47,目光凌厲兇狠,白天光第一次看到現(xiàn)實中自己人這副兇狠模樣。林根本的手與AK47的結(jié)構(gòu)如此貼合,它們緊緊地結(jié)合成一體,呈現(xiàn)出手指與槍機(jī)紐結(jié)的可怕冷漠力量。白天光看得牙根發(fā)緊。這時的林根本與前些日子中接觸的林根本判若兩人,林根本那種內(nèi)心蟄伏著的暴力在此刻處于極端的邊界,隨時都會引發(fā)暴烈的子彈瞬間擊發(fā)。白天光一下覺得可怕起來。林根本的眼角余光掃到了白天光,冷漠地說,別想在這樣的時刻充好人善人,沒用。白天光說,我知道,差一點你就殺人了。林根本仍然冷漠地說,不是差一點,我心里已經(jīng)殺人。聽著林根本說話,可怕的平靜、冷漠,白天光感覺冰冷的寒意沿著脊背往上升。同來的陳阿姨、陳小六、王阿根、王大能,也都是狠角色,但在白天光的直覺中,他們都沒有林根本可怕。白天光總覺得林根本不但冷漠、狠毒,而且心里想的比他們都要多,且多得多。
接下來的事是搜刮船上的財物,雖是一條大貨輪,但是能夠到手的財物并不多,包括每個船員身上的現(xiàn)金、手表、佩飾。白天光被王大能指使搬了一箱罐頭。王大餅對著船長與大副說,老子上來也就是要點東西,可你們也太窮了點!雖然明知道船長與大副聽不懂自己的話,但王大餅就愛這么說話。王大餅說,我知道你們聽不懂我的話,但總能聽到我的聲音吧,老子的聲音也能嚇唬死你們!林根本說,你的聲音算個鳥,還不是靠手中的AK47,它比什么話都管用!林根本對王大餅說,這次收獲并不大。王大餅說,能帶的東西全帶走。
五
王大餅他們洗劫了大貨輪后回到白卵船上,大家亢奮了好些天。這些天王大餅不是玩梭哈就是喝酒,陪王大餅喝酒的基本是王大能、王不能、陳小六、陳阿姨幾個,玩梭哈也是這幾個。林根本不喝酒,也不參與梭哈牌局。白天光參加了幾局梭哈,但是王大餅不喜歡白天光的風(fēng)格方式,幾次之后不再叫白天光參與梭哈,喝酒自然也不叫了。這樣,白天光顯得比他們更加無聊。在茫茫大海上,整日無所事事,就船上屁大點的活動空間,白天光感覺這種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奇怪的是林根本卻是一如既往地安靜,沒一點點無聊與煩惱的表現(xiàn),就好像是船上一個極其普通的物件,沒有生命、沒有靈魂、沒有歡樂、沒有煩惱與痛苦。林根本唯一的動靜就是每天一次的AK47拆卸、重裝,然后舉槍往天空掃射一梭子彈。在林根本掃射子彈的過程中,王大餅他們要么在喝酒,要么在玩梭哈,所有的人都無動于衷。可見林根本這樣做于他們而言已經(jīng)習(xí)以為常了。
林根本端著AK47對空掃射過后,白天光感到很不安。與王大餅他們不一樣,白天光是白卵船上的新人,對船上的人與事相對敏感。白天光想,林根本這么理性的人,竟然會拿著AK47對空掃射,這得有多大的負(fù)面情緒郁結(jié)在心里。有著精湛槍術(shù)的林根本,又這么有心思,而王大餅又這么仰仗他,他要是想在這白卵船上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就能輕而易舉地做到。如果這件事是殺人呢?太可怕了!白天光想到這,突然害怕起來。他的感覺與王大餅他們不一樣,他對白卵船上每一個人都是敏感的。雖然白天光被綁到白卵船上的最初是林根本關(guān)照他,越是這樣白天光就越覺得可怕。要是一個與自己關(guān)系最好的人是一個心里狠毒時刻想著要殺死某個人的冷血無比的家伙,想到這里,白天光覺得身上涼涼的,冷汗都出來了。
三天后,白天光患了重感冒,船上的常用藥就是幾盒泰諾,泰諾唯一的作用是止一下鼻塞,不一會又恢復(fù)原癥狀。服了泰諾的白天光仍然高燒不退,昏昏沉沉,整個人飄著的感覺,原本在船上時就一直處于海面的起伏之中,現(xiàn)在加上重感冒就感覺更加飄了起來,白天光有點虛幻感。白天光重感冒的幾天里倒是林根本來看過他幾次。林根本說是來看白天光,白天光的感受卻是冷嗖嗖的,他怕林根本的眼神,不動聲色,冷漠,狠惡。他怕自己燒迷糊了,被扔進(jìn)大海里。當(dāng)林根本的臉龐出現(xiàn)在正躺著的白天光上方時,白天光很害怕。他感覺林根本就是來看自己疾病的進(jìn)展,等著自己被燒昏迷,這樣他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把自己扔進(jìn)大海。而這樣,王大餅一眾人定會贊成林根本的做法。現(xiàn)在船上包括白天光共九個人,在這個數(shù)字的海盜群體,一個人的增減是件值得考慮的事,但還沒有到一個人的增減是大事的程度,對這個群體來說,減了一個,就再增一個,這也是容易的事。當(dāng)然,若是這個群體少到總數(shù)四五個人時,則增減一人是一件很大的大事。因此,就目前的狀況王大餅也并不對白天光上心,對他與他手下的人來說,就是白天光沒了,也不會有多少影響。白天光迷迷糊糊、似夢非夢、似醒非醒,醒來之后回想起,總好像聽到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沒聽到。如果有聽到的話,好像是林根本與王大餅討論是不是把白天光丟進(jìn)海里的話,但是白天光醒來后印象全無,也就是說,這些話,林根本與王大餅可能說過,也可能沒有說。
當(dāng)然與林根本不同的是,實際上王大餅的原則是不出命案,目的是不出命案相對而言陸上或水上公安的打擊力度會不那么緊迫,最重要的事是給各個家里人知曉大家都活著,無事,家里也就會放心了。白天光高燒退了后,也就多了一樁心事。白天光總是想著在自己似醒非醒的狀態(tài)下林根本與王大餅說的那些話,雖然無法確定林根本說沒說過這些話,雖然另一個可能是自己的幻覺與幻聽,但是它已經(jīng)是一樁明確的心事裝在白天光的心里了。
林根本從白天光對自己的戒備中已看出了白天光的心事,知道他是害怕自己的。林根本說,白天光,你那點心思是瞞不過我的,你怕我什么呢?你是不是怕我把你扔到大海里喂魚去?
白天光說,你會嗎?
林根本說,這決定權(quán)在你不在我。
我有什么決定權(quán)?
取決于你是不是能夠安心聽話與做事。
我也做不了什么事。
你至少不要做相反的事。
白天光說,我能做什么相反的事呢?我也不可能做與你們相反的事。
林根本說,不要說你,就是我,有時也會有想做相反的事的沖動。因此你說的不是你的真實想法。
與林根本這樣的人精對話,白天光是處于下風(fēng)的。
因此白天光不再說什么,也知道即使自己有過做相反事的沖動,但也絕對是做不成的,在白卵船上,單憑自己一個人不可能做得成任何與這船上的人相反的事。
白天光感覺林根本仍然是一個捉摸不透的人。
如果林根本不是自己直覺判斷中的人,那么,林根本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白天光總是覺得,這個冷漠、狠惡、超級理性的人,在白卵船上,不管怎樣,都是一個可怕的存在,雖然王大餅也一樣的狠惡、冷漠,但在白天光看來林根本比王大餅更加可怕。
六
白天光的重感冒終于好了,卻傳染給了王大餅。
得了重感冒的王大餅脾氣極端暴躁,不但把船上的物件摔得到處響,而且逮住誰都要惡狠狠地罵上一通。
狗生的王大能、王不能!
狗生的陳小六!
狗生的白天光、林根本!
狗生的陳阿姨!
這幾天王大餅唯一沒罵過王阿根,因為王阿根這幾天從不到王大餅的身邊轉(zhuǎn)悠,王大餅也好像忘了有王阿根這個人一樣。
王大餅的感冒越來越嚴(yán)重,發(fā)燒,摸額頭有點燙手。連續(xù)吃藥效果也不大。林根本說,其實問題不大,過幾天就好了,感冒嘛就這樣。
慢慢地,海上起了風(fēng),聽收音機(jī)里的一周預(yù)報,無太平洋臺風(fēng)消息,就現(xiàn)在這樣的風(fēng),就算再增大些,也問題不大。只是海浪的波長增長后,船只的起伏與搖擺程度也隨之加大。只要不來臺風(fēng),王大餅是享受這種海上顛簸的。每當(dāng)這樣的海風(fēng)到來,王大餅就會躺在船上享受拋起又跌落,跌落又拋起,無窮無盡的往復(fù)循環(huán)的起起落落。王大餅常常說,狗生的,沒有起起落落沒有顛簸那還算是在海上嗎?王大餅常常罵的是大海本身,狗生的,這海上的日子簡直不是人過的!狗生的,你們不要說這海,不要說海上的無聊!王大餅罵人是常態(tài)邏輯,往往是后面對前面的自我否定。王大餅是一個奇怪的矛盾體。現(xiàn)在處于重感冒中的王大餅,雖然罵遍了白卵船上的人,雖然罵得沒了氣勢,缺乏了平時的那股罵人的狠勁,但是罵人時的那種惡毒勁仍在。
王大能與陳小六因小事杠上了,事由是陳小六潑掉喝剩的涼開水時被王大能看到了,王大能說,這么大手大腳的也不知道節(jié)約用水。陳小六見王大能這么說自己就不高興了,說,這么屁大點的事也要管,你是我親生父母嗎?
王大能說,在這條白卵船上,我們大家的命都是捆在一起的,說你一句又怎么了!
陳小六就完全不認(rèn)同王大能把這不是事的事上升到這么重要的程度來說,頓時暴怒了。
陳小六怒吼起來,你他媽的別沒事找事,別以為你兩兄弟在船上,別人就不敢怎么的,老子不怕。
王大能也高聲起來,我說錯了嗎?你陳小六要是不在白卵船上,老子才懶得理你呢!
王大能的話音未落,陳小六就撲了上來,迅速出手,狠狠地給了王大能一拳。這一拳把王大能打得鼻血亂飆,兩人就互相扭打在了一起。這情景剛好被林根本看到了,林根本也不勸架,只在旁邊冷漠地看著他倆扭打。王大能完全處于下風(fēng),根本招架不住。陳小六一點都不留情,每次出手都非常兇狠,雖然王大能也是強(qiáng)悍的,但是陳小六卻是不要命的,自己雖然也不斷被王大能的重拳回?fù)簦瑓s依然緊扭著王大能狠打,拳拳擊打在王大能的頭部。遇到陳小六這么狠的出手,王大能唯一能做的就是拼了命地反擊。最后的結(jié)果是兩敗俱傷,都被對方打趴在船艙里。
林根本說,我看你倆打得還不夠狠,沒傷,也沒骨折,還都好好的,海盜打架得用刀子捅才是,得捅出滿艙的血才是。白卵船上的任何人打架,我都不會攔著,不會勸架,哪怕是真的打死。
王大餅說,我倒是希望你們經(jīng)常互相打打架,打折打傷都沒關(guān)系,我不要大家友愛團(tuán)結(jié),我要的是你們每個人都像狼一樣!
白天光聽了林根本與王大餅的話,雖然不吃驚,但心還是沉了一下。白天光知道,白卵船上的人,遲早一天都會成為可怕的魑魅魍魎,這之中當(dāng)然也包括自己。到最后,白卵船將成為一條可怕的死亡之船。白天光想,難道林根本不知道嗎?林根本當(dāng)然明白得很,但這正是林根本想要的,也是王大餅想要的,他倆是想這船上的人都成為互相的仇人,這樣才有動力生存下去,雖然這樣很殘酷,但對白卵船是好事。
林根本看出了白天光的心思,林根本說,白天光,你不要覺得奇怪,白卵船在大海上孤立存在,無親無戚,不僅無任何支援,反而面臨時刻被剿滅的危險。
白天光沒接林根本的話。
白天光想,白卵船確實如林根本說的那樣,每個人的危機(jī)感也因此而來,行動的動機(jī)與動能也因此而來。
王大能與陳小六兩個人的互毆,反而使王大餅的暴脾氣消掉了許多,雖然王大餅還在重感冒中,但罵人的次數(shù)明顯地減少了許多。
白天光吃過晚飯早早地在船艙里睡下。十二點左右,他在睡夢中被驚醒,睜開眼睛看到了王阿根坐在邊上。外面風(fēng)有點大,噪聲也大。
王阿根壓低了聲音說,白天光,你知道我為什么找你嗎?
白天光說,有事白天不說,偏要這半夜三更里說?
我在這船上有話沒人說,所以想找你聊聊。
你知道我就是能夠說話的人嗎?
就是想找你聊聊,感覺我可以與你說。
我要是把你的話傳給王大餅或林根本呢?
你不會的,所以我才跟你聊。
好吧。
我來這船上一年半了,這一年半有多么難過你知道的。
是的,我知道,熬過來確實不容易,但是你就跟我講這點屁事嗎?
這不是你我第一次說話么,也得熱絡(luò)一下再說其他才是。
這時白天光坐了起來,說,看你王阿根平時不聲不響,半夜里說話倒是很有門道啊。
王阿根與白天光的說話慢慢地進(jìn)入了正題。這正題遠(yuǎn)不在白天光的意料之中。因為白天光想不到在白卵船上第一個與自己說這些話的人不是林根本,不是王大能王不能,不是陳小六陳阿姨,而是平時悶聲不響的王阿根。
王阿根把聲音壓得更低了,說,你想不想回到大陸上去,想不想回到自己的家里?
白天光聽到王阿根說出這樣的話,心想,這應(yīng)該是王阿根的真實想法,但又有點不放心,要是王阿根是林根本或王大餅派來探自己底的人呢?自己要是順這話進(jìn)去,商量回大陸的事情,那不是找死嗎?但是,如果不與人合作,或者僅僅只是自己與王阿根兩個人,想逃離白卵船是不可能的。
白天光說,在船上待得好好的,而且來錢也容易,干嘛要回去?我雖然剛到船上時很想逃走,但是現(xiàn)在我安下心來了,不想回去了。
王阿根聽了,好長時間沒說話。白天光想,他是在判斷我這句話的真假嗎?當(dāng)然王阿根很快就判斷出了白天光這句話是虛假的。王阿根并不是一個平淡的人,他其實是一個會深思熟慮的人。
王阿根說,你別跟我說這些假話了,你以為能糊弄得了我嗎?當(dāng)然,你也可能是怕我來套你的話,所以用這話來試探我。
我對你說的事不樂觀,你我根本就不可能從這船上逃出去。白天光說了真實的想法。
王阿根說,這不著急,一是先要想出最可靠的辦法,得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二是有了辦法,還要有機(jī)會;三是就只你我還不夠,至少還得有一人加入才行。
白天光心里是認(rèn)可王阿根的說法的,心想,王阿根確實是一個能做事的人。但白天光的表態(tài)并不積極,說,你說的三條當(dāng)然很有道理,真要是三條齊備了離成功就不遠(yuǎn)了。
王阿根說,不是遠(yuǎn)與近,而是要鐵板釘釘,要絲毫不差。
白天光說,這八字還沒一撇,說這話太早了。
王阿根說,是的,但是要有這個思路,哪怕什么都還沒做,一定要事先就想好。
王阿根說,你想想看,白卵船上還有誰有參加這件事的可能?
白天光說,我想到一個人。
王阿根說,你是不是想說林根本?
白天光不置可否。王阿根接著說,只有他參加了,這事才有可能,如果沒有他參加,那么這事就難成,或許根本做不成。
白天光說,你這么肯定?為什么?
王阿根說,我到白卵船上這么長時間,肯定知道這船上最有心計的就是林根本。
白天光說,那你有把握他會參加嗎?
王阿根說,沒把握,林根本這個人太讓我捉摸不透了。
七
自此后,白天光對林根本開始抱有幻想,這幻想就是王阿根所說的,如果林根本能夠加入,那這事肯定能成了。要是讓白天光來策劃這件事的話,那么應(yīng)該具體到什么樣的一些步驟呢?比如三個人對付五個人雖然力量對比有點懸殊,但三個在暗處,五個在明處,這樣一來在暗處的三人是有優(yōu)勢的。比如在五個人比較集中的時候,可以突然用槍頂著,然后把他們捆綁起來。或者用更下三濫的手段,就是往飯菜里加蒙汗藥,麻翻之后再捆上。或者還有其他辦法,但是白天光的思維僅僅到此為止。
這一夜之后,王阿根與平時一樣,言語不多,沒什么與平時不同的其他跡象。即使白天光有意識地與王阿根說話,王阿根也幾乎不理不睬。
越是這樣,白天光越是心安,這說明王阿根是一個不輕易外露而心思縝密的人,這樣的人做事會非常可靠、有效。白天光想,王阿根甚至比林根本更加深藏不露,也更加值得信賴與依靠。
白天光也更加關(guān)注林根本,隨時隨地觀察林根本的話語、表情、動作,以此猜測林根本心里所想的。此時的白天光恨自己觀察能力太弱,幾乎揣測不出林根本的所思所想,要是能被輕易揣測出心思那還是林根本嗎?雖然觀察效果微之又微,但白天光不會放棄繼續(xù)觀察林根本的一切。
氣象臺發(fā)布了今年第九號臺風(fēng)的消息,在東經(jīng)131度、北緯17度已經(jīng)生成,初始風(fēng)力每秒18米,8級。雖然臺風(fēng)離白卵船的海域還很遠(yuǎn)很遠(yuǎn),得五六天才會經(jīng)過這里,但是人在茫茫大海上,對一切即將到來的危險都要及早作出預(yù)防。大多漁船都會提前駛進(jìn)避風(fēng)港避臺風(fēng),以減少損失,確保人員安全。也有少數(shù)漁船鋌而走險,在臺風(fēng)前魚群最活躍的時候捕撈最后一網(wǎng)。王大餅并不急著去避風(fēng)港避風(fēng),每當(dāng)在這個時候,他就會干最后一票,就如漁民的最后一網(wǎng)。好處是在臺風(fēng)的前兩天,幾乎所有船只都進(jìn)避風(fēng)港了,包括漁政船、邊防巡邏艇也一樣。
王大餅他們這一票干得很輕松也很成功,搶到了錢財物資。搶到了貨物的白卵船開足馬力趕在臺風(fēng)來臨前回到了先前的那個島嶼。雖然臺風(fēng)的預(yù)測路線圖不經(jīng)過這個島嶼,但還是受到了臺風(fēng)外圍的影響。
來避風(fēng)的船只多,酒店里就更加烏煙瘴氣。醉酒的、互罵的、打架的,這些在臺風(fēng)天是常事。隔著房間的木門,白天光聽到酒店走廊里兩個閩南口音的在互罵。接著就開始傳來動手的聲音,咬緊牙關(guān)的搏擊聲,刀子在空中急速劃過的聲音!先是其中一人悶叫了一聲,仿佛布匹被撕開,最后傳來另一人的一聲慘叫。兩人斗毆時,王阿根在另一端目睹了全過程。
事后,王阿根向白天光描述了這兩人斗毆的過程。斗毆的是同一條船上的兩個閩南人,一人被捅了腰部,一個被挑了腳筋,兩敗俱傷。在這樣的天氣、在這樣的場景,往往一言不合就開罵,一開罵就動手,一動手就是亮刀子,惡、狠、致命。這樣結(jié)下仇恨的兩個人,還要繼續(xù)在同一條船上相處,其后果完全不可預(yù)測。
王阿根說,知道嗎?在海上,斗狠閩東南人第一,其次是廣東潮汕人,再就是浙江溫臺人。
王阿根又說,除了我與林根本是福建的,你們?nèi)钦憬瓬嘏_人。
白天光說,那么你也是一個兇狠的人了。
王阿根說,那看遇到什么事。
白天光說,我知道,力量爆發(fā)肯定與自己的切身事情有很大關(guān)系。
王阿根說,我見過打斗打死人的,像我們這樣的情況,打死人也是一件正常的事,這海上沒法院、沒公安,就是有,你敢去嗎?不敢去,所以一切只能靠力量與兇狠取勝。
白天光說,別忘了,還有智慧。
王阿根說,你說的智慧,那是頭頭腦腦們的事,是一伙對一伙的事,個對個,靠的是力量與兇狠,靠的是豁得出去自己的一條命。
王阿根說,不說了,走吧,帶你洗腳去。
王阿根帶白天光來到了一個良子足浴店。
白天光問洗腳妹,大陸上到處是良子足浴店、足浴中心,想不到連鎖開到了這太平洋的小島上來了。
洗腳妹說,我們這家店與大陸的良子毫無關(guān)系,是山寨的,是假的良子。
王阿根對白天光說,一樣的洗腳,你管他真的還是假的呢,洗就是了。
白天光其實并不喜歡洗腳,在家里的時候,在外面與朋友吃排檔喝酒晚了,就去足浴店里洗個腳,好回家能夠放松睡覺,但白天光經(jīng)常借故不去而直接回家。白天光對洗腳時洗腳妹搓腳極為不適,他怕癢,一搓腳,心臟就繃得緊緊的。
店外面的風(fēng)雨漸漸加大。洗腳妹高興地說,臺風(fēng)天了,避風(fēng)的船多了,人也多了,這幾天的生意就好了。
王阿根說,臺風(fēng)也是好事,至少可以在這島上好好休息幾天。王阿根很享受洗腳的過程。閉目、舒氣,一副神游八極的樣子。外形看上去粗獷的王阿根肯定是一個內(nèi)心極其細(xì)致的人,細(xì)致是好,但是太細(xì)致了就會影響到行動的果敢與效率。
八
臺風(fēng)過后重新出海,船上一直很平靜。王阿根與平時沒什么兩樣。好幾天來,王阿根再沒提起說過的那件事,仿佛從沒說過那件事。白天光因此對王阿根有了幾分戒心。他想,王阿根會不會暗中聯(lián)合別人出賣自己,干掉自己以邀功獲利?在這樣的白卵船上,任何事情都不能想得太好,凡事往最壞處預(yù)測,這是對處境的警惕與對最壞情況的預(yù)防。
白天光也基本不說話。
白天光的心思都在王阿根的眼里看著。自從白天光與王阿根有過密謀之后,白天光的一舉一動都進(jìn)入了王阿根的視野之中。這讓白天光在船上感覺很難受,還不如原先的那些日子。那些日子里,盡管白天光也是難受的,但遠(yuǎn)沒有現(xiàn)在這樣難受。現(xiàn)在是更加地提心吊膽,萬一王阿根不再信任自己,那后果與危險比原來不知會增加多少倍。使得白天光防備王阿根的心思比防船上其他人更費精力。
白天光決定還是要毫無保留地信任王阿根。只有毫無保留地信任王阿根,才能獲取王阿根同樣的信任。原先的密謀雖然都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礎(chǔ)上,但那種信任還僅停留在互相需要、互相嚴(yán)密做事的基礎(chǔ)上,還不夠真誠,這樣的唯目的論雖然某種程度上有利于成功,但出于純粹目的論時,萬一有個變數(shù)就極易身首異處,所以白天光決定與王阿根進(jìn)一步發(fā)展,其目的是為了自己的安全。
白天光雖然心里是這么決定的,但是因這件事確實是關(guān)乎生死存亡的大事,一不小心露了餡,就完全沒有挽回的余地,就是說到那時肯定得葬身大海。
白天光沒法不這樣想,越是不想這樣想,卻越會這樣去想。
這樣一來,白天光就遠(yuǎn)沒有了王阿根那樣的沉著與穩(wěn)定。
白天光越來越覺得自己與王阿根不但根本搞不定林根本,而且覺得林根本有意無意地注意到了他倆的一舉一動。王阿根卻不一樣。王阿根說,你心理素質(zhì)太差了,是干不了大事的人,我很后悔與你商量這個事。
白天光說,性命不是小事,你看林根本,就不可能成為我們的人。
王阿根說,林根本成不了我們的人,但我們可以利用他。
白天光說,怎么利用?
王阿根說,走一步看一步,但步步不能踏空,要絕對。
白天光說,我是沒有信心,這事不是演戲,不是玩兒,是搭著自己性命的事。
王阿根說,不要說什么性命不性命這話,在這船上了,誰又能保證平安無事,說不定哪天就被扔到了大海里。你要知道,有時這樣做并不需要什么理由。
白天光說,我知道,時刻都有被扔進(jìn)大海的可能,其實也包括你。
九
林根本發(fā)給每人一個小紙盒,每個盒里裝著一盒蓮花清瘟,一瓶布洛芬,一盒泰諾。
林根本說,全世界都是新冠,總有一天新冠會傳到我們船上,到時會用到這些藥。
白天光拿了紙盒后就有一種感覺,心想,全船人死光才好。這心思卻被陳小六隨口說了出來。
陳小六說,哪一天船上人全死光了就好了。
林根本說,死還不容易嗎?
陳小六說,他媽的,死不容易,活也不容易。
王大餅說,屁話。都想什么呢,死不了!
自從發(fā)了藥之后,大家心里開始別扭起來。吃飯如廁行事說話,突然間就感覺到怪怪的。大家之間的話比平時少了許多。王根本,陳阿姨,包括王大能、王不能,基本上不說話了。
到了夜里,白天光睡不著,想,這藥會不會是林根本的一個詭計呢?用以探測船上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或者探測每個人的情緒?林根本做事有時太令人捉摸不透了。林根本的可怕就在這里,你根本就猜不透他的意圖。
白天光關(guān)注著王阿根,王阿根平靜得很,也沒有要與白天光說話的意思。白天光也不知王阿根心里在想些什么。他不再想前段時間說過的事了嗎?白天光想。
這幾天白天光越注意王阿根,王阿根越沉默。王阿根肯定也注意到了白天光在注意自己,但是他就是沉默不語。
白天光想,這個王阿根,原先說過的話就當(dāng)放屁了嗎?萬一他回過頭去,告自己一狀那可就死定了。想到這,白天光打了一個哆嗦。轉(zhuǎn)而又一想,不可能,王阿根這樣不是把他自己置于死地嗎,王大餅、林根本能信任他嗎?這樣一想,白天光又放下了心。
這幾天仍然是吃了睡,睡了吃。王阿根仍然是沉默。白天光試著與王阿根說話,王阿根當(dāng)作沒聽見,不回應(yīng),不說話,仍然是死一樣的沉默。
這期間,白卵船在海上補(bǔ)給了一次物資,食物、淡水等東西。
入夜,白天光想,王阿根為什么這么沉默?他遇到什么特別的事了嗎?或者他根本就放棄了原先的想法與打算?
白天光想,自己原先對林根本的策反設(shè)想是多么的不靠譜,多么的幼稚可笑。這樣一想,不禁倒抽一口冷氣,幸好沒有試探實施,不然的話,自己包括王阿根早被投海喂了大魚。這個事,真是容不得絲毫的偏差。
這樣一來,白天光徹底放棄了與王阿根商討的想法,也理解了王阿根的這種改變與狀態(tài)。
王阿根仍然沉默,一切都回到了原先的狀態(tài)。
下午,王阿根終于與白天光說了一句話,還是老老實實待在這船上好。
白卵船上終于迎來了一波新冠。先是林根本嗓子疼,全身肌肉持續(xù)酸疼,繼而發(fā)高燒。那紙盒里的備用藥根本沒有療效,起不到任何作用。林根本還用抗原測試了一下,果然是陽性。
王大餅說,測試個鳥啊,怕什么,死不了人。
林根本喘著氣說,這是我這一輩子最難受的時刻,寧愿死了。
看著林根本臉上痛苦的樣子,白天光心生恐懼,要是林根本真的死了,那么白卵船上會發(fā)生什么樣的變化呢?
林根本的咳嗽越來越厲害,這期間,王大餅、陳阿姨、王大能、王不能、王阿根,白天光,大家都先后得了新冠。一開始都是嗓子眼刀割一樣地痛,接著陸續(xù)發(fā)燒、酸痛、迷糊。
林根本的病情更加嚴(yán)重,臉色發(fā)青,嘴唇干裂。除此以外,嚴(yán)重程度就算陳阿姨了,陳阿姨很怕死,不斷地問,我會不會死啊,會不會死啊。林根本則明確地知道自己狀況很不好,生的希望已不大,但他的話很少,只是時不時從眼睛里透出微光,絕望,黯淡,隨時要熄滅的樣子。大家都看出林根本很快就將不行了。只有王大餅還對著林根本喊,林根本,你個狗生的,你不會死,一定會好起來的。林根本聽到,硬擠出一絲苦笑,隨即又回到迷糊狀態(tài)。
接著,白天光自己包括王大餅、王大能、王不能等人也都到了林根本前幾天的那種狀態(tài)。有好幾個人都吃不下飯,喝水也困難。
白天光想,這次自己真的會死么?重感冒才過去沒多長時間,又緊接著感染了新冠,別說在這條船上,就是在大醫(yī)院也不一定能扛得過去。白天光看東西有些發(fā)虛,虛弱到了極點。
得了新冠的王大餅也很難受,他又像上次重感冒那樣開始破口大罵。這次白天光已經(jīng)見怪不怪了。王大餅邊罵人,邊摔東西,一個一個把大家罵了個遍。白天光想,王大餅這次死得了嗎?林根本已經(jīng)快撐不住了,如果林根本真的死了呢?林根本可是船上的二號人物,他于白卵船而言,甚至比王大餅更重要。王大餅是靠逞匹夫之勇與舍得拼命當(dāng)上老大,他是全靠了林根本一起掌控了全船人。
王阿根對白天光說,看來林根本熬不過這次了。
白天光見王阿根這次主動說起林根本,不知他肚里是不是又要起什么計劃。想要繼續(xù)先前的打算嗎?在白天光看來,王阿根城府甚至比林根本更深,更不可測。
白天光說,可能熬不過去的不止林根本,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過去,實在是太難受了,就像要馬上死去一樣。
王阿根說,我也一樣,全身酸疼得一塌糊涂。
林根本真的不行了。
他最后張了張嘴,想交代什么,也沒能夠說出來,就閉上了眼睛。
王大餅最悲傷,哭著說,林根本你他娘的就甩下兄弟們走了,也太不地道了,太不夠哥們了。
大家都沒力氣,儀式很簡單,王大能、王不能用床單裹了林根本,又用繩子捆緊,放到海里,任他漂走了。
十
白天光一覺醒來,又聽見了王大餅在破口大罵。這次是罵王大能、王不能兩兄弟。王大餅罵,你兩個狗生的,平時吃老子的喝老子的,這次竟然綁老子!
白天光聽了,心里一個激靈,難道王大餅被王大能兄弟倆控制了?
這時,大家都來到了甲板上。王大能對王大餅說,我倆早就想綁你了,只可惜沒機(jī)會,這次大家都得了新冠,我倆才有機(jī)會綁你。
王大餅說,怪我沒聽林根本的話,他叫我小心你兄弟倆,叫我先下手,沒想到你倆比我先下手,太惡毒了。
王不能說,惡毒就惡毒吧,不惡毒我們還不是像狗一樣任你辱罵指使。
王大能轉(zhuǎn)而問王阿根,王阿根,你支持我兄弟倆吧?
王阿根說,其實我心里也一直有與你倆一樣的想法,干掉林根本、王大餅,我還與白天光暗中商量過這事呢。
白在光說,正是正是,太想有今天的結(jié)局了。
王大餅又破口大罵,我他媽真是瞎了眼,白養(yǎng)了你們這群白眼狼。
王大能說,你有人命在身,我們沒背過人命,回陸地上我們與你是有根本的區(qū)別的,我們還能好好地生活。
王不能這時用刀抵著王大餅的脖子,說,信不信弄死你?只要我們不說,沒有人會知道你的死,你就會像條死狗一樣被扔到了大海里。
王不能說了這話后,王大餅終于停止了辱罵,沒有了威勢,像一條臨死的魚只翻著一雙白眼。
白天光也后怕,回想當(dāng)時幸好沒與王阿根一起去接觸林根本,不然的話事情一定會往相反方向發(fā)展,自己會與王阿根一起被扔進(jìn)大海里喂魚。
現(xiàn)在這條白卵船上都聽王大能兄弟的。白天光想起,王大能兄弟倆會說臺州話也會說閩南話,所以他倆與一船人相處得還都不錯。加上兄弟倆的實力,現(xiàn)在一船人自然而然地都聽他倆的。白天光還有一個疑問,王阿根與林根本都是福清同鄉(xiāng),為什么兩人基本不談話不聯(lián)絡(luò)?也許是林根本太敏銳太有本事,太能夠洞悉別人的心理,所以王阿根不敢與林根本多接觸。
白天光回想起剛到白卵船時,對王大能兄弟倆并沒多少好感,想不到偏偏是他們兄弟倆救了大家的命,解了大家的套。船上還有一個得新冠死去的人是陳阿姨,王大能兄弟倆也像對林根本一樣為他舉行了極簡單的海葬。
這一天,白卵船改變了航向,向玉環(huán)方向駛?cè)ィ抢锸峭醮竽堋⑼醪荒苄值軅z的家鄉(xiāng)。
而王大餅則越來越絕望,他又開始了破口大罵,但是誰都不理他,就當(dāng)一條狗在狂吠。
大家的新冠也都差不多到了尾聲,心情也在不斷地轉(zhuǎn)好。
白天光突然覺得,這半年多時間,就好像做了一個十分荒誕的夢。之后,他又突然驚醒,回到了現(xiàn)實之中。回想起來,一切都那么恍惚、虛幻,不知身在何處,不知做了什么,不知開始,不知結(jié)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