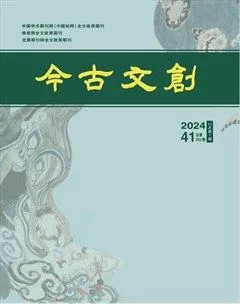認知與本體
【摘要】“道德形上學”這一概念本身具有回應西方哲學質疑、澄明儒學中超越性層面的含義。道德形上學的超越性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以“認知決定模式”為特點的獨特認知機制,所謂“認知決定模式”,即以認知層次的提升消解本體論的理論取向,這一思想傳統可追溯至中國佛學的般若中觀與“一心開二門”,其核心便是超越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另一方面則是“以天論德”的本體論層面,儒學的“生生”本體在創生萬物的過程中生動開展著自身,而人亦能以自身之仁德參天地之化育,進而呈現出“生春氣象”。因此,道德形上學是會通天人之學,從這兩個維度探究其特征,正可以窺見道德形上學徹上徹下、春風化雨的獨特意涵。
【關鍵詞】認知;本體;一心二門;心統性情
【中圖分類號】B2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41-0070-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19
一、道德形上學的認知決定模式
民國以降,新儒家學者談及“道德形上學”的概念較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回應西方哲學家對于中國哲學(尤其是儒學)缺乏超越性的質疑,其本義便是澄明儒學中隱而未發的本體論層面。其中不乏立論深刻的學者,如熊十力依唯識學唯識無境之理,認為所謂具有超越性的“天”也是心所構建的現象而已,因此天人本無二,離心更無所謂天。“天不人不成” ①,道德形上學的旨歸在于以人之實踐證成天之德性。牟宗三更是以康德哲學會通陸王心學,以坎陷論、兩層存有論等證明道德之為本體的可能,力圖構建完善的道德形上學體系。不同學者對于這一概念的論述方式不同,但他們在同一觀點上達成了共識,即儒學并非沒有超越的存在論基礎。這一道德本體發端于孟子的本心,孟子通過“以天論德”的方式,將道德與超越之天相關聯,論證道德本體的超越性。這一“道統”延續至宋明理學,雖程朱、陸王就“理”“性”“心”等范疇意見殊異,但不可否認,他們都確立了一形而上的充滿道德色彩的本體基礎。
然而,道德形上學依然有時會被忽視,其原因在于它過早地超越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而將一形而上的本體落實到實踐層面,而這徹上徹下的體系本身因其并未特別地彰顯超越特質而遭到否定。在西方哲學中,康德孤明先發,提出實踐理性的重要性,認為道德比知識更為基礎,且人只有在道德法則中才能貫徹意志的自主性,因此道德成為人類尊嚴之體現。康德這一如此彰顯人類意志的理論,使他成為首個以高度形而上獨立性賦予人類的西方哲學家,甚至可以說,他粉碎了哲學上歷史悠久的重智主義傳統。然而,這并不影響康德成為一個道德上的消極主義者,他不認為人能夠真正克服感性官能和意欲的墮落傾向,因而只能永恒地投身于自我完成的過程之中。所以,康德并不會認可儒家的“孔顏樂處”,在康德的實踐哲學中,踐行道德并不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相反,“道德”是人性中善與惡交互掙扎的場域所在 ②。因此,在人性中體現的是“原始的二元性”,這種二元性不僅是實然與應然之間的,更是規定了人只能于無限對有限禁囿的框架中實現其意義,因為“意義”本就是基于“目的”而言的,而目的便昭示了那原始的二元性、那對完滿的趨向與無法臻于智慧的永恒矛盾。
于是,作為一個眾所周知的二元論者,康德認為所有宣稱人能實現與超越之物冥合的一元論都只是密契論者的狂囈,那些把人類靈魂神化的努力歸根到底是一種虛榮的產物。據此觀點來看,道德形上學的合法性便是可疑的。但并非如此,因為中國哲學中的“道德形上學”,并不只包括本體論層面,它其中有更為重要的“認知決定模式”,而這一隱藏的傳統蘊含著以認知的提升消解本體論之困境的理路。所謂“認知決定模式”,是指在中國文化的眾多關鍵點處,最為根本的并非是本體論層面的建構,而是認知層次的提升。這一特性可以溯源至佛學領域的“一心開二門”思想,《大乘起信論》提出,“真如門”與“生滅門”的差異只在于認知不同而已。所謂前念著境即煩惱,后念離境即菩提,代表常樂我靜的真如與代表煩惱執著的生滅,二者的差距只在一念,因此,人是可以憑借認知獲得超越性的。同樣的,在道家,作為《莊子》內七篇核心的《齊物論》,其旨歸也是落實在認知領域的。“萬物一齊”的觀照就建立在現象界看似千差萬別的事物中,結尾處“萬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更是暗示認知層面的徹底悟解可以超越時間之為先天直觀形式的限制。“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通為一”的背后隱含著“以道觀之”的主體,“以道為樞,以應無窮”的逍遙境界后也赫然彰顯著一心無滯礙的真人形象。而儒學之“道德形上學”自然繼承了這一“認知決定論”的傳統,道德本心便是溝通認知與本體的中介,更是被設定為認知的最高境界。我們會發現,這一“認知決定論”是即現實、即超越、即煩惱、即菩提的。它并未強調現實世界與永恒國度的矛盾,而是將視野轉換,于喧囂的塵世中證見近在咫尺的天國。于是我們看到,認知上的超絕消解了本體的超絕。因此,并非儒家只關注現實層面,而是只有在現實層面才能體現這一簡約貫徹的本體,而這就是道德形上學的現世性格所在。
中國哲學史上的認知超越傾向在佛學般若空宗首次得到了系統的說明,而后隨著佛性論的發展,人性與佛性相會通,暗合了儒學天人合一的傳統。最終朱熹以“心統性情”完善了道德形上學在認知領域的學說,自然也就完成了對這一傳統的承繼。
二、從“般若中觀”到“心統性情”——認知決定模式的發展脈絡
(一)般若中觀的非本體論傾向
以認知超越本體,這種傾向肇端于僧肇的《肇論》。在當時六家七宗競相格義的背景下,人們通常將佛學“空”的思想理解為道家“無”之本體。在這種背景下,僧肇提出“即物自虛”“非有非無”。與前人理解不同的是,“有生于無”的無是本體,而“非有非無”的空則赫然呈現出非本體論的傾向。僧肇在《不真空論》中論述道:
尋夫不有不無者,豈謂滌除萬物、杜塞視聽、寂寥虛豁,然后為真諦者乎?誠以即物順通,故物莫之逆;即偽即真,故性莫之易。性莫之易,故雖無而有;物莫之逆,故雖有而無;雖有而無,所謂非有;雖無而有,所謂非無。如此則非無物也,物非真物;物非真物,故于何而可物。故經云:“色之性空,非色敗空。”以明夫圣人之于物也,即萬物之自虛,豈待宰割以求通哉?③
此處僧肇說得很明白,所謂“空”并不是萬有之外另設一超絕的本體,而是萬物本身就是空。所有將本體與現象分為兩段的理論都以本體為本,以萬物為末,只是“宰割以求通哉”而已。乍一看,“非有非無”違背了邏輯學中的同一律原則,然而,僧肇正是通過這種違反常識的方式來破除人們在經驗世界的名言概念和思維中的對象化、定格化的認識,其目的便是取消外在本體 ④。以方便言教之法啟發人們將視野從本體論的思維移開。
(二)離妄還源,卷舒自在——華嚴宗的“一念”
中國佛學的發展從性空轉向了妙有,華嚴宗以四法界說確立了一真如本體,似乎否定了之前般若學的非本體、重認知的思路,然而并非如此,事實上在某種程度上華嚴宗人甚至擴展了這一認知決定論的傾向。華嚴宗認為,凡圣的差別只在“一念”,而這一念就是決定性的認知層次上的原因。
華嚴宗區分象征本體的“理法界”與人們日常生活中認識的“事法界”,在此之上又提出“理事無礙法界”與“事事無礙法界”。華嚴宗人進一步闡明,法界為體,緣起為用。正因緣起之大用,故十方理事齊彰,凡圣眾生并顯。法藏在《華嚴義海百門》中說道:
觀體用者,謂了達塵無生無性一味,是體;智照理時,不礙事相宛然,是用。事雖宛然,恒無所有,是故用即體也。如會百川以歸于海,理雖一味,恒自隨緣是故體即用也。如舉大海以明百川,由理事互融,故體用自在。若相入,則用開差別;若相即,乃體恒一味。恒一恒二,是為體用也。⑤
由此可見,華嚴宗的理事既相即,又相入。相入,則用起開示差別,映現出千差萬別、恢詭譎怪的塵世間;相即,則體顯恒常一味,理事圓融,卷舒自在。而華嚴宗之所以講法界觀,除了出于其作為“圓教”的理論需求外,也是為溝通人性與佛性所做的理論基礎的準備。由理事無礙,人們發現本體不再不可企及,佛性本就貫穿于一切眾生之中。生佛不二,凡圣一如,諸佛與眾生相異的原因不是由于被賦予了不同的位格,而是由于眾生產生了妄念,而從“自性清凈圓明體”跌落至那念有念無、執著分別的凡夫境界。《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云:“若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惟一真如,故言海印三昧也。”因此人若想成佛所依靠的不是信仰,而是認知上的轉變。即“離妄還源,只在一念”。至此,華嚴宗勾勒出了一個相較于之前中印佛學流派更加簡約且充滿希望的理論,而這個理論是以認知的境界為核心展開的。
由此可見,以“空”為核心的佛學并未徹底否定本體論,只是認為對于本體的討論應放在認知提升之后。只有認知提升了,人們才能理解那佛性遍照的真如本體,理解眾生與佛本來無二,只是迷悟不同。所謂諸佛不過是指引人們脫離妄念的方便施設,而所謂眾生也只是基于妄念分別的自我掙扎。佛與眾生不外是隨緣所立之假名,約權體施之外號。正如法藏在《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中所言:
夫滿教難思,窺一塵而頓現;圓宗叵測,睹纖毫而齊彰。然用就體分,非無差別之勢,事依理顯,自有一際之形。其猶病起藥興,妄生智立,病妄則藥妄,舉空拳以止啼。心通則法通,引虛空而示遍。既覺既悟,何滯何通。百非息其攀緣,四句絕其增減,故得藥病雙泯,靜亂俱融,消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
這段話中,“病起藥興,妄生智立”可謂一語道破天機,所有佛法只是針對眾生執迷所開的藥方,所謂彼岸也是受限于人的認知能力而開拓出的理想國。佛學之“理”的真義在于破除執著、轉換認知,而不在構建完善的本體論結構。
(三)心統性情——朱熹理學的綜合性闡釋
在宋代儒學中,自程頤提出“理本論”,而被朱熹承繼以來,“理學”成了那一時期中國哲學的代稱。其中,“心統性情”是宋代理學認知機制的重要表述。透過朱熹對這一理論的闡釋,我們可以看到其與“一心開二門”的認知決定論傳統的親緣關系。朱熹曾這樣表述“心統性情”的認知機制。
性無不善。心所發為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卻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為不善者,情之遷為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于性而善者也。其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性不是別有一物在心里,心具此性情。⑥
在朱熹“心統性情”的理論中,“性”即理,是天理本體于個體上的生發。用朱熹的話講,“性是實理,仁義禮智兼具。”性是純然之善,是張載所說的“天所性者”;“情”則是對當下境域所做出的情緒反應;而“心”則湛然虛明,無善惡、非動靜,其存在狀態是統合性與情,且在邏輯層次上高于二者。此處可以看到,朱熹“心統性情”的理論承繼了“一心開二門”的邏輯框架,又引入了倫理層面,做了符合儒學價值取向的發揮,在認知機制上既保留了“認知決定論”超越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特點,又凸顯出儒家的道德宗骨,實可作為道德形上學在認知領域的學說總結。
此時的理學一方面吸收了以往“認知決定論”的傳統,朱熹推重的“心統性情”與佛學“一心開二門”存在著家族相似性 ⑦;另一方面又開顯出涵蓋乾坤、造化天地的道德的本體。從此,理本論與人性論得以打通,儒家一貫強調的仁義與道德有了本體的基礎。于是,充滿儒家特色的“道德形上學”便形成了。因此,佛學與儒學的真正差異在于儒家的“道德形上學”的覆蓋范圍除了認知層面,也綜合了本體論層面,對這兩個層面的綜合成了儒家道德形上學的重要特點。
三、道德形上學“生春氣象”的本體性特征
如果說對認知之超越性維度的重視是道德形上學對佛學思想的吸收,那么對于具有生春氣象的本體的體認,就是儒家的核心特征所在。儒學的本體論從來都不只是對“超越性存在”的冰冷解釋,而是將“創生”義與“道德”義緊緊相聯,這一傾向表現在理論中便是儒學獨特的“生春氣象”——充滿盎然生機的春意落實到了本體之中。
儒學理論在很早便完成了“天”與“德”的連接,這使得儒學雖未明確提出,但已有了“道德形上學”的傾向。早在周朝,統治者為論證自己的政權合法性,便提出了“以德論天”的主張,《尚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指出天意將歸宿在有德之人。到了戰國時期,孟子進一步將天的超越意味賦予人的道德心。孟子認為,成就道德的快樂是最高級的快樂,他提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將道德之樂與天進行了聯系。從先秦時期“天”與“德”的關系可以看出,自周朝,“以德論天”到孟子“以天論德”的轉變,這其中大有深意,便是確立了道德的形上基礎。這一形上基礎實際上回答了一個問題——人為什么要行善?為什么要做一個好人?對于這種問題,儒學將道德的終極根據置于天上,這種將天與人相連接的做法對后世將春意與道德相聯系起到了非常微妙的作用。
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在系統理論中提出以“春”作為天之屬性的思想家是董仲舒,董仲舒以“春”代指“天之德”。他在《春秋繁露》中提出:“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為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后發德。”董仲舒的理論首次提出了陽春發育萬物的功能與天德的匹配關系。
到了唐代,孔穎達在解《周易》時候,將元、仁、春相互聯系,認為作為萬物之始的“元”具有春之生意,而這種春意落實到人性中就是“仁”。除此之外,元亨利貞與春夏秋冬、仁義禮智也是相互對應的,正如他在《周易正義》中所說的“元者,善之長也”以及“天之體性,生養萬物”。如此一來,春意生發之氣象便與創生之源聯系起來了。
到了北宋,程顥更是注重“生春氣象”與天道間的關系,他曾多次論述春之仁德作為天理本體的觀點,“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缊,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后來生長,不可道卻將既生之氣,后來卻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都是講天地間最為根本的,便是仁之生生。然而,這種生生之德并不是脫離于人的,而是可以通過靜思冥慮“直觀”到的,“靜后,見萬物皆有春意。”那宇宙生發之春能切實為人所感受到,宇宙萬物都包裹在變動不居、周流無滯的生發過程中。人也因此可以參天地之造化與那盎然春意相匯通,進而呈現出與原先截然不同的氣象。程顥細化了“氣象”的理論,其落腳點便是要說明人之滿腔仁心可以和生發萬物之春意渾然一體。元氣流行雖難以窺測,但最終還是要披拂于人,春風化雨。這便是“生春氣象”的旨歸所在。
朱熹延續了程顥對于萬物之春意的重視,與程顥不同的是,朱熹更注重“理”在其中發揮的作用,而將天道之生生納入了理本論中。朱熹認為,理難見,氣易見,天理幽微難測,卻可以從春氣流行中對其進行把握。“理無跡,不可見,故于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是一個渾然溫和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也就是說,可以從盈天地間的陽春之氣窺見天地生物之理。朱熹還對生生本體與四時、四德的關系做了比對,他在《仁說》中提道: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
那么,道德形上學中的“理”是實體嗎?對這一問題,牟宗三在《心體與性體》中指出,“故就統天地萬物而為其體言,曰形而上的實體,此則是能起宇宙生化之‘創造實體’。”儒家的天理是實體無疑。由此可見,牟宗三對這一問題持肯定態度。然而也有學者指出,儒學的生生倫理學是反對天理實體化的。對于這一問題的不同觀點,其核心在于是否應該以西方傳統的本體論去比附儒家的道德形上學?答案應是否定的,如果以西方哲學中本體論的定義來看待代表儒家道德形上學的理學,則會發現理學并不與其完全一致。一方面道德形上學具有超越的本體,另一方面這一本體具有自身的儒學特色,即以“生生”為基礎的創生存有的特點。
儒家道德形上學中的“理”從來不是一個對于現象界袖手旁觀的高維本體,而是活潑的、充滿生機的道德之天。它處在不斷地創生活動中,為世間萬物賦予道德價值,因此人們的善性有了本體論的基礎與歸宿。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儒家將天與德進行了關聯,因此其本體論也實際上趨向了一本體、道德、創生即三而一、密不可分的理論傾向。故而,只以傳統的本體論去解釋道德形上學是不準確的,儒家的本體論思想實際具有更廣闊的含義。
四、結語
通過對儒家“道德形上學”的梳理,可以看到,“道德形上學”的超越性包括兩個方面,即以“心統性情”為代表的認知決定模式與“生生”之本體論。其中“心統性情”很大程度受到來自佛學“一心開二門”的思想,呈現出以認知提升消解本體論的傾向。而以“創生”與“春意”為核心的本體論則延續了儒家“以天論德”的傳統,以道德屬性會通天人,天通過大化流行實現對萬物的創生,于絪缊化醇的持續性過程中生動地開展著自身;而人亦能參天地之造化,以仁德體會天地之春意,進而呈現出“生春氣象”,于灑掃應對、動容周旋之中實現對有限性的超越。這兩個方面一道構成了道德形上學區分于一般意義上的認識論與本體論的特點。會發現,在這兩個方面中,人擔任著重要的角色,“心統性情”與“以天論德”的背后均有著隱藏的主體,而這便是道德形上學貫徹到人的原則的體現。事實上,成就君子人格、完善圣人氣象正是道德形上學的最終旨歸。程頤在評價程顥之人格時曾這樣寫道:“觀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澈視無間。”便是稱贊程顥之人格如春風拂面,其仁德流行,有如天理生發之春意。
由此可見,道德形上學的本質是落實到人的,它的超越性首先是認知層面的超越,其背后是人作為最高認知的主體,是繼承了中國哲學中“克服二元對立”思維傳統的結果。同樣的,它的本體論也不只是懸設了超越、外在的天理作為世界的客觀教條,而是春意盎然的生生之理。這個“理”不僅以動態的過程創生著道德存有,構造可供理解的意義世界,而且更以“理一分殊”的方式映照在每個人身上——人不僅是大化流行的一個產物,更是能以自身之仁與天地合其德的最終價值本身,人就是宇宙的意義。這種希圣、成圣之學在今天看來仍具有意義。
總之,道德形上學在認識論和本體論上均呈現出區別于西方哲學的儒學特色,而這種特色既是會通中西方哲學的必要因素,也是儒學在當代得以展開自身、澄明其價值的理論基礎。
注釋:
①《原儒》下卷,《全集》卷6,第570頁。
②關于康德“道德上的消極主義”,可以參見克朗納《論康德與黑格爾》第93頁中的論述。克朗納認為,康德“毫不含糊地顯出他根本不相信心靈上的凈福心境之可能性”。雖然以關子尹為代表的很多學者認為,康德只將上帝置于一個過渡的位置上,最終目的是達到“悟發信謝”的道德自律。然而不可否認康德確實認為人類在現世中踐行道德是一掙扎的過程,并提出“德福一致”的問題加以討論。
③僧肇:《肇論·不真空論》。
④此處的“外在本體”并非單指貴無論,也包括“萬物獨化于玄冥之境”的獨化論。僧肇對自生與他生的否定實際澄清了般若空觀破斥實體性、生成性思維的特征。
⑤法藏:《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
⑥《朱子語類·卷五》。
⑦朱熹與佛學的“家族相似性”這一概念由董占梅教授與石義華教授在文章中提出,文章闡述了“理”與“性”、認識論與工夫論等諸多方面的相似。具體可參見董占梅、石義華《朱熹理學與禪學的家族相似性》,《齊魯學刊》2023年第2期。
參考文獻:
[1](梁)真諦譯.大乘起信論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 1992.
[2]釋印順.大乘起信論講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0.
[3]賴永海.中國佛性論[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0.
[4](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4.
[5](宋)黎靖德.朱子語類[M].北京:中華書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