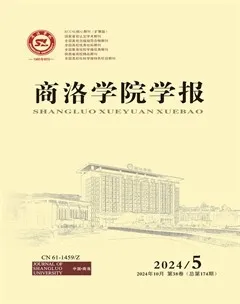錢穆的體育人生及其體育教學觀
摘 要:錢穆既是聲名顯著的國學大師,又是卓有成就的教育家。除在學術思想方面有極深的造詣外,他的教育理念越益受到重視,其體育教學觀同樣值得關注。錢穆不同時期的體育活動,無不是當時社會生活的縮影,也是當時大中小學體育教育的真實寫照。他早年參加的體操課程,深受軍國民教育的影響;實踐體操課程的生活化,既受西方自然主義的影響,又有自己立足實際的愿景;把體育當成“游藝”更是其對生活、學問的感悟,蘊含著其追求身心合一、道藝合一的深意。
關鍵詞:錢穆;軍國民體育;自然主義體育;游藝化體育
中圖分類號:G633.9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033(2024)05-0065-06
引用格式:宋紅寶,盧慶輝.錢穆的體育人生及其體育教學觀[J].商洛學院學報,2024,38(5):65-70.
Qian Mu's Life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is
Views on Physical Education
SONG Hong-bao, LU Qing-hui
(Zhuzixue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 Shangrao 334001, Jiangxi)
Abstract: Qian Mu was not only a renowned m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but also an accomplished educator. In addition to his profound achievements in academic thought, 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has gained increasing attention, and his views on physical education are equally noteworthy. Qian Mu's involvement in physical activities at various stages of his life reflects the social landscape of the time and serves as an authentic represent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The gymnastics courses he participated in during his youth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militarized national education. His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gymnastics into daily life was shaped by Western naturalism while incorporating his own practical vision. Furthermore, Qian Mu regarded physical education as a form of "recreation", reflecting his insights into life and scholarship, and embodying his pursuit of the unity of body and mind, as well as the harmony of Dao and the arts.
Key words: Qian Mu; militarized n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naturalistic physical education; recre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錢穆是近代以來著名的學術宗師,同時也是一位聲名遠播的教育家。對于錢穆的學術成就,不少學者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探討,其教育思想近年也逐漸受到學者的重視,何方昱[1]指出,錢穆所提倡的“鍛煉體魄、陶冶意志、培養情操、開發智慧”的中學教育目標更符合中學生的心理和生理特征,對學生的健康成長更為有益。陸玉芹[2]認為錢穆具有獨特的大學教育觀:提倡“通人尤重于專家”的通識教育,反對偏而狹的專門教育;提倡“為學與做人并重”的德性教育,反對將人附庸于學;提倡大學教育是“蘄想人生最高理想之一種事業”的人生教育,反對教育中的急功近利。杭建偉[3]強調,錢穆在新亞書院培養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其在這一時期提倡的“從知識與人格和諧發展、身心和諧發展、個體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和諧”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是先進的,是和諧教育的一個成功樣本。張默農[4]表示,錢穆教學風格主要體現在教師感情豐富充沛、教學內容選取獨到、教學方法運用靈活、教學語言藝術生動等方面,這一鮮明的教學風格與其教育思想緊密相連。殷清華[5]強調,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與錢穆人文主義教育“培養理想完整之人格”相通;分析錢穆人文教育思想,能為當今思想政治教育弊端提供借鑒。龔孟偉[6]認為,錢穆提出的“培育學生健全的人格是文化教育的宗旨、通識與專長并重是文化教育的課程設置理念、歷史闡釋是文化教育的基本路徑”等系統的文化教育思想,對當代教育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與啟示作用。羅亞利[7]指出,錢穆從文化本位的視角出發,以“執兩用中”的教育理念為核心,提出培養“文化人”的教育目的,從以“專”為慮、以“通”為重、“通” “專”融合等角度解讀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及兩者的關系,并在其教育實踐中落實相關舉措,強調師“有道”、生“誠明”、學“自由”的教育方法,對現今我國高校通識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和參考價值。總體上,現有研究既有從不同學段、不同學科等展開闡述的,也有從其教學風格、教學影響等展開分析的。相對而言,學界對錢穆有關體育教育思想的研究則較為稀缺。
早年在鄉間小學教書時,錢穆就十分重視體育教育。這為其日后作為教育管理者,有效推行體育教育起著很好的鋪墊作用。錢穆對體育并沒有較為完整和系統的論述,其著述中僅有“片言只語”的述說。隨著自身閱歷的增加與教學經驗的豐富,錢穆越發認為,體育應該符合個人的實際,非但不能強迫,反而必須與德育、智育、美育緊密結合,以至于成就完美的人格。錢穆的體育人生大致可分為軍事化體育、自然化體育及游藝化體育等三個階段。本文擬以錢穆的體育活動經歷為對象,藉此探討其所反映的我國近代體育教育的時代特征與影響。
一、自強:錢穆早年歲月參與的軍事化體育教育體驗
教育家葉瀾認為:“凡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中產生深遠影響的教育家,都是時代精神在教育領域中的代言人,他們思想的光彩是時代精神在教育領域的獨特折射。”[8]作為卓有成就的教育家,錢穆一生的教育實踐無疑體現了時代精神。或者說,時代的影響對其教育思想的推行、實踐形成及推行、實踐頗為重要。據陳勇介紹:“錢穆的一生與甲午戰敗以來的時代憂患相終始,他的治學始終充滿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和愛國家、愛民族的真情。”[9]16事實上,除了治學充滿強烈的民族意識以外,錢穆所從事的教育實踐活動同樣也為國家、民族與社會培養人才。
錢穆作為中小學生同樣也是其教師實踐教育思想的對象,而這些早年的受學經歷同樣也潛移默化到其日后的教學生涯中。錢穆七歲入私塾讀書,十歲進新式小學學習。自進入小學后,就接受了正式的體育教育。錢穆最初的體操教師是其同族錢伯圭先生。錢伯圭曾游學上海,對錢穆的教導更多是文化方面。據其后來的回憶:“余之畢生從事學問,實皆伯圭師一番話有以啟之……余自幼即抱民族觀念,同情革命民主,亦由伯圭師啟之。”[10]34由體操教師的一番話而走上學術之路,看似偶然,或屬巧合,但這一事實當可展現民元前后江南地區中小學堂的體育教學概況。幾年后,錢穆由果育小學校升學到常州府中學堂。在中學堂同樣要練習體操。他說:“時體操課學步德日,一以練習兵操為主。(劉)伯能師在操場呼立正,即曰:須白刃交于前,泰山崩于后,亦凜然不動,始得為立正。遇烈日強風或陣雨,即曰:汝輩非糖人,何怕日。非紙人,何怕風。非泥人,何怕雨。怕這怕那,何時能立。后余亦在小學教體操課,每引伯能師言。久知此乃人生立身大訓也。”[10]53當時的中小學體育,首先是提倡學習德日等國。之所以效仿德日,主要是鑒于它們“最重強權且勇武可敬”,也是通過改革而從弱國轉變為強國的。其次是以體操為重要內容,而體操又以兵操為主。中小學體育以軍國民教育為基礎,目的無疑是強身健體,崇尚紀律、服從管理、抗敵御侮、保家衛國。由此可見,體操或者兵操在當時的學生體育課上的地位。一個簡單的“立正”動作,就有如此的講究和嚴格的要求。“立身大訓”決非錢穆的自夸,而是體操課的長遠目的所在。隨著學生年齡的增加,訓練強度自然也隨之增加,要求肯定也是更加嚴格。錢穆后來不懼風雨、不畏險阻,其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等剛毅性格的形成,與其少年時期練習兵操多有關聯。
騎馬是錢穆早年體育生活的另一項重要內容。他曾說:“在鐘英之前半年,最受刺戟者,乃是清晨薄暮環城四起之軍號胡笳聲,以及腰配刺刀街上邁步之陸軍中學生。使余油然引起了一番從軍熱。最所希望乃能出山海關,到東三省,與日本俄國兵對壘,那是一件何等痛快之事。余雖未償所愿,但亦因此學會了騎馬。每逢星期天上午,三幾個同學,在鐘英附近一馬廄租了幾匹馬,出城直赴雨花臺古戰場,俯仰憑吊,半日而返。成為余每星期最主要之一門功課。”[10]58南京城內的“軍號胡笳聲”,街頭邁步的陸軍中學生,無不對錢穆少年之自強自立思想產生深刻影響。當時雖不至于舉國皆兵,舉校皆兵,但國家形勢及學校的教育現狀,都促使其注重鍛煉身體,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錢穆雖然沒有參軍成功以致上陣殺敵,但也因此學會了騎馬。騎馬并不是學校體育必修課之一,但錢穆在當時學會騎馬,似乎并不是為了享受情懷,更多的還是為了健身、強魄。
無論是兵操還是騎馬都顯示出當初學校體育教學具有濃厚的軍事色彩。這是和當時的社會環境、國際形勢緊密聯系的。我國體育歷史雖然悠久,但“體育”一詞則是近代才出現的外來詞語,是19世紀末我國主張維新改革的有識之士從日語詞匯中翻譯而來。這也是我國近代以來體育教育深受日本及歐美影響的具體表現。梁啟超曾稱:“歐洲各國,靡不汲汲從事于體育。體操而外,凡擊劍,馳馬、蹴鞠、角抵、習射、擊槍、游泳、競渡諸戲,無不加以獎勵,務使舉國之人,皆具軍國民之資格。”[11]在其看來,培養學生和全體國民的尚武精神,必須具備三方面的能力:心力、膽力和體力。近代以來,面對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日益成為當務之急。國家要想強大,國民自身的身體素質必須強大,國民的身體素質尤須鍛煉。學校更是培養和鍛煉學生身體素質的最佳場所。
在這種背景下,“強國強種” “尚武救國”自然也就成為學校體育教育的主導思想與理念。光緒三十二年(1906),《學部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折》明確規定:“凡中小學堂各種教科書,必寓軍國民主義”,“體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戲、體操發育其身體,稍長者以兵式體操嚴整其紀律。”[12]在內憂外患的困境下,清政府仿照日本建立新教育制度,開設體育課,實施體操和兵式體操,這一時期的學校體育可稱之為“軍國民體育”。即使在民國肇造之際,體操(兵操)也是中小學體育教育的必修課之一。蔡元培曾把軍國民教育列入民國教育方針五項內容之一并在全國推行。武昌起義后,錢穆就讀的學校不得不解散。他也因之被迫返家并結束學生生涯。數月之后,他前往三兼小學任教。
成為鄉村教師以后,錢穆同樣重視體操課教育。據其回憶,“民國二年(1913),余不再去三兼,即轉入鴻模任教。三兼學校高初兩級僅分兩班。余原則上任高級班,除理化課由仲立任之,圖畫手工課由仲立幼弟任之,其余國文、史地、英文、數學、體操、音樂等,皆由余一人任之。”[10]75初為人師的錢穆,工作認真負責,凡是能夠勝任的,都當仁不讓地承擔。錢穆不僅擔任知識學科的教學任務,同時也從事著體操、音樂課等藝術課程教學。他最初的體操課教學活動,無論在初級小學,還是在高級小學,都與其學生時受到的教育一樣,完全以強身健體、保家衛國為宗旨。錢穆的體操課教學,之后也因其轉任其它學校、其它課程而暫告段落,然而其強調體育的觀念并沒有因之中斷,只是面臨著重要的轉變。
二、自然:錢穆青年時期奉行的自然化體育教育經歷
隨著時局的變化和體育事業的發展,以軍國民體育為標志的強兵、強種、強國等理念,逐漸遭受到質疑和挑戰。時人越益從體育的本質去評判體育活動。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民主和科學的呼聲日益高漲。軍國民體育雖然在保家衛國方面做出重要貢獻,但這一準軍事化的教育模式悖于自由、平等理念,則受到很多學者的指責。如陳獨秀就宣揚:“軍國民教育的時代過去了。”[13]毛澤東在《新青年》雜志發表的《體育之研究》一文,宣揚體育與德育、智育對立統一、相互依存、相互消長。國外某些學者對此也表達異議。如受胡適邀請來華講學的杜威就說:“吾人試觀中國的教育,實根源于日本,是直接模仿日本的教育,間接模仿德國的教育,而不懂得要確定一國的宗旨和制度,必須根據國家的情況,不考察需要,而胡亂地仿效他國,這是沒有不失敗的……我期望中國的教育家一方面實地研究本國本地的社會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學說作為一種參考資料,如此做法,方才可以造成一種中國現代的新教育。”[14]美國自然主義體育思想隨著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學主張開始傳入中國,其倡導者們提出“體育即生活”口號,提倡體育要適合兒童的興趣和個性發展。而在教學內容上則主張采用跑跳等所謂“自然活動”,反對“非自然的” “人工的” “呆板的”體操。自然主義體育思想和方法為中國帶來了較為系統的體育理論,它強調從人的生理、心理、社會和個人需要的角度看待體育,使自然主義體育思想在當時集中表達了“實用”的核心價值觀[15]。
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盛行“新”體育教學觀時,錢穆還在江南的鄉下默默耕耘。錢穆后來回憶,“因報載美國杜威博士來華,作教育哲學之演講,余讀其講詞,極感興趣。但覺與古籍所載中國古人之教育思想有不同,并有大相違異處。因念當轉入初級小學,與幼童接觸,作一番從頭開始之實驗,俾可明白得古今中外對教育思想異同得失之究竟所在。”[10]95不可否認的是,杜威的實用主義之所以能在我國興起一陣風潮,自有其價值所在及合理性的一面,畢竟教育有很多共通性的東西。錢穆因之也在其所任教的學校進行了諸多嘗試與探索。雖然他積極吸收西學中的有益養分,但也沒有全盤接受而是有所取舍。他“逐月看《新青年》雜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來,卻已決心重溫舊書,乃不為時代潮流挾卷而去。”[10]82除了對杜威教育思想極感興趣以外,他更愿意從本國和家鄉的實際出發,作一些有益的研究和嘗試。多年的一線教育經歷,使錢穆更能關注到學生的身心實際。1919年某次課后,他對同事說:“余有一理想,當使一切規章課程盡融在學生之生活中,務使課程規章生活化,而學生生活亦課程規章化,使兩者融歸一體,勿令學生作分別觀。若使彼等心中只分出一部分生活來服從學校之規章課程,另保留一部分生活由其私下活動,此決非佳事。”[10]97兩位同事皆表示認可并讓錢穆講一些具體的措施與辦法。他進而指出:“欲求課程生活化,先當改變課程,如體操唱歌,明是一種生活,但排定為課程,則學生亦以課程視之。今當廢去此兩課,每日上下午必有體操唱歌,全體學生必同時參加,余等三人亦當參加,使成為學校一全體活動。”[10]97在錢穆看來,體育應該融入到學生的生活當中。體育即生活,兩者應該融為一體,確切地說,“兩者”也并不允當,應該是一體之兩面,不應分彼此,這樣才不會厚此薄彼。體育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還把體育當成課程來教學的話,那么學生(包括教師)都不會特別重視。生活與體育互相滲透,體育教學生活化必然會極大地豐富體育教學的形式和內容,體育教學自然也能得到更好的效益。學生從生活體育中收益,必然也會促進其它課程的學習。把體育當作是人們在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的話,那這種體育方才是最好的學習方式、生活方式。體育課堂教學與生活的有機結合滲透,無疑會更有利于學生自身素質的發展,個性也因此會得到張揚。當體育成為人們生活中一種不知不覺的良好習慣時,人們自然也就不會在把它當作可有可無的東西。
“體操生活化”是錢穆體育教學觀念的重要內容。他清醒地認識到:“僅有理想不顧經驗,此屬空想。但只仗經驗,不追求理想,到底亦僅是一習慣,將無意義可言。”[10]97-98錢穆對此做出大量嘗試。如要求學生“課畢皆須赴操場游散,勿逗留課室中。”[10]98即使以現在的“后見之明”來看,這也是十分必要的。具體來說,它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課后到操場游散,有利于緩解疲勞,促進身心健康發展;第二,有利于區別課上與課下的特征與要求,緩和課堂甚至是師生之間的壓力與矛盾,實質提高課堂教學的效率。尤為重要的是,錢穆認為應該把課間還給學生,真正做到“學習生活化”而不是簡單意義上的“生活學習化”。他還強調:“體操唱歌課同為每日全校師生之共同必修課。”[10]103
對于中學教育,錢穆建議:“當盡量減少講堂、自修室、圖書館工作時間,而積極領導青年為戶外之運動。自操場進至于田野,自田野進至于山林,常使與自然界清新空氣接觸……當使學校一切田野化,山林化”[16]233-234。中學教育應以“鍛煉體魄” “陶冶意志” “培養情操” “開發智慧”為主,而這種“田野山林之氣”無疑也是自然化體育需要提倡與遵循的。他還指出:“儒者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以今日學校課程言,體操、唱歌即猶禮樂。衡以儒家理論,此兩科當為學校教育之最高科目。日日必修,不可或缺。師生并習,無分上下。”[16]235晨夕勞作、健身游戲、郊外遠足,都是開拓情趣、暢悅胸襟的重要形式,而這些貼近自然的生活方式也為其后來生成游藝化體育思想作出重要鋪墊。
體育對于錢穆的健康長壽非常重要。他自己就說:“余體弱,自辛亥年起,幾于每秋必病。一日,讀日人一小書,論人生不壽,乃一大罪惡,當努力講究日常衛生。余時適讀陸放翁詩,至其晚年作品,心中大奮發。念不高壽,乃余此生一大恥辱,大懲罰。即痛于日常生活上求規律化,如靜坐,如郊野散步等,皆一一規定。”[10]80錢穆早年體弱可能與遺傳或者家境有關。自從把身體鍛煉、陶冶情操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行為習慣之后,錢穆自身也由體弱逐漸體強。錢穆平日以澹泊寧靜自期,讀書散步自然也有一番消散閑適意味。除了靜坐這一養身的體育方式以外,他還有一些其它的體育興趣愛好。這些興趣愛好,伴隨著錢穆一路走來,從無錫到廈門,從蘇州到北京,從香港到臺灣。這其中不僅有一種修身養性、陶冶情操的理念,而且也有一種自覺的生命意識。這種體驗“自然”的體育理念也在后來的歲月中得以升華。
三、自“游”:錢穆中年以后推崇的游藝化體育教育實踐
隨著閱歷的豐富與學識的精進,錢穆對于傳統文化日益表現出溫情與敬意。其對于儒家經典的解讀與體悟也越發深刻。他對《論語》的解說多有妙語。錢穆晚年“綜六藝以尊朱”,其對于《論語》的解讀,除了深受朱子的影響以外,更因之而發現朱子的“偉大”。對于“游藝”一詞,朱子早有專門解釋:“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余,而心無所放。……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不失其先后之序,輕重之倫,則本末兼賅,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賢之域。”[17]
錢穆在朱子“游藝”詮釋的基礎上,進一步解說,“游,游泳;藝,人生所需。孔子時,禮、樂、射、御、書、數謂之六藝。人之習于藝,如魚在水,忘其為水,斯有游泳自如之樂。故游泳于藝,不僅可以成才,亦可以進德。”[18]192他認為,古代的騎馬射箭(射、御)等體育活動,雖說在現代或許形式與內容都發生了改變,但體育活動本身卻是人們日常生活所必須的。人們學習這些技巧,就好像是魚必須在水中生活,既離不開水,更主要的還是要忘了在水中。對于每一個個體的人而言,既要學習掌握技巧,同時也要忘掉技巧,真正做到“渾然不知”——這樣的生活才有自如的、自在的樂趣。錢穆對于經典的感悟加深了其對于體育的認識水平,錢穆對體育的實踐同時也深化了其對于《論語》中“游藝”概念的詮釋程度。
錢穆早年在常州府中學堂求學時即好圍棋。1914年起,他在無錫縣第四高等小學任課,閑暇之時更廣羅晚明以下各種圍棋譜,課余或與人對弈,或自行擺譜,可謂樂此不疲。后因一棋友外出進修學藝歸來,無論執黑還是執白,都不能輕易取勝于自己,錢穆于是弈興大減,以后近二十年不再下棋,直到抗戰期間流落云南時“始再復弈”。錢穆二十年不下棋,自然有“不愿爭勝”的想法,其后來重操舊業,并非為了爭名奪利,而是為了更好地鍛煉智慧、陶冶性情,享受對弈帶來的從容與閑適。他曾批評當時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今人又每好舉行圍棋名人賽等,則亦如其他運動會比賽,爭取冠軍,求名求利,其所用心,則亦不如其已矣。”[19]165他對于時人在體育比賽中一味追求名利頗不以為然。比賽關注輸贏本是無可厚非的,但若只是為了冠軍而追名逐利甚至有違道德法律,顯然非君子所為。對于象棋,雖然他認為是“小藝”,但也覺得其中蘊含教育意義。象棋對壘必置對方死地,而黑白博弈卻為了自活,因而圍棋的品格顯然是高于象棋。錢穆早年對于麻將牌也持批評態度,認為賭博是頹廢的行徑,而后則以為“四人一桌,只求自己十三張牌和,即算勝,略與圍棋相似。以人生原理論,每一人只求內部生活和,已立于不敗之地。”[19]166賭博技巧竟與和諧之道相通,看似荒唐滑稽,但錢穆卻側重其中隱藏著中國文化傳統的最高教訓。
在香港新亞書院當校長時,錢穆提倡大學生也要多下棋,多打太極拳。他晚年在撰寫《朱子新學案》時,經常與身患頑疾的楊聯陞討論學問,還不忘建議楊氏要多練習太極拳,想來錢穆自己對太極拳或也多有體悟。學得初步功架或可謂是小事,更為關鍵的當是心境的涵養,心胸一旦開闊,或也有助于學問的博通,自然也有利于頤養性情、強身健體。如此一來,則諸多體育活動都可以娛樂化、藝術化。錢穆還認為:“健全的生活應該包括勞作的興趣與藝術的修養。”[20]健康的體育運動生活,健康的身體無疑是成就偉大修養、偉大人格的必要條件。錢穆不太注重競爭,因而也很少參與競技體育,身體對抗的體育活動更是鮮有參加。他甚至一度還引用孔子所謂“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的主張,來辯解射、御活動雖是時戰所需,亦是當時人生藝術精神之一種表演。游藝化的體育,更注重內心的滿足。這是道德與藝術的統一,身體與精神的統一。
錢穆對登山、遠足等健身運動也頗有興趣甚至還很擅長。其登山不但比年齡相仿的教授矯捷,就是與年輕的學生相較也絲毫不差。其在北平教書有年,多次出游,或結伴而行,或一人獨游。爬長城,登泰山、游廬山、馳馬塞外、閑思湖上,多地名勝古跡都留下了他矯健的身影。就是訪學歐美,身處異國他鄉,錢穆也能抽空回歸自然,放飛自我。錢穆曾對學生李埏說:“向來只聞勸人讀書,不聞勸人游山。此說恐有誤。孔子《論語》上說,‘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即教人親近山水。朱子書中,亦有勸人游山之說。太史公著《史記》前,早已遍游全國山水。從讀書中懂得游山,這才是真游山,才是真樂。從師交友,亦當如讀書游山般。”[9]88錢穆性喜游歷,“徜徉湖山勝處”,既是一種能力又是一種心境。
錢穆對讀書與游山玩水亦有獨到的見解。他說:“就小學言,先教書數,即游于藝。繼教以孝弟禮讓,乃及掃應對之節,即依于仁。自此以往,始知有德可據,有道可志。……志道、據德、依仁三者,有先后無輕重。而三者之于游藝,則有輕重無先后,斯為大人之學。若教學者以從入之門,仍當先藝,使知實習,有真才。繼學仁,使有美行。再望其有德,使其自反而知有真實心性可據。然后再望其能明道行道。”[18]192登山、下棋等體育活動皆是技藝,哪怕是灑掃應對甚至走路散步都有學問。只要是能悠游其中,涵養其內,必能對生活有更大的體悟。當然,游藝對于依仁、成德、志道還是有輕重之差別的。游藝固然重要,但是和其它幾種學問相比,重要性自然是要輕些。不過,如果預先身懷包括體育技巧在內的真才實學的話,成德似乎也會事半功倍。可以說,體育可以完善道德,道德也可以成就體育。
錢穆對于“游藝”的認識,隨著他教育思想的發展而逐步深化。他強調:“中國教育則在教人學為人。”[19]154其中尤為重要的是教其“心”,易言之,就是從“性情”做起。也就是說,包括體育在內的諸多教育活動都可以藝術化,也應該返求之己之心,己之性情。錢穆認為,藝術本之自然,偏向內,偏重心,或為人生之本體。其實,體育何嘗不本之自然?或許也可以偏向內,偏重心,如此可言,體育亦為人生之本體。自然化體育與游藝化體育思想,確實有許多相似之處。兩者的區別在于,游藝化體育較之自然化體育,多了幾許古典的味道,多了幾分“人文”的色彩。他強調,“中國人又有靜坐養氣養神,以延年益壽之術。養神即養其心,心亦即是神。西方人則惟知運動健身,不知靜坐養神,此又觀念不同而方法亦隨之不同之一例。”[19]40-41在錢穆看來,西方人重身,而中國人重神。自然化體育對于知識與技能的提升多有器重,而游藝化體育更崇尚學生自身品格與理想的完善。
四、結語
錢穆的體育活動既是當時社會生活的縮影,也是當時中小學體育教育的注腳。雖然他的體育活動在近代體育史上不曾掀起大的波瀾,但對其體育活動及其體育教學觀的觀察,可以加深人們對于近現代體育思想演進的理解與感悟。如上所說,他的體育教育活動既受社會影響之深,同時也有自己的特色和寓意。錢穆不同階段的體育活動,自有其前后相承的順序。從他不同時期體育生活關注的重點,可知悉他對體育認識的漸進性。他的一生都處于時代的風云變幻之中,其體育思想與其學術思想一樣,也是從少年時期的“隨風逐流”到青年時期的“乘風破浪”再到中年以后的“迎風待月”,最終成為博綜貫通的國學宗師。錢穆體育教學觀最為重要的方面是,在自然化體育與游藝化體育之間,更傾向于后者,即希望通過體育這種游藝的活動形式,達到道義合一,人格完善。
參考文獻:
[1] 何方昱.高揚文化教育“人才教育”——錢穆中等教育思想及實踐述要[J].歷史教學,2005(4):54-58.
[2] 陸玉芹.錢穆的大學教育觀[J].歷史教學問題,2008(5):71-74,43.
[3] 杭建偉.錢穆和諧教育思想探析[J].江南大學學報,2008,28(1):7-10.
[4] 張墨農.錢穆教學風格研究[J].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37(4):252-254.
[5] 殷清華,劉曉梅.錢穆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對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啟示[J].知識經濟,2019(12):143-144.
[6] 龔孟偉.錢穆文化教育思想及其當代啟示[J].大理大學學報,2022,7(3):90-95.
收稿日期:2024-05-07
基金項目:江西省教育科學規劃重點課題(20ZD072);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課題(JD19112)
作者簡介:宋紅寶,男,江蘇響水人,博士,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