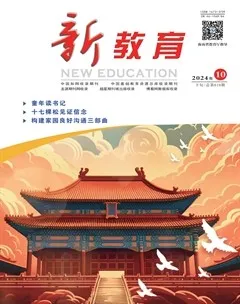童年讀書記
我小時候,我們村里有一個老人家,我們都叫他許爺爺。許爺爺的腦袋里裝滿了故事,夏天的每一個夜晚,他都端著水杯坐在曬谷坪里給我們講故事。無論大人還是小孩,都喜歡聽他講故事。他總是講一些神話故事、民間傳說和他聽來的歷史故事。
我很迷戀許爺爺講的神話故事,總幻想自己變成故事里那個會魔法的主角。媽媽讓我去割魚草,我就站到水塘邊對魚兒說:“魚兒,魚兒,你自己跳到岸上來吃草吧,吃飽了再跳回水里去。”因為在許爺爺的故事里,有一個男孩子就擁有這樣的魔力,他可以和所有的動物說話,讓它們聽他的話。后來,媽媽發現我一個下午都沒有去割魚草,她很生氣,埋怨我說:“你怎么這么傻呀,分不清現實和故事。”
再后來,許爺爺老了,他講不動故事了。上學后我就自己到處找書看,但在20世紀80年代的鄉村,孩子們基本上沒有什么課外書可閱讀。雖然那時候城里已經有了書店,但對鄉下的孩子來說,能讀到的書極其有限。大人不可能花錢給我們買書看,甚至連一張報紙都很少見到;但我總有辦法弄到書,每次得到一本書都如獲至寶。
小時候為了讀書我還做過一些“瘋狂”的事情,比如冬天的夜晚等爸媽睡著了,我端著煤油燈躲在被窩里看書,頭發常常被燈火燎燒。后來被媽媽發現了,我就改為打著手電筒躲進被子里看書。
讀過我的長篇小說《路過一棵開花的樹》的孩子都知道女孩木小樹愛看書,而且書的來源多半是哥哥姐姐從外面借來的,其實我的現實情況亦是如此。我閱讀的書籍主要來源于我的哥哥姐姐。我剛上小學時,我姐姐也上小學,后來她小學畢業上了初中,我哥哥那時候上高中,他們隔三差五就會帶書回來。
記得有一次,我在哥哥的枕頭底下找到一本《苦菜花》,那是一部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對那時候的我來說,那本書讀起來有點難懂,要是放到今天我未必能讀得下去那樣一本書,但那時候真的是沒得選擇。
上初中后,情況有所改善,能借到的書慢慢多了起來。我也不再看小人書,而是啃大部頭的書,我甚至讀過六百多頁的歷史故事書。
初二的一個暑假,因為我家離學校近,我的英語老師也是我家的一個遠房親戚,她要我幫她看家。她養了幾只雞,我需要每天早上打開雞籠子喂雞,晚上再喂一次,然后鎖上雞籠子。我很開心為她做事,因為她家臥室有滿滿的一墻壁書。
那個暑假是我最快樂的一個假期。英語老師家里藏書豐富,世界名著、中國古典文學等應有盡有,每一個晚上我都在閱讀。我現在還記得我當時讀得最過癮的一本書叫《呼家將》。
初中畢業那一年的暑假,沒有暑假作業,除了幫家里干活,我所有的時間都用來讀三毛的書。我有三本不同顏色的日記本,里面全部是摘抄下來的好句子。三毛的書是我姐姐帶回來的,她那時候在縣城上高中,每年寒暑假她都會背一袋子別人不要的書和雜志回來。
要說小時候對我有影響的書,一是三毛的散文。我讀她的《撒哈拉的故事》,其中有一個章節叫《沙漠觀浴記》,她寫撒哈拉威女人洗澡,用一片小石頭沾著水,刮自己的身體—每刮一下,身上就出現一條黑黑的漿汁似的污垢,她們不用肥皂,也不太用水,要刮得全身的臟都松了,才用水沖。因為沙漠缺水,她們三四年才洗一次澡。這樣的場景在我幼小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那件事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三毛寫她用廢棄的汽車輪胎吊起來做椅子,用沙漠中死亡的動物頭骨做飾物;寫撒哈拉威人的故事,寫她在自家門口地上看到一串用麻繩串起來的項鏈,撿回家掛在脖子上,沒有想到奇怪的事就接二連三地發生了……這些故事新奇有趣,為我打開了世界的另一扇窗,從那扇窗中我看到了從來不曾想象過的豐富多彩的世界。
它不再是家鄉的田野、山坡、河流那樣的世界,它讓我對外面的世界充滿了向往。原來在世界的某一個地方,還有人過著那樣的生活,它激發了我對外面世界的好奇。雖然我不能去那些地方,但書本可以讓我到達那里。
巴金的作品對我也影響深遠,我大約是在十二三歲的年齡—小學畢業到初一初二年級那個時間段,讀到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那套書也是我哥哥帶回來的,他喜歡把書藏在枕頭底下,我每天都趁他出門干活時偷偷看。
很快我就被書里的內容吸引住了。我喜歡覺民和覺慧,而對覺新有時候喜歡有時候“恨”。“恨”他那么容易放棄,那么輕易妥協。我深深地同情梅表姐、瑞玨和鳴鳳,讀著讀著我就哭了,哭得很傷心,我為書中每一個人物的命運擔憂。
哭完之后,我就想自己來寫這個故事:我要讓覺新和梅表姐結婚,讓他們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覺慧帶著鳴鳳遠走高飛;讓那個專橫、虛偽而冷酷的高老太爺后悔去……
這也許是我在寫作上最初的萌芽,就那樣種下了一粒小種子,只是我當時并不知道,也未曾察覺到它對我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