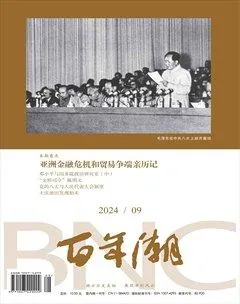鄧小平與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中)
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政研室毫無懸念地成為集矢之的。運動剛開始時,中央打招呼會只點了教育部周榮鑫和科學院胡耀邦、李昌的名,沒有提胡喬木的問題。這可能與當時政研室做的大多是幕后工作、不大為外界所知有關。即便如此,胡喬木想到劉冰的信是教育部副部長李琦交給他,他交給鄧小平秘書的,所以,1975年11月15日在和鄧小平談話時,胡喬木主動提出自己要對黨、對中央講清楚為劉冰轉信的經過。鄧小平要他不必提轉信的事,以免事情復雜化。這件事雖然被壓下了,但政研室在運動中畢竟處于風口浪尖,不可能幸免一劫。果然,1976年初,政研室里貼出了批判胡喬木的大字報。接著,有人通過姚文元,向毛主席送去了揭發胡喬木的信,說他積極鼓吹“右傾翻案風”,運動以來按兵不動,要求中央派人來領導運動。這封信被毛主席批示印發政治局,變成文件,在機關里進行傳達。這一下不得了了,政研室成立了臨時領導小組,雖然胡喬木在其中做掛名的組長,但寫告狀信的那位被任命為副組長和機關黨支部書記,成了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貼第一張大字報的和另一位從中央黨校來的運動積極分子成為領導政研室運動的骨干。那幾個人天天主持揭發批判大會,拿著毛主席的批示當“令箭”,逼迫政研室除李鑫之外的幾位負責人揭發胡喬木,逼迫胡喬木交代問題。盡管胡喬木和那幾位負責人并沒有講出鄧小平和政研室反對“四人幫”的要害問題,
但在政治高壓的氣氛下,也難免不涉及諸如參與修改《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
《工業二十條》和起草《論總綱》這樣的事。于是,qa+KEue5lai/El2KQ2hffYhkgNzWSjM6HoK+kNp9Nfo=被“四人幫”控制的報刊給政研室戴了兩頂大帽子:一為“鄧記謠言公司”,說鄧小平是總經理,胡喬木是副總經理;一為“右傾翻案風”的“黑風口”,尤其那三份文件,更被說是“三株大毒草”,印成批判材料,發動全黨全國人民批判。不過,讓他們始料不及的是,原本大家還沒看過那三份文件,這一下反倒讓大家看到了,使大多數人在內心里產生了共鳴,認為這些文件是正確的,不是“毒草”,而是香花。
由于“四人幫”實在太不得人心,所以,1976年1月周總理逝世后,社會上自發產生了把矛頭對準“四人幫”的悼念活動,直至發生“四五”事件;9月毛主席逝世后,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代表黨和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了“四人幫”,贏得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全國上下開展了“揭批查”(即揭發、批判“四人幫”罪行和清查其幫派體系)運動,政研室也毫無例外地罷免了那位臨時領導小組副組長的職務,成立了“揭批查”辦公室,清查室內與“四人幫”有關系的人和事。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原本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被打壓的政研室,在“四人幫”被粉碎后,不僅沒有恢復工作,相反,被勒令限期撤銷。好在當時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支持政研室在撤銷之前要完成對“四人幫”有關系的人和事的清查清理工作,并要參觀大慶大寨的訴求,使政研室的撤銷得以拖到了鄧小平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恢復工作。
記得十屆三中全會閉幕的第五天,即1977年7月26日,剛巧我在機關值班,接到鄧小平秘書王瑞林的電話,說小平同志當天下午約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去他家里談話。鄧小平在談話中明確表示,政研室的攤子不要散,并讓胡喬木先去主持闡釋毛主席“三個世界”理論的寫作班子。組織上隨后決定,要我擔任胡喬木的秘書。再后來,黨中央、國務院任命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擔任在學部基礎上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院長和副院長。此前,有人建議將政研室與社科院合并,鄧小平主張政研室還是單獨保留下來為好,負責人可以兼兩個單位的職,“名稱就叫國務院研究室。還是你們這個班子。寫文章,出資料”。于是,政研室改名為國務院研究室,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被任命為研究室正副主任(此前,李鑫已被任命為中辦副主任,并和吳冷西、熊復、胡繩一起被任命為中央新成立的毛主席著作編委會辦公室的副主任)。從那時起,政研室再次成為鄧小平的得力助手,協助他進行了同“兩個凡是”方針的斗爭。
粉碎“四人幫”初期,政研室頂著被勒令解散的壓力,積極投入揭批“四人幫”的戰斗,以“向群”為筆名,陸續寫出并發表《打著反復辟的旗號搞復辟》《敵我關系的根本顛倒》等文章,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反響。據《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一書披露,在“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1977年2月7日社論提出“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后,鄧力群便向王震反映了這一提法的錯誤,引起王震重視,遂在國防工辦的一個會議上公開批評了“兩個凡是”的提法,并向鄧小平作了反映。據《鄧小平年譜》記載,鄧小平在這之后同王震談話時,“對‘兩個凡是’的提法提出異議,認為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4月10日,他在同汪東興、李鑫的談話中明確表示:“‘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從那之后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他講話的一個中心內容,便是反對“兩個凡是”;政研室工作的一個中心內容,則是協助和配合他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
就在1977年7月26日鄧小平明確指出政研室的攤子不要散,并讓胡喬木先去主持“三個世界”文章寫作之后,鄧于8月3日又約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去他住地,商議為他起草黨的十一大的講話稿。他再次強調:“‘兩個凡是’不行。形而上學多了,害死人。有一種風氣,不采取老實態度,就是吹。這不行。要講老實,吹只能騙自己。你不講多少產量,但外國人一算就算出來了。這個稿子要寫得生動些,要從實際出發。我講過,不能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語損害毛澤東思想體系。講毛澤東思想,不在引用很多毛主席的話,而在發揮他的根本思想。”8月18日,他在黨的十一大閉幕會上致閉幕詞,指出:“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起碼標準。”
8月3日鄧小平同政研室三位領導的那次談話,還談到按勞分配問題。他說:“應該有適當的物質鼓勵,少勞少得,多勞多得,說得清楚。現在有人把不是毛主席的東西,強加給毛主席,說按勞分配產生資產階級。這根本不行。50元工資加到100元,加到200元,也變不了資產階級。”之所以談到這個問題,是因為當時仍然有人借口遵循毛主席關于資產階級法權的講話,反對貫徹按勞分配的原則。所以,政研室打算就這個問題寫文章。1978年4月,政研室將寫好的文章送給鄧小平審閱。4月30日,鄧小平約政研室三位領導談話,就《貫徹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文章的修改發表意見,指出:“資產階級權利問題(資產階級法權一詞當時已被改譯成資產階級權利—筆者注),要好好研究一下,從理論上講清楚,澄清‘四人幫’制造的混亂。工資級別一定要有,而且定級一定要以技術為主。工人的工資不一定是八級,還可以考慮多幾級。總之,八級工資制需要作些改革。行政人員的工資級別,也有一個改革問題。獎金一定要搞,問題是怎么搞得更合理。”5月5日,該文署名特約評論員,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這篇文章比《光明日報》那篇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還早了六天。這兩篇文章都是射向“兩個凡是”方針的利箭,都在解放思想、沖破“兩個凡是”思想牢籠的斗爭中
發揮了重要作用,故可看作為姊妹篇。
政研室在協助鄧小平反對“兩個凡是”方針中做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為鄧小平起草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為了起草這篇講話,鄧小平于1978年5月30日約胡喬木等人談話,指出:有的同志對這次政治工作會議的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政治工作,要保證人民解放軍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提法,同毛主席講的人民軍隊的革命本質不一致。總而言之,只要你講話和毛主席講的不一樣,就不行。毛主席沒有講的,你講了,也不行。怎么樣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講的,全部照抄才行。這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這是當前一種思潮的反映。這些同志講這些話的時候,講毛澤東思想的時候,就是不講要實事求是,就是不講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馬列主義哲學的概括,是馬列主義理論、馬列主義方法的概括。它同各種機會主義思想都是完全對立的,包括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左”的右的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要把這個意思寫進講話稿中。這是毛主席經常講的道理,也是他講得最多的道理,列寧也講得很多。我們講要繼承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培育的優良傳統,第一個就是實事求是。歸根到底,這是涉及什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什么是毛澤東思想的問題。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不從現在的實際出發來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這樣天天講四個現代化,講來講去都會是空的。他還指出:“我放了一炮,提出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后來又加了一句毛澤東思想的體系。有人說我這個提法是同華主席唱對臺戲,結果華主席用了我這個話,這些人不吭氣了。還有知識分子的問題,也有人說我的講話背離了毛澤東思想。
這些事都不是孤立的。”
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我們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是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不同實際情況相結合,就沒有生命力了。我們領導干部的責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級的指示同本單位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不能當“收發室”,簡單地照抄照轉。第二天,《解放軍報》在發表這篇講話時,特意加了一個標題,說講話“精辟闡述毛主席關于實事求是的光輝思想”。這篇講話的發表,對贊成和支持真理標準的廣大干部群眾,無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任何一種社會思潮都有其慣性。新中國黨的工作重點自從20世紀60年代逐步由經濟建設轉移到階級斗爭,直到70年代中后期“四人幫”被粉碎后,在事實上已逐步轉了回來。但在形式上,在黨中央對工作的部署上,仍然延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提法。那時提出的“新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在所謂“天下大治”的八項要求中,“抓革命、促生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只排到了第四位。因此,人們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經濟以及各項業務工作中,依然頗多顧慮,不能放開手腳,理直氣壯地抓生產、抓業務。對這種現象,第一個提出疑問提出要改變的是鄧小平。
前文說到,早在1975年全面整頓時期,政研室根據鄧小平提出以毛主席“三項指示為綱”的思想,撰寫了《論總綱》一文。文章雖未發表,但在“批鄧”運動中被揭發出來,遭到“四人幫”的猛烈抨擊,《紅旗》雜志發表了題為《一個復辟資本主義的總綱》,說“以三項指示為綱”完全是為了對抗“以階級斗爭為綱”。姚文元在《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上旁批,說它是“歪曲馬列,回到唯生產力論”。其實,“四人幫”把“以三項指示為綱”和《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說成是“唯生產力論”,才是“歪曲馬列”;但說“以三項指示為綱”的核心是“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實質是以經濟建設代替“以階級斗爭為綱”,倒是確實的。鄧小平是這個思想,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也是這個思想,而且,自從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這個思想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就沒有變過。正因為如此,他們經常會和“左”的思潮發生碰撞。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總理主持中央工作,提出批判極左思潮,把政治掛帥掛在業務上,是一例;1975年全面整頓中,鄧小平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的思想,又是一例。
1978年9月,鄧小平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朝鮮后,路過東北,一路走一路講要重視發展經濟的問題。他說:“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到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幫’也好,怎樣才叫搞好了,要有幾條標準。”“對搞運動,你們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遠沒有徹底的事。”“運動不能搞得時間過長,過長就厭倦了。……究竟搞多久,你們研究。有的單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結束”。這些話放到今天,人們可能會認為這是很自然很平常的道理,但在當時卻是需要解放思想、需要理論勇氣的。因為,自從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斗爭以來,把政治運動放在首位,用政治運動來帶動和促進經濟建設與各項工作,已成為人們的一種思維定式。正因為如此,鄧小平提出這個想法,很大程度上帶有試探性、啟發性,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點火”。他說:“我是到處點火,在這里點了一把火,在廣州點了一把火,在成都也點了一把火。”
回到北京,鄧小平于10月3日找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談話,請他們幫助修改由其他人為他準備的代表黨中央在工會九大上的致詞稿。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把他在東北講的話講得更清楚更明白了,他說:“現在到了這么個時候,‘四人幫’當然要批,但不能老是說什么都是‘四人幫’搞的。外國人有個議論說,你們什么都歸罪于‘四人幫’。歸罪于‘四人幫’還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以后一直都歸罪于‘四人幫’的干擾破壞。我想從這個講話開始,講一下這個道理。這次我在沈陽軍區講揭批‘四人幫’的問題,我說揭批‘四人幫’運動總有個底,總不能還搞三年五年吧!要區別一下哪些單位可以結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這個百分之十結束了,就轉入正常工作,否則你搞到什么時候。我們要把揭批‘四人幫’的斗爭進行到底,那么就要問‘底’在哪里?
現在可以暫時不說。”
后來,胡喬木等人把鄧小平的這個意思寫進了工會九大致詞。這篇文稿已收入《鄧小平文選》,其中就有這么一句:“很明顯……我們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幫’的斗爭進行到底。但是同樣很明顯,這個斗爭在全國廣大范圍內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們已經能夠在這一勝利的基礎上開始新的戰斗任務。”這里沒有用工作重點轉移這個詞,因為要改變黨的工作重點,需要黨中央正式作出決定,但看得出,所謂“開始新的戰斗任務”,就是工作重點轉移的意思。
10月中旬,胡喬木為了修改他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發言,到天津、上海搞調研,中途接到鄧力群的電話,說小平同志從日本訪問回來后要找喬木同志談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起草問題,請他29日趕回北京。胡回京后,即到鄧小平家中談話,接著便著手起草這篇講話稿。那時,鄧力群已經組織國務院政研室寫作組的林澗青、蘇沛、滕文生等幾位同志,按鄧小平的意思搞了個初稿。胡喬木看后,向他們進一步交代了思路,自己寫一部分,讓他們起草另外兩個部分。開始,由于鄧小平11月5日又要到東南亞訪問,胡喬木很是著急。后來,鄧決定從國外回來后再談講話稿的事,胡喬木這才松了口氣。11月8日,也就是工作會議前兩天,講話稿的初稿全部搞完,發給了鄧辦。鄧小平是11月14日晚上出訪回國的,16日即約胡喬木去他家談講話稿的事。那時,中央工作會議已經進行了六天。19日,胡喬木按鄧小平的意思把稿子改好,交我謄寫,
再次發給了鄧辦。
前些年,香港出了一本內地人寫的書,上面講11月5日,胡耀邦找馮文彬、阮銘和這本書的作者去,說鄧小平的講話由胡喬木起草,著重講工作重點轉移;葉劍英的講話讓作者和阮銘起草,著重講分清是非問題,都要在三天內寫出初稿。過了幾天,聽說他們起草的講稿基本被通過了,而胡喬木起草的講稿卻被否定了,并且獲得了一個“看來他不行了”的評語,講稿改由別人另擬云云。作者還說他看過那份講稿的復印件,稿子是胡喬木向秘書口授,秘書記錄,然后胡喬木親筆修改而成的(可能是指我謄寫的那份)。這些說法只要同我親身經歷的過程對照一下便可看出,它們不僅違背事實,而且帶有很大的演義成分。關于他們起草的葉劍英同志的講稿是否被通過的事,我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書中有詳細披露,這里不說,只說鄧小平的這個講話稿。
前文講到,這個稿子在10月下旬就按鄧小平交代開始寫了,11月16日,鄧小平約胡喬木談話,是談已寫出的初稿。初稿的定稿是19日發給鄧辦的。但過了沒幾天,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25日全體會議上已代表政治局宣布了一系列平反決定,加上天安門事件公開平反后在黨內和社會上引起的巨大反響,使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原來的講話稿按照鄧小平的意思,中心講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胡喬木的構思是先講重點轉移的意義,然后講怎樣才能實現這個轉移,其中講要解放思想,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要改革不適應發展生產力需要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等等。但會場內外形勢的變化,使重點轉移已經不成為問題了,突出的問題變成了真理標準討論、發揚民主、團結一致向前看和經濟管理體制等等。這樣一來,胡喬木為鄧小平準備的講話稿便顯得不適用了。于是,12月2日,當中央工作會議進入后期時,鄧小平再次約見胡喬木等人,談講話稿問題。那時,胡喬木按中央決定,正在集中力量修改《關于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稿,而鄧力群又隨國家經委的代表團去日本訪問,不在國內。按照政研室起草文件的工作程序,一般是胡喬木為第一層次,鄧力群為第二層次,以林澗青為首的寫作組為第三層次。任務來了,先由胡喬木談個想法,然后通過鄧力群交給林澗青,待寫作組拿出初稿后,交鄧力群先改一道,最后送胡喬木。鄧小平此前的幾個重要講話稿,包括為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準備的第一個講話稿的起草,都是這么運作的。所以,胡喬木在12月2日去鄧小平家談話之前,叫上了代替鄧力群作為政研室代表參加會議的于光遠(鄧力群那時剛好去國外訪問),準備讓他作為第二層次,組織林澗青等人先搞出個初稿。
1997年夏天,《百年潮》上發表的《一份鄧小平珍貴手稿的發現》上說,鄧小平在談話時拿出了自己寫的講話提綱,共七條,手稿仍在于光遠家里。文中還說:“小平同志的講話稿是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寫成的。最初請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個稿子,小平看了不滿意。他就自己親擬了這份提綱,召集胡耀邦、于光遠等談起草講話稿的問題。”鄧小平的這個提綱,我估計是在12月2日那天,由于胡喬木要讓于光遠先組織人寫初稿,所以交給他拿走了。不過,當起草的寫作組按八個問題寫出第一稿后,鄧小平在12月5日又找胡喬木等人去談話,說他考慮只講四個問題。胡喬木事后對我說過大意,我記得的是:“這次別的問題都不講了,只講四個問題:第一,解放思想。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的確是一個思想路線問題,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是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第二,發揚民主。當前最迫切的是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民主選舉的范圍要逐步擴大。第三,向前看。對過去搞錯了的要糾正,也要給犯錯誤的同志認識和改正錯誤的時間。對毛澤東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評價,要從國際國內的大局出發,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第四,研究和解決新問題。要用經濟辦法管理經濟,要特別注意加強責任制。要用先使10%—20%的人富裕起來的辦法,擴大國內市場,促進生產發展。”后來,鄧小平在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講的就是這四個問題。
胡喬木如何向起草同志作交代,我不在場,不清楚,但他們每寫出一稿都送到胡喬木手里則是確實的。僅我記錄,胡喬木就改過兩次。一次是12月6日,林澗青他們按照鄧小平12月5日的談話,把稿子分四個問題寫完后送來。記得那天晚上,胡喬木并沒有動筆,但第二天早飯后,他卻把改過的稿子交給了我。我問他是什么時候弄的,他說是半夜2點爬起來,用了兩個多小時改好的。鄧小平看后,于12月9日再次約胡喬木等去,說這回稿子差不多了,并提了一些小的修改意見。另一次修改是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當天,鄧小平下午4點就要講話了,午飯后,胡喬木還在對講話稿進行最后的文字潤色,直到下午2點才脫手。由于距離開會時間很緊迫,他要我坐他的車,將講話稿直接送到鄧小平住地,親手交給了王瑞林秘書。
以上情節,我早在為紀念胡喬木逝世兩周年而寫的《胡喬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一文中就已作過披露,文章發表在《黨的文獻》1994年第5期上。那時,還沒有什么人,無論內地的還是海外的,在媒體上說到鄧小平講話稿的起草問題。從這個過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第一,胡喬木在11月19日前為鄧小平準備的講話稿是根據鄧本人幾次談話精神寫成的,之所以重寫,是因為鄧小平回國那天,中央工作會議已經進行了四天,會議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存在什么鄧小平對那個稿子“不滿意”的問題。第二,胡喬木從始至終參與了對第二個稿子的起草工作,并參加了在鄧小平家中的幾乎所有談話,不存在“看來他不行了”“改由別人另擬”的問題。
關于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前文已經說到,自從“四人幫”被粉碎后,大部分地方和部門在實際工作中已經轉向了經濟和其他領域的建設,只是在黨的路線、方針層面還沒有轉過來。因此,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工作會議一開始就宣布,從明年1月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是這次會議的中心思想。華國鋒在講話中解釋說:粉碎“四人幫”后的兩年,揭批“四人幫”運動是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推動了全局。現在的問題是,揭批“四人幫”運動已經達到什么火候了?恰當地估量運動的發展狀況,是我們提出轉移全黨工作著重點的重要依據。人們現在知道,政治局的這個決定是常委的建議。從以上材料可以斷定,所謂常委的建議,實際上就是鄧小平的建議。不同的是,鄧小平在10月3日同胡喬木等人談話時講的“可以暫時不說”的“底”,到了中央工作會議之前已經明確為1978年底,就是說,1978年底結束揭批“四人幫”運動,1979年1月全黨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關于這一點,胡耀邦在1980年11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曾明確說過:“1978年9月份,小平同志在東北提出了全黨工作著重點的轉移,為三中全會的方針,為今后黨的工作方針,作出了決策。”這些過程說明,工作重點的轉移絕非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臨時動議,而是從1975年開始就在黨內醞釀,并在粉碎“四人幫”之后經過反對“兩個凡是”方針,使時機逐漸成熟后作出的決策。
華國鋒在宣布中央政治局關于從1979年1月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定時,前面還有一句“要在新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的指引下”。而所謂“新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一個重要內容是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所以,“要在新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的指引下”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表述,實質是說要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引下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這顯然變成了兩個重點、兩個中心,與鄧小平提出的工作重點轉移的含義完全不同。另外,他在講話中解釋重點轉移的理由時,強調這是國內國際形勢的需要。這引起了胡喬木的注意。
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進入小組討論后的第二天,即11月12日下午,午睡一醒,胡喬木就叫我到他房間,說:“把工作重點的轉移講成是形勢的需要,這個理由不妥。應當說,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就要把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建國后,我們已開始了這種轉移,但是沒有堅持住,這次轉移是根本性的轉移,而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轉移。不能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今天形勢需要,就把工作重點轉過來,明天不需要了,還可以再轉回去。”他要我幫他查幾條馬列和毛澤東的有關論述,說在下午的小組會上要用。下午,他在發言中引用了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話,說明“我們的一切革命斗爭,終極目的是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立場,是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并不是任何階級斗爭都是進步的,其是否進步的客觀標準,就是看它是否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創造條件”;“經濟脫離政治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政治脫離經濟也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他說:“除了發生戰爭,今后一定要把生產斗爭和技術革命作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只要我們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國內的階級斗爭也
不會威脅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心地位。”
胡喬木的發言很快被簡報全文刊用,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贊同。在他后來負責起草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上,這個意思也寫了進去。公報說:“毛澤東同志早在建國初期,特別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黨,要把工作中心轉到經濟方面和技術革命方面來。”“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應該按照嚴格區別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針去解決,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去解決。”這就在實際上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提法,賦予了“工作重點轉移”這一命題以更大的科學性、穩定性,使它有了更強的生命力。
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至今已有40多年了。新中國成立后近75年,包括十一屆三中全會后40多年實踐的反復檢驗,證明這一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也是符合社會主義社會客觀實際和廣大人民意愿的。對此,我們應當一如既往,堅定不移。同時也要看到,說以經濟建設為全黨工作的重點,不等于說其他工作,比如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設工作、反腐倡廉工作等等就不重要;改變“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提法,不等于社會主義社會就沒有一定范圍內的階級斗爭、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就過時了。更不等于說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階級斗爭也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了。對這些問題,我們要全面理解,否則也會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出現另一種片面性。那同樣是不符合實際的,同樣會給我們的事業帶來
損失。(責任編輯 楊琳)
作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陳云與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