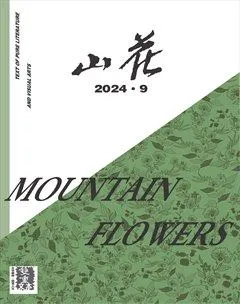孤獨(dú)及其所創(chuàng)造的
春天時(shí),我下定決心,搬離鬧哄哄的市區(qū),在北京的遠(yuǎn)郊,找到一處四面環(huán)山的山谷,開(kāi)始了某種并不算徹底隱居的山居生活。
從市區(qū)到這里,只有一條路可走,朋友開(kāi)玩笑說(shuō),若是深冬大雪封山,你出都出不來(lái)了。去往山谷,跨過(guò)水面寬闊的永定河后,要接連穿過(guò)兩座隧道,分別名為苛蘿坨與潭柘寺。待車(chē)穿過(guò)兩座山的黑暗山體,重入光明之時(shí),原本朝同一方向行駛的車(chē)輛,高架邊的萬(wàn)家燈火,屬于城市生活的嘈雜聲浪,盡數(shù)被隧道攔截,周遭驟然寂靜,群山顯現(xiàn),靜默環(huán)繞,天地間,仿佛只有我了。
這是我為自己找到的某種“縱身入孤獨(dú)”的方式,某種物理意義上的“與世隔絕”。
搬家的那一天,粉色山桃花開(kāi)得漫山遍野,我朝著山的方向不斷靠近,腦海中不斷循環(huán)著同一句話,“如果我們縱身入孤獨(dú)呢?如果那就是喜悅呢?”
這句話來(lái)自我翻譯的一本隨筆集——《孤獨(dú)故事集》,我忽然意識(shí)到,恰好是一年前的這一天,我交掉書(shū)稿,結(jié)束了探索二十一顆孤獨(dú)心靈的旅程,仿佛一種暗示,整整一年后,我自己的生活完成了與書(shū)籍的互文,我終究“縱身入孤獨(dú)”了。
喜悅嗎?的確是喜悅。同時(shí)也有一種隱約的希望,在未抵達(dá)山谷的半路上,我已經(jīng)想象出在與世隔絕的山中,閱讀,寫(xiě)作,隔離人事,盡情向內(nèi)探索。所以我縱身?yè)淙氲模敲麨楣陋?dú)的希望,希望自然同喜悅相連,因?yàn)樯形磳?shí)現(xiàn),因?yàn)橛袑?shí)現(xiàn)的可能。
搬完家的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孤獨(dú)故事集》的譯者樣書(shū)。時(shí)隔整整一年,這一年的時(shí)間刻度上,又塞滿了我翻譯的其他作品,我自己寫(xiě)下的故事,所以這本書(shū)中的一段段人生碎片與細(xì)節(jié),都被掩埋在了記憶的汪洋之下。
但我沒(méi)有急著重新閱讀它,因?yàn)楹退黄鸬诌_(dá)的,還有另一本書(shū),名為《我所告訴你關(guān)于那座山的一切》,初初搬到山中的我,自然先打開(kāi)了這一本。
但是在翻開(kāi)這本書(shū)前,我并不知曉這會(huì)是一本讓我如此心痛的書(shū),我不知道作者劉宸君的生命定格在了十九歲,定格在了尼泊爾的山中巖洞;更無(wú)法想象與旅伴困守絕境四十多天的她,內(nèi)心都經(jīng)歷了怎樣的跌宕與煎熬,是懷著怎樣的心情寫(xiě)下那些筆記與書(shū)信?而她唯一的旅伴,又是怎樣在她離世后,獨(dú)自在山洞中又熬過(guò)了三天,最終等到了救援,帶著她的遺體與遺稿,重返人間?
書(shū)中有兩句話刺痛了我。
一句是她問(wèn)自己的老師吳明益,“害怕孤獨(dú)的人可以寫(xiě)作嗎?”
一句是她在洞穴中寫(xiě)下的,“我還是想要活下來(lái)。”
在無(wú)情而短暫的一生中,她落入了名為孤獨(dú)的絕望。
我看向窗外輪廓嶙峋的群山,它帶來(lái)喜悅,也帶來(lái)絕望;它亙古綿延,也轉(zhuǎn)瞬崩塌;它已經(jīng)存在了很久很久,并將繼續(xù)存在。人步入山中,制造出千萬(wàn)種命運(yùn),一如步入孤獨(dú),締結(jié)出千萬(wàn)種果。
無(wú)論是主動(dòng)尋求孤獨(dú),還是因懼怕而躲避孤獨(dú),最終,孤獨(dú)好像都會(huì)成為最適合文學(xué)發(fā)生的土壤,擁抱孤獨(dú)或懼怕孤獨(dú)的人,都會(huì)以形形色色的痛苦與喜悅,澆出了一片瘋長(zhǎng)的花園。
我想,孤獨(dú)大概本就是文學(xué)的起點(diǎn)吧。古老先民在莽荒深夜點(diǎn)起篝火,結(jié)繩記事,鑿壁作畫(huà),編織故事,口口相傳,人類(lèi)不就是靠著深夜的一點(diǎn)光亮和一筆故事,蹚過(guò)孤寂的深夜,打發(fā)無(wú)所事事,寂寞無(wú)聊,綿延到今天?從有了人開(kāi)始,就有了孤獨(dú)。
正是在這樣一個(gè)時(shí)刻,我重新翻開(kāi)了《孤獨(dú)故事集》,迎面又遇見(jiàn)那句“如果我們縱身入孤獨(dú)呢?如果那就是喜悅呢?”
二十一位風(fēng)格與背景天差地別的作者,二十一段毫不遮掩的人生故事,這些小說(shuō)家從虛構(gòu)人物背后走了出來(lái),撕碎語(yǔ)言上的重重委婉與粉飾,直白地寫(xiě)下了自己的脆弱,痛苦,不堪。隨著我一篇篇重讀,那些在這一整年中被遺忘的孤獨(dú)的不同形態(tài)又逐漸浮出迷霧,一一被我打撈出水面,漸次清晰起來(lái),而在翻譯過(guò)程中的唏噓與共鳴,也都如退潮的海浪重返潮間帶,駐足海岸線的我,全都想了起來(lái)。
我想起這本書(shū)里形形色色的孤獨(dú),關(guān)于性別、欲望、移民、成癮、疾病等等,有許多孤獨(dú)的形態(tài),我都不曾切身經(jīng)歷,卻完全可以感同身受。也許,就像這世上所有的山脈都是彼此相連,這世上所有的孤獨(dú)也同樣殊途同歸,是同一片海洋里誕生的浪花,只是呈現(xiàn)出不同的色澤、形態(tài)與強(qiáng)度。只要我們體驗(yàn)過(guò)孤獨(dú),就能理解彼此的孤獨(dú),理解從孤獨(dú)出發(fā)而創(chuàng)造出的一切。
隱于生活的B面
娜塔莉自幼病弱,常常要請(qǐng)假在家休息,因此度過(guò)了許多獨(dú)自一人的時(shí)光。在擁有過(guò)多獨(dú)處機(jī)會(huì)的漫長(zhǎng)少女時(shí)代,她喜歡上了閱讀,甚至主動(dòng)尋求這種獨(dú)處的時(shí)刻。她想到,這種被迫陷入孤獨(dú),又反過(guò)來(lái)?yè)肀Ч陋?dú)的體驗(yàn),或許并非只在自己身上出現(xiàn),因此決定編纂一本以“孤獨(dú)”為主題的作品集。她向諸多作家發(fā)去邀約,回應(yīng)她的女作家要遠(yuǎn)遠(yuǎn)多過(guò)男作家,所以她在序言中說(shuō),“這本書(shū)更多地容納了她們對(duì)于孤獨(dú)的觀點(diǎn)。”
全書(shū)有三分之二的篇目出自女作家之手。男作家們書(shū)寫(xiě)的孤獨(dú)涉及種族問(wèn)題,以及對(duì)夢(mèng)想的追求,對(duì)科技社會(huì)的反思;而女作家們所寫(xiě)的孤獨(dú)則更內(nèi)向,更微觀,更復(fù)雜,也更隱匿,隱匿于日常生活的一舉一動(dòng),隱匿于稀松平常的日復(fù)一日,隱匿于無(wú)比正常又尋常的一餐一飯。
因此,我們是否也可以說(shuō),熱熱鬧鬧的現(xiàn)實(shí)生活,其實(shí)也更多地容納了屬于女性的孤獨(dú)?抑或是,無(wú)數(shù)女性將自己的孤獨(dú)隱藏了起來(lái),所以生活才有了熱鬧的面目?這種隱匿的孤獨(dú)發(fā)不出聲響,無(wú)法慷慨激昂地表達(dá),無(wú)法呼救,甚至飽含難以道明的矛盾。我們從這些女性故事中不難發(fā)現(xiàn),女性往往和娜塔莉一樣,一邊感受著孤獨(dú),一邊又追求著孤獨(dú)。
在翻譯這本書(shū)的過(guò)程中,同樣身為女性寫(xiě)作者的我,仿佛參加了一場(chǎng)奇異的聚會(huì)。姐妹們坐在一起,聊著各自的生活,剖析各自的痛苦,信息密度極高,卻又是不聲不響的。我在這種無(wú)聲的傾聽(tīng)與傾訴中,不斷代入自我,不斷回憶過(guò)往,不斷點(diǎn)頭,不斷理解,忽然間,就弄清楚了有關(guān)女性孤獨(dú)的那個(gè)悖論:原來(lái)身為女性,我們并不是一邊感受孤獨(dú)一邊求索孤獨(dú),而是當(dāng)我們看清并接受自身的孤獨(dú)處境后,決定只身上路,看看孤身一人能走到哪里。我們不是去追求孤獨(dú),而是追求遠(yuǎn)方某個(gè)模糊的目標(biāo)。我們并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哪里,會(huì)得到什么,沒(méi)有想過(guò)得到獎(jiǎng)勵(lì),甚至從出發(fā)的那一刻就作好了被命運(yùn)贈(zèng)予一場(chǎng)空的最壞打算,我們只是決定離開(kāi)此地,去往他方,親身實(shí)踐一場(chǎng)屬于英雄的奧德賽史詩(shī)。
就像海倫娜·菲茨杰拉德在《一種奇異而艱難的喜悅》中提及的,經(jīng)典文學(xué)中滿是英雄,其中絕大多數(shù)都是男性。他們之所以成為英雄,就是因?yàn)樽呱狭斯陋?dú)求索之路。在這樣的追尋敘事中,男人斬?cái)嗨猩鐣?huì)紐帶,在孤獨(dú)的試煉中完善自我,再高奏凱歌重返社會(huì)。《奧德賽》及它的仿效之作都是追隨一個(gè)男人的成長(zhǎng)展開(kāi),他在冒險(xiǎn)與悲劇事件之中失去了所有同伴,也失去了與社會(huì)的全部聯(lián)系,不得不找尋回歸的路途,穿越重重險(xiǎn)阻,孤軍奮戰(zhàn)。當(dāng)這些男人最終結(jié)束英雄漫游歸來(lái)時(shí),社會(huì)仍舊原封不動(dòng)地等著他們,因?yàn)榕藗円恢痹谡展芤磺小E运坪鯊膩?lái)沒(méi)有這樣的獨(dú)立機(jī)會(huì),也鮮少得到同樣的機(jī)遇去沖破社會(huì)桎梏,去發(fā)現(xiàn)自我,并作為英雄回歸日常,被褒獎(jiǎng),被傳頌。
恰恰相反,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女性因?yàn)椴辉ネ椋辉袛嗯c社會(huì)的聯(lián)系,所以整個(gè)社會(huì)傳統(tǒng)都期待她們通過(guò)社交與情感將一切人事物彌合起來(lái),離經(jīng)叛道的女性不是英雄,而是瘋子。社會(huì)法則一廂情愿地認(rèn)定,女性需要被保護(hù),不需要承受試煉。仿佛是好意,是溫情,而這,反而成為了女性孤獨(dú)感的來(lái)源。最無(wú)助的是,一旦你表達(dá)出你因此而孤獨(dú),得到的回饋可能是“矯情”,因此你選擇了沉默,將一切藏匿。難道這樣的孤獨(dú)就不值得書(shū)寫(xiě)嗎?在我看來(lái),這份孤獨(dú),反而更接近于人類(lèi)真正的孤獨(dú),在女性的身上,往往寄宿著人本身的困境與出路。所以,當(dāng)英雄神話的時(shí)代落幕,當(dāng)代的女性們選擇在人生中孤身上路。
艾米·謝恩在《孤身行路的女人》這一篇里,就提及了這樣一個(gè)女人。一個(gè)名叫莉莉安的東歐移民,忽然離開(kāi)紐約,獨(dú)自步行前往西伯利亞。對(duì)于她的出走,眾說(shuō)紛紜,但莉莉安自始至終不曾開(kāi)口肯定任何一種揣測(cè),回應(yīng)任何一種爭(zhēng)議。她于平安夜出發(fā),身穿連衣裙,腳踩普通的網(wǎng)球鞋,戴一條頭巾,沉默不語(yǔ),一路向北。
艾米在下班回家的地鐵上,通過(guò)播客聽(tīng)到了莉莉安的故事。那一刻,她身處沙丁魚(yú)罐頭一樣的地鐵車(chē)廂里,被婚姻、家庭、工作、書(shū)稿壓得喘不過(guò)氣,她忽然不知道了,自己和莉莉安相比,究竟誰(shuí)更孤獨(dú)?
紐約一如這顆星球上所有的巨型城市,因?yàn)樘^(guò)擁擠,反而讓人成為了人潮之中的孤島,地鐵上密密貼在一起的身體間,有著無(wú)法跨越的鴻溝。在這樣的城市生活中,身體的距離越近,心的距離就可能越遠(yuǎn)。因而對(duì)莉莉安來(lái)說(shuō),獨(dú)處,獨(dú)自長(zhǎng)途跋涉,投奔某個(gè)應(yīng)許之地或應(yīng)許之人,反而成為了最不孤獨(dú)的選項(xiàng)。艾米忽然意識(shí)到,自己之所以感到孤獨(dú),好像正是因?yàn)樽约簭奈垂律硪蝗耍纳磉吺冀K有丈夫,有孩子,有密不透風(fēng)的陌生人,所以她無(wú)比孤獨(dú)。
她渴望去一個(gè)靜謐之地,有陸地,有天空,獨(dú)自一人,頭腦清醒,心中念著他人,而不是被他人占據(jù)頭腦,連自己都被擠了出去。她渴望體驗(yàn)與世界有所連接的孤獨(dú)狀態(tài),而不是身處熙熙攘攘的陌生人之中,卻覺(jué)得自己如此疏離。
就像安妮·林德伯格在《大海的禮物》中所寫(xiě)的,如果一個(gè)人與自己失去了聯(lián)系,那么他就無(wú)法觸及他人……只有當(dāng)一個(gè)人與自己的內(nèi)核建立聯(lián)系,他才能夠與他人建立聯(lián)系。而這一內(nèi)核,往往能夠在獨(dú)處中尋得。
艾米選擇用另一種方式對(duì)待家庭與工作,她搬了出去,為自己租了個(gè)小房子,從日常中剝離出了一小塊空間與時(shí)間,把與丈夫毫無(wú)深入交流的朝暮相對(duì)、圍繞孩子的公轉(zhuǎn)運(yùn)動(dòng)統(tǒng)統(tǒng)屏蔽在門(mén)外。在這個(gè)由她親手撕裂的時(shí)空中,她讀書(shū)、寫(xiě)作、思考、聽(tīng)音樂(lè)、廣交友,并計(jì)劃著長(zhǎng)距離的徒步,在寫(xiě)下這些時(shí),她說(shuō)她的不快樂(lè)業(yè)已蒸發(fā)殆盡。
在這本故事集里,艾米不是唯一選擇以孤獨(dú)對(duì)抗孤獨(dú)的女性,甚至不是少數(shù)派。在古老的敘事中,享受孤獨(dú),離群索居的女人被刻畫(huà)成怎樣呢?女巫,怪胎,熬制毒藥,不懷好意。曾經(jīng),女性懼怕被這樣看待,被這樣評(píng)價(jià),沒(méi)人想成為那個(gè)“閣樓上的瘋女人”;但今天,這本書(shū)里的女作家們卻說(shuō),獨(dú)居讓人成為森林中的女巫,強(qiáng)大,警覺(jué),沉默,讓訪客不寒而栗,她們?cè)趯儆谂椎哪强阱佒校靖闪四欠莶豢鞓?lè)。
這種身處鬧市卻形同孤島的不快樂(lè),正是隱匿于日常生活的B面,翻開(kāi)來(lái)便意味著觸碰了禁忌與羞恥。
你明明有著幸福美滿的婚姻,忠誠(chéng)的丈夫,可愛(ài)的孩子,為何感到孤立無(wú)援?
當(dāng)你因?yàn)樵杏律惺苤T多疼痛時(shí),朋友與丈夫都愿意體諒你,理解你,為何你還是覺(jué)得無(wú)人能感受你的切膚之痛?
為什么脫離日常生活的軌跡,剝脫熟稔的身份,獨(dú)自在陌生城市工作、生活,走在真正陌生的人群中,會(huì)讓你無(wú)比自在?
當(dāng)所有人都表現(xiàn)得很快樂(lè),很合群,你為何要不合時(shí)宜,談?wù)撘粋€(gè)不快樂(lè)的話題,成為冒出來(lái)的那顆釘?
然而事實(shí)上,若我們認(rèn)真審視自己的生活,會(huì)發(fā)現(xiàn),正是這些被壓抑、不見(jiàn)天日的“不快樂(lè)”,為孤獨(dú)感提供了源源不絕的能量。不能與他人言說(shuō)之困境,當(dāng)然是一種精神上的隔離。如果我們始終無(wú)視生活的B面,那我們只是在假裝生活。
幸福絕不是來(lái)源于敷衍與自欺,所以作家們選擇暫停歡愉的樂(lè)曲,抽出卡帶,翻過(guò)B面,重新按下播放鍵,仔細(xì)聆聽(tīng),深入思考,勇敢地自我剖白,筆亦如手術(shù)刀,徑直探入自己體內(nèi)真正的病灶。而如此對(duì)待自己,恰恰是因?yàn)椋麄兿胍徑膺@份孤獨(dú),找到與孤獨(dú)溫柔同處的方式。在這個(gè)求索的過(guò)程中,娜塔莉說(shuō),“孤獨(dú)感縱然極具破壞力,但我發(fā)現(xiàn),它也能充當(dāng)通往美與探索的門(mén)戶(hù),這就足夠動(dòng)人心弦。”因此,有了這本《孤獨(dú)故事集》。
而開(kāi)篇第一個(gè)故事,梅根·吉丁斯就鼓勵(lì)想要寫(xiě)作的女孩們獨(dú)自去電影院看電影。她認(rèn)為,在開(kāi)始藝術(shù)生涯時(shí),無(wú)需考慮他人、只在乎自己的所見(jiàn)所聞與喜好的自由感是不可或缺的,而這種自由感可以通過(guò)獨(dú)自去看一場(chǎng)電影來(lái)實(shí)現(xiàn)。我們完全可以“只看向自己的內(nèi)心,由此去了解周遭的世界”,不要恐懼獨(dú)自去做些什么,這份敢于在世間冒險(xiǎn)的勇氣,是寫(xiě)作所需要的,也是生活所需要的。
因此她熱衷游泳、皮劃艇等諸多運(yùn)動(dòng),甚至險(xiǎn)些因此喪命湖中。她說(shuō)得最多的話就是,“我不害怕。”
深夜,我站在寂靜山腳下仰望山的輪廓,漆黑的山在漆黑的夜空里勾勒出參差嵯峨的色塊,不言不語(yǔ),充滿了壓迫感,與白晝時(shí)它所展現(xiàn)的溫柔連綿截然不同。在直面山的那一刻,我想到的也是,“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
其實(shí),“我不害怕”與“孤身上路”都是作家們?yōu)樽约旱睦Ь痴业降拇鸢浮I硐莨陋?dú)的囹圄,所以決定“孤身上路”;被迫面對(duì)未知與動(dòng)蕩,因此只好自言自語(yǔ),“我不害怕。”
生活中這些看似矛盾的行動(dòng),恰恰構(gòu)成了文學(xué)之中的正當(dāng)邏輯。
書(shū)中這些用行動(dòng)詮釋“我不害怕”的作家,幾乎可以說(shuō)是別無(wú)選擇,因?yàn)樗麄兌际亲约核幁h(huán)境中的那個(gè)“極少數(shù)”,與他人有著表面上醒目或內(nèi)在上根本的區(qū)別,無(wú)論是被大多數(shù)人感知到這種不同,還是自我認(rèn)知到這種區(qū)隔,都意味著一種“孤軍奮戰(zhàn)”的處境,這份身為“異鄉(xiāng)人”的孤獨(dú),要與之共處,只能選擇不害怕。
比如身為黑人的杰弗里·艾倫,由在白人家中做女傭的單身母親撫養(yǎng)長(zhǎng)大,本就成長(zhǎng)在夾縫求生的環(huán)境,偏偏又患有哮喘,因此不擅交際,沉默敏感。當(dāng)他第一次在電影院看到李小龍的電影時(shí),他為拳腳功夫而狂熱。其實(shí)拳腳功夫不過(guò)是勇氣的具象化表現(xiàn),是他可能擁有的、對(duì)抗歧視的武器。
比如用英文寫(xiě)作的華裔作家郭珍芳,無(wú)論是小小年紀(jì)跟隨家人初到美國(guó),還是結(jié)婚生子定居北歐,在西方世界里,她永遠(yuǎn)是個(gè)與眾不同的面孔,永遠(yuǎn)無(wú)法拋棄屬于東方人的思維方式。小時(shí)候,她貧窮困苦,在同齡人中得不到理解,于是她拿“雄心壯志”填補(bǔ)了這一切,通過(guò)自學(xué),考入哈佛大學(xué)物理系,寫(xiě)出暢銷(xiāo)書(shū),把生活的主導(dǎo)權(quán)奪回到手中。這份雄心壯志,便是她的“不害怕”。
再比如出生并成長(zhǎng)于考文垂的英國(guó)作家彼得·戴維斯,在他的回憶之中,童年生活黯淡無(wú)光,乏善可陳,因?yàn)樗麩嶂钥苹梦膶W(xué)與電影,但在考文垂,他找不到可以交流的同類(lèi)。縱然考文垂是他的故鄉(xiāng),縱然家人朋友都在身邊,縱然這就是他在世界上最熟悉的地方,可他仍覺(jué)得格格不入,人生于他,仿佛一場(chǎng)星際迷航,在茫茫的宇宙中,他只能獨(dú)自航行,尋找能夠并肩一段路的同伴。
還有伊朗的作家蒂娜·耶納里,少女時(shí)代,她和家人成為難民,背井離鄉(xiāng),非法移民到美國(guó)。她學(xué)會(huì)了在沒(méi)有朋友的情況下生活,因?yàn)樗l(fā)覺(jué)自己無(wú)法成為任何人的朋友,只能成為他人慈善的接受者,是所有人憐憫的對(duì)象。那時(shí)的她,做了和郭珍芳一樣的選擇,努力學(xué)習(xí),取得成就,逃離過(guò)往。這個(gè)過(guò)程當(dāng)然稱(chēng)不上順利,她做過(guò)很多傻事,經(jīng)歷過(guò)很多次挫敗,暴露過(guò)很多次脆弱,也隱藏了許多的不堪。無(wú)論她把生活粉飾得如何熱鬧,總有那么一個(gè)光照不到的黑色角落。
在故事的最后,她是這樣寫(xiě)的,“隨著每一章徐徐展開(kāi),都有一個(gè)新的黑色角落出現(xiàn),每一個(gè)都以自己驚人的方式丑態(tài)百出。但十年后,我仍然會(huì)說(shuō),下一次,我會(huì)勇敢的。”
我忽然從這些截然不同的作者身上,看到了屬于人類(lèi)的共性,我們遇到的一切現(xiàn)實(shí)層面的難題,似乎都可以通過(guò)精神層面予以解決。無(wú)論那個(gè)現(xiàn)實(shí)的難題有多復(fù)雜,只消一句簡(jiǎn)簡(jiǎn)單單的“我不害怕”,好像我們真的就可以壯起膽子走夜路了。
其實(shí),在說(shuō)出“我不害怕”時(shí),就代表著他們已經(jīng)感受到了膽怯的存在。但無(wú)人能給他們壯膽,他們也不能調(diào)頭逃跑,所以只能自己推著自己,硬著頭皮往前沖。這種人生經(jīng)驗(yàn)絕對(duì)不是屬于這些作家的個(gè)例。我始終相信,沒(méi)有人次次都站在大多數(shù)那一邊。在我們一生中的某個(gè)階段,某些時(shí)刻,某些處境中,我們一定都成為過(guò)那個(gè)“異鄉(xiāng)人”,我們一定都有過(guò)那種格格不入,與他人不同,無(wú)法融入的尷尬體驗(yàn)。
大到只身留學(xué)、移民,進(jìn)入截然不同的文化環(huán)境,小到參加一場(chǎng)派對(duì),除了組織者外你誰(shuí)都不認(rèn)識(shí),而在場(chǎng)所有人早已相互熟絡(luò),抑或是更換工作,承受新團(tuán)隊(duì)對(duì)你的防備與疏離,在這些時(shí)候,我們都會(huì)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異鄉(xiāng)人”。
消化這種孤獨(dú)所需要耗費(fèi)的時(shí)間、情緒、能量,都需要我們獨(dú)自承擔(dān)。無(wú)論是一晚上,還是一年,甚至十年,我們一定都像這些作家們一樣,告訴過(guò)自己,“我不害怕”。是的,無(wú)論是我們,還是書(shū)中的作家們,在千差萬(wàn)別又殊途同歸的異類(lèi)感中,似乎真的沒(méi)有更好的辦法與經(jīng)驗(yàn)可以模仿或傳遞。
畢竟,我們都是孤身來(lái)到這個(gè)世界,也將孤身離開(kāi)這個(gè)世界,這兩者才是僅有的真正意義上的普遍經(jīng)驗(yàn),卻沒(méi)人能夠傳授給我們,因此我們每個(gè)人,其實(shí)都是這世上永遠(yuǎn)的異鄉(xiāng)人。
永遠(yuǎn)的異鄉(xiāng)人
如果說(shuō)上述種種孤獨(dú)都是有解的命題,有一些“異鄉(xiāng)人”所面對(duì)的,卻是另一種孤立無(wú)援的處境。“我不害怕”縱然可以支撐我們走下去,但有些痛苦如同疤痕,終生伴隨,隱隱作痛,哪怕遇到與你有相似傷口的人,也依然無(wú)法讓你釋?xiě)逊趾痢?/p>
同樣的痛苦降臨到不同的人身上,痛苦不會(huì)被稀釋?zhuān)總€(gè)人承受的依然是完完整整的痛苦。我在這本書(shū)里,就讀到了這樣的痛苦,幾乎全部來(lái)自醫(yī)院。
身患多種慢性免疫疾病的依曼妮是住院部的常客,她知道自己以比他人更快一些的速度,走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這太殘酷。作為一個(gè)內(nèi)向的創(chuàng)作者,日常生活中她頻繁贊頌獨(dú)處的美好,可是一旦住到病房里,獨(dú)處的慰藉便不復(fù)存在了,門(mén)外的腳步和嘈雜與她無(wú)關(guān),她感受到被世界拋棄的寂靜,獨(dú)處在此刻成為了不能承受之重。
我曾在體檢時(shí)查出一些模棱兩可的問(wèn)題,在一次次的深入檢查、不確定、等待、反復(fù)檢查中,我第一次真正直面疾病與死亡的關(guān)聯(lián)。此刻我才清楚地意識(shí)到,無(wú)論我在小說(shuō)中虛構(gòu)過(guò)多少種死亡,做過(guò)多少次練習(xí),在親自等待命運(yùn)宣判的那一刻,那種全世界被消了音的寂靜感,無(wú)法同任何人言說(shuō),哪怕是父母,哪怕是愛(ài)人。
但與此同時(shí),同恐懼、敏感、焦慮并存的,還有一次詭異的平靜,在回想過(guò)往,想象將來(lái)的時(shí)刻,對(duì)身邊的人們懷著更溫柔的愛(ài)意。
所以我非常理解依曼妮在故事的最后,用充滿疼愛(ài)的口吻提及孩子,她說(shuō)“孩子們散發(fā)的陽(yáng)光,穿透了孤獨(dú),每一次都救了我”。孩子不必理解她的孤獨(dú),但孩子可以治愈她。
正如我的家人無(wú)法理解坐在核磁共振檢查室門(mén)口的我有多么孤獨(dú),但沒(méi)關(guān)系,他們依然讓我感受到了慰藉。
另一個(gè)作者杰絲米妮在新冠期間失去了她摯愛(ài)的丈夫。他們擁有堪稱(chēng)完美的愛(ài)情,丈夫?qū)⒋罅繒r(shí)間與精力投入給她和孩子,幾乎時(shí)時(shí)刻刻陪伴在她身邊,是溫柔細(xì)膩又可靠的伴侶。
我向來(lái)很懼怕看到或想象這樣的故事,因?yàn)槲仪『靡灿羞@樣一個(gè)細(xì)膩而可靠的伴侶,我常常想到數(shù)十年后,我們將徹底從世上消失,成為宇宙里的微塵,每念及此,我就會(huì)感到某種宏大的虛無(wú)籠罩下來(lái)。
七年前,他曾因中樞神經(jīng)感染突然暈厥,我人生中第一次撥打了120。他住進(jìn)醫(yī)院,直到三周后出院,都沒(méi)有查出確切病因。他住的醫(yī)院在北京最熱鬧的商區(qū)三里屯。那段時(shí)間正是臨近農(nóng)歷新年,我每天頂著凜冽的朔風(fēng)往返家中與醫(yī)院,走在因?yàn)橛有履甓b扮起來(lái)的街頭,覺(jué)得自己仿佛被罩在一個(gè)玻璃罩內(nèi),周遭的鼎沸人聲與車(chē)流都顯得那么沉悶,那么遙遠(yuǎn),像遠(yuǎn)遠(yuǎn)退去的潮水,在我與海洋之間空出貧瘠裸露的灘涂,晶瑩的浪花在遠(yuǎn)處跳蕩,而我獨(dú)自站在岸上,與世隔絕。我覺(jué)得自己變成人潮中唯一的灰色,與整座城市割裂開(kāi)來(lái),所有人的笑臉都令我厭惡,或者說(shuō)嫉妒。
此刻回想,那就是孤獨(dú),我在獨(dú)自承受生活中的變數(shù),哪怕知道與我擦肩的陌生人可能也同樣在經(jīng)歷痛苦不幸,但我的孤獨(dú)并不會(huì)因此得到絲毫緩解。說(shuō)實(shí)話,我并不懼怕獨(dú)處,我可以獨(dú)自去餐廳吃九宮格火鍋,獨(dú)自去異國(guó)他鄉(xiāng)旅行,獨(dú)自看電影,獨(dú)自思考,獨(dú)自散步,正因喜歡長(zhǎng)時(shí)間獨(dú)處,我才選擇了寫(xiě)作與翻譯作為終生職業(yè)。主動(dòng)尋求的獨(dú)處是迷人的,但被動(dòng)陷入的孤獨(dú)卻是致命的,所以我懼怕的是一種徹底失去某個(gè)人的可能。
杰弗里·艾倫說(shuō),外婆去世時(shí),母親失魂落魄,說(shuō)了一句,“現(xiàn)在我誰(shuí)也沒(méi)有了”。
他不明白,他認(rèn)為母親明明還有他,怎么能說(shuō)誰(shuí)都沒(méi)有了呢?
可是,當(dāng)他終于也經(jīng)歷了母親的離世后,轟然間就有了同樣的感覺(jué),“現(xiàn)在我誰(shuí)也沒(méi)有了”。
這是只有經(jīng)歷過(guò)或被虛晃過(guò)一槍的人,才能聽(tīng)懂的語(yǔ)言。
瑪雅·朗恩也同樣經(jīng)歷了失去母親這一痛苦。但不同于死別,她所經(jīng)歷的是母親罹患阿爾茨海默癥,母親一天天、循序漸進(jìn)地將她遺忘,同她進(jìn)行著緩慢但殘酷的告別。她下決心親自照顧母親,時(shí)刻陪伴左右,但逐漸力不從心,眼看自己的世界不斷縮小,自己的時(shí)間與家門(mén)外的時(shí)間出現(xiàn)了裂隙,外界一往無(wú)前,可她停滯不前,無(wú)法寫(xiě)出新的作品,無(wú)法申請(qǐng)教職,因此日漸孤立無(wú)援,對(duì)自己失望透頂。
作為旁觀者,我們當(dāng)然可以輕飄飄地說(shuō)一句,送去專(zhuān)業(yè)看護(hù)機(jī)構(gòu)就好,母親可以得到更專(zhuān)業(yè)的照護(hù),女兒也不會(huì)因此搭上自己的人生。沒(méi)錯(cuò),說(shuō)這話是出于關(guān)心,道理也是如此,但又恰是因?yàn)槿绱耍瘳斞胚@樣的女兒才會(huì)感到更加孤立無(wú)援吧?這就是我所說(shuō)的,陷入了“永遠(yuǎn)的異鄉(xiāng)人”的境地,只要落入這樣的境地,從此你只能講一門(mén)自己才能聽(tīng)懂的語(yǔ)言。
照顧失智老人的辛苦難以想象。好友曾時(shí)常提及她的母親,為了照顧失智的外婆,原本熱衷唱歌跳舞、社交生活極為豐富的母親徹底足不出戶(hù),成為二十四小時(shí)待命的全職女兒,并且要承受外婆認(rèn)不出自己并辱罵自己的痛苦。她非常心疼母親,但每次提及要不要換一種照顧的方式,母親都會(huì)發(fā)脾氣。我相信她母親的內(nèi)心一定被復(fù)雜的痛苦所占據(jù),體力上的辛苦,精神上的消耗,情感上的劇痛,在陪伴外婆最后七載的時(shí)間里,母親成為了那個(gè)無(wú)人能夠理解的“永遠(yuǎn)的異鄉(xiāng)人”。一切的關(guān)心對(duì)她而言都是不痛不癢的,是無(wú)效的。
還有的作者寫(xiě)到了離世的父親,夭折的孩子。最終你會(huì)發(fā)現(xiàn),最具殺傷力的孤獨(dú),竟然不是心靈上的孤獨(dú),而是肉體上的隔絕,是物理意義上的不可觸及與徹底失去。在那些看得見(jiàn)、摸得著、能夠感知的困境面前,我們還能斗膽一戰(zhàn),可生死卻完全超出了我們的維度。
可生死卻是我們唯一逃不開(kāi)的孤獨(dú),只要我們活著,就一定會(huì)面臨疾病和死亡,面臨他人或自己的離開(kāi),面臨人生的戛然而止,面臨人事物的遺憾收?qǐng)觥N覀兞?xí)慣在遭遇不幸時(shí)說(shuō)一句“時(shí)間能治愈一切”,但最不幸的就是,孤獨(dú)這件事,似乎只會(huì)隨著年歲的增長(zhǎng)而越來(lái)越濃墨重彩,越來(lái)越像一匹脫韁野馬。在很多描述永生的奇幻故事中,作者都將重音敲在永生之人的孤獨(dú)上,因?yàn)樗麄儗⒎捶磸?fù)復(fù)承受親友的老去與離開(kāi),使得明明常駐這世界的他們,成為了那個(gè)真正意義上的“異鄉(xiāng)人”。這些故事是用極端的情境告訴我們,我們終究得接受,哪怕全世界有幾十億人,哪怕我們從不缺愛(ài)與理解,可孤獨(dú)無(wú)比公平,哪怕你此刻還未感知到,將來(lái)也一定會(huì)與之狹路相逢。
但我想,這本名為“孤獨(dú)”的故事集,給了我們一種很好的示范,就算孤獨(dú)始終存在,不能被消除,并且可能隨著時(shí)間推移更加突顯,但這不代表我們不能做些什么,不代表我們做什么都是徒勞。
當(dāng)你感到孤單,與人隔閡,與世隔絕,不被理解,無(wú)人體諒,孤立無(wú)援,并因此悲傷、恐懼、憤怒、自憐、自艾,或許,你可以選擇像書(shū)里的作家們一樣,把你的孤獨(dú)寫(xiě)下來(lái),無(wú)論這種孤獨(dú)是慢性疾病,還是急癥發(fā)作,是痛徹肺腑,還是蜻蜓點(diǎn)水,你都可以把它寫(xiě)下來(lái)。畢竟無(wú)論你做或不做什么,這段孤獨(dú)的時(shí)光都得熬過(guò)去,那不如就把自己內(nèi)心的脆弱一筆一劃地寫(xiě)下來(lái)。
你可以對(duì)此追根溯源,向童年深處一路打撈,到任何人身上、任何經(jīng)歷之中去尋找原因。
你也可以只記錄當(dāng)下的感受,像拆開(kāi)被貓撓亂的毛線團(tuán)一樣,一根一根,一縷一縷,一尺一寸將內(nèi)心的煎熬與疑惑記錄在案,同時(shí)扮演傾訴者與傾聽(tīng)者,一人分飾兩角。
你也可以抱怨,可以咒罵,可以反思,也可以任憑意識(shí)流淌向任何地方,可以自責(zé),也可以責(zé)怪他人,但重要的是,要對(duì)自己坦誠(chéng),不要感到羞愧或?qū)擂巍?/p>
已經(jīng)有無(wú)數(shù)寫(xiě)作者證明,“寫(xiě)下來(lái)”這個(gè)舉動(dòng)就是這么神奇,在你寫(xiě)下來(lái)的時(shí)候,你將獲得前所未有的寬慰,并找到最強(qiáng)有力的陪伴——自己。
這個(gè)答案或許不能令你滿意,原來(lái)說(shuō)到底,我們還是只有自己。
但書(shū)里的二十一段人生故事,每一個(gè)都在講述他們?nèi)绾闻阒约憾冗^(guò)人生中最孤立無(wú)援的日子,從而獲得愛(ài)與理解的能力。在書(shū)中的《在地平線》一篇里,作者麥吉認(rèn)為,我們對(duì)自己負(fù)有最基本、與生俱來(lái)的責(zé)任,哪怕使盡渾身解數(shù),也不可能將其拋下,這份責(zé)任就是一種不可撼動(dòng)的孤獨(dú)。我們雖然可以用肉體與思想同他人建立聯(lián)系,感受親密,但這種親密是有限的。
那么怎樣的親密是無(wú)限的呢?麥吉結(jié)合自身經(jīng)歷與諸多素材資料,發(fā)現(xiàn)人處在生死攸關(guān)的情境或創(chuàng)傷中時(shí),大腦就會(huì)創(chuàng)造出一種幻象,塑造出一個(gè)“第三者”,為我們提供某種陪伴、引導(dǎo)與鼓勵(lì)。許多身陷險(xiǎn)境,瀕臨死亡的人,他們拼盡最后一絲氣力,幻化出的不是一頓飯,一張床,而是一個(gè)“同伴”,就像賣(mài)火柴的小女孩,在火光中看到的是家人。
生而為人,我們仿佛是地球上最貪婪的物種,但生死關(guān)頭,我們渴望的,只是不再孤單。
如果人人都在不同時(shí)刻,不同地方,感到孤獨(dú),或許那恰好說(shuō)明,解藥不在任何他者身上。把我們的孤獨(dú)盡數(shù)寫(xiě)下來(lái),這樣做,并不能讓我們不再孤單,但能讓我們劃亮火柴,映照出人生路上最忠實(shí)的伴侶——自己。看看我們能夠一起走到哪里,一起在這條孤獨(dú)的路上,創(chuàng)造出一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