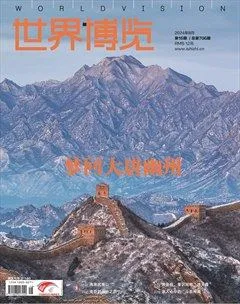再來(lái)武夷山

從武夷山市開(kāi)車到程墩村,差不多2小時(shí)左右。出了武夷山市,幾乎一路都是山路。盤山公路兩邊的紅土,喚起我30多年前的記憶。
如今的武夷山最大的變化就是,所到之處皆是茶園。茶葉,布滿了武夷山的每一寸土地。目所能及都是茶。睜眼是茶,閉眼是茶,勞動(dòng)是茶,聊天是茶,吃飯還是茶。茶,已經(jīng)完全滲透了每一個(gè)武夷山人的血脈。只要說(shuō)起武夷山的大紅袍、巖茶、肉桂……每一個(gè)武夷山人臉上,都是欣慰與滿足。

路,越走越險(xiǎn)。越往大山深處,我越是有點(diǎn)不敢相信,我當(dāng)初怎么會(huì)有這么大的膽量,一個(gè)人、一個(gè)麻袋,走那么久、那么遠(yuǎn)的征途。
馬路兩邊時(shí)而是云遮半腰的高聳山峰,時(shí)而是寬闊通透的山坳平地,但都無(wú)法掩飾它的美和它的媚。
遠(yuǎn)處翠綠疊嶂的山坳平原上,零零散散的幾戶人家,不規(guī)則地安插在茶園里,點(diǎn)綴了茶園,生動(dòng)了視野。可謂:小橋流水人家,擔(dān)柴炊煙茶花……
離表哥給的定位越近,我的心情越是波動(dòng)。不知道大舅、大妗子現(xiàn)在的身體怎么樣了。一別又是五年。盡管表哥每次通話都會(huì)說(shuō)他們身體很好,勿念,但畢竟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
我不知道大舅是否還記得我。表哥說(shuō),盡管大舅的身體還算健康,但記憶力越來(lái)越差,也經(jīng)常語(yǔ)無(wú)倫次,不知道他到底想說(shuō)什么。
我曾想過(guò),我為什么會(huì)對(duì)程墩這個(gè)小小的村落有這么深的感情,其實(shí)我在程墩修理“防火帶”前后也不過(guò)一個(gè)月的時(shí)間而已。也許不僅僅是因?yàn)檫@是我人生第一次出遠(yuǎn)門,更重要的是難以割舍大舅和大妗子對(duì)我的那份愛(ài)與關(guān)懷。
表哥和表姐很多年之前就在市里上班了。每次接大舅大妗子進(jìn)城居住,沒(méi)幾天老兩口就嚷嚷著要回程墩,覺(jué)得住在城里不習(xí)慣也不舒服。

清他。
他們還是懷念程墩的山山水水,更懷念那個(gè)已經(jīng)居住了幾十年的老宅子。即使現(xiàn)在,大舅也還是繼續(xù)著砍柴種菜、燒火做飯的日子。表哥表姐擰不過(guò)他們,也就由著他們?nèi)チ恕?/p>
表哥發(fā)了一個(gè)視頻和定位。視頻里,表哥身后那個(gè)不經(jīng)意的小臺(tái)階帶我走進(jìn)了記憶,居然還是三十多年前的樣子。我就是踩著那個(gè)臺(tái)階來(lái)到了大舅家。人生何處不是攀爬?是的,人生處處都是臺(tái)階,不管是上還是下。隨著命運(yùn)的波浪,起伏跌宕。
山路兩邊的山峰越來(lái)越緊密。下了一個(gè)山坡,拐進(jìn)了一個(gè)小山坳。程墩村,就在眼前。心情異常激動(dòng)。
是的,這就是那個(gè)闊別三十多年的地方,這里曾經(jīng)留下過(guò)我成長(zhǎng)的印記。在我的青春里,它的駐足,看似蜻蜓點(diǎn)水,卻烙下了濃重的一筆。
說(shuō)實(shí)話,程墩村變化不大,村頭那棵不知名的大樹(shù),居然還矗立在村頭,枝葉繁茂,在初夏的陽(yáng)光里愈發(fā)翠綠。不出工的時(shí)候,我經(jīng)常爬上它的樹(shù)梢,去暢想自己未來(lái)的人生之路。
再次踩在程墩的土地上,說(shuō)不出心里到底是什么樣的感覺(jué)。有些激動(dòng)、也有些酸楚,有些興奮、也有些恍惚。似乎是在尋找我青春踩踏過(guò)的夢(mèng)想的足跡。記憶中那個(gè)兩塊大石頭為標(biāo)志的公交車站已經(jīng)不見(jiàn)了。那排兩層伐木場(chǎng)的宿舍樓一如既往地立在馬路邊,還是當(dāng)年的模樣。臺(tái)階上斑駁的青苔,似乎在沉淀著這幾十年來(lái)的故事。
臺(tái)階分為三層,大舅家住在臺(tái)階的最上方。踏上臺(tái)階的一瞬間,一位干癟的老人,站在我的視線盡頭,是大舅。我?guī)缀跏桥苤忌吓_(tái)階。大舅知道我們要來(lái),早早就站在院子里張望。我跑到大舅身邊:大舅,我是上海。
鄉(xiāng)音,是副良藥,我不知道是我的鄉(xiāng)音,還是我的乳名,讓大舅的眼睛有了閃光的東西。他仔細(xì)地端詳著我,從頭看到腳。我分辨不清楚他的眼神里是什么,似乎有質(zhì)疑、有欣慰,但那股溫暖,是他眼神的全部底色。
85歲的大舅,身形消瘦,從他走路的節(jié)奏和體態(tài)來(lái)看,大舅的身體狀況還是非常不錯(cuò)的。那雙原本炯炯有神的眼睛,卻因?yàn)檐嚨湺兊糜猩駸o(wú)魂。但那股倔強(qiáng)剛強(qiáng)的勁,卻依然如同血脈牢牢地駐長(zhǎng)在大舅的身體里,從未消失過(guò)。
他額頭上方因?yàn)檐嚨溋粝铝撕脦讉€(gè)并排的疤痕,坑坑洼洼,尤為明顯。可想而知當(dāng)初車禍的慘烈,也能想象得出來(lái)大舅遭受的痛苦有多大。我指著大舅坑坑洼洼的額頭,心疼地用鄉(xiāng)音問(wèn)他:還疼嗎?大舅怔怔地看著我,我堅(jiān)信是我的鄉(xiāng)音喚起他的記憶:上海,我知道你是上海。大舅答非所問(wèn)。 我能清晰地感覺(jué)到,大舅的眼睛是看著我的,但他的思緒卻不知道去了何方。
大舅使勁地?fù)u搖頭,緊接著從口袋里掏出一個(gè)早已磨損的獎(jiǎng)狀:你看,這是我見(jiàn)義勇為,省里發(fā)給我的獎(jiǎng)狀……你這次過(guò)來(lái)是不是帶我回山東?回莒南?這瞬間,我好像看到大舅眼神里的堅(jiān)定又回來(lái)了。他使勁地盯著我。我的心一下子被什么堵住了。
我趕緊接過(guò)大舅手里那個(gè)獎(jiǎng)狀,我捧著證書(shū)看了一遍又一遍,仔細(xì)地咀嚼著每一個(gè)字,短短的幾行字,結(jié)結(jié)實(shí)實(shí)地夯實(shí)了大舅在我心中的英雄形象,一股驕傲的情緒溢滿心間。
的確,大舅是個(gè)大好人。大舅是有50年黨齡的優(yōu)秀共產(chǎn)黨員,福建省見(jiàn)義勇為三等功臣,同時(shí)也是福建省年齡最大的見(jiàn)義勇為模范。我有些激動(dòng),對(duì)著大舅豎起了大拇指:大舅,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個(gè)大英雄。“我知道你是上海……這次是不是來(lái)接我回老家?”大舅一如既往地在自己的世界里來(lái)回游蕩。
大舅說(shuō)話的口音和語(yǔ)調(diào)其實(shí)是有些變化的,畢竟離鄉(xiāng)已有六十多載。但味道,還是那口純正的山東沂蒙味,煎餅卷大蔥的味。
大妗子緩緩地從屋里走出來(lái),激動(dòng)地握住我的手,淚眼婆娑:你大舅聽(tīng)說(shuō)你要來(lái),昨晚一夜都沒(méi)睡,非要給你看他的獎(jiǎng)狀,昨晚睡覺(jué)前,就把獎(jiǎng)狀裝進(jìn)了口袋……說(shuō)實(shí)話,大妗子的身體狀況沒(méi)有大舅好,她因?yàn)檠鼈绸劦糜行﹨柡Α5谴箧∽拥哪樕苁羌t潤(rùn),我想也許跟這方天然氧吧的水土有關(guān)。
大妗子還說(shuō),大舅是撿了一條命,他做了一輩子好人,做了一輩子好事,老天爺不忍心收他。
如今,大妗子已慢慢習(xí)慣了大舅現(xiàn)在的樣子。盡管很多時(shí)候跟他對(duì)話像是對(duì)牛彈琴,又云里霧里的,但只要大舅的身體還算健康,大妗子已經(jīng)很知足,也很幸福。畢竟是死過(guò)一回的人了,大難后重生,更懂得彼此的珍貴。
大舅拽著我來(lái)到一個(gè)小房間,從口袋中掏出一把鑰匙,打開(kāi)了一個(gè)上鎖的陳舊櫥柜,從里面拿出兩個(gè)大麻袋,一股腦地全都倒在我的面前。里面是各種獎(jiǎng)狀、榮譽(yù)證書(shū)、工作筆記本……“這都是我的,上海你看看,這都是我的。你大舅還可以吧?”\u2028大舅的臉掛上了神采。 “他說(shuō)他一定要你看看,他在福建生活了一輩子,都在這里了。”大妗子在旁邊悻悻地說(shuō)。
我看著滿地的榮譽(yù),和大舅急切的眼神,起身到了窗口,不敢看,心里堵得難受,說(shuō)不出來(lái)到底是什么樣的心情……這一張張的榮譽(yù)背后,大舅要付出多少辛苦和努力?除了大舅本身的信仰和追求,這也承載著姥爺和姥娘對(duì)他的無(wú)限期待和囑托。
大舅1958年從山東老家到福建支援森林建設(shè),用盡自己的全部力氣,一定要做到最好、最優(yōu)秀,要用最好的自己向父母證明沒(méi)有給父母和家鄉(xiāng)丟臉。 對(duì)那個(gè)年代的窮苦孩子來(lái)講,一旦有了施展的機(jī)會(huì),就一定會(huì)竭盡全力,奮不顧身地扎進(jìn)去,去改變自己的命運(yùn)。大舅,就是這樣一個(gè)人。這中間的辛苦與不易,只有自己知道。
大舅之所以像個(gè)做件好事或者取得了一點(diǎn)成績(jī)之后,急切地想得到家長(zhǎng)認(rèn)可和肯定的孩子,堅(jiān)持讓我看他滿地的榮譽(yù),滿臉期待我的認(rèn)可,正是因?yàn)樵诖缶说臐撘庾R(shí)里,他知道我既是自己的家人,又是家鄉(xiāng)的來(lái)客,我可以把他的光輝成績(jī)帶回家鄉(xiāng),告訴家鄉(xiāng)的親朋好友。大舅的內(nèi)心是樸實(shí)地驕傲著的。我感動(dòng)這份樸實(shí),更接受他的驕傲。他的驕傲?xí)屓擞X(jué)得如此安心踏實(shí),如此寬慰,又是如此美好。
聽(tīng)母親說(shuō),大舅在老家的時(shí)候沒(méi)有上過(guò)一天學(xué)。但是大舅工作時(shí)便開(kāi)始自學(xué),上夜校。后來(lái)大舅讀書(shū)看報(bào),做工作筆記,每一樣幾乎都是他們那個(gè)群體里的一個(gè)榜樣。
大舅居住的房子也還是老樣子,幾十年來(lái)幾乎沒(méi)變過(guò)。但是大舅家院子里的那棵桂花樹(shù)已經(jīng)不見(jiàn)了,看著空蕩蕩的院子,我有些失落。表哥說(shuō),那棵桂花樹(shù)早就砍掉了。但第一次聞到的那股桂花香味,一直在我的記憶里飄蕩。它鋪滿了我整個(gè)關(guān)于武夷山程墩村的記憶。在那桂花香里,三十多年前的那個(gè)毛頭小伙子,跟大舅和大妗子坐在桂花樹(shù)下吃飯聊天的畫(huà)面一直都在。我所有關(guān)于程墩村的記憶都是有味道的,就是那股濃濃的桂花香味。
人到暮年,記憶里只有故鄉(xiāng)、親情和美好相守相伴,這是何等幸事。感恩歲月有情,天地有意。在大舅的垂暮之年,還是給了他一個(gè)健康的身體,同時(shí)幫他過(guò)濾了世間的糟粕,給了他一個(gè)精神的真空世界。讓他能在這么美麗的青山綠水間,心揣美好,頭枕故鄉(xiāng),安享晚年。如此說(shuō)來(lái),大舅,是幸福的。
當(dāng)我離開(kāi)大舅家,走下臺(tái)階,來(lái)到小馬路上,回頭時(shí),看到大舅站在臺(tái)階上,認(rèn)真地用他的“望遠(yuǎn)鏡”在目送我。
回來(lái)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大舅“望遠(yuǎn)鏡”里的我會(huì)是什么樣子?在他的“望遠(yuǎn)鏡”里,是不是也看到了我的母親?看到了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還有姥爺、 姥娘?或者是不是也看到了,在山東沂蒙山的那個(gè)“南唐樓子村”里,他們兄弟姐妹六個(gè),正在院子里玩“老鷹捉小雞”“過(guò)家家”的游戲?二哥揪了一下大妹妹的辮子,小妹妹抓掉了大哥的帽子,小弟跟二妹滿院子邊哭邊跑……姥爺滿頭大汗地在清理豬圈,裹著小腳的姥娘,頭上系著一個(gè)深藍(lán)色的頭巾,蹲在門樓子底下,看著六個(gè)孩子,邊烙煎餅邊嘟囔著:沒(méi)有一個(gè)省心的……
車,慢慢走遠(yuǎn)。大舅依舊站在墻角,舉著他的“望遠(yuǎn)鏡”久久沒(méi)有放下來(lái)。而我,已淚流滿面。
起風(fēng)了,有點(diǎn)飄起了小雨。村頭那棵不知名的大樹(shù),在微風(fēng)和細(xì)雨中,憨憨地靜觀著程墩村里每一個(gè)生命的過(guò)客。再見(jiàn),大舅,再見(jiàn),大妗子。愿你們永遠(yuǎn)幸福安康。
(責(zé)編:劉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