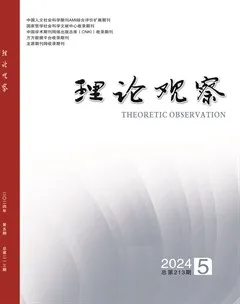納粹時期德國知識分子遷移與土耳其高等教育現代化研究
摘 要:在土耳其建國之初的現代化改革進程中出現了相當多的德國流亡學者身影,他們緣何來此,作用如何,值得探究。從土耳其立國之初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標與困境,土耳其如何與德國流亡學者接觸并引進,以及德國流亡學者在土耳其的具體工作與進展來分析其背后的歷史根源。經分析可知:以高等教育改革為代表的現代化改革是新興的土耳其共和國為擺脫落后,實現民族崛起的主動選擇。特別是德國流亡學者的到來解決了高等人才的缺乏問題,在土耳其政府大力支持下,這些德國流亡學者在土耳其有了用武之地,并助推土耳其快速建立高等學府,完成高等教育改革,加速其現代化改革的進程。
關鍵詞:凱末爾;大學教育;德國流亡學者;猶太人
中圖分類號:K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24)05 — 0120 — 09
一、緒論
1933年,根據3月23日《授權法》規定的立法權,希特勒以政治或種族為由,頒布《重設公職人員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 tentums),宣布解聘所有與納粹主義原則不相符的公職人員。因此,有相當一批具備創新力和活力的學者被迫流亡他國尋找新的工作崗位。然而多數“旁觀者(國家)”為避免麻煩,擱置這些學者的就職申請,使得許多學者在最初的時候要么被迫從事與其專長相去甚遠的工作,要么因種種原因只能在暫居地待業。而彼時,與眾多國家拒絕流亡學者不同,土耳其選擇接納與包容這些“知識性難民”,給予這些優秀學者平等待遇:提供適合的工作崗位,給予充分信任,讓他們教導土耳其的高等人才。這項政策從結果看影響巨大,對土耳其的國家建設發揮巨大作用。那么,為何當時的土耳其能夠實行這項如今看來頗為超前的人才引進政策呢、該政策究竟有何收益、人數眾多的流亡學者如何在近代化程度發展較低的環境中開展工作?這些學者離開后土耳其的高等教育發展又是怎樣呢?
筆者因著這一線索,將視線投向土耳其,探尋其以開放、合理的人才引進政策為指導,如何一步一步地剔除封建教育的影響,建立現代高等教育體系,進而推動國家的科學技術和文化思想走向新的高度。
二、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及其高等教育困境
對于土耳其國家歷史而言,20世紀初這一時段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方面,土耳其在西方列強與東歐各新興民族國家的共同撕咬下,成功地通過革命與戰爭擺脫了被瓜分的命運,建立起土耳其民族國家;另一方面,在總統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 1881~1938)領導下,土耳其開啟政治現代化改革,走上世俗化道路。然而土耳其共和國所繼承的是一個破敗的國家、一套瓦解的行政機構和一部過時的法律體系。所有這些都與凱末爾及其支持者想要建立世俗國家的信條完全不相容。凱末爾曾講道:“新的土耳其不能與伊斯蘭教法(Mecelle)①綁在一起,這不符合我們今天的需要。用100年前、500年前或1000年前頒布的法律來管理,是粗心,是無知。”②當時的土耳其是一個疲憊而貧窮的國家,凱末爾非常清楚,這個國家必須經歷一個快速的轉變。年輕的共和黨人充滿理想和熱情,實現其理想的動力幾乎是無限的,但實現這些理想的手段卻非常有限。社會希冀政府可以為其帶來改變,為孱弱的土耳其共和國注入新的活力和發展前景,擺脫曾經“西亞病夫”的蔑稱。
(一)土耳其的基礎教育改革
在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之前,宗教教育是奧斯曼帝國神權政治的支柱,其目的是將伊斯蘭教派的價值觀傳遞給更多的青年,以求實現對“蘇丹—哈里發”統治的認同。③而到1869年,土耳其政府才愿意承擔起基礎社會教育的責任,但是執行這項任務的責任仍然在宗教學校的控制之下,政府對土耳其青年一代的教育始終沒有脫離宗教神學的范圍。直到1913年,在青年土耳其黨人的影響下,土耳其政府頒布了《預備小學教育法案》(Provisory Primary Education Law),規定小學應教授以下內容:《古蘭經》(對穆斯林);其所屬宗教的知識(對非穆斯林);閱讀和寫作;奧斯曼語;地理,尤其是奧斯曼帝國的地理;算術和幾何;歷史,尤其是奧斯曼帝國的歷史;公民學、科學和衛生;美術、工藝和繪畫;宗教和愛國詩歌;體育及在校運動;為男生提供軍事訓練;為女孩提高家務和縫紉學習。④然而因為一戰的爆發和國民經濟的長期凋敝,這項政策的推行始終達不到預期效果,土耳其國民長期處于神學的愚昧思想之下,基礎文化素質極低,無法為國家的現代化發展貢獻具備良好文化素質的工人群體。
集中力量應對經濟問題,實現共和國的工業化經濟固然重要,但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持續性發展應該始于良好的現代化教育體系,故此,隨著土耳其“國家資本主義”計劃的推進,作為社會變革核心的教育改革迅速展開。首先,政府重新統一教育,在1924年3月3日,教育部將教育權收歸國有,并規定婦女和農村人民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其次,土耳其對國內的教育機構進行重組:一方面,在1924年3月13日,政府下令廢黜包括伊斯蘭學校(當時奧斯曼帝國高等教育的唯一公共形式)在內的所有宗教學校;另一方面,1926年3月2日立法重組包括小學、中學和高中在內的基礎教育體系。再次,為了有效推動教育的普及,土耳其還于1928年11月1日正式啟用拉丁字母,放棄阿拉伯字母,在全國進行掃盲運動,讓大部分人接受這種新字母教育。最后,政府還支持人文學科的研究協會建立,以助力教育改革的推進:1931年4月12日土耳其歷史協會成立;1932年7月12日土耳其語言協會成立,1932年7月12日進行全面語言改革。
(二)高等教育困境
凱末爾政府的教育改革是全面立體的,其眾多精準到位的改革措施也頗為有效,然而這些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基礎教育領域,體現一個國家科技文化水平的高等教育改革卻遲遲未能推行。在當時倘若一個國家想要快速追趕西方強國,不僅需要建立適合自己的政治體制為發展提供保障,更需要在根本上提高這個國家全體公民的思想文化素質,建立一整套現代化的高等教育體系,進而產生影響整個國家的教育理念、民族精神和科學技術,唯此通過穩定的制度和高素質的公民以及大量科學技術人員,弱國才能在政治、文化、經濟上保證獨立發展且繁榮。
顯然,當時的土耳其并不具備這樣的高等教育體系,繼承于奧斯曼帝國的學校沉浸于宗教理論的研究和過時軍事器械及戰術的培養,完全沒有任何可以稱得上“現代化”的大學。在19世紀早期之前,奧斯曼帝國從來沒有計劃過培養任何近代化的學術或研究人才,國家只愿意培養適合其發展的軍事和官僚官員,因此在1933年之前,這個國家真正意義上建有的官方學校屈指可數:1735年在法國人亞歷山大·博內瓦爾幫助下建有一所炮兵學院;1773年建立皇家海軍工程學院(Muhendishane-i Bahr-i Humayun)以培訓海圖師和造船師;1795年成立了皇家軍事工程學院(Muhendishane-i Berr-i Humayun)以培養技術人才;1827年建立帝國醫學院;1834年建立帝國軍事學院;①1854年建立名義上第一所大學“科學院(Darülfünun)”。②
土耳其鮮有適合現代化大學的教育人才,以往的學校里盡是宗教先知、神學講師和封建式軍官,哪怕少數幾個具備科學素養的外國講師,也因動蕩的土耳其國情早已逃離。“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帝國傾向于從那些外聘官員、專家和科學家中獲益”,③并不在意培養本土教育人才。沒有教室,可以新建更宏大的講堂;沒有學生,可以號召有識青年積極參與;沒有科學器械,可以花大價錢突破封鎖從西方購買;然而沒有教師,這一切都是徒勞。
當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誕生時,繼承于羸弱的奧斯曼帝國的教育體系大約有400多所伊斯蘭宗教學校,并且殘存兩所軍官院校、一所土木工程學校和四所中等專門學校,④以及一所“準”大學,即科學院,后者設計建立的初衷是嚴格培訓公務員。然而科學院幾乎是一個中世紀的機構,在那里,業余教師年復一年地從他們破舊的筆記本上重復著同樣的講座,他們很少進行研究,也很少出版科學書籍。⑤這些便是共和國初期教育體制中的基本情況,絕大多數學校不僅無助于這個國家社會的現代化,甚至還可能成為這場現代化的阻力,因此它們很快被盡數關閉。如此僵化的舊體系明顯不具備支持雄心勃勃的共和國締造者實現高等教育理想的條件,“大學現代化”顯然是必要的,而第一步就需要招聘教育人才。
(三)高等教育人才引進計劃
為實現建立現代高等教育體系的計劃,土耳其教育部長雷西特·加利普(Resit Galip, 1893~1934)于1932年邀請瑞士教育學教授阿爾伯特·馬爾奇(Albert Malche, 1876~1956)前往土耳其考察,并要求馬爾奇考察后提交一份關于土耳其教育改革的報告。馬爾奇于1932年1月18日抵達土耳其后立即展開工作,于5月29日撰寫了名為《伊斯坦布爾大學報告》(Rapport sur l’universite′d’Istanbul)的文件。⑥
正是以這份文件為基礎,土耳其政府形成了以西歐大學為模式建立完全現代化高等教育體系的理念。該報告總結土耳其高等教育的問題在于:1.科學院教育質量較低,只對學生進行百科全書式的教學,且實驗性實踐不足;2.科學生產力和獨創性水平很低,任職教師幾乎沒有進行任何科學研究,且出版物極少,質量水平差;3.教員的語言能力很差(多數不會使用西歐語言),不足以跟上現代的進步;4.各部門之間不存在良好的協調性,工作效率低下。⑦馬爾奇還表示,計劃建立的新大學體系尚不能聘請到足夠數量的本國學者來支持正常教學運轉,建議派遣新一代學生出國培訓并聘請外國學者來暫時彌補教職的空缺。為此馬爾奇繼續提議,為適應土耳其高等教育發展,建議土耳其政府邀請在德國因《重設公職人員法》而失業的學者到土耳其任職,以滿足對教學人才的需要。
三、德國學者的流亡與土耳其的聘任
(一)德國的“文化流亡”
此時的德國正在解雇許多大學教授、醫生和其他專業技術和管理人員,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或有猶太血統的社會黨和共產黨人,或者只是在名義上不能也不會接受納粹主義的普通人。德國在1933~1945年頒布的多項政府法案禁止了近1200名科學工作者進入其教育及科研機構,至戰后其中約650人成功移民。⑧
由于《重設公職人員法》的規定,⑨所有德國大學、研究所以及醫學院中有猶太血統、有民主進步思想的科學家,其地位都受到質疑,因而很快導致了上千人的解聘。?輥?輮?訛瘋狂的“解聘風波”不僅沖擊了德國,而且伴隨著納粹戰前擴張政策的成功,在1938年繼而沖擊到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學術界。因此,在納粹德國統治的整個中歐,“以無與倫比的、無法抹殺的,偉大而非同凡響的文化成就為標志的德意志——猶太共生現象走到了終點。”①
這些德國學術人才被驅離后,引發一場世界性的學術人才大交換。當1933年3月,納粹德國政府還在醞釀《重設公職人員法》時,許多對政治較為敏感的學者就已經預感即將到來的可怕事情,因而能夠較早地離開德國。其中就有匈牙利裔猶太學者、法蘭克福大學著名病理學教授菲利普·施瓦茨(Philipp Schwartz,1894~1977),他帶著家人一起逃到瑞士。由于在瑞士沒有找到工作,施瓦茨便與流亡到此的其他科學家們一起,于1933年3月在蘇黎世成立了“在外國的德國科學家緊急共同體”(Norgemeinschaf Deutscher Wissenschafiler im Ausland)。該組織的宗旨是“幫助遭受納粹迫害的猶太及非猶太學者在接收德國流亡學者的國家中找到工作。”② 當瑞士的馬爾奇應邀對土耳其教育體系進行考察并給予聘請外國學者的建議后,作為施瓦茨的岳父西奈·舒洛克(Sinai Tschulok, 1875~1945)教授的密友,馬爾奇意識到這是拯救生命與幫助土耳其的雙重機會,于是聯系了施瓦茨。③土耳其政府聽取馬爾奇的建議,向施瓦茨伸出橄欖枝。
(二)土耳其的聘任
雖然納粹的行為對德國來說是恥辱,但對土耳其來說卻是重要機會。正如前文所提,土耳其在推進教育改革過程中面臨的關鍵問題就是高級人才教育的嚴重匱乏。于是,在了解馬爾奇教授的報告后,土耳其教育部長加利普返回安卡拉,正式向凱末爾提出建議:伊斯坦布爾大學師資嚴重短缺,而大量失業的德國教授是流離失所者,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前途堪危;土耳其能否找到一種機制,邀請其中一些人到伊斯坦布爾大學任教或者擔任各部委的顧問?④凱末爾的反響非常積極;在經過快速需求評估后,土耳其政府開始正式與那些愿意來土耳其的德國教授和司法學者進行溝通。
在馬爾奇教授建議下,秉持對德國科學和文化的好感,并認識到機遇的出現,土耳其于1933年7月5日邀請施瓦茨前往安卡拉商議招聘流亡學者的事宜。7月6日商談會議開始,與會雙方的任務是選出某一學科的最高學歷者和對應目前土耳其最需要的專業的學者。經過9個小時的談判,雙方在聘用移民教授的名單上達成了一致,共35名教授得到聘請。施瓦茨代表德國海外科學家協會,與土耳其政府擬定了一份為期五年的就職合同。合同要求來土耳其任職的教授需要使用土耳其語授課,并翻譯或出版相應的土耳其語教科書,且在工作的五年間擔任各學科的主任直到培養出優秀的接班人后再進行修改。
教育部長加利普在協商會議中表示:“500年前,當我們來到伊斯坦布爾時,拜占庭的科學家和藝術家離開了這個國家。他們中的許多人去了意大利,在那里他們開始了文藝復興。現在是歐洲把我們失去的東西還給我們的時候了。我們希望您能將創新帶入我們的祖國,以便我們能夠跟上現代秩序,并向新一代展示現代科學發展的道路,我們作為一個國家表示我們的感謝和敬意。”⑤會后,土耳其公共教育部宣布:“作為國家請來的客人,前往土耳其的德國科學家不與大學簽約,而與土耳其公共教育部簽約。在與德國教授訂立的國家合同中已經寫明,這些流亡學者的薪金將遠遠超過土耳其本土教授的薪金”。⑥后來,當伊斯坦布爾大學的外國講師之一格哈德·凱斯勒(Gerhard Kessler, 1883~1963)在回憶錄中稱贊他獲準進入土耳其時,他說,“我將感謝永遠感謝這個具備高尚而紳士精神的土耳其給我這個機會”。⑦對于聘請人和被聘請人來說,有如此感慨足以證明這個“應聘”過程是愉快且滿意的。土耳其得到了夢寐以求的高等教育教授,而眾多流亡學者不再受流離失所的煎熬,仍可保持熱情繼續他們傾覆一生的學術研究。
聘請名單的確定使得土耳其可以相當充分地準備高等教育改革:“土耳其政府與一些教授簽訂合同,并同意支付給他們遠超土耳其籍教授的工資。土耳其政府的目的是將伊斯坦布爾大學的學術水平提高到西歐大學的水平。”⑧在1933~1945年間,總計有190多名來自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科學家和藝術家被土耳其所接納,這也使它成為接受流亡科學家第三多的國家,僅僅排在美國、英國之后。①如此之多的德語流亡學者的到來,對教育體系產生很大影響。他們不僅帶來高水平的科學知識,也帶來自洪堡時代以來德國大學的先進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直接促成土耳其舊有高校體制的改革和重組,從而使這個國家的大學教育現代化向前邁出決定性的一步。
四、德國流亡學者對土耳其高等教育改革的影響
土耳其政府對高等教育體系進行徹底改革的政策是必然要實現的,而這些偶然來到土耳其的德國學者使得這項政策可以快速地推進。在短短15年間,土耳其初步建立起較為完善的高等教育體系,來自各個領域的流亡學者在不同學院、不同機構中任職,他們在落后的教室里傳授給這個新的國家各種先進的知識、技能和思想。待這些學者離去dA1tpweDFxIpE+6m/uXYFOp6FpYJmuT7XK383nznXtg=后,土耳其將繼承自那些優秀學者的知識發揚光大,也將獨立發展新的技術和知識。
(一)高等教育體系改革
根據馬爾奇教授的建議,土耳其政府于1933年7月31日正式取締舊有科學院,同時取消所有現任教師的合同;8月1日正式成立新“大學”(即伊斯坦布爾大學),并于1933年11月向學生開放授課。從這天起,土耳其擁有了符合現代化標準的高等教育體系。而這所以德國大學模式而建立的新大學,被所有現有的媒體通報,不僅在大城市,即使是在一個位于安納托利亞中心的小鎮約茲加特,其周報進行頭版標題都是“科學院成為歷史,新大學已建立!”②
新的伊斯坦布爾大學由醫學、法律、科學和人文學院組成,另外還有8個研究所:伊斯蘭研究所、土耳其革命研究所、國民經濟研究所和社會學研究所、土耳其地理研究所、形態學研究所、化學研究所和機電研究所。土耳其的知名學者被選任為校長以及各學院院長,如校長內塞特·奧馬爾,醫學院長為陶菲特·薩利姆帕夏,人文學院院長克普里扎德·福阿德等。③
在前期的籌備過程中,土耳其教育部也已經與一些德國流亡學者簽訂合約,在1933年11月10日之前,這所大學已聘用35位德國學者。在美國駐伊斯坦布爾大使的信中,對這35人有進一步描述:“據我所知,伊斯坦布爾大學有35名新聘用的外國教授,其中30人已經抵達,除一名奧地利人和一名瑞士人外,其余都是德國猶太人,他們要么被驅逐,要么因為最近的政治動亂而離開德國。”④而在此后數年間,數百名德國流亡學者紛紛來到土耳其,他們隸屬不同學科,滿足了土耳其政府“要使伊斯坦布爾大學的學術水平提升至西歐大學的水平”的要求,以至伊斯坦布爾大學被當時的人們普遍視為“世界上最好的德國大學”。⑤
這些學者的專業范圍極其廣泛,科學、理學、文學、商學皆有涉及,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伊斯坦布爾大學和安卡拉大學這兩所大學中工作,其余的少部分學者分散在各研究所甚至政府部門中。無論身處何處,從事何種工作,他們都以其專業技能為土耳其教育現代化貢獻自身力量,有些學者因突出的專業能力被另聘為政府官員,直接負責土耳其的某些現代化建設任務,而這些學者也因這種信任和重視更加愿意在土耳其生活、工作,他們中的部分人雖然在1938年后因政治變革而選擇離開,但是大部分學者依然在土耳其生活了10年之久,甚至有幾位學者選擇加入土耳其國籍并終老于此。對土耳其來說,得到數量眾多的優秀教育人才,不光為其高等教育建設提供了最基礎的保障,而且還加速了土耳其近百年的現代化發展繁榮道路。
(二)德國學者的工作
來到土耳其的流亡學者以其專業的不同被分配到各類崗位中,其中大部分人任職于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還有少部分任職或兼職政府顧問和工作人員。他們與土耳其人共同努力,快速建立起高等教育體系,推行新的教育,培養了許多學術和研究人才。在土耳其,德國的流亡教授擔任12個基礎科學研究所中的8個主任,以及伊斯坦布爾醫學院17個科室的6個主任,其教學方法,教育理念無不仿照當時代表世界一流學術水平的德國大學模式,一時間伊斯坦布爾大學被評為“世界上最好的德國大學”。①
出于工作的需要,德國學者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語言障礙。在課堂中,學生和教授都必須不斷地學習新的語言,并在不同語言之間進行轉換:從舊的土耳其語到新的土耳其語,從一種歐洲語言到土耳其語。②這些來自異鄉的學者幾乎都承擔起了翻譯家的工作,他們將不屬于這個國家的語言更貼切地翻譯成土耳其語,以便這些學生更有效地學習。德國學者對土耳其的教育貢獻首先體現在這一點上,他們為土耳其建立了符合時代的科學語言,使得來自世界各地的所有知識得以順利地在土耳其傳播。德國學者對土耳其的教育貢獻首先體現在這一點上,他們為土耳其建立了符合時代的科學語言,使得來自世界各地的所有知識得以順利地在土耳其傳播。
在教學過程中,雖然合同上沒有規定,而且德國教授也不愿自己準備教材,但為了更好地開展教學,在伊斯坦布爾大學工作的教授中大約有80%都至少出版了一本書,60%則出版兩本或更多。醫學系教授出版圖書的數量最多,人均出版三本或四本。③除此之外,同樣出于教學需要,一些德國學者還翻譯了許多專業書籍,例如為土耳其化學學科奠定基礎的阿恩特教授,70多年后,他的一位學生、伊斯坦布爾大學化學工程系退休教授伊斯邁特·古爾吉(?smet Gürgey, 1923~2009)指出在為土耳其科學教育做出重要貢獻的移民學者中,應該包括“奧德教授、弗里茨·阿恩特博士,也許被認為是最重要的……他為土耳其帶來了當代化學的基礎和原理。”④因為在每本書的結尾,阿恩特都以現代土耳其語、奧斯曼土耳其語、德語和英語列出所有化學術語和概念。“閱讀這些小詞典,尤其是在將奧斯曼帝國的術語和概念與土耳其語同義詞進行對比之處,就有可能看到化學語言的提純程度,這些術語和概念沿其簡化之路一直延續到今天。但是,這絕不會削弱他所取得的成就。在他的書中,沒有一種渴望使用德語、英語或奧斯曼語的術語的感覺。除了阿恩特教授在化學領域對土耳其語言精煉以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數學、人文學科、藝術和專業也有這類語言改革的代表。”⑤
同樣是出于教學和工作的需要,土耳其的圖書館和學術雜志也快速發展起來。出于科研的需求,德國教授們列出他們需要的書籍和期刊,并經常為這些來自歐洲的出版物撰寫報告和文章。而土耳其政府和大學行政管理人員也不遺余力地滿足他們的要求。短時間內,圖書館內匯集了大量德語、英語和法語書籍,恩斯特·赫希(Ernst Hirsch)教授帶著助手擔任圖書管理員,對書籍進行登記、整理。
學術研究的目的是為回饋社會,學術研究的進步也離不開同行的交流與評議,因此每年夏季會在不同地方召開開放式的“大學會議”和“大學批判”研討會。一批學術雜志,如《法學雜志》和《科學學院學報》(1935)、《羅馬學雜志》(1937)、《醫學學院學報》(1938)、《經濟學院學報》(1939)、《心理學和教育學雜志》(1940),也紛紛創刊。⑥
二戰結束后,這些流亡的德國學者除個別留在土耳其外,大多選擇離開,一些人去了美國、巴勒斯坦或回到他們的故鄉。⑦ 留下來的學者依然對土耳其的科學教育與研究做出杰出貢獻,如阿爾弗雷德·埃里克·弗蘭克教授和科特·科斯威格教授,為感謝他們的付出,在他們在離世后,土耳其為其舉行了國葬。⑧ 而德國流亡學者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在土耳其這10多年的教學經歷也留下了突出的成果,即: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時,高等教育領域有221名講師和2462名學生。15年后,這些數字增長到855名講師(增長287%)和10213名學生(增長314%);1933年共有3437名學生被伊斯坦布爾大學錄取,其中884人被醫學院錄取;1933年至1946年間,共授予博士學位41個。①
德國學者離開后,他們培養出的土耳其學生成為后來土耳其社會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的主力。例如學習經濟的雷菲·蘇克魯·蘇維拉(Refii ?ükrü Suvla, 1908~1962)曾多次為央行和其他國有銀行提供建議;穆利斯·埃特(Muhlis Ete, 1903~1975)成為商務部長;奧斯曼·奧基爾(Osman Okyar, 1917~至今)在中東理工大學任教,后來成為埃爾祖魯姆大學校長等等。這些學生至今仍在土耳其高等教育領域和政府中為土耳其的現代化踵事增華。
德國學者留下的遺產不僅僅表現為他們直接培養的人才,還表現為他們幫助建立和完善的高等教育體系繼續為土耳其培養人才。而伊斯坦布爾大學作為土耳其政府著力建設的高等院校,也是聘用德國流亡學者最多的大學;在此后十幾年間,它在土耳其科學領域的影響性首屈一指,同時也領導著土耳其啟蒙運動和現代化運動。安卡拉大學于1946年正式合并多個學院而成,其中就包括1935年的歷史和地理學院和1943年的理學院,二戰期間有許多德國流亡學者在這里工作。伊斯坦布爾科技大學前身是1773年成立的公共工程學院,1924年改名為伊斯坦布爾科技大學,以工科為重,許多工科領域的德國專家曾在這里工作,使其在相關學科有了巨大進步,并為土耳其培養出大量建筑、工業領域的人才。②
德國學者的到來直接幫助土耳其各大學建立了一整套現代化的大學學科,眾多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的學者為土耳其帶來了如經濟學、化學、生物學、天文學、物理學、圖書館學等科學,③這些科學此前從未在土耳其的土地上出現過,但在德國學者的支持下,他們扎根在土耳其的高等教育體系中,為土耳其國家現代化發展不斷培養各學科人才。而土耳其高等教育的發展在德國學者離開后也十分突出。一方面,大學的學科體系不斷完善,如伊斯坦布爾大學設立之初有4個學院8個研究所,現在擴展到17個學院、5個系、12所高等教育培訓學院及數十個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安卡拉大學根據社會需求不斷設立新學科:政治學院(1950)、藥學院(1960)、牙科學院(1963)、教育學學院(1965)、傳播學院(1965)等,截至2015年9月,土耳其共有193所大學(不包括軍事類院校),其中公立大學109所,私立大學76所,高等職業院校8所。④ 這些數量龐大、學科健全的高等院校機構不斷為土耳其共和國輸送人才,為土耳其共和國的發展添磚加瓦。
五、德國學者在土耳其的生活和離開
在那個時代,這些流亡的德國學者的經歷是坎坷的,他們被從故鄉驅逐,流離失所,多數人在找到容身之所前窮困潦倒,他們的命運與那個動蕩的時代一樣波瀾起伏,但他們的形象卻又如星辰一般閃耀于人類文化的最高殿堂。
(一)德國學者在土耳其
學者們被從德意志驅逐,卻因為當時盛行保守主義的世界而無處可去,但又因人性的高尚而絕處逢生。在1933年,當土耳其決定聘任35位德國學者時,希特勒命令時任德國大使弗朗茨·馮·巴本(Franz von Papen)干預這些流亡學者入境土耳其,巴本在回憶錄中寫道:“希特勒命令我收回所有在土耳其的德國流亡者的護照,并剝奪他們的德國國籍。我拒絕了這個命令,并告訴里賓特洛甫(Ribbentrop),大多數移民已經得到了政府的許可離開了德國,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在土耳其的大學任職……我無法執行他的指示。”⑤由此這些顛沛流離的德國學者得以順利到達土耳其繼續從事他們為之自豪的工作。
而這些來到土耳其的德國學者在新生活的伊始并非如想象般順利,異國他鄉的生活所帶來的陌生感和文化隔閡在一開始就困擾著學者們的心情。弗里茨·諾伊馬爾克(Fritz Neumark)在其回憶錄中提到:“我們想念那里的風景,尤其是‘我們的’語言。很難說哪一個對我來說更糟糕,可能是語言。卡爾·扎克梅爾(Carl Zuckmayer)在《格林兄弟》(The Brothers Grimm 1948)一文中提到了‘語言思鄉’,并準確地指出,對于一個流亡在外的作家來說,這是‘最痛苦的思鄉形式’——而我們幾乎都是作家。”⑥對納米技術突破有重大貢獻的馮·希佩爾(Von Hippel)教授曾記載道:“我們這些新來的人,骨子里帶著因流放而產生的失落感,當發現自己被一種陌生文化中的陰謀所包圍時,任何成功或不幸都會影響到我們所有人。”①德國流亡學者懷揣著此類心理困境而在土耳其展開工作,但重回故土的希望卻因戰爭的到來而一點點破碎。
可是他們面臨的窘境并不只有這些不斷的思鄉情,在生活中他們必須面對來自被他們占據工作崗位而失業的土耳其各行業從事者的仇視。在土耳其本土教授的眼中,本該屬于他們的待遇良好的工作崗位和高工資被分配給了外國人,而他們的工資卻比德國學者少了許多,這種不公是不可接受的;同時,醫學教授在整個土耳其醫學界的支持下表達對德國學者的厭惡,而原因是德國學者提供的醫療服務遠好于本土醫生,這使得原有的土耳其醫生診所的生意大大減少。②為此洛克菲勒基金會評價道:“土耳其人有一種強烈的反德情緒。”③然而在學術圈內及大學體系下的敵對態度并不能代表整個土耳其社會的想法。我們可以很高興地看到整個國家從上到下都對這些流亡學者秉持著良好的歡迎姿態,他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著——流亡學者是這個國家“尊貴的”客人。
時任德國報紙駐伊斯坦布爾代表維克多·穆勒(Victor Maurer)在其向德國的報告中表示:“應邀到該大學任教的許多德國教授(其中有猶太人)受到土耳其輿論的友好歡迎,從而促進了德國文化的宣傳。”同時期的土耳其報紙頭版上都在詳細報道德國流亡教授的信息,無不表示了對這些學者的歡迎。而在政府建設工作中,安卡拉當局試圖為德國教授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讓他們繼續工作。同時他們在實驗室和醫院的設備上花費了大量的資金,人們可以看到土耳其醫院的設備與世界上任何一家醫院不相上下;在安卡拉的高層人士中存在著對這些教授的大力擁護者和保護者,對他們提出的任何投訴都被國會充耳不聞。④這些支持和尊敬不僅體現在政府的工作上,更表現在國家慶祝活動中對流亡學者地位的肯定。1933年,土耳其舉辦共和國成立10周年的慶典活動,當時到達土耳其的許多德國學者都受到邀請出席這一重大的慶祝活動。恩斯特·赫希教授在其回憶錄中寫道:“一位德國教授,在他的祖國德國作為猶太人而受到鄙視,因為他的‘劣等’種族(身份)而被辭去了職位……但在‘遙遠的土耳其’卻被認為是該國前千名之一的精英!”⑤這種極高的尊重感動著流亡的學者,讓他們在異國他鄉的土地找回了在祖國失去的尊嚴,而我們在那個時代的土耳其見到的是對知識的尊重和對國家富強的期待。
(二)德國學者的離開
很可惜的是大部分德國流亡學者并沒有在土耳其生活和工作太長的時間,他們在土耳其的歷史煙塵中逐漸消去,轉而回到人類歷史的宏偉舞臺中繼續表演。這也正是在土耳其的流亡學者比流亡美國或其他各地的學者知名度更低的原因。
大部分流亡學者在兩個時間段——1938和1948年——集中離開了土耳其,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選擇去往美國尋求更好的生活條件或去往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重建家園,少部分人選擇回到德國。
而1938年是個特殊的年份,在這一年第一批來到土耳其工作的學者的五年工作合同已經到期,而他們要面對的,是因凱末爾去世而帶來的土耳其民族主義抬頭而產生的敵視態度。除此之外,在這一時期土耳其的經濟發展狀況逐漸惡化,而政府并沒有實行補償性工資調整并缺乏相應的養老金計劃,使得學者們在1938年簽約時獲得的工資因通貨膨脹而不再有吸引力。⑥種種因素疊加起來使得許多學者決定在這一年離開土耳其去往他國尋求出路。
到1948年,世界各地都在進行復興建設。這一時期離開的學者多為續簽了兩次合同但要面臨第三次續簽的學者,戰爭的結束為這些學者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土耳其的挽留并不能改變這些客人的決定,只能按照合同與他們解約。雖然他們離開了生活了十五年的土耳其,卻留下了一個建設完好的高等教育體系。而對土耳其來說,這些尊貴客人的離開并不會阻礙這個國家的持續發展,土耳其從此將創新發展道路,延續由流亡學者帶來的知識,創造更符合時代的高等教育體系。
六、結語
“歷史中充滿了意外事件,有些是災難性的,有些則是幸運的。有時一個國家的不幸卻能夠成為另外一個國家的幸運,這種情況就發生在土耳其的大學改革時代。”①當納粹德國因為極端民族主義傾向大規模清洗那些優秀的學者時,未曾預料到那些被歧視排擠的人會成為另一個落后國家日后發展的重要保障。當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為前途擔憂四顧無望時,怎么也不會想到命運會將大量的優秀學者送來這個羸弱的國家,幫助其建設夢寐以求的高等教育體系,而這個體系是一個國家在現代競爭中的基石。
建國之初的土耳其共和國面對落后封建教育的困境,開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取締一系列奧斯曼帝國時期的學校,在現有基礎上建立起一個較為優秀的基礎教育體系,保證了世俗化的穩步推進。而為了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的思想文化教育水平,建設獨立自主的科技體系和文化體系,土耳其的締造者及時利用了德國民族主義激化后的反猶反社會主義浪潮,引進大批優秀學者充實其高等教育體系,在短時期內興建眾多模仿德國教育的高等院校,并培養了眾多優秀的高等教育人才。
當1933年10月25日以施瓦茨為首的35位德國流亡學者到達伊斯坦布爾時,這個國家的現代化列車終于添加了一罐優質的燃料,正式駛向新的時代。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共約190位學者在教學、圖書、翻譯、科研等領域幫助土耳其快速建立起一個比肩西歐的大學體系,這些學者在戰后多數離開了暫居的土耳其,但是其付出卻永遠被記載于土耳其的百年史冊里。
土耳其的大學改革運動是其發展道路上必然的選擇,新生的國家想要實現現代化和繁榮必然要經歷學習、仿造到研制、創新的過程,這個過程或許漫長,但卻是至關重要的一步,唯此才為國家的前途夯實基礎,構建框架。德國流亡學者的到來卻是偶然的,沒有他們的貢獻土耳其現代化的進程可能要推后更久的時間,流亡學者就像是為這輛即將飛馳的汽車進行改良修理的機械師,為土耳其的現代化過程更換了性能更佳的發動機,加速了其發展。
〔責任編輯:包 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