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與“二師兄”相伴相生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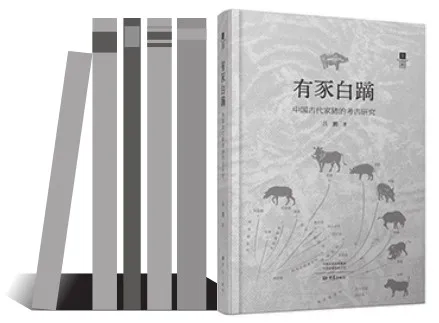
有豕方有家。這可以由漢字“家”的構成一目了然。中國古代先民在殷商時期所創制的甲骨文中,將“家”字分成兩個部分,上面是“宀”字頭,代表房屋,即居住之所,下面是“豕”字,即“豬”。從“家”字的構成可以看出至少在漢文字發明之前,“豬”已作為被馴化的動物,與人類同居一室,并成為人類家居生活的重要“伙伴”,乃至重要一員,是構成“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之一。
即以我個人而言,對豬抱有特殊的情感。在20世紀80年代的豫西南山村,糧食作物因“包產到戶”可以自給,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但生活用度中需要花錢的地方仍然顯得捉襟見肘。好在二姨家贈送母豬秧子一頭,幾個月后開始抱窩下仔,且每窩大都在10只左右,以每只小仔10元計算,付后可得百元,且母豬秧特別“甜歡”人,以兩年三窩的頻率連續生產多年,極大地改善了我們家庭的經濟狀況,兄妹三人的學費及家里的日常開支基本得以滿足。
或許是這種情感使然,當得知呂鵬所著《有豕白蹢:中國古代家豬的考古研究》(大象出版社2024年1月版)面世以后,在第一時間即得以拜讀。
壹
該書作者呂鵬博士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實驗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長期從事考古遺址出土動物遺存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攻讀碩士學位期間,呂鵬的研究方向即“鎖定”動物考古方向,碩士論文為《試論中國家養黃牛的起源》,后在考古所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廣西邕江流域貝丘遺址動物群研究》在我國著名動物考古學家袁靖教授指導下完成,于2012年獲得由教育部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頒發的“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
該博士論文以廣西邕江流域的“貝丘遺址”為范疇。“貝丘遺址”,是一個考古學專有名詞,貝丘是古代人類居住遺址的一種,大都屬于新石器時代或稍晚之青銅時代,其特征是此種遺址包含有古代人類吃剩食物拋棄的動物貝殼,一般位于盛產貝殼類動物的河流、湖泊、海洋附近。由于貝殼質地堅硬、富含鈣質,可以長期存留,考古工作者可以依據貝丘遺存,了解水位線、海洋地質變化、古生物乃至氣候以及人類生活的形態等等。
在博士論文中,呂鵬通過對邕江流域貝丘遺址群中動物種屬構成、原始居民對動物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包括對家畜飼養方式和人工魚類養殖方式是否出現的探討以及用“狩獵壓”“捕撈壓”獲取動物資源的方式等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探討,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對廣西地區乃至全國貝丘遺址中所包含的豐富多彩的人地關系進行了仔細的爬梳及系統的研究。
貳
《有豕白蹢:中國古代家豬的考古研究》一書,沿襲作者碩士論文有關中國黃牛的研究路徑,結合博士階段對于動物考古、古生物研究的成果寫成。全書37萬余字,近450頁碼的篇幅,以嚴謹的科學態度(每個章節所附注釋共計頁碼146,注釋數量共計1351)、活潑清新的語言、引人入勝的情節,從家豬的起源、飼養技術、資源利用以及如何有機融入中國文化的故事娓娓道來。
有關“六畜”等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動物馴化史遠超過一萬年。考古學界認為,狗是中國先民最早獨立馴化成功的動物,距今遠逾萬年。
有關狗是中國先民最早馴化的動物的考古證據來自河北保定南莊頭遺址。南莊頭是一處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早期考古遺址,其年代距今11500—9700年,是目前唯一一處同時發現動物馴化和粟黍種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袁靖等考古學家認為,該遺址出土狗遺存的下頜骨形態特征和測量數據表明這是中國考古遺址出土年代最早的狗,其主要依據便是南莊頭遺址狗的下頜緣有一定的弧度,下頜骨及齒列長度與現生狼相比,牙齒排列緊密,卻在尺寸大小上有進一步變小的趨勢。同時,侯亮亮等人也對該遺址出土動物遺存物中的碳氮穩定四位素進行了科學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此一時期狗的食物種包含了一定比例的C4類食物,這類食物極大可能來源于粟黍及其副產品。這足以表明距今10000年前的南莊頭先民已經可以使用栽培農作物及其副產品對狗進行馴化。
在漢代以前,狗已經成為中國境內廣泛存在的家養動物。其后向南擴散到東南亞、新幾內亞、澳大利亞以及太平洋諸島;向北則擴散到東西伯利亞極地地區。
狗的馴化成功,為人類所用,給中國先民馴化野豬,使其成為“家”畜提供了經驗積累和技術借鑒,起到了導夫先路的作用。
從中國先民成功馴化“六畜”的時間先后順序言之,豬是繼狗之后的第二個馴化成功的動物,可謂名副其實的“二師兄”。
據作者介紹,著名考古學家羅運兵、袁靖等人通過對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第七次發掘中出土的豬骨遺存進行全方位的研究:骨骼形態、年齡結構、數量比例、文化現象、病理學、幾何形態測量、碳氮穩定同位素和古線粒體DNA等,得出了明確的結論:該遺址是中國最早的家豬起源地,由中國先民獨立完成馴化,時間定位在距今9000—8500年前。
當先民們成功地將野豬馴化為“豕”之后,約束或者管理豬的方式不外乎放養、圈養以及放養+圈養三種方式。馴化初期,人類居住條件有限加之農業技術落后,不可能有太多“余糧”供豬食用,讓豬在“家”或聚落周邊自由覓食。自我解決溫飽問題的“放養”方式應是主要的飼養模式。此種方式的好處,除了節約成本之外,尚有使其與野豬交配獲得更加健康的后代等作用。
豬圈是中國古代先民的重要發明創造之一,其好處甚多。比如可以通過圈養保證豬的“人身安全”“食品安全”;積攢豬糞,可作肥料,提高農作物產量;有效控制改良品種,使其產肉率提高。對此,連英國著名生物學家達爾文也贊嘆不已。在其1868年出版的《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中高度評價:“中國人在豬的飼養和管理上費了很多苦心,甚至不允許它們從這一個地點走到另一個地點”,認為用此種方法豢養的中國家豬“顯著地呈現了高度培育族所具有的那些性狀”。
在對豬的馴養過程中,先民們還掌握了對豬的閹割技術,有過農村生活經歷的人,大都會對早年走街串戶的“劁豬匠”“騸牛匠”印象深刻。正是閹割技術的發明與應用,對家豬品種的改良、肉質的提高、產量的增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文獻記載中有關家豬飼養者以北魏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為最早。該書對母豬選育、護理、閹割、飼料、管理等方面均有論述。對后世中國的家豬養殖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三字經》有言:“馬牛羊,雞犬豕。此六畜,人所飼。”后人《訓詁》曰:“馬能負重致遠,牛能耕田,犬能守夜防患,則畜之以備用者也;雞羊與豕,則畜之孽生以備食者也。”
作為與中國先民關系極為密切的馴養動物,家豬對人類的最大功用是源源不斷地提供肉食。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中,豬骨遺存破碎且數量較多。考古發現其死亡的年齡正是人們食用的最佳階段,證明賈湖先民在9000多年前已將豬肉作為主要的肉食來源,且已掌握了通過敲骨吸髓的方法將豬骨弄開,以獲取其中更多的蛋白質。
此后,歷朝歷代豬肉的地位——在人們的食物結構中雖有些許起伏,總體來說,一直綿延不絕。時至今日,豬肉仍然在大部分國人的餐桌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除了肉食,養豬的第二大好處是積肥,即利用家豬圈養過程中產生的糞便給農田施肥。一頭豬平均每年可以產糞一噸左右,將其積攢起來當作有機肥料,撒施在莊稼地里,既可以使莊稼長得更好,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防土壤板結,改良土壤結構。考古學家在對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出土的漢代豬骨進行碳氮穩定同位素研究后發現其中的S15N值有顯著提高,認為這是人類用施肥后的農作物“反哺”給家豬后的結果。此研究結果也表明,下王崗時期的先民們已經掌握了積糞技術且已較為普遍地應用于農業生產中。
像其他動物皮被先民廣泛用于制革,豬皮除了可以作為衣服蔽體御寒之外,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也被開發出了許許多多的用途,比如可以做成食物,用豬皮熬制后之皮凍至今仍是許多地方一道下酒佳肴;豬皮也可以在醫藥領域發揮作用,以豬皮等豬下腳料熬制而成的膘膠,作為黏合劑,可廣泛運用于木材加工過程中。
豬鬃也較早被制成刷子使用,除用以制作日常清潔刷具和工業領域對機器進行清洗外,豬鬃還具有重要的軍用價值。二戰期間,中國出口的大量豬鬃被美國政府列入A類戰略物資,用來清洗槍炮、給軍艦等軍用設備涂抹防銹漆等。
古代先民在將豬肉作為重要食物來源時,對其所包含的保健與營養等醫藥價值有著相當充分的認識。東漢名醫“醫圣”張仲景在其《傷寒論》中便記載有“豬膚湯方”“豬膽汁方”等由豬皮、豬膽制成的方劑,豬骨也常常被制成工藝品。
叁
在與人類長期相伴相生的歷史進程中,“二師兄”除了為人類提供優質的動物蛋白,豐富了東方乃至世界各族的物質生活之外,還用渾身的寶物無私奉獻給人類,可謂粉身碎骨死而后已。
物質層面之外,家豬還承載起了文化方面的擔當,給予東方民族精神領域以深遠的影響。
對于早期先民來說,豬與人的關系主要體現在豬牲的使用以及用以制作卜骨兩個方面。
誠如《左傳·成公十三年》所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之禮儀是中國古代社會中國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考古發現表明動物祭祀所用多為家養動物。陳星燦認為此種現象背后的原因在于家養動物是人類馴化和飼養的,而野生動物經由漁獵得之,是生的或非我的,因此不可以作為祭祀品獻給祖先供其尊享。
社稷祭祀自周代開始納入國家禮制體系,社稷在一定意義上演化為國家政權的象征并為歷代王朝所沿襲。大體而言,無論在國家層面還是在民間社會,無論“大牢”“小牢”何種級別的祭祀物中,總會有豬的身影出現。尤其在民間祭祀中,獻祭物中豬的使用頻率遠遠高于牛、羊二牲。對于平民百姓,在家廟或祠堂中祭祀列祖列宗,在神龕、牌位、畫像等物面前,陳豕于室,合家而祀,這正是“家”字含義的最佳詮釋。即使在當下的大部分民間祭祀中,豬仍然是奉獻給先祖和神祇的重要貢品。
豬的肩胛骨是制作卜骨的重要來源之一。中國最早的卜骨見于距今5800年前甘肅青海一帶,甘肅武山傅家門遺址中出土的帶有陰刻符號的6件卜骨中,主要由豬、羊和牛的肩胛骨或盆骨制作而成。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在1999—2006年共發掘出土卜骨160件,其中以牛肩胛骨制成卜骨80件,豬卜骨43件,其余為羊骨等制成。
在長期的相伴相生過程中,人類跟“二師兄”的關系從實用層面逐漸上升到文化層面,從而進入到人類生活的精神界面,成為人類日常生活中須臾不可或缺的親密朋友。“‘豬’字的演變折射出人類對豬的諸多關注——豬還是豬,卻因為人類的所用、所思、所想而衍生出令人或驚嘆、或可笑、或深思、或自豪的故事與內涵。”
肆
豬是世界上最聰明的動物之一,其智力相當于人類3—5歲的小孩,具有一定的認知能力。經過馴化,甚至可以像黑猩猩、海豚一樣解讀一些比較復雜的問題;它具有靈敏的嗅覺器官,可以幫助搜查毒品、危險品。法國、荷蘭的科研人員發現家豬不僅能夠理解一些簡單的符號語言,掌握涉及動物和物體的復雜符號和標志,同時還具有某些情感特征。
或許正是有了上述這些特征,豬在中國文化乃至東亞文化圈中被賦予極其濃厚的文化內涵和多彩的文化形象。
考古學證據表明豬是中華龍的原型動物之一,豬龍主要借用了豬的頭部特征,其形象主要在遼西地區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中得到傳承與發展,黃河中游和長江下游地區的豬龍形象便深受其影響。
在生肖文化中,豬也占有一席之地。用十二個動物生肖與十二地支相結合,形象直觀地記錄時間和空間,是中國先民的重要發明之一,至今仍與來自西方“陽歷”和平共處,以紀年。
在民俗文化中,豬是國人最重要最熟悉的家養動物,與人類生活有著極其親密的關系。在創立文字時,把“豬”的形象置于“家”之下面,成為故土和家園須臾不可分割的共同體。從此層面解讀,可以說,無豬,無以“家”為。
在吳承恩的筆下,豬八戒被稱為“二師兄”,是廣為人知的藝術形象之一,其好吃懶做、笨頭傻腦、貪利好色,卻又溫和良善、憨態可掬的形象是豬作為文學人物在民俗學層面的最好注腳。
在作者的筆下,豬具有了更為深遠的儀式性用途和文化內涵:它是祭牲和祭器,是禮制的標志,是龍的原型和十二生肖之一,是家庭富足的象征,是藝術創造的源泉。讀者可以順著此種思路,在其動物考古的視野之下解讀豬型文物,進而領悟人類馴養和利用家豬的歷史進程以及在此過程中所激發出來的人類精神與藝術追求。
伍
對家豬進行考古學研究,是動物考古領域中一個專門的學問,欲對其進行全面深入研究,需要一定的專業背景知識,且對動物醫學、分子生物學、食品工程學、文學、歷史學、民俗學、宗教學等也多有涉及。因此,呂鵬能夠在《有豕白蹢:中國古代家豬的考古研究》這樣一部部頭不大的著作里,對各種資料旁搜遠紹、爬梳剔抉,在起源、技術、用途和習俗四個維度,在物質、精神兩個層面,向普通讀者全方位多角度講述作為六畜之一的“豬”的價值及意義,實屬難能可貴。
最令我這個非專業人士感佩的是,出生于豫北農村的呂鵬博士,以“小鎮做題家”的身份,進入中國的最高學術殿堂,在動物考古領域打下一片天地。從他《后記》中對少年時期家鄉院落里“有豕有家”諸多場景的回憶,反思成長過程中的熱淚與足跡,望著再也回不去的山河故里,用專業明志,高聲吟誦出“圈槽安樂,終不免引頸一刀;山野多險,卻有別樣風光”,著實令人動容。
是的,本來無憂無慮地生活于山水之間的野豬,被我們的先民們馴化之后,“由浪跡天涯到被拘泥于圈舍,由陶煮白肉到珍饈美食,由口中食到祭上牲,由實用功能到文化符號”,體無完膚地被人類榨干榨凈。聰明卻被人罵作“蠢豬”,尊貴卻被斥為“豬狗不如”。對此,作者體現出了極度的人文關懷與文人情愫,發出如此清醒而發人深省的感嘆:
人類不能凌駕于動物之上,無論人類還是動物,我們都只是地球這顆藍色星球的匆匆過客,人類與豬相伴相行近萬年之久,如何在未來繼續和諧相處,人類或許會有遠見卓識的選擇。
在此,我愿意做一次“文抄公”,直接引用呂鵬著作《有豕白蹢:中國古代家豬的考古研究》第94頁中描繪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先民們最早馴化豬的場景,作為這篇小文的結束語:
距今9000—8500年前,賈湖先民們開始飼養豬和狗、種植水稻,率先唱響了春天的故事。賈湖遺址出土的動植物遺存及人工遺物的研究為我們鮮活地勾勒出史前生業圖景:聚落內,豬和狗四處游蕩,人們開始從事?“似農非農”的生業方式,喝上了用稻米、蜂蜜、山楂、(野生)葡萄等釀造的酒,一位巫師吹奏起用鶴的尺骨制成的骨笛,另一位巫師一手搖龜甲響器,一手握叉形骨器,指揮眾人將豬下頜和整只狗埋下;聚落外,稻花飄香,鳥獸歡鳴……
(作者系文心出版社總編輯,編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