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生育行為如何影響子女反哺?
2024-08-02 00:00:00劉豐付裕
財經問題研究
2024年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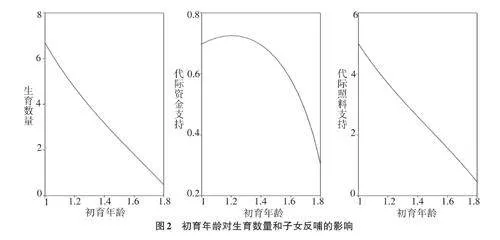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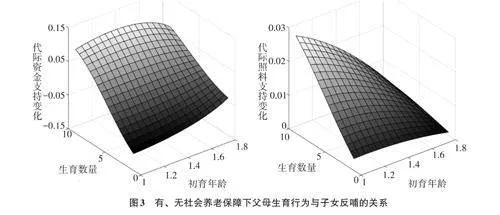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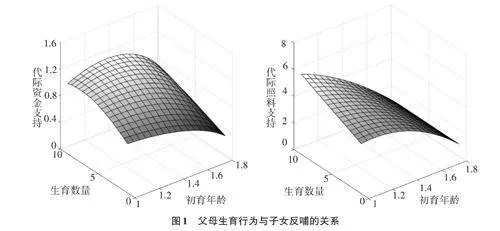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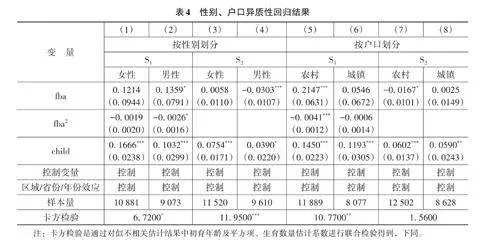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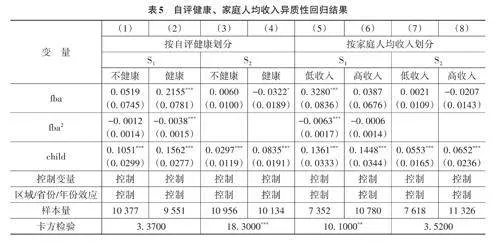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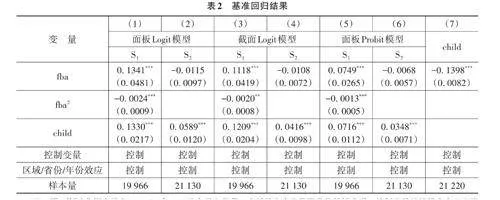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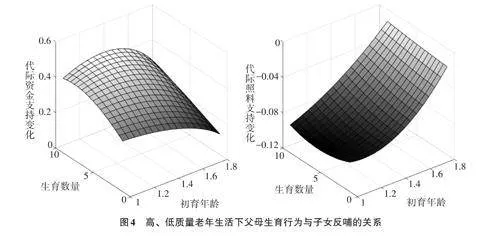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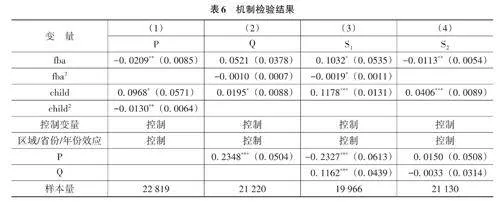


關鍵詞:父母生育行為;初育年齡;生育數量;子女反哺;全生命周期
一、問題的提出
未富先老、快速老齡化和超大規模老年人口等特征,將是一個長時期的重要國情。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深刻體現了應對人口老齡化這一戰略任務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其中,保障老年人老有所養尤為重要,這與老年人能否有尊嚴地享受晚年生活息息相關。目前,盡管中國養老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但社會養老保障的第二、三支柱仍比較薄弱,“時間銀行”等以服務換服務的自我養老范式尚未健全[1],家庭養老仍在各種養老模式中發揮重要作用[2]。然而,伴隨著中國生育率的兩次轉變[3],一系列現實問題不斷凸顯。例如,育齡女性規模下降、初育年齡推遲、生育意愿不強、老年人與子女分居[4-5]。就獨生子女家庭而言,“四二一”家庭結構加劇了子女對父母的照料負擔[6]。截至2022年,中國育齡女性平均初育年齡推遲至28歲,總和生育率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且家庭規模逐漸呈現小型化特征;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規模高達2. 8億人,加之高齡化、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比重上升,子女贍養父母的反哺式家庭代際向上支持功能受到嚴峻挑戰[7]。
為破解中國少子老齡化背景下的養老難題,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生育政策和養老政策。中國逐步提出二孩政策、三孩政策,并通過取消社會撫養費和提供生育補貼等方式助力家庭生育意愿釋放[8-9]。中國還通過建立長期護理險試點、醫養結合示范點、贍養老人專項附加扣除和父母戶籍隨遷等政策優化社會養老保障體系。……
登錄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