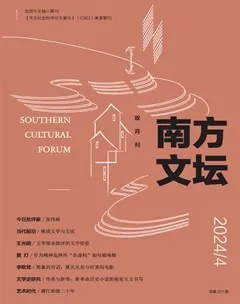1980年代文學主流與支流的辯證性互動
在當代文學史書寫中,大多以“朦朧詩/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第三代詩”等線性發展與“主流”更迭的敘事線索對“新時期”文學加以整體把握。在以往的1980年代文學研究中——或以“新時期”文學加以替代——文學進化論或顯或隱地發揮著重要作用,并將“新時期”文學思潮的演進確定為朝向“現代”范式更迭的典型模式。即使是在晚近興起的“以八十年代作為方法”的重返80年代研究新視角,也同樣口號鮮明地預設了新時期文學思潮的固有演進模式。但問題在于,“文學思潮”的主流階段性演化與更迭,是否是真實的歷史現場?還是說其更接近于一種“文學現代性的歷史目的論敘事”?如果加以細勘就可發現,所謂的“文學主流”與“文學支流”之間,并不存在絕對的劃分與分隔,反倒顯現出辯證性互動的格局。
一
原本身處“地下潛流”位置的文學支流浮現于“地表”,更迭為“文學主流”。如趙振開的中篇小說《波動》,在1981年正式發表于武漢《長江》文學期刊之前,就已然在“文革”后期以手抄本的形式傳閱于青年中;靳凡的書信體小說《公開的情書》寫作于1972年,在1979年正式發表于《十月》之前,也曾以“地下”傳播的形式在讀者中產生一定的影響。這兩部中篇小說,在尚未“正式”亮相之時,已然出現此后“傷痕小說”的初緒,如批判“文革”、抒寫一代青年對時代的懷疑及失落情緒,進而思索“人的存在”命題。
再如之于1980年代文壇重要的新詩潮之一的“朦朧詩”,其成為“文學主流”之前,也同樣在“文革”時期經歷過長時間的“潛流寫作狀態”,如1960年代初期,高干與高知子弟組建的地下文學沙龍X詩社和太陽縱隊已然顯露出“朦朧詩”詩風的征兆;“上山下鄉”運動中出現的知青地下沙龍以及在此時期詩人食指的創作,同樣是新時期“朦朧詩”出現的前兆;“白洋淀詩群”芒克、多多、根子等人的詩歌寫作在“文革”時期,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于“地下”。對此,眾多研究者已經有了翔實且系統的考察①。“第三代”詩歌運動在大規模流行成為“文學主流”之前,也尚且只是地域性的口語詩狂想,如“莽漢詩”的發起,始于李亞偉等少數幾個1983—1984屆的四川邊域大學生,尚未形成席卷大江南北的“第三代詩歌”浪潮。
1985年之后亮相的“先鋒小說”,實則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就已然出現;但在彼時“批判政治性”的文學思想張揚之際,“現代派”的創作尚未得到重視,如王蒙的意識流小說三部曲《夜的眼》《春之聲》《海的夢》、宗璞的超現實主義小說《我是誰》等作品;但在1985年之后,如劉索拉《你別無選擇》、殘雪《山上的小屋》、馬原《岡底斯的誘惑》、余華《十八歲出門遠行》、格非《迷舟》、蘇童《桑園留念》、孫甘露《信使之函》等帶有鮮明現代主義特征的小說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學主流”。如余華所說:“僅僅是在幾年前,我還經常讀到這樣的言論,大談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智慧已經成為中國文學傳統的一部分,而20世紀的現代主義文學卻是異端邪說,是中國的文學傳統應該排斥的。”②余華在論述中設定了一種超越1980年代早期“現實主義”文學的、具有刷新性及突破性的“現代主義”文學秩序觀;如果余華的論述還不夠明確,那么在李陀的認知中,則能更為明確地體認到1980年代知識分子對“先鋒小說”的“優越性”定位以及由此伴生的“現代主義”文學史目的論的線性進化秩序:“(19)85年以后……出現了汪曾祺、阿城、莫言、韓少功、李銳、王安憶、劉索拉等人的寫作,開始打破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在表面上進行‘變革’、實際上卻沿襲‘工農兵文藝’路線這樣一個文學局面……真正的文學革命正在1987年發生。”③他們對1980年代前期具有現代主義文風及技巧的創作的有意忽視,一方面是為建構具有“純文學”指向的文學“現代性”秩序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文學主流的線性發展觀成型之后——正如同柄谷行人所說——認知裝置形成之后,遮蔽了“秩序”生成的歷史語境及建構手段。再往前追溯,不僅是1980年代前期的現代主義文學創作“支流”已然顯影,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周作人、李金發、魯迅、戴望舒等人的創作文本中,“現代主義”也從未缺席。
尋根文學同樣如此,在1984—1985年尋根小說主張者正式發表“尋根文學”宣言之前,“尋根詩歌”在1982年已然出現,諸如楊煉的《半坡》組詩、《自在者說》,四川地域的整體主義詩人宋氏兄弟、劉太亨、石光華等人的創作,新傳統主義詩人廖亦武、歐陽江河等,但1980年代前期的“尋根詩”卻尚未成為文學主流;再往前追溯,在阿城、韓少功、王安憶、莫言等人的小說中出現的對“鄉村風俗圖景”及“地域文化”的“尋根式”發掘,在汪曾祺1980年代早期的作品《受戒》《端午的鴨蛋》以及沈從文的《邊城》中也早有跡象。因而,1980年代“文學主流”與“文學支流”的更迭及朝向“現代性”的線性發展路線,只能在某個標準化的文學史敘事中成立。而這一“標準化”的當代文學史敘事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其“形成的目的”是什么,同樣值得追問。
二
同時期的“文學支流”與“文學主流”之間,相互借鑒著視角與共享著底層思想架構。各個所謂更迭的“文學主流”也都處于相互借鑒的互動格局中,如尋根文學的出現,本就與知青小說密切相關,如《棋王》《孩子王》《樹王》本身就可歸類于知青小說,在《小鮑莊》和《老井》等小說中隱含著知青小說的視角④。“尋根小說”的口號是在1984年12月杭州“新時期文學:回顧與預測”會議中正式醞釀出來的,而尋根小說口號的提出者幾乎都參加了此次會議,這一群體也同樣具有“知青”經驗,因而,與其說“尋根文學”思潮的出現,是一種新舊更替的現象,不如說在“文學主流”及“文學支流”的更迭中,本身就包含著思潮主體之間的連續性聯系及互動。再如“尋根文學”與“先鋒文學”實驗潮流之間,也存在著頻繁而無法割裂的重疊,如莫言的《紅高粱》、鄭萬隆的“異鄉異聞”系列等創作中的神秘鄉土氣息及荒誕表現手法,本就受到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等現代主義手法的影響,因而“尋根文學”在某種程度上也同樣是“先鋒文學”的形式實驗產物。當然,僅僅勾勒出各個思潮中作品的“相似及相通之處”是遠遠不夠的。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新時期的各個“文學主流”及“文學支流”的更迭,在整體上是以1950—1970年代的“革命政治文學”主流為參照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等一系列“文學文化主流”的顯現及文學支流的更迭過程中,它們共享著同一套文學思想理路,并因與社會思潮動態協調的方式不同呈現出不同的“文學主流”面貌。這一套文學思想邏輯即“反政治性”及凸顯自然化與本質化的“人道主義”。“傷痕文學”,是在新時期政治反撥之際最先生成的文學思潮,在劉心武的《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等作品中,以揭露批判“四人幫”為主要靶向。可以見得,“傷痕文學”的創作帶有強大的歷史慣性,在筆觸之間,依舊流露出革命文學的“政治性呼喊”的筆調;但從另一方面可見,恢復由階級斗爭的單一關系破壞的“人情”與“人性”之美的呼聲也同樣顯影出來,實則已然具有由“政治”命題向“文化”命題滑動的趨向。在《傷痕》中可見,雖然通篇中充斥著“政治性”的表述氣氛,但最終的落腳點在于恢復由階級革命破壞的家庭倫理及人情美。《班主任》也同樣如此,小說的背景是在將要開始的改革“新時期”——同樣也是革命時代的終結——但吊詭的是,在這樣一個“尾聲”中,在經歷了漫長的“革命時期”之后,除謝慧敏之外的其他人,似乎都具有“蘇醒后的人情美”,“人情美”與“人性美”快速復蘇的“不合理性”在小說中變得“合理”,作者借此“顛倒的風景”意圖凸顯“人道主義”之于“革命政治”的優越性及“自然性”。在《抱玉巖》中,可以看到“愛情”的線索是貫穿全文的,乃至突破了“師生”的身份之隔,這種“突破”在極大程度上質疑了“階級成分”所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隔膜。
因而,“文學即人學”的文學思想早在新時期初期的傷痕小說中就得以顯現,而“自然化”與“本質性”的“人道主義”也在新時期初期就定下了基調,并成為此后的文學潮流所共享的思想框架。
“反思文學”與“改革文學”亦如是,在文學史的“成規”認知中,傷痕、反思、改革同為新時期變革之際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依舊維持著“政治性”的書寫慣性——在很大程度上呈現為“反政治性”的面貌——但實則,在新時期初期的三個重要文學思潮的文學史敘述是值得商榷的,“反政治的政治性”固然是一個顯性特征,呈現在諸如《苦戀》《布禮》《芙蓉鎮》《蝴蝶》《剪輯錯了的故事》等作品中,但“反政治的政治性”闡釋框架又如何解釋改革文學作品《喬廠長上任記》《沉重的翅膀》《禍起蕭墻》《男人的風格》中大力提倡新時期四化建設的政治性表達的努力?因而,在新時期初期的三大文學思潮中,“反政治的政治性”僅僅只能解釋部分作品的不完全特質:更深入的特征在于寫作者們設定了一個“人”與“非人”之間的預設的對立敘述模式。正如同《班主任》中的“謝慧敏—其他同學”的“認知顛倒”格局,作為剛剛經歷過漫長的階級斗爭政治氛圍的“其他同學”,相對于“謝慧敏”卻極快地且“本質化”地表現出“自然的人情與人性”特質。換句話說,本應該在階級斗爭時期將“政治及階級斗爭原則”視為“常態”的認知,在新時期變革初期,卻能以極快的速度調轉為“變態”,并將“人情與人性美”設定為“應有的常態”。因而,“階級斗爭”的政治性模式被視為本質化的“非人”模式,而“人情與人性”特征被視為本質化的“人”的模式。
在“改革文學”作品中,寫作者們所注目的也并非是“實務”面向的四化改革的具體層次——或者說,不再著重書寫單純的革命與改革激情——正如與《抱玉巖》中所敘述的“革命的反撥”與“愛情的收獲”的進行同步態,在《喬廠長上任記》中,伴隨著喬光樸的“重返工業改革崗位”事件的展開的是與戀人“童貞”的重逢;在《赤橙黃綠青藍紫》中同樣如此,團支部書記解凈在劉思佳眼中,其“革命身份”逐漸被“愛慕”心緒的沖動覆蓋。在這樣一種“戀愛氛圍”中,寫作者有意設定了“人情人性”本質于且先天于“革命政治”的敘事秩序,同樣也設定了“人”與“非人”的對立結構。如果說這種“結構”在傷痕、反思、改革三大思潮中還處在隱秘不顯的狀態,那么“尋根文學”的創作則通過回避“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的方式彰示“人的文學”的本質性與優越性。“尋根文學”命題的提出,看似是為“尋民族之根”,是關于文學與文化的民族性表述;但問題也在于,眾多文本中所彰示的“文化民族性”卻是由邊緣的、地域性的、少數民族的文化質素構成,唯獨是主流正統的中原儒家等民族文化質素被排除在“尋根”范圍之外。如《爸爸爸》描繪的楚地苗族文化、《系在皮繩扣上的魂》書寫的藏族地區神秘風土、《最后一個漁佬兒》中呈現出的吳越文化等。韓少功在“尋根文學”的宣言《文學的“根”》中設定了一個本質化的“民族的自我”,“民族文化”的本真卻不存在于主流的規范化文化層中,而是處在文化層的“第三層”⑤,“一個完全的歷史時期,雖經劇烈的摩擦與破壞還是巍然不動……是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具”,正如同“屬于不規范之列”的“鄉土中所凝結的傳統文化”,如“俚語,野史,傳說,笑料,民歌,神怪故事,習慣風俗,性愛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鮮見于經典,不入正宗,更多地顯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⑥。與韓少功構建的“規范文化層—非規范文化層”的“表面—本真”對照關系序列的“尋根”話語類似,李杭育則認為“民族文化之精華”,更多是保留在中原主流的文化規范之外,“規范的、傳統的‘根’,大都枯死了……規范之外,才是我們需要的‘根’,因為它們分布在廣闊的大地,深植于民間的沃土”⑦。李慶西則更為直白地指出“尋根文學”是“超越了現實的(亦已模式化的)政治關系的藝術思維”,并從原有的“政治、經濟、道德與法”的“社會表層”演化到“自然、歷史、文化與人”的“文化的深層”⑧。
固然,一方面,眾多文學史認為“尋根文學”深受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這一“影響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尋根文學”的發生同樣應當放置在“新時期”改革與對“革命政治”的反撥的社會歷史譜系中觀視。也就是說,對“主流民族文化傳統”的規避與對“邊緣、民間及地域文化根系”的重新發掘(或者說重新闡釋),延續了新時期初期三大文學思潮的“人—非人”對立模式的思想架構,也同時顯現出“尋根”作家們重塑“民族文學”根系的文化危機感(在1980年代普遍的“西化熱潮”中)以及為新時期“改革”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賦能的另類“文化政治性”沖動。與此同時,之所以是“尋根”而非“重塑根系”(實際上這一本質化的“文化根系”是為“尋根文學”作家及理論家所建構的),其話語體系內部便預設了一個先天性存在的“中華民族文化根系”自然性歷史敘事。因而,“尋根文學”的寫作看似是“文化層面的民族根系再發掘”,與“政治性反撥”無涉,但其在設定出“本質化的非規范化的民族文化”與“表面化的規范化政治文化”的對照系之時,就已然相承了傷痕、反思、改革文學思潮中先定的“人的文學”與“非人的文學”的比照秩序,顯示出尋根文學創作及理論建構與“新時期社會歷史變革”的政治性動能緊密關聯的性質。
在1980年代中后期,文學“向內轉”的趨勢顯現,先鋒主義與文學技法實驗潮流的出現,實則與“人的文學”“人道主義”的“文化政治性”命題無法徹底割裂;也就是說,所謂的“向內轉”與形式實驗,是對于“人道主義文學”的“政治性”思想的反撥,也同時是“人道主義文學”的延展與另一種“意識形態性”的體現。“先鋒文學”實驗現場的自述是將“文學現代性”作為“社會現代化”的標志來確立“現代派”的合法性的,如徐遲所說,西方現代派的出現以及文學藝術的變化多端,是因為其社會物質生產力的提升與經濟生活的豐裕⑨,在某種角度上說,這是對新時期社會歷史變革的“動態性”適配。在革命政治文學時代,革命意識形態的優越性及“現代性”,體現在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批判環節,即在“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生成,而徐遲對西方現代派文學生成的“合法性”闡釋,則將原本“革命政治文學”序列中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批判環節,替換為“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因而也取消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在新時期“變革”語境中的“先進性”。在某種程度上說,徐遲的論述是將新時期文學的“先鋒文學實驗”的出現及發展,嵌入到“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的社會歷史動態語境中,從而實現“先鋒文學實驗”的先進性及“文學進化”優越性辯護。另一方面,李陀的認知在1980年代文學現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認為1985年之前的傷痕、反思、改革等文學思潮是“舊模式”,“基本上還是工農兵文學那一套的繼續和發展,作為文學的一種潮流,它沒有提出新的文學原則、規范和框架,因此傷痕文學基本是一種‘舊文學’”,而1980年代中期之后出現的汪曾祺、阿城、莫言、韓少功、王安憶、劉索拉等人的文學創作“超過了五四以后的任何一個時期”⑩。李陀在訪談中設定的1980年代“文學進化論”,將“先鋒文學實驗”視為“新時期文學”創作的斷裂性突破——在忽視1980年代之前“現代派”文學支流已然初顯的文學現象的前提之下——與此同時,他也將新時期“先鋒文學實驗”的先進性界定為對“文化專制主義”與意識形態的沖決,以“怎么寫”取代“寫什么”。而這種“新時期文學進化論”的線性敘事也同樣為此后的當代文學史所沿用,余華的認知恰可闡釋“線性進化論”的背后意圖:“中國的先鋒派只能針對中國文學存在,如果把它放到世界文學之中,那只能成為尤奈斯庫所說的后先鋒派了……中國差不多與世界隔絕了三十年,而且這三十年文學變得慘不忍睹。”他認為先鋒文學實驗的意義就在于“不再被拋棄,為了趕上世界文學的潮流”。因此,“進化論”的背面是對“世界文學”的趕超——實際上是西方設定的“現代性”秩序——“趕超”的隱藏含義則在于融入“世界文學”秩序。聯系新時期的社會經濟政治變革動態來看,融入“世界文學”的“文學自律性”語言實驗田地的構建,實則與新時期社會融入“世界自由主義市場”的趨向具有同步性;因而,如李陀所言的“先鋒文學”的“去意識形態化”,在某個角度上來看,非但沒能實現,反倒是從中國語境的“革命政治”意識形態跳躍到“自由主義市場”主導的意識形態構造中去了,與社會歷史動態的深切互動,由此可見其在“非意識形態”過程中的“意識形態性”。
如果說1980年代中后期的先鋒文學實驗之于前期的傷痕、改革、反思等文學思潮確實存在一種“顛覆”與“斷裂”現象,那么其關節點可能并不在于對于“革命政治”創作范式的“反叛”與否,因為兩個時間段的創作可以說共享著同一套“反政治性與人的文學”的文化思想框架;而在于“反叛”的程度如何。如果說1980年代前中期的各個文學思潮,尚未找到如何有效反叛“內部革命政治意識形態”主導的文學創作范式,那么在中后期的“先鋒文學”及“現代派文學實驗”中,先鋒作家們試圖“重新”借助西方的現代派文學規范來實現與“新時期改革”歷史動態深層互動(反撥“階級革命政治性”)的“新意識形態”建構意圖。而同時需要重申的是,“人的文學”與“純文學”等文學思想的歷史語境限約性。
三
1980年代趨向“純文學”自律性場域的文學思想主流的顯影,恰恰內在于革命政治文學時期(1950—1970年代)的“潛在支流”脈絡之中。1980年代文學思想的形成是以“文革”的結束與“新時期”的到來為大背景,換句話說,如若不從“改革開放新時期之于‘文革’的政治性反撥”的角度審視1980年代文學制度與文學思想,那么對“新時期文學”的考察是無以立足的。從某個角度來說,新時期文學的各個“文學主流”的顯影本身是內在于1950—1970年代的革命政治文學脈絡之中;與其說新時期文學的“文學主流”——如“反政治的政治性”“現代派文學”等——是“革命政治文學”的延續,毋寧說革命政治文學在1950—1970年代所遮蔽(或隱形批判)的對象,即地下文學資源在新時期被轉換成“主流文學”。按照《全國內部發行讀書總目1949—1979》的統計,在30年間,共出版了“內部書籍”18310種,其中社科類的有9766種之多。在1960—1970年代中,出版界曾經開展過兩次較大規模的“內部讀物”出版潮。第一次是1960年代初期的中蘇論戰中,關乎“返修斗爭”的需要,由世界知識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三聯書店等出版單位大規模出版了一批國際共運中各種思潮流派或稱“修正主義”思潮的和有助于了解蘇聯修正主義、西方資本主義的著述及文藝作品。第二次出版潮是在1970年代初期,隨著中蘇關系的緊張與中美關系的解凍,大規模出版了不少批判“蘇修”的理論及文藝作品,以及與中美關系相關的歷史傳記文學作品等,并且還舉辦了《摘譯》,介紹國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思潮及文藝作品。因而,富有歷史反諷性的是,“這些原應當由‘革命一代’去批判、去鏟除的‘封資修’的毒草,卻成了孕育、萌發他們思想啟蒙的最重要的養素”。細勘“內部讀物”的具體書目可以發現,其可大致分為幾類:其一是19世紀西方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作品,如《戰爭與和平》《羅亭》《怎么辦?》《前夜》《雙城記》《約翰·克利斯朵夫》《紅與黑》《凱旋門》《斯巴達克思》《九三年》等;其二是被判定為蘇聯修正主義以及右傾主義的作品,如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索爾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西蒙諾夫《生者與死者》、葉甫圖申科《〈娘子谷〉及其他》、阿克肖諾夫《帶星星的火車票》等;其三是20世紀現代主義作品,如《厭惡及其他》《憤怒的回顧》《局外人》《麥田的守望者》等;其四是與中蘇反目、中美解凍的社會歷史動態相呼應的中美訪談、國際關系研究、歷史傳記等作品,如《斯大林時代》《赫魯曉夫主義》《西行漫記》《杜魯門回憶錄》《尼克松其人其事》《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等。而對照1980年代的“文學思潮”更迭中的文本,可發現“內部讀物”扮演了如何重要的角色,正如一位北大“共產青年社”讀書會成員回憶:“經歷了一個全面的壓迫和苦難,我們的精神陷入了一種困惑。而最終使我們沖破十幾年的教育灌輸給我們的思想模式,得益于兩本灰皮書的點撥,一本是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托氏的書無疑是困惑之中出現的一縷明晰的光。那年冬天,我又找到了德熱拉斯的《新階級》。至此,有關政治和社會的認識,我們終于擺脫了夢魘般的桎梏和愚昧。”
因而,1950—1980年代宏觀整體的“文學支流”與“文學主流”的互動及“位置”移換現象,也可解釋為什么在新時期的社會改革初期,乍一出現的“傷痕文學”中就已然具有了自然化與本質化的“人道主義”的潛在“前提”。換言之,在“八十年代”來臨之前,潛行于歷史地表以下的諸多“文學支流”在“新時期”內部文化體制反撥與外部自由主義市場壓力的“現實主義”危機之際,重新顯現于“歷史地表”。
余論
但是僅僅揭示出1980年代“新時期”文學的“主支流”辯證互動面貌是遠遠不足的。從揭示出“辨證性互動”的面貌中可見,1980年代文學思潮的更迭遠非“文學史”所建構的涇渭分明的“朝向現代性的衍化進化”面貌。因而,問題在于,為什么“事實”與“話語”建構之間會存在如此逆反的裂隙?或者說,眾多當代文學史(甚至是1980年代歷史現場的文學史敘事)之所以設定“朦朧詩/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第三代詩”主流更迭進化路線,其深層原因是什么?這需要我們返回社會歷史動態現場,以實現“福柯式”的反查。
【注釋】
①黃平:《〈今天〉的起源:北島與20世紀60年代地下青年思想》,《文藝爭鳴》2017年第2期;徐國源:《從“地下”到“地上”——傳播視野中的朦朧詩》,《江蘇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亞思明:《“朦朧詩”:歷史的偽概念》,《學術月刊》2013年第9期;霍俊明:《當代詩歌語言的“慣性”機制——以“地下”詩歌、“今天”詩歌和“第三代”詩歌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10期。
②余華:《兩個問題》,載《我能否相信自己:余華隨筆選》,人民日報出版社,1998,第174、174頁。
③⑩李陀、李靜:《漫說“純文學”——李陀訪談錄》,《上海文學》2001年第3期。
④李潔非:《十年煙云過眼——小說潮流親歷錄》,《當代作家評論》1993年第1期。
⑤第一層為“浮在表面上的是持續三四年的一些生活習慣與思想感情,比如一些時行的名稱和時行的領帶,不消幾年就全部換新”,第二層為“略為堅固些的特征,可以持續二十年、三十或四十年,像大仲馬《安東尼》等作品中的當今人物,郁悶而多幻想,熱情洶涌,喜歡參加政治,喜歡反抗,又是人道主義者,又是改革家……要等那一代過去以后,這些思想感情才會消失”。參見韓少功:《文學的“根”》,載《文學的根》,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第80頁。韓少功所揭示的第二層“文化層”的描述,意有所指,或是對革命政治文學與文化的界定。
⑥韓少功:《文學的“根”》,載《文學的根》,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第80-83頁。
⑦李杭育:《理一理我們的“根”》,載謝尚發編《尋根文學研究資料》,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7,第87頁。
⑧李慶西:《尋根:回到事物本身》,載謝尚發編《尋根文學研究資料》,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7,第11頁。
⑨徐遲:《現代化與現代派》,《外國文學研究》1982年第1期。
1977年8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并將“文革”結束后的時期命名為“新時期”。
中國版本圖書館編《全國內部發行讀書總目1949—1979》,中華書局,1988。轉引自廖亦武主編《沉淪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第2頁。
蕭蕭:《書的軌跡:一部精神閱讀史》,載廖亦武主編《沉淪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第5-6、11頁。
(魏巍,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黃英豪,西南大學文學院。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想史”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9ZDA274;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中國現代文學的半殖民體驗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2022NDYB141;重慶市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CYS22252;西南大學2035先導計劃項目“現代漢語詩學話語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關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SWUPilotPlan;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助創新團隊項目“中外詩歌發展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SWU200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