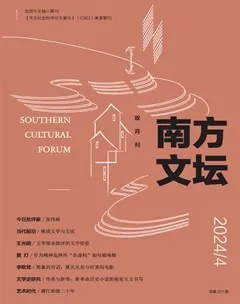文學理論批評的文學價值
為什么要談文學理論批評的文學價值問題?20世紀90年代文化轉向以來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雖然取得了新的成就,但也出現一些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迫切需要重提文學的本體價值,同時必須以新的文學觀念與批評方法面對當代新出現的文學現象。
20世紀90年代,由于中國社會急劇向商業化、市場化轉型,先鋒文學話語實踐的自我調整,教育和學科體制的恢復,傳統的以經驗和意識形態為背景的社會學批評(無論是意識形態批評還是打著“審美”旗號的反意識形態批評)失效了,兩本新出版的文化評論著作引起了許多批評家的關注。一本是英國文化批評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了中文譯本。該著作努力以馬克思的存在與意識、經濟關系與上層建筑的思想探討近現代英國社會的思想文化變遷。另一本是《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由留學美國、畢業后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年輕學者唐小兵編選,1993年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后來又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所謂“再解讀”,就是以新理論梳理老問題,重新理解一些已有結論的經典文本,按其編者的表述,就是“重新進入文本,重構文本的語境和體制,并由此進一步梳理和解讀文本與泛文本之間的間隙、共謀、不對稱和互相補充。……使我們更好地進入當代日益發達、并開始無微不至地滲透進我們的文化、精神生活的資本主義現實主義進行批判,并由此‘著手新的開放型文化的建設工作’”。這兩部著作改變了20世紀80年代大學中文系師生和文學批評家對新批評及其經典《文學理論》的熱愛,諸多從事文藝學、中國現當代(特別是當代)文學的研究者,從文學文本的審美閱讀轉向文化研究立場的閱讀,博士生、碩士生的論文選題也從作家和文學作品本身的研究,轉向了文學文本的生產機制、歷史語境和權力關系的研究。
文學研究立場的轉變,不僅改變了文學理論批評試圖通過“內部研究”“審美方式”改造簡單粗暴的社會學批評的路線,也使馬上要發熱的后現代思潮很快退燒。文學理論批評擴張了自己的版圖,泛化了概念與方法:文學作品成了文本,文學創作變成了寫作,一些文學教授成了“新左翼”或公共知識分子。“再解讀”重新理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以“大眾文學”的概念置換“通俗文學”,從“雅俗”關系中脫身,重點關注文學的歷史主體和社會運動,實際上已經把文學文本視為意識形態文本(如果我們使用威廉斯比較中性的說法,將意識形態視為“產生意義和價值的社會共同經驗”的話)。而“解讀”這些文本,所致力的方向,已經不是釋放文學語言、形式中的能量,而是探究社會歷史在不同文本中的權力運作。這種理論批評,在優秀者手里,尚能借助新歷史主義、羅蘭·巴特、福柯的理論與方法,找到文本背后的底層文本。而在追逐時尚又消化不良者或訓練不足的年青學者手里,則繞開了文學文本閱讀與分析,轉而從媒介、文學制度、社團、刊物、稿酬、評獎等方面搜集材料,證明社會歷史的決定性。至于一些平庸者,則輕松愉快地回到了庸俗社會學的懷抱,無視文學與生活的特殊關系,以社會、歷史、現實生活和大眾的名義,成為商業化時代的幫閑,或是道德綁架的衛道士。
文化批評有許多形態,但無論直接以大眾生活或后現代“亞文化”為對象的批評,還是將經典化了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作為文化現象進行重新解讀,雖然理論參照、角度與方法千差萬別,新歷史主義的、女性主義的、后現代主義的、后殖民主義的或“新左翼”、新馬克思主義的,都無一例外試圖通過泛化的文本讓人看到語境制約的根本力量,看到歷史與現實權力的運作,看到階級、性別、種族的壓抑,以及形形色色的社會訴求。近二三十年文學批評的文化轉向,大大拓寬了理論批評的視野,介入了歷史與現實生活,介入了時代的意識形態進程,開放了社會科學。它顛覆了文學的特權,消除了神秘色彩,解構了本質主義的文學理論,使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獲得了同樣的價值和權力。同時,也推動了傳統社會學批評的變革,找到了一套新的理論概念、研究方法和論述策略,從而也以它的長處和問題,解構了文學理論批評、文學研究自身的莊嚴與神圣:理論批評與學術研究,原也不是什么“公器”,具有“價值中立”的公信力,它們同樣取決于社會歷史語境、文化站位和利益訴求,文化批評家得出的結論,其實也被自己設計的問題所決定,取決于身份、處境,取決于希望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它們早已被福柯一語道破:任何話語都有誰在說、說什么、怎樣說的問題。
不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批評的文化轉向也暴露出不能無視的問題。從理論上說,文學觀念不應該是本質主義的、純粹的和自我封閉的,作家也是一個說話的人,不應享有特權。但世間的話語千萬種,是不是各有其類型性,不同類型的話語是不是各有其面對的基本問題,是不是各有主體與客體、功能與結構的微妙關系?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當然都是話語實踐,但任何一種話語實踐,都是歷史慣例與個人才能的互動,它們可以無差別對待嗎?我們該如何理解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的信》中的經典論述:巴爾扎克違反自己的階級同情與政治偏見,不加掩飾地贊賞自己政治上的死對頭,同時把自己心愛的貴族,描寫為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這類詭異的、連作家自己也不能做主的現象,是不是小說創作才有的?而從實踐上看,沒有寫作與創作的區分,沒有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的界限,沒有文學的分類與分層對待,沒有一般讀者與專業讀者的區別,勢必造成話語實踐的混亂,造成平庸寫作與用心創造的無差別對待,造成社會輿情與文學批評的混淆。新媒介爭論“梨花體”、“烏青體”、余秀華與賈淺淺,簡單、粗暴和情緒化,吸引了眾多的圍觀者,專業性批評卻無從插嘴或許也根本不想插嘴;而對臧棣、陳東東這樣新語言觀背景下得失參半的詩歌實驗的隔膜,缺乏中肯的批評,是不是詩歌批評感受力與理解力的缺失?
理論批評的文化轉向出現的這些問題,一部分是原生性的,是理論上的缺失,因為它用單一的文化分析應用于復雜的文學話語實踐,將處理感覺、想象、趣味的語言歸結為歷史與現實權力的運作。在一篇談論文學史的短文中,我曾以我國最偉大的小說《紅樓夢》第一回那首具有反諷、自嘲意味的五言詩“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為例,討論文學與歷史的矛盾。文學理論批評面對的是一個景虛情真的世界,其核心關注是語言的創構力量,即使用文字生產意義與價值的方式,是借助語言跨越邊界而不是在邊界內做囚徒。米勒(J.Hillis Miler)在反思文學的文化研究時就說過:應該把現今在“文化研究”“弱勢論述”或“新歷史主義”中許多有關的文學研究排除在文學理論的范疇之外。因為其關心的是決定文學的脈絡,而不是文學作品借以產生意義與價值及影響個人生活和社會的方式,由于它們忽視文學創世的、構成的力量,所以它們不是文學理論的一部分。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文化立場的研究沒有意義,而是想指出幾十年來我國文學理論批評的文化轉向還存在另一方面的問題:對文學文本的簡單化約。這也與我們對文化批評理論與方法本身的理解、接受的簡單化和不充分有關:我們是在沒有經過形式主義批評的洗禮,沒有改變傳統語言觀的背景下,從庸俗社會學批評走向文化批評的,這樣得到的,很可能只是“第二次發明的自行車”。
因此,在經歷了這一段得失都有的文化批評話語實踐之后,我主張在回望與反思的基礎上重新面對“文學性”問題,正視文學創造的無可替代的潛能,正視文學的特殊意義與價值。在這個什么都被量化、數字化、JDP化、網格化、智能化的后工業社會,人類身心與靈魂像難民一樣被驅來趕去,無處安放,似乎只有文學話語還能開啟一個無法被形形色色權力簡化與管控的世界,翻越高墻伸展個人的感受、記憶和夢想。文學開啟世界,翻越高墻呼吸自由的空氣,不是我的發明,而是海德格爾通過研究荷爾德林等人的詩歌得出的結論:雖然沒有本質主義的文學,文學形式也不是永恒的形式,但一方面,這是一種能夠創世的語言,這種語言具有踐行力量,打開世界,促使感覺、想象與意念的生成;另一方面,它注入了“時間信息”,讓我們“經驗著語言與必死性之間的關聯”,因而可以像埃及金字塔或其他紀念物那樣,從屬于過去的傳統向未來說話。海德格爾承認,詩歌的聲音是微弱的,也是可破碎和可能消失的,不像浪漫主義認為的那樣,是永恒的天才的表達。但是,不管社會如何變化,科學技術如何發展,唯一可能的當代真理經驗還是詩和藝術的經驗,因為它否定形而上學派發的屬性,不遵循涵義理論而被思考,復活消逝了的蹤跡與記憶。
不過,重新重視文學性,并不是回歸20世紀80年代熱衷的俄國形式主義或英美“新批評”式的文學性,以“內部研究”作繭自縛。文化研究批評實踐所打通的文學文本與社會歷史的關聯,必須正視。不同之處只是,它們不是決定與被決定、文本與底層文本的關系,而是復雜的互動關系:文學以語言“做事”,創造“世界”,進入現實與歷史。尤為重要的,被真正的文化理論批評演繹的符號化語言觀,也可以啟發我們重新思考文學與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關系,特別是文學以語言“做事”的特殊方式。耶魯的保羅·德·曼(Paul de Man)認為文學理論是有關語言的語言,文學批評的正業是探究文學對語言的運用。他說:“文學理論產生的時候,是接近文學文本的方式不再根據非語言的考慮,也就是說,歷史和美學的考慮,或者用比較委婉的方KKkIT65BcBDGh7B2g9IuzImCydFobg9tDldI+vbg+kg=式說,當討論的對象不再是意義和價值,而是建立意義和價值之前它們的生產和接受的模式——這里暗示的是,這種建立所具有的疑義,足以要求一個獨立自主的批評探究的行業來考慮它的可能性及其狀態。”(“”)這話將歷史與美學的考慮排除在外,不是說它們不值得考慮,而是強調文學理論批評的主業,是關注語言和其生產意義與價值的方式。首先是對語言本身的認知,語言當然作為記憶、作為物的符號見證存在,指引人們關注外部世界。但語言的組織同時也是精神樣式、思維方式,寄托人的感覺、思緒、意念等微妙的東西。因此,福柯提出:“語言不是作為物的有形書寫而存在,而是在表象符號的一般狀況中發現了自己的空間。”(《詞與物:人文科學的考古學》)這樣就有了第二重使命:理解文學運用語言的方式,不只在語法關系、指代關系、涵義關系內編織意思網絡和文本,也在所指、能指、語法的外面演繹語言文字的可能性,讓文本獲得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以語言的認知與文學對語言的運作特點的把握為前提(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可能性與運作理路),文學理論批評應該通過釋放文學的能量來反抗權勢,持護完整的人性。一個文學理論批評家的工作,“不是使文學適應事先制定好的歷史結構,而是應當視文學為一個連貫的結構,它被歷史地限定但卻形成自己的歷史,它以自己的形式對外部的歷史過程作出反應但又不為其所決定”(弗萊:《批評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