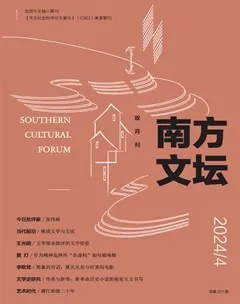論弱的普遍性:基于兩首當代詩的文本細讀
讀西渡的《天使之箭》和楊鍵的《神奇的事情》這兩首詩,我意識到當代詩中某種新的歷史主題正在生成,因為這兩首詩所傳達的不合時宜以及變幻莫測的意蘊,恰恰是對時代困境思考的結果,并應和了當代詩的歷史訴求,令人試圖探究隱身于其中的無形。無形乃是晦暗與幽深,如海德格爾所言,是人借以度量自身的尺度,即詩的奧義。《天使之箭》通過此種晦暗與無形,傳達著一種弱的普遍性,使我激動的正是這樣一種弱的普遍性,帶著啟示的信息,呼應著困境自身所無力承擔的探求,以詩的音節跌宕起伏凸顯,試圖開拓出當代詩的新圖景。而《神奇的事情》則如螢火蟲之光,如于貝爾曼所說,僅有征兆的、奇異的、碎片一般的閃光,但表現出某種苦弱的救贖之力,暗示著“扭轉”的潛在勢能,則對當代詩提出新的要求,展示了行動的詩之可能。本文以弱的普遍性為主題,通過細讀這兩首杰作,試圖探討當代詩歌的未來維度。
一
假如有人正好在你面前落水,
你伸手還是袖手?可能的選擇
與水性無關。或者你也落水
你幫助別人,將使你更快下沉;
你拒絕幫助別人,就有天使
從空中向你射箭。你要怎樣行動?
或者再換一種情形,你救自己
就拖別人的后腿,否則滅頂。
如何讀一首詩?如《天使之箭》所示,整首詩明亮、陡峭、崇高、決斷,周轉于明與滅、善與惡、虛無與實有之際,層層展開愛的火焰,變換著人的種種境遇,而指向了生活的根基。但是,詩中令人驚喜的“天使之箭”難道不是詩人的情感淤積而自我致幻的結果?或者,這首詩中無處不在的道德意識,不是已經在暗示我們,“天使之箭”乃是良知的代名詞?幫助他人,以自己的全部之力,甚至承受著滅頂之災,這難道不是和康德的道德律令一樣絕對、純形式一樣的要求?反復閱讀這首詩應該會知道,“天使之箭”、“別人”與“愛”構成了一組奇妙的聯合,搭建起支撐整首詩的拱頂,“別人”如列維納斯的“他者”一樣,作為赤裸的面孔開啟著人性的無限,在“落水”的虛弱中向“我”呈現,“愛”則同樣帶有列維納斯的意味,并非是自愛,而是轉向他人的愛,“愛,就是為他人而怕,就是對他人的虛弱施以援手”①。所以,詩人說:“這世界上,只有愛是一種發明,/教會我們選擇,創造人的生活。”
那么,“天使之箭”呢?這是超驗的意象與激進的想象,此乃是一切的重點。西渡的很多詩中其實遍布這種超驗的意象,這也正是令我欣喜的地方,如“迷津中的海棠”,涉險而來,“高舉落日之杯”(《迷津中的海棠》);“眾樹的合唱——那搖撼眾生的歌聲”(《花粉之傷》);“星空像天使的臉/燃燒,廣場頓時沸騰起來”(《消息——為林木而作》);“新來的神被釘上十字架,流遍天空的血,神的遺言”(《秋歌》);“在我們身上,正有一對新人/神秘地脫胎,向著亙古的新”(《喀納斯——致蔣浩》);等等,啟人深思。德布雷說:“如無超驗,則沒有真正的表達。好比沒有落差,則不能產生能量。”②在這個意義上,“天使之箭”所具有的超驗和崇高色彩與日常生活的庸常、封閉、陣痛形成了落差,所帶來的勢能動搖著經驗的邊界。我們所熟知的關于日常生活主題的詩歌,大半是反諷的、焦慮的、虛無的、懷疑的、經驗的、反崇高的、反超驗的,對應著時代的歷史狀況,彼得·布魯克的經驗,更準確地告訴了我們這一事實:“在這個時代,懷疑的、焦慮的、矛盾的、驚恐的戲劇似乎比指向崇高的戲劇更真實。”③也正是因為如此,“天使之箭”代表一種反向,以微弱的拯救色彩。
救自己還是救你的鄰人?
每天面臨著的選擇考驗著
脆弱的自我:所謂人的出生
也許就是被愛我們的所遺棄。
隨時可死,卻并非隨時可生,
就是這原因讓哈姆萊特的選擇
變得艱難。這暫時的血肉之軀
我們加倍愛它的易于隕滅。
與“天使之箭”、“別人”與“愛”這一組意象相對的是,“上帝”、“脆弱的自我”與“救”這三位一體的意象。“上帝”乃是被宣告死亡的那個上帝,無視時間里的苦難,這個“上帝”是現代性的永恒問題,任何一首現代詩都無法避免對這一問題的回應。在這首詩中,“上帝”明顯帶有“神義論”的色彩,而被置于理性的審查之下。“脆弱的自我”同樣的一個永恒的現代性問題,與“上帝”問題互為表里。正如帕斯卡爾的表述“自我是可恨的”,其所堅持的內在與超越都變得荒誕與無常,唯有在“新的光線”之中實現靈魂的轉向。在這首詩中,“脆弱的自我”則更加孤立置于生死的邊緣,短暫易于隕滅,因此,“救自己還是救你的鄰人?”這句詩中包含的洶涌音調震撼人心,催促我們轉向自身探望最真實的聲音,以此獲得行動的依據。
上帝并非善心的父母,置我們
于生死的刀刃,觀察我們受苦。
人間的情形從來不曾改善,
天神何嘗曾聽到你我的呼告?
魔鬼卻一再誘惑我們的本性。
活著,就是挑戰生存的意志;
這世界上,只有愛是一種發明
教會我們選擇,創造人的生活。
而這一切都建立在超驗的隱喻之上,秘密地運轉著啟示的真理,一旦強行翻譯成理性的語言,遵循章法分門別類,試圖在現實中尋找客觀對應物,就失效了。理性的語言毫無疑問正是強的普遍性,驅逐幻覺與內在的私密性,痛斥無法言說的沉默。這意味必須超越語言的事實層面而直接進入隱喻的啟示,必須警醒強的普遍性。在我們的時代,隨處可見的是強的普遍性,比如資本與技術的強普遍性,構建了日常生活的總體性架構;圖像與影音的強普遍性,定義了現實的呈現方式;權力與政治的強普遍性,塑造著歷史的格局與走向,諸如此類等等不一而足。一個人無法直接反抗這種強的邏輯,或者反抗則意味著與時代的脫鉤,而詩歌守護著弱的普遍性,在強的邏輯之外,以隱喻的計算法則。弱的普遍性,如詩中所寫:“上帝并非善心的父母,置我們/于生死的刀刃,觀察我們受苦。/人間的情形從來不曾改善,/天神何嘗曾聽到你我的呼告?”這是在宗教的強邏輯之外,來重新定義我們的處境,“生死的刀刃”,乃全然無救贖只有個體的幸存,萬物自行其是,自我解救,“呼告”乃全然的孤零零而無所依傍,個體唯一的依靠是與未來的角力,通過“愛”而創造“人的生活”,這是生存之弱,以最渺茫的希望,以微弱之力去穿越生存的閘門,弱乃是無力甚至無用的形象,格洛伊斯因而如此來定義這種弱普遍主義:“通過這種減法,前衛藝術家們開始創造出一種對他們來說似乎異常貧窮、軟弱、空無的形象,這種形象或許能夠在每一種可能的歷史性大災難中幸存下來。”④
我的討論借用了格洛伊斯的定義而試圖展開一首詩的普遍與絕對。《天使之箭》通過上述兩組意象的衍生、演化,蔓延著切入現實與歷史的契機,沖破時間的既定規則而重新定義時間。兩組意象之間的聯合與拆解,不斷地構造新的契機與向度,同時也試圖解散僵死與固化的關系,并依靠聲音、語調、節奏、韻律的變化與轉換,決定詞語與事物的先后順序、位置、方向與輕重緩急,進而奠定了這首詩的“理念”與普遍,這也正是一首詩的奧秘。
最后還是讓我們回到“天使之箭”這個意象,“你拒絕幫助別人,就有天使/從空中向你射箭”。這是個嶄新的意象,在已知與晦暗之間貢獻著未來的信息。需要強調的是,在格洛伊斯那里,“減法”所針對的是之前的藝術成規和法則,這也是一種強的普遍性,從強的普遍性中脫身、溢出,就是減法的要義,與德勒茲的“解域”同出一轍。“貧窮、軟弱、空無的形象”在另一個意義上意味著嶄新的形象,曾經與當下在一閃現中聚合而成的歷史意象,播散著拯救的韻律,比如本雅明的“星叢意象”。我們所熟知的《歷史哲學論綱》中的“天使”,啟用的正是這樣一種形象,在廢墟與未來之間,醞釀著某種轉機的出現。里爾克的《杜伊諾哀歌》中則遍布著這種天使的形象,他寫道:“愿有朝一日我在嚴酷審察的終結處/歡呼著頌揚著首肯的天使們。”里爾克自己對此的解釋是:“哀歌中的天使是那種受造物,在他的身上,我們所嘗試的從可見之物到不可見之物到轉化似乎已經完成。”⑤是的,無論是本雅明還是里爾克的天使,都已經脫離基督教的傳統形象,以嶄新的面目脫穎而出,但并不是最終的完成者,而是轉化者,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橋梁。“天使之箭”是決斷的,有它自己的衍生譜系,當代詩歌史里有一條關于“拯救”主題連續發展的線索,但至今并未得到很好的了解。海子和駱一禾均是這條線索上的重要節點,簡單來說就是,“天使之箭”是海子和駱一禾之后的一個發展。很多時候,我也正是這樣來理解西渡的詩,并企圖細致察看其“轉化者”的意象。
海德格爾1918年寫給伊麗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中寫道:“生活到底如何塑造,必然到來的生活。我們唯一的救助到底是什么,一切都不清楚。不過,有一點是確定而且不可動搖的,這就是對真正的精神的人生的追求,此時此刻不能怯懦,而是要親手把握決斷的領導不放,……只有那些內在貧乏的唯美主義者,以及一直以有才智的身份玩弄精神的人,他就像對待金錢和享樂一樣對待精神,才會在這個時候崩潰,根本不要指望從他們那里得到任何幫助和有價值的指示。”⑥關于這個問題,詩給出的答案是,堅守弱的普遍性并與歷史的意象對質,《天使之箭》是我多次回讀的一個文本,因為其本身關乎這個答案的來源。
二
人世間最神奇的事情乃是這些荒寒貧瘠的泥土,
轉眼被塑成觀世音菩薩的容顏,
在大殿里被供奉,被朝拜,
在病痛者、困苦者、虔誠者的夢里出現。
昨天,它還是平凡的泥土,
坎坷、灰暗,在耕耘者的腳下……
——《神奇的事情》⑦
與西渡的《天使之箭》相似,這首短詩的基調崇高而決斷、素樸而有力,化具象為抽象,將一個日常經驗轉化為某種衡量現實的法則。這種轉化乃是詩的基本運作機制,也就是卡夫卡所說的:“只有當我將這個世界提升到一個純粹、真實、不變的境地,這種幸運才會降臨。”⑧進一步講,詩的普遍原理并不是所謂的再現或表現,也不能被單純定義為創造,而是轉化,通過締造某種詩歌函數將聲音轉化為韻律,將雜多歷史經驗轉化為純粹的真實,將過去轉化為未來的期待,將微弱的、渺茫的轉化為某種至高無上。海德格爾的一個著名說法是:“眾所周知,一首詩就是創造。甚至看來是描述的地方,詩也在創造。”⑨可以說這個表述將詩理解為某種轉化但并不全面,因為轉化既是轉變、轉向、運轉、扭轉,也是生產、制作、制造、創造,也是誕生、生成、復活與拯救,這一過程猶如暗箱,能夠看見的一邊是經驗,另一邊是詩。詩人楊牧說:“我們化具象為抽象,因為具象有它的限制,而抽象普遍——我們追求的是詩的普遍真理。”⑩同樣是談論轉化的機制,著眼于可見與不可見的換算,更為重要的是,楊牧指出這一轉化機制就是詩的真理,通過這一機制,世界從散文的世界轉變為真與美的不平凡的詩之世界,給予人度量自身的尺度。《神奇的事情》的主題正是這種轉化。
通過細讀可以看到這首詩包含了三重轉化。第一重轉化,從泥土到觀音的轉化,如詩人所寫,荒寒貧瘠的泥土,如此之微不足道,平凡無用,甚至被踐踏漠視,但竟然可以被轉化為觀世音菩薩,供人供奉膜拜寄托許愿,而無從察覺觀音的容顏從泥土而來,這一無覺察使得虔敬的信徒和困苦的求拜者得以安慰。這種具象與抽象的轉化方式是楊鍵比較典型的寫法,比如“當不幸,終于把我變成屋頂上的炊煙……”(《通向山上的石子路》)“我的心里是世界永久的寂靜,/透徹,一眼見底,/化為蜿蜒的群山,靜水深流的長河。”(《這里》)“一對戀人像老首老歌,/相依在古橋上。”(《在橋上》)“他的形體在消融。/他要把自己縮小到一朵小花里,/一堵墻邊的小花里。”(《在公園里》)“冬天,/人世凝成了/鵪鶉的瑟縮模樣。”(《冬天》)通過經驗的提煉和情感的躍遷,這一轉化帶來了新的感知和視野,將現實和歷史暫時懸置,為一種將來者打開空間,此乃是詩之真理的第一層顯現。
第二重轉化是一種弱被轉化為至高無上,詩人將此稱為“人世間最神奇的事情”,簡直是不可能的可能,因為灰暗而平凡的泥土是如此之弱,無可再弱,是一種苦弱,一種本不可能成為“強”的弱,但通過某種不可測的法則實現了轉化,從而連通了虛無與實有、虛構與現實、當下與歷史。也就是通過這一轉化,詩為現實提供了法則來矯正現實,盡管只是一種弱的普遍性,但卻持續地轉化著,以等待一個“扭轉”的實現,比如楊鍵的其他詩句:“湖面上的早晨之光,/仿佛萬物的根源。在我們的頭腦里/映現著冷杉高聳的德行。”(《高聳的德行》)“一縷殘陽,猶如受難者/臨近解放的淚滴。”(《香椿樹》)“從今往后,/迅捷的水鳥,/混合在蒼穹的光里,/變成遙遠的鐘聲。”(《述懷》)“哭泣,/把我變成萬物里一條清涼的小河,/一道清爽的山坡。”(《哭泣》)“如果我不能成為光,/一切,就是我的心絞痛。”(《獅子橋》)“在冬日荒漠一樣的土地上,/他們如同兩粒讓人警醒的麥種。”(《記憶》)此乃是詩之真理的第二層顯現,事物顯現出其普遍性的面貌,溝通著當下與未來,賦予現實與歷史以法則。
第三重轉化就是轉化本身,也就是這首詩的轉化機制被同時書寫出來,“泥土”與“觀音”、“貧瘠”與“豐饒”、“困苦”與“神奇”的轉化方式如同一個范式被展示出來,這些意象可以被替換、更新與升級,比如替換為“詞語”與“新生”等。事實上,這首詩的轉化機制即在于“柔弱”與“挽救”通過“神奇力量”的過渡,而這就是詩之真理的第三層顯現,也就是詩的核心無論如何都是對經驗、歷史、事物、事件的挽救,正如楊鍵在另一首詩中通過喇叭花而得到的啟示。
那么柔弱,有一種不為人知的挽救。
清寒之家,
庭院冷落。
誰也不知道我從這里汲取了什么神奇的力量。
——《陌生人墻上的喇叭花》
這首詩與《神奇的事情》一脈相承而有所拓展,主題和風格都一貫顯示出“崇高性”。所謂崇高在于通過某種痛苦經驗的轉化而得來的情感意識,這種意識朝向生命真實而超越的一面以尋求更高力量的援助。“柔弱”、“挽救”與“神奇”這一組關鍵詞,通過“奇異的崇高性”表達了詩的弱普遍性。哈羅德·布魯姆將此表述為“重生的感覺”,人經由這種重生感而成為詩人,詩人經由重生感而獲得詩的真理。
楊鍵的作品中,除“柔弱”這一主題外,“哭泣”與“淚水”這樣的意象,也是非常重要的“弱”的主題,比如,“哭泣,是為了挽回光輝,為了河邊赤條條的小男孩,/他滿臉的泥巴在歡笑,在逼近我們百感交集的心靈”(《啊,國度》),“哭泣”作為一種軟弱,并不在于所謂的“凈化”,而是“挽回”,就像未曾遭受損壞一樣,就像可以回到原初一樣。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這首詩素樸而崇高的風格,語言簡潔、直接、單純、赤裸,直取事物的核心,通過某種移情和共振去打動人心。按照席勒所言,素樸而崇高的詩,往往是詩人與自然和諧一體,詩人為遭遇的事物所感動,因而他的作品能夠直接傳達,無須反思迂回,但往往具有被動性。荷爾德林發展了席勒這一命題,并不將素樸的詩局限為古代的詩,而是將其視為高超詩藝的表現,并帶來一種深不可測的沉思:“簡潔是眾所公認的崇高的標志。‘上帝說要有光,于是就有光’——這句話被認為是高超詩藝的頂峰。在感覺到它的瞬間,對于我們是深不可測的東西,或者覺察它的剎那間,心靈對于其邊界沒有明確觀念的東西,我們稱所有這些為崇高的。”透過荷爾德林,這首詩素樸而崇高的風格所帶有的弱普遍性被揭示出來,語言使事物和真理無遮蔽地呈現。
三
除詩歌書寫之外,關于詩的弱的普遍性觀念,當代詩人早有探討,以此應對當代詩的困境。但并未形成有效的、可持續探究的詩學命題,因而值得進一步展開。楊鍵的詩學短文《詩人之弱》最具有代表性,直接而具體地探討了弱普遍性的當下含義,他的結論是:“詩人之弱正是詩人之強。”從而挖掘出了弱普遍性的救贖層面,具體的含義可類比于本雅明的“苦弱的彌賽亞之力”以及喬治·迪迪-于貝爾曼《螢火蟲的殘存》中所寄希望的微弱光亮。在此之前,肖開愚的訪談《詩在弱的一面》已提出了這個問題,但沒有展開。肖開愚認為,詩歌“比任何時候都獨立、孤立。獨立是現代詩人和現代詩的先決條件。不做官、不能做官,是幫助詩人和詩真正、卓然地獨立的偉大改變”。與格洛伊斯的表述基本一致,將其置于強普遍性的對立面來思考。更早之前,葉嘉瑩從古典詩詞中提煉出“弱德之美”,對于困境中的當代詩頗有啟發意義:“這種美感所具含的,乃是在強大的外勢壓力下所表現的不得不采取約束和收斂的一種屬于隱曲之姿態的美。如此我們再反觀前代詞人之作,我們就會發現,凡被詞評家們所稱述為‘低徊要眇’‘沉郁頓挫’‘幽約怨悱’的好詞,其美感之品質原來都是屬于一種‘弱德之美’……就是豪放詞人蘇軾在‘天風海雨’中所蘊含的‘幽咽怨斷之音’,以及辛棄疾在豪健中所蘊含的沉郁悲涼之慨,究其實也同是屬于在外界環境的強勢壓力下,乃不得不將其‘難言之處’變化出之的一種‘弱德之美’的表現。”“弱德之美”所具有的普遍性在于將生命美學化,將難言和無言轉化為詩的永恒性,以抵抗強普遍性的專斷。
楊鍵的《詩人之弱》是對葉嘉瑩的發展,他開篇就宣稱李白的《玉階怨》是抵抗之詩,并宣稱“抵抗也要優美柔弱地抵抗”。這正是“弱德之美”。以內在的真實性,以詩性的超越性,以潛在的生成性來抵抗。所謂“柔弱”意味著即使抵抗也會遭遇失敗。詩在我們這個時代被動地成為柔弱的,因為在現代世界作為人性基礎的自然被“丑陋的機器”毀壞,扼殺心靈和人性的事物比比皆是,對美漠視的靈魂自然也敵視詩歌,也就是史蒂文斯所說的“所有偉大的事物都被否定”。楊鍵因此贊美乾隆對英國喬治三世國王要求通商的拒絕,將此行為詩意化,認為是對即將開始的全球化浪潮的抵抗。“西方的算計被乾隆非常尊嚴而又很有禮儀地拒絕。我甚至覺得這篇文章應當選入中學課本,以增國人之信心。但是乾隆的話在今天看來已是如此可笑,我們今天已如此西化。”正是在這樣的邏輯下,楊鍵提出了詩的弱普遍性的核心觀點:
詩在今天如此之弱,但它不僅是撫慰和故園,也可以證明在心靈大面積死亡的狀況下,我們還是一個幸存者。
雖然詩人的文字之箭剛一射出即開始減速、生銹,未到中途即已墜地腐爛。毀壞文字力量的外在因素太多了,詩人奮力想要達到的美以及善,早已不是民眾的目標。詩人已如此軟弱,他因被駁為毫無依據者而被棄置一邊,他已如此貧瘠、如此空洞,愿望卻如此之大之強烈:我們不愿意變成沙漠。
在楊鍵看來,詩的衰弱對于大眾來說,是詩之真理的不顯,詩變得無用甚至空洞貧瘠。但對于真正的詩人來說,詩的衰弱反而是在向我們證明,我們是一個偉大傳統的幸存者。這個傳統并未斷絕,而是在真正的詩人身上繼續存在,盡管是隱而不顯的。或者說,詩的判斷力和審美光芒在向我們證明,我們是保有完整心靈的幸存者,盡管詩人在我們的時代無法創造偉大的詩歌。現代化的浪潮將一切堅固的連根拔起,劫掠人的精神世界使其赤貧,詩人可以堅守而不被“沙漠化”。
“幸存者”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不僅是對于楊鍵,對于整個20世紀詩歌都是如此。“幸存者”與“將來者”(海德格爾)、“受難者”(施米特)、“守護者”(阿蘭·巴迪歐)、“見證者”(米沃什)、“扭轉者”(詹尼·瓦蒂莫)、“轉化者”(里爾克)等概念具有相似的含義,共同表達了詩的弱普遍性含義,即在否定中堅守某種不可能的可能性。阿蘭·巴迪歐對曼德爾施塔姆的解讀,將此種邏輯表達得極為清晰:“在對馬拉美的承襲中,20世紀建立了另一種形象,詩人成了失落的思想的殘余物。在語言中,詩人是一個對遺忘的開端的保衛者;用海德格爾的話說,詩人是‘開敞的守護者’。”詩人守護著一個在現代世界搖搖欲墜的古老傳統,并試圖以新的歷史契機來開啟另一個通往新世界的開端。所謂否定,即是現代世界的強普遍性,科學的、經濟的、技術的、政治的等等對詩的否定,詩也否定一個物質的、欲望的、逐利的、去精神化的盲目當下世界。
如此看來,楊鍵的《詩人之弱》與里爾克《穆佐書簡》中的一段文字有著相似的邏輯和表述,兩者的核心觀點是一致的,即詩的弱普遍性,對照來看則易于展開其中豐富的含義。
如今,空洞的無足輕重的事物從美國涌來,虛假的事物,生活的贗品……被賦予生命的、被經歷的、同樣熟悉我們的事物即將耗蝕一空,再也不能被置換。我們也許是還了解這些事物的最后一代人。我們肩負著責任,不單單保持對它們的懷念(這恐怕不夠,況且靠不住),而且保持它們的人文價值和守護神的價值。(家神意義上的“守護神”。)大地再也沒有別的避難所,除了變為不可見的:在我們心中——正是我們以自己的本質的一部分參與了不可見之物,我們(至少)具備分有它的憑證,當我們在此期間,我們能夠拓展我們所擁有的不可見性;只有在我們心中才可能實施這種親密的持續的轉化,即把可見之物轉變為不可見之物,后者不再依附于可見與可即的此在,一如我們自己的命運在我們心中變得既更實在又不可見。
此段文字中主旨見于“耗蝕”“守護”“轉變”三個關鍵詞,這正是《杜伊諾哀歌》的核心主題,所謂“耗蝕”是現代世界的物化邏輯對生命內在靈性的損耗和銷蝕。生命被計算、量化、資本化、政治化,生命超越性維度被虛無化,真實的事物隱而不見,而所謂的虛假和贗品,幻象與擬像成為現實的原則,置換著可見與不可見的比例,大地滿是“苦難國土的星群”。然而,“守護”意味著期待,等待有朝一日的將來“一個幸運降臨”,正如第九首哀歌所寫:“事物日益消逝,/而強迫替代/它們的,則是一樁沒有形象的作為。/是表皮下的作為,一旦行動從內部生長出來/并呈現另樣的輪廓,它隨時欣然粉碎。”“守護”因而是對過去某種詩性殘余和遙遠記憶的守護,這記憶當中存儲著未來。詩人的“通感”能力對記憶和遙遠顯示的傾聽,使這一切變得可能,“記憶因為它擁有當下,就會變為未來。從那時起,保存記憶就是詩人的職責”。伽達默爾的觀點與阿蘭·巴迪歐非常接近,詩人在20世紀的使命是堅守詩性的記憶,以抵抗誤入歧途的現實,“這就是詩人的使命:他是這個時代的領唱者。他唱出未來將要出現的東西。記憶演變成期待,保存演變成希冀”。里爾克以詩句表達了同樣的含義:“你走過打開的窗前,/有一柄提琴在傾心相許。這一切就是使命。”“轉變”,此乃是將可見轉變為不可見,第六首哀歌承擔著這一主題:“未經夸耀,就將你純粹的秘密/催入了及時決定的果實。/像噴泉的水管你彎曲的枝椏/把汁液驅下又驅上:它從睡眠中/幾乎還未醒來,就躍入其最甜蜜成就的幸福。/看哪,就像大神變成了天鵝。”將純粹的秘密注入無花果,宙斯變成天鵝,都改變了事物的形態,事物被賦予了精神的灌注,因而不再是其本身而變得不可見,這意味也就是在危險之中實現了“扭轉”,正如本雅明的“寓言”概念所論證的,過去的記憶通過不斷的重復而顯示為神跡。
四
扭轉就是拯救。荷爾德林《帕特默斯》中的詩句:“但有危險的地方,也有/拯救生長。”(林克譯)深刻講述了這種扭轉的邏輯與含義,此乃是詩的弱普遍性的核心和主旨。楊鍵所謂的“詩人之弱正是詩人之強”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有價值,因為詩的未來性,“弱”真實地蘊含著扭轉“強”的隱藏力量。海德格爾《技術的本質》《轉向》等文章多次引用荷爾德林的那句詩,構造了危險與拯救的歷史關聯,“危險乃是救渡,因為它從其隱而不顯的轉向性本質中帶來了救渡”。通過荷爾德林,海德格爾更為深刻地表達了詩的弱普遍性:“這個時代是貧困的時代,因此,這個時代的詩人是極其富有的——詩人是如此富有aHmgaXZ8drZIFUqE7K8Kr6PXXI603QSwhcxGlks3iMI=,以至于他往往倦于對曾在者之思想和對到來者之期候,只是想沉睡于這種表面的空虛中。然而詩人堅持在這黑夜的虛無之中。由于詩人如此這般獨自保持在對他的使命的極度孤立中,他就代表性地因而真正地為他的民族謀求真理。”此闡述也揭示了詩之真理就在于堅守某種未來性。時代的貧困顯示出歷史之急難,詩人的富有不僅在于對遙遠記憶的呼應,而且能夠真正進入到世界之黑夜。因為時代的貧困是人們并不能知道其貧困,進入世界黑夜的詩人,能夠知道世界喪失其根基而立于深淵之中,他由此才能真正地為他的民族謀求真理。弱的普遍性的實現就是詩之真理的實現,《詩人何為?》在這一意義上對我們構成啟發,追究“詩歌何用?”在何種意義上寄希望于“苦弱的彌賽亞之力”或者本雅明在超現實主義者那里獲得的“世俗啟迪”。
比較里爾克的“耗蝕”“守護”“轉變”,海德格爾“急難”“回響”“扭轉”三個概念與之有共同的思想含義,而將20世紀問題化為虛無主義時代。與“耗蝕”相似,所謂“急難”就是不知其時代貧困的“貧困”,就是“存在之離棄狀態”,就是集置的偽置,“首先必須開啟一種急難,在其中,并非始終只有存在者是可疑可問的,而且存在也將變得大可追問”。急難中,存在者以及存在者的依據都是懸置的,一種拒不給出、拒不回答的急迫顯示出具有優先地位的統治阻礙著現實與歷史。“回響”則是對“存在之離棄狀態”的否定,是對存在的思念。《詩人的獨特性》中,海德格爾寫道:“這樣思念著,我們轉向一種記念(Gedaechtnis),它記念那在詩化及思化之道說(dichtenden-denkenden Sage)中向人訴說的和被遺贈(vermacht ist)給人的東西。在這樣的記念中,對于人的本性的最高規定成為現實,因為這規定是從存在本身(Seyn selbst)的深處被奉獻給這記念的。”詩性記憶通過這種思念被激活,更高的規定性通過某種饋贈涌現出來,“通過一種回憶使這種被遺忘狀態作為在其隱蔽強力中的遺忘狀態顯露出來,其中就有存有之回響。對急難的承認”。“扭轉”也是將可見變為不可見,與里爾克使用的“催入”不同,海德格爾的“扭轉”是通過“閃入”來實現,“在被遺忘狀態自行轉向之際,在世界作為存在之本質的守護轉投而出現之際,便發生世界向物之荒蕪的閃入(Einblitz)。這種荒蕪乃是以集置之統治地位的方式而發生。世界向集置的閃入,就是存在之真理向失真的(wahrlose)存在的閃入。閃入是在存在本身中的本有(Ereignis)。本有乃是有所居有的洞見(eignende Er?ugnis)”。
海德格爾因此也啟發了詹尼·瓦蒂莫提出“微弱的思想”,一種弱的力量,一種削弱和弱化,以及弱的扭轉。瓦蒂莫認為,藝術的沒落與邊緣是形而上學終結或者說上帝之死的一個后果,而并非是藝術本身或自然而然的問題。值得重視的是,這種沒落是一種信號,因而構成一個事件與歷史角力,瓦蒂莫因此說:“它是一種事件,一種構成我們在其中運動的歷史和本體論之星座的事件。這個星座是歷史和文化事件之網和從屬于它們、并且同時描述和共同決定了它們詞語之網,就其是我們命中注定的東西這個歷史意義上講,藝術死亡與我們有關,而且是我們不簡單忽視的某種東西。”也就是,此種沒落和衰敗孕育著扭轉并因此帶來新的未來,“藝術的衰退是更加普遍的形而上學終結情境中的一個層面,在這種情境中,思想被召喚去實施形而上學的‘扭轉’”。
與瓦蒂莫類似,約翰·卡普托同樣提出了一種弱的思想,他將之命名為“苦弱的神學”。一種苦弱的神學對應的是強力神學,是通過德里達和本雅明將保羅的思想系統化和激進化。卡普托對此的表述是:“瓦蒂莫是第一個使用苦弱這個修辭的人,而我本人最初采用苦弱這個語詞是來自德里達提及的本雅明的‘苦弱的彌賽亞之力’,而如果回過頭來看,吸引我注意到是圣保羅,因為在他看來‘上帝的苦弱’,使世界的力量遭受挫敗(林前1∶25),苦弱的思想不再求助根本的形而上學作為支持。取消形而上的根基,使其衰弱,意味著形而上力量的萎縮,因而,思考由它自身的力量來驅動——這即是去解釋。”解釋就是去使事物松綁脫困,就是試圖走向開放性的播散倫理學,就是對“強”的解構,使其衰弱,“非作”,停止運轉,如卡爾·巴特,真理只在現存真理被否定時才有可能。在這個意義上,苦弱的神學乃是一種詩學,憑借的是語言的運作,而不是先驗原則。也就是所謂語言的運作并不是重復,按照既定規則的演繹,實際上語言的每一次運作都變成了一架新的機器。詩歌語言尤其如此,每一首詩都意味著語言的重新展開。卡普托因此強調:“苦弱的神學不再尋求思索性—形而上學的支持與超自然的保證,具有反叛性的苦弱神學是一種詩學,它沒有進一步的偽裝——這樣的詩學匯集了隱喻和轉喻,修辭性的轉義與意想不到的語言學轉向,充斥著敘事學、寓言,它日積月累,以語言的方式對一種根本性的生命形式進行表達。”與強力神學不同的是,苦弱神學懸置了超驗與上帝,只保留了上帝之名,以期待一種不可能性的可能。也就是所謂事件的發生,例外或奇跡的降臨,事件即扭轉,“苦弱的神學意味著敢于將上帝懸置起來支持事件,敢于閱讀事件的蹤跡,傾聽召喚的回聲”。這樣,通過呼求和召喚,重復的遞歸,蹤跡的捕捉,生命的強度,將未來作為一個幻象來實現。“弱”在此意味著不可能性,現實中的不可能,因為現實被強普遍性把持守護著,弱的普遍性也就在不可能性的可能,也就是卡普托著重強調的:“所有的事物只有憑借不可能才成為可能。”這一命題是他所有著作的出發點。
關于弱的普遍性,喬治·迪迪-于貝爾曼延續著海德格爾、本雅明、瓦爾堡等人的思考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命題:“螢火蟲的殘存。”螢火蟲雖然微弱,但確實在改變著什么,尤其是在漆黑的夜晚,對于渴望一絲光亮的人來說無異于拯救,尤其是在現代世界,螢火蟲在耀眼的燈光下根本無法顯現,而且面臨著某種滅絕。所謂的“殘存”不僅在于一種過去的存留,而且是帶有某種啟示和拯救的殘存,“這個問題是重要的,毫無疑問也是復雜的。因此,沒有教條的答案可以獲取,我是說,沒有一般性的、根本性的、總體性的答案。僅僅有征兆的、奇異的、碎片——短暫、微弱的閃光。螢火蟲,是我們當前僅能使用的表達”。于貝爾曼對但丁《神曲·地獄篇》第26章中的“螢火蟲之光”的闡釋,更真實地說明了這一切。
在天下的照明者最少隱沒,
把容顏展露得最明顯的季節,
當蒼蠅飛退,蚊子逐漸增多,
一個農夫,要是在山上停歇,
會看山谷里——也許就是他墾土壤、
采葡萄的地方——螢火蟲時明時滅。
當第八個深坑的谷底在望,
只見全坑閃爍著火焰,數目
之伙,和農夫眼中的螢火蟲相當。
如但丁所寫,作為“殘存”的螢火蟲之光將隱藏的事物展露,并標示出不同的方位和某種未言明的癥候、姿態、欲望和深度。“時明時滅”意味著某種循環的反復,在剎那間被辨認捕捉,與“谷底”中的火焰構成某種辯證,深層的歷史時間藏匿于其中,懸置于過去與未來之間的虛線被連接,并不斷釋放出未來的信息。與約翰·卡普托的通過不可能而成為可能一樣,這預示著某種未來詩學的方向,當代詩中遍布著這樣的螢火蟲之光,需要被挖掘和捕捉,但首先需要轉換我們的歷史意識,也就是那種二元論表征模式所確認的線性歷史意識,從而使得弱的普遍性得以顯明。
【注釋】
①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朱剛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第246頁。
②雷吉斯·德布雷:《圖像的生與死》,黃迅余、黃建華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第42頁。
③彼得·布魯克:《空的空間》,王翀譯,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9,第49頁。
④格洛伊斯:《走向公眾》,蘇偉、李同良等譯,金城出版社,2012,第139頁。
⑤里爾克:《穆佐書簡——里爾克晚期書信集》,林克、袁洪敏譯,華夏出版社,2012,第216、215-216頁。
⑥呂迪格爾·薩弗蘭斯基:《來自德國的大師——海德格爾和他的時代》,靳希平譯,商務印書館,2007,第116-117頁。
⑦楊鍵:《古橋頭》,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第327頁,本文所引用楊鍵詩句均是出自此書。
⑧卡夫卡:《卡夫卡日記:1914—1923》,鄒露譯,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20,第168頁。
⑨海德格爾:《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1999,第8頁。
⑩楊牧:《詩與真實》,載《一首詩的完成》,臺北洪范書店,2020,第211-212頁。
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剖析:文學作為生活方式》,金雯譯,譯林出版社,2016,第5頁。
荷爾德林:《荷爾德林文集》,戴暉譯,商務印書館,2003,第160頁。
凌越:《詩在弱的一面——肖開愚訪談》,《書城》2004年第2期。
葉嘉瑩:《清詞叢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59-60頁。
楊鍵:《詩人之弱》,載譚克修主編《明天(第5卷)·中國地方主義詩群大展專號》,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第135、136頁。
阿蘭·巴迪歐:《世紀》,藍江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第24頁。
里爾克:《杜伊諾哀歌》,載《里爾克詩選》,綠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第476、433、460頁。
伽達默爾:《荷爾德林與古希臘》,載《美學與詩學:詮釋學的實施》,吳建廣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第15頁。
伽達默爾:《荷爾德林與未來》,載《美學與詩學:詮釋學的實施》,吳建廣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第26頁。
海德格爾:《同一與差異》,孫周興、陳小文、余明鋒譯,商務印書館,2011,第114、116頁。
海德格爾:《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2014,商務印書館,第52頁。
海德格爾:《柏拉圖的真理學說》,載《路標》,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14,第276頁。
轉引自張祥龍:《海德格爾論老子與荷爾德林的思想獨特性——對一份新發表文獻的分析》,載《思想避難:全球化中的中國古代哲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第319頁。
海德格爾:《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12,第113頁。
詹尼·瓦蒂莫:《現代性的終結——虛無主義與后現代文化詮釋學》,李建盛譯,商務印書館,2013,第102、114頁。
約翰·卡普托:《上帝的苦弱:一個事件的神學》,芮欣譯,橄欖出版有限公司,2017,中譯本作者序xiv、xvi、xvii,第179頁。
Georges Didi-Huberman translated by Lia swope mitchell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9,p.19.
但丁:《神曲·地獄篇》,黃國彬譯注,海南出版社,2021,第454-4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