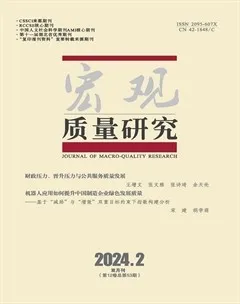財政壓力、晉升壓力與公共服務質量發展
王增文 張文雅 張詩琦 余天倫



摘 要:公共服務質量是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條件和重要保障。中國式分權下,財政收支壓力和官員政治晉升壓力深刻影響著公共服務質量發展,但關于三者的關系并沒有達成共識。鑒于此,利用2011—2019年中國285個城市的面板數據,實證考察財政壓力、晉升壓力以及兩者交互關系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研究發現:財政壓力與地方公共服務質量間呈“倒U”形關系;基于政治激勵視角發現,現有綜合考核體制下,晉升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有顯著正向影響;在共同作用于公共服務質量的過程中,財政壓力先強化后削弱了晉升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促進效應。綜上所述,為推動我國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一方面,應從“開源”和“節流”兩方面釋放地方財政壓力,強化民生服務保障的責任;另一方面,厘清央地責任劃分,對不同公共服務項目采取差別式考核標準和策略,引導形成綜合有效、科學的政績考核機制。
關鍵詞:公共服務質量;財政壓力;晉升壓力;熵權法
一、引言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引領下,國家持續增進民生福祉,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十四五”公共服務規劃》將“健全國家公共服務制度體系、補齊基本公共服務短板、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作為主要目標任務,并強調要“突出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保障中的主體地位”。在此背景下,逐步提升公共服務質量成為現階段增進人民福祉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現實選擇。
基本公共服務的性質決定了其主要供給責任應由政府承擔,因此,公共服務質量的發展受國家固有的財政體制和官員晉升制度的影響。作為我國頂層制度設計的具體體現,一方面,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逐漸形成了“財權集中、事權下放”的中國式分權體制,地方政府主要依靠有限的財政收入推進和改善公共服務質量;另一方面,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逐漸形成一種經濟激勵和政治激勵相結合的官員晉升制度,高質量發展要求下,地方政府承擔著“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保民生”等多重目標任務。隨著黨中央、國務院對民生問題的愈加重視,各級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逐漸將財政支出結構向醫療、就業等民生領域傾斜。那么,當地方政府面臨財政壓力與晉升壓力時,如何進行多目標治理?這種行為會對公共服務質量有何影響?此外,在我國具體情境下,“中國式財政聯邦主義”與“官員晉升錦標賽”往往同時作用于民生領域,兩者是否會產生某種交互機制進而影響公共服務質量?這是本文重點關注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有助于為探索地方驅動經濟與民生良性發展的可行路徑提供依據,進而為規范政府財政收支行為、優化支出結構以及保障公共服務質量提供有針對性的理論拓展和經驗參考。
既有文獻圍繞公共服務已進行了較多探討,無論在學理層面還是在經驗層面都對公共服務體系的研究有所推進,與本文相關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財稅體制對公共服務的影響效應。以中國式財政聯邦主義為代表,該觀點認為分稅制改革背景下,地方享有的財政收入成為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內在激勵(Montinola等,1995),但與此同時,財權與事權的不匹配給地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財政壓力。國內多大數研究表明,在我國財政壓力的約束下,地方政府傾向于削減教育、醫療衛生以及社會保障與就業等民生支出(吳敏和周黎安,2020;左翔等,2011),從總量上縮小公共服務供給的規模,優先發展高稅收行業(陳曉光,2016)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以緩解財政壓力。但隨著我國公共服務供給目標從“規模”向“質量”轉變,財政壓力與公共服務供給背后的關聯發生了新的變化。陳碩(2010)利用省級面板數據研究表明,財政分權反而有助于改善地方公共品的供給水平。
二是晉升制度對公共服務的影響效應。最具代表性的是“晉升錦標賽”理論,該理論認為中國存在一種“以經濟績效為核心”的官員晉升激勵制度(Li和Zhou,2005),地方政府為發展地區經濟以及獲得短期任職內的政治晉升,傾向于將有限的財力投向經濟性領域,而非見效慢的公共服務領域(胡玉杰和彭徽,2020)。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環境、條件、任務和要求的變化,學者們開始對“晉升錦標賽”的作用程度提出質疑。唐睿和劉紅芹(2012)認為政府考核目標多元化,GDP并不是唯一指標;朱建軍和張蕊研究(2016)發現,黨的十八大以來,民生、安全、環保和地方民意支持(汪立鑫等,2010)等要素被視為上級政府對地方官員考核的重要依據。
三是公共服務質量方面的研究。關于公共服務質量的研究主要圍繞三個方面展開:其一,基于公共服務質量概念,構建多維度公共服務質量指標體系,如謝星泉(2018)從過程、要素、功能和作用四個支點搭建基本公共服務質量的評價框架;鄧悅(2014)從總體形象、質量投入、質量信息提供、質量安全預警、消費者環境創造、消費者教育與救濟六個方面設計質量公共服務評價體系。在此基礎上,有學者利用熵權法、主成分分析法與DEA模型等綜合測度地區公共服務質量(史衛東和趙林,2015;趙晏等,2011)。其二,利用省際層面或地市級層面的數據測度某一維度或者特定群體的公共服務質量,如劉瓊等人(2021)以中國30個省份2008—2017年的面板數據為基礎,測評科技公共服務質量對區域創新水平的影響;王成和丁社教(2018)則針對政府購買居家養老服務展開質量評價。其三,采用理論闡述、案例研究、對比分析等定性方法,總結公共服務質量的政策變遷與發展邏輯(翁列恩和胡稅根,2021),探索面向未來的公共服務質量改進的新范式(蘭旭凌和范逢春,2019;楊鈺,2020)。
綜上所述,既有關于財政壓力、晉升壓力與公共服務質量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但仍存在繼續研究的空間。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
第一,現有關于公共服務質量指標體系構建的內容及方法已較為成熟,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將“萬人出租汽車數”補充納入到交通維度,將“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率”與“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補充納入到環境維度,從而構建出一套覆蓋教育、醫療、環境、文化與交通的綜合性公共服務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同時采用熵權法合成285個城市的公共服務質量指數。
第二,既有研究側重于對財政分權與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線性關系的探討,未能充分根據民生供給政策目標的變化考慮現階段公共服務支出具有剛性這一特征,故現有研究結論存在一定爭議。對此,本文首先厘清不同時期我國政績考核目標任務的演變邏輯,在此基礎上,依據目標任務變化情況實證考察財政壓力與公共服務質量之間的動態關系。
第三,大多數文獻僅單獨分析財政壓力或者晉升壓力對公共服務的影響,較少將三者納入統一體系中進行系統研究,更多研究集中在對其中兩者之間關系的探討,或是以公共服務某一細分領域,如醫療衛生、環境治理、成果分配、住房保障等為論述靶向。本文將財政壓力、晉升壓力與公共服務質量納入同一分析框架,將多維度與多領域的綜合性公共服務質量作為研究靶向,除檢驗不同壓力源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實際影響效應外,還揭示兩者的交互機制在公共服務質量領域的作用效果。
第四,從方法層面來看,現有研究多使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對財政壓力,晉升壓力與公共服務質量間的關系進行探討,而采用系統GMM以解決模型的內生性問題。考慮到公共服務質量具有一定的遞延效應,且使用系統GMM方法雖可修正未觀察到的遺漏變量偏差、測量誤差以及潛在的內生性問題,但難以解決雙向因果帶來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選擇使用系統GMM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效應進行實證分析,同時,試圖尋找工具變量并利用2SLS進一步排除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關系。
后文具體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第三部分為研究設計,對主要變量和數據來源進行解釋和說明;第四部分為實證結果分析;第五部分為結論與政策啟示。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政績考核目標任務的演變邏輯
20世紀80年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掀起了地方圍繞GDP增長展開“晉升錦標賽”的熱潮,對經濟績效的考核導致地方官員重視經濟增長,忽視對民生發展的投入。進入21世紀,繼科學發展觀提出后,中央對地方的績效考核內容試圖在經濟增長和民生發展間尋求平衡,為此,地方政府積極、主動開展公共服務質量評價活動,重塑公共服務的目標責任。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將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完善公共財政制度的目標。“十一五”之后,隨著財政投入的持續增加,我國基本公共服務的制度框架已初步形成。隨后政府針對保障和改善民生出臺了系列規劃和文件,引導財政資源向民生領域持續投入(姜曉萍和吳寶家,2022),以努力提升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和均等化程度。如圖1所示,2011—2019年,我國民生領域的財政支出只增不減,各領域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穩中有增,其中,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以及環境保護領域的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年均增速分別達到3.1%、3.36%和4.09%,遠高于其他民生領域。在此之后,中央對地方的實績考核越來越強調民生保障,關注高質量發展綜合績效2020年11月,中組部印發《關于改進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政績考核的通知》,強調要把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為評判領導干部推動高質量發展政績的重要標準。。可見,中央會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調控政績考核目標,而地方有較強的動力圍繞中央設定的考核指標展開治理與競爭(姚洋和張牧揚,2013),這直接決定了地方應對不同領域工作任務的優先緩急次序。
(二)財政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
根據財政聯邦制理論,地方政府追求整體財政收入最大化,或者地方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林毅夫和劉志強,2000)。在此目標下,財政聯邦考察的是包括地方一把手和其他官員在內的集體決策,追求地方政府整體的利益與發展。由于地市級領導平均任期為3—5年,流動性較強,不可避免地會存在“機會主義”傾向,而其他官員大多在當地長期任職,自身利益與地方長期發展有關,更關注長遠利益(劉紅芹和耿曙,2023),故集體決策使得地方領導的機會主義行為受到一定約束,地方政府在追求財政收入可持續的過程中,不至于過分短視,自然會考慮到短期利益與長期發展的平衡(Ji等,2005;張晏和龔六堂,2005)。
具體而言,在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地方政府通過合理配置財政資源以優化整合公共服務質量。隨著財政壓力的增加,一方面,地方政府可能會通過借助轉移支付等形式統籌協調公共服務供給(馬海濤和秦士坤,2022),平衡民生保障與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采取措施緩解財政壓力,但支出的剛性使得政府削減開支這一行為難以實現,從圖1中也可得出,近10年來,我國民生領域的財政支出只增不減。再加上地方政府向外獲取收入來源的空間相對有限,故政府更偏向于通過提高財政效率來影響轄區公共服務質量(Hayek,1945)。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方面具有中央無法比擬的信息優勢和治理經驗(張騰等,2021),可以實現公共服務成本與收益的內在化,進而提高公共服務質量(Cantarero等,2007),即適度范圍內的財政壓力可促進公共服務質量的提升。但隨著財政狀況的持續惡化,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賴于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招商引資來提高稅基增長。基建支出等具有直接支出的性質,能迅速拉動GDP增長(傅勇和張晏,2007),但在一定程度上擠占了公共服務支出的增長空間,從而不利于公共服務質量的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財政壓力與地區公共服務質量之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關系。
(三)晉升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
根據“晉升錦標賽”理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逐漸形成了以GDP增長為核心的官員選拔與績效評價機制(Chen和Li,2005),在激烈的晉升環境下,官員個體需在任期范圍內圍繞中央設定的考核目標創造盡可能高的政績以獲取政治晉升(羅黨論等,2015)。具體而言,晉升壓力主要通過兩個方面影響公共服務質量:
其一,現行官僚體制下,地方官員被賦予經濟建設與民生保障兩項任務,這兩者之間并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民生財政支出的增加,如教育支出,可改善生產要素中的勞動力質量,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其二,現階段中央對公共服務、社會穩定和生態效益等民生指標的高度關注,使得民意支持成為促進地方官員推動公共服務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Zuo,2015)。由于公共服務質量直接決定了公眾的效用和滿意度,民眾往往通過跨轄區比較來選擇流入到社會福利水平較高的地區,而地方官員擔心居民“用腳投票”致使本地區人口大量流出,以致于吸引不到足夠的人才支持城市發展(張騰等,2021),故積極推動地區公共服務質量的提升,以此獲取較多的民意支持和政治獎賞(孫玉棟和席毓,2021)。同時,當地社會福利的增加,有利于地方官員聲望的積累,對官員晉升大有裨益。綜上所述,理性的地方官員在面對晉升壓力時,是有動力將公共資源投入到公共服務領域的,進而在提高當地社會福利水平、改善公共服務質量的同時獲取更高的政績認可(皮建才,2008;王家庭和李艷旭,2018)。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晉升壓力對地區公共服務質量提升具有促進作用。
(四)財政壓力、晉升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
當前,財政聯邦體制與官員晉升體制同時作用于民生領域且相互影響,按照上述兩者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邏輯,收支兩端帶來的財政壓力會改變地方政府的行為策略(Tiebout,1956)。而在分級分稅預算管理體制下,不同地方政府面臨的財政壓力有輕重緩急之別(趙永輝等,2020),外部財政約束的差異性導致作為理性經濟人的地方官員改善公共服務質量的晉升動機是存在異質性的(郭平等,2022)。
在財政負擔較輕的地區,財政壓力并沒有成為制約地方民生治理能力提升的關鍵性因素,地方政府有更強的激勵與能力來改善公共服務質量,統籌推進地區經濟發展與民生保障進而獲得上級認可(趙永輝等,2022)。對比財政壓力較大的地區,地方需要依賴“財力小馬”拉動各項龐大支出,提供公共服務的任務難度較大,而關于公共服務的財政投入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帶來績效,這些投入并不能立竿見影地緩解地區財政負擔過重的困境(郁建興和高翔,2012)。因此,在此情形下,晉升制度對公共服務質量產生的激勵效應不足以支撐地方官員將有限的財政資源大量投入到公共服務領域(郭平等,2022;張嘉紫煜等,2022),也無法直接對中央的考核做出積極的顯示性回應。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3:
假設3:財政壓力先強化后削弱了晉升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促進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計量模型構建
為系統全面考察財政壓力與晉升壓力對我國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本文選用兩步系統GMM模型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效應進行實證分析。根據上述理論分析,財政壓力與公共服務質量之間的關系可能呈現非線性,而晉升壓力與公共服務質量之間呈現線性關系,為此,本文將具體模型設定為:
PSQit=β0+β1PSQit-1+β2VFIit+β3VFI2it+β4FSit+β5Controlit+θi+μt+εit(1)
式中,i表示時間,t表示城市,公共服務質量(PSQ)為被解釋變量,財政壓力(VFI)和晉升壓力(FS)均為核心解釋變量,Control為各類控制變量,ε為隨機誤差項。考慮到公共服務質量具有一定的遞延效應,可能受到上期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本文在模型中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同時控制了時間效應(θ)和地區效應(μ),以剔除外生影響。
(二)變量定義與說明
1.公共服務質量的度量
公共服務質量評價指標是綜合了各個維度的結果。已有研究傾向于從過程控制、民眾感知與回應、績效測量方面理解公共服務質量(Guenoun等,2016),鑒于公共服務質量測量的準確性和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參考“十四五”公共服務規劃中對公共服務的維度劃分以及借鑒詹新宇、王蓉蓉(2022)對公共服務內容范疇的劃分,重點選取教育、醫療、文化、交通與環境5個維度共15個基礎指標來反映公共服務質量的評價范圍,上述指標均為正向指標。在具體操作中,由于各個維度之間可能存在較強相關性,直接放入估計模型中將產生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因此,本文采用熵權法對指標體系進行賦權(夏怡然和陸銘,2015),熵權法是一種客觀賦權方法,其原理是根據個指標的變異程度,利用模糊評價矩陣和輸出的信息熵計算出各指標的熵值,并基于熵值對指標權重進行修正,從而得到最終權重(郭軍等,2021)。其計算過程如下:
假設共有r個年份,n個地區,m項指標。
第一步,將各個指標進行去量綱化處理并進行數據平移,以x′ijk表示第i年,第j個地區,第k個指標標準化后的值,由于標準化后可能會出現0值,因此對標準化后的數據進行平移得到x″ijk,表1中各項指標均為正向指標:
第二步,計算第k項指標的權重qijk:
第三步,計算第k項指標的熵值ek與差異化系數gk:
第四步,計算第k項指標的權重wk:
第五步,根據熵權法計算出各項指標的權重大小(見表1),結合全國285個地級市標準化后的面板數據,最終計算2011—2019年各地級市公共服務質量得分sij:
2.財政壓力的度量
財政壓力來源于地方政府支出責任與收入的不匹配。1994年,我國實行分稅制改革,中央財權集中程度和收入不斷增加,地方財政壓力問題逐漸凸顯。現有文獻關于地方財政壓力的度量主要有以下四種方法:一是從財政分權的角度直接測算地方財政收支不匹配現狀,即財政縱向失衡度。在財稅體制改革下,縱向財政平衡程度會隨著政策沖擊發生改變,故縱向財政失衡度的變化趨勢從宏觀層面上反映了中國式分權下地方財政壓力的變化情況(儲德銀和遲淑嫻,2018),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VFI表示財政縱向失衡,α與β分別表示財政收入分權與財政支出分權,gap表示地方財政自給缺口率,rd與sd分別表示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及支出,cr與ce分別表示中央公共預算收入與支出。
二是用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的缺口來度量,具體使用一般公共預算收支差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表示(孫開和張磊,2019);三是采用稅收分成比重的變化來表示,根據所得稅分享改革國務院決定從2002年起,實行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中央政府在維持地方政府既有所得稅基數不變的基礎上,對增量收入部分與地方政府實施五五分成,2003年又推進到六四分成。
,測算出地市級政府的分享比變化和收入損失;四是采用外生沖擊來反映地方財政壓力的變化,用取消農業稅、企業所得稅改革等某個事件形成的財政沖擊來度量(陳曉光,2016)。本文在此以縱向財政失衡度(VFI)為主要解釋變量進行基準回歸。
3.晉升壓力的度量
本文的另一個主要解釋變量為地方官員的晉升壓力。目前主要有兩種方法測算晉升壓力:一是采用各地區實際利用外資占GDP的比值作為晉升壓力的代理指標,其數值越小,晉升壓力越大。外商直接投資是地方官員推動當地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地方官員一般會通過吸引外商投資來促進地區經濟增長,以此獲得晉升機會(林江等,2011)。二是根據“晉升錦標賽”理論,上級對地方官員的考核以經濟效益為主,但近年來有關注民生的傾向,故本文借鑒錢先航等(2011)的做法,選取通過GDP增長率、財政盈余以及失業率三個指標計算得到的綜合壓力指數(PS)來衡量地方官員的晉升壓力財政盈余 =(地方財政收入-財政支出)/地方財政收入,失業率=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城鎮登記失業人員數+從業人員數)。,這也是地方政府關心的主要方面。考慮到上級對地方官員的考核壓力通常會采取相對績效評價,因此本文將樣本城市分為三類:普通城市、副省級城市和直轄市。在具體操作上,對于普通城市,將以上三個指標分別與所有普通城市的加權平均值進行比較,副省級城市與15個副省級城市的加權平均值進行比較,直轄市與4個直轄市的加權平均值進行比較。在計算方法上,對GDP增長率和財政盈余小于當年加權平均值賦值為1,否則為0;對失業率則是大于當年平均值為1,否則為0;然后再將得分相加就得到地方官員的晉升壓力指數,該變量取值范圍為[0,3],且數值越大晉升壓力越大。
4.控制變量
在借鑒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選取了產業結構、人口因素、經濟發展與地方政府方面的控制變量:(1)產業結構:第二產業與GDP之比表示(second),第三產業與GDP之比表示(third);(2)人口因素:人口數量(pop)采用各地區年末人口的對數來衡量,人口密度(density)采用城市人口與其面積之比表示,人力資本(capital)采用各地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占年末總人口之比表示;(3)經濟發展:固定資產投資率(invest)采用各地區固定資產投資額與GDP之比表示,經濟實力(strength)采用人均GDP的對數表示;(4)地方政府方面:稅收負擔(burden)采用稅收收入與GDP之比表示,政府參與度(participation)采用各地區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與GDP之比表示。
(三)數據來源與統計特征
基于數據可得性以及缺失值的考慮,本文剔除了三沙、儋州、海東、鶴崗等城市,并剔除存在明顯不合邏輯關系的樣本值,最終對2011—2019年中國285個城市的動態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文章所有原始數據均來自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各省份統計年鑒、各城市財政收支預算以及國家統計局資料,個別變量的缺失值按照所在城市2011—2019年該變量的均值進行補齊,主要變量的統計特征如表2所示。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
本文采用兩步系統GMM估計法對2011—2019年我國285個城市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逐步將各類核心解釋變量引入模型中進行回歸,同時控制時間效應和地區效應。表3中(1)、(2)、(3)列均加入公共服務質量滯后一期作為解釋變量,為了修正未觀察到的遺漏變量偏差、測量誤差以及潛在的內生性問題,參考王宏揚和樊綱治(2018)、董有德和夏文豪(2022)的研究,選擇PSQit最大滯后階數為二階的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根據表3中的估計結果可知,0.1
可能的原因在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我國財稅體制進行了調整并明確指出,重點支出領域將不再與財政收支或生產總值掛鉤,這實際上解除了地方政府受到的一些不合理的財政預算管制。高質量發展階段下,公共服務支出具有剛性,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會隨著地方財政壓力的上升迅速減少該領域的相關支出。然而,面對財政壓力激增時,地方政府往往難以通過收緊的財政預算兼顧各方面支出責任,此時,地方政府更傾向于通過干預基礎設施、生產建設性以及經濟效益更好的生產性投資以提高財政收入,即“重投資,輕民生”,這一轉變將對公共服務支出空間產生擠壓效應,繼而累及公共服務質量的提升。
表3第(2)列為單獨考慮晉升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影響效應的回歸結果,基于政治激勵視角發現,晉升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顯著為正,假設2得到驗證。其主要是因為,現有綜合考核體制下,官員晉升的考核標準不再簡單“唯GDP”,公共服務質量也成為地方官員獲得晉升機會的重要政策工具,晉升激勵的積極效應促使地方官員更有可能改善轄區內的公共服務質量。此外,相較于中央政府,轄區居民作為公共服務供給的直接受益者,更易根據本地區公共服務供給的相對水平評判公共服務質量的高低,無形中構成外部壓力推動地方政府改善公共服務質量,尤其是涉及教育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服務(Brosio和Ahmad,2008)。表3第(3)列表明,財政壓力和晉升壓力對地方公共服務質量具有差異化影響,在同時考慮財政壓力和晉升壓力時,財政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依舊呈現“倒U”形,而晉升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有顯著正向影響,結果與第(1)、(2)列保持一致。
表3中,L.PSQ為公共服務質量的滯后一期值,其在第(1)、(2)、(3)列中的系數值均大于0,且回歸結果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說明當期公共服務質量會影響到下一期公共服務質量的提升。從控制變量來看,首先,在產業結構方面,第二產業占比和第三產業占比的擴大均顯著提高了公共服務質量。產業結構的變化可以反映地區經濟實力,以第二、三產業為代表的產業發展,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吸引和留住人才,擴大當地內需和積累人力資本,為地方政府提供長期可持續收入來源。另一方面,促使地方政府不斷提升公共服務質量以優化人才居住和發展環境。同時,該影響路徑也表明人力資本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與地區產業發展與結構調整息息相關,城市人才紅利優勢可顯著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其次,在人口特征方面,城市人口數量過多可能不利于公共服務質量的提升。原因在于,城市人口的快速聚集雖可充實勞動力資源,推動城鎮化發展,但也帶來城市公共資源負擔沉重和分配不公等問題,對公共服務供給形成巨大壓力。不同于人口數量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效應,人口密度的提高有利于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以及其他領域節省人均投資,并提高運行效益,進而使其有動力和條件改善公共服務質量。最后,稅收負擔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體現了各地區政府稅收負擔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程度。在稅收負擔加重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可能會通過招商引資來拓寬稅源和增加本地區稅收收入,繼而減少民生性領域的支出,而這不利于地方公共服務質量的改善和提升。
(二)內生性檢驗
式(1)中的財政壓力和晉升壓力可能是一個會引起誤差的內生變量,使用系統GMM方法雖然能夠修正未觀察到的遺漏變量偏差、測量誤差、滯后項與擾動項存在相關性等問題,但難以解決雙向因果帶來的內生性問題,即公共服務質量的變化會影響財政壓力和晉升壓力。為進一步排除反向因果關系,本文試圖尋找工具變量,并使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對模型進行檢驗。
一是借鑒吉富星和鮑曙光(2019)的研究,選取財政自給率作為財政壓力的工具變量。根據結果可知,第一階段F統計值大于10,通過了弱工具變量檢驗,但第二階段回歸結果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因篇幅原因,具體過程和數據結果可向作者索取。。二是參考Brover和Arellano(1997)、劉樹鑫和楊森平(2021)、閆坤和黃瀟(2022)的研究方法,將財政縱向失衡的滯后二期、晉升壓力的滯后二期作為工具變量,采取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對基準回歸結果進行檢驗,同時使用穩健標準誤差估計。因財政壓力與公共服務質量之間的關系呈現非線性,在此參考侯治平等人(2020)的做法,當核心解釋變量為一次項時,工具變量為財政縱向失衡的滯后變量,當核心解釋變量為二次項時,對財政縱向失衡滯后項取平方項做工具變量。表4第(1)列報告了工具變量兩階段回歸結果,由此可知,采用工具變量估計的財政縱向失衡的系數仍然先正后負,且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財政壓力對地方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呈現“倒U”形關系。由表4第(2)列結果可知,在考慮了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后,晉升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程度雖有所變化,但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保持一致。
(三)交互作用分析
前文分別考察了財政壓力、晉升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效應,現實情境下,我國的財政聯邦體制與官員晉升體制是相互影響的,為了進一步分析財政壓力與晉升壓力的交互關系在公共服務質量領域的作用效果,本文加入了財政壓力的一次項、平方項與晉升壓力的交互項。
表5第(1)、(2)列分別展示了納入控制變量前后財政壓力和晉升壓力交互項的回歸結果,此處主要關注交互項系數的符號和顯著性。對比分析發現,列(1)、列(2)回歸結果顯著性及符號均保持一致,表明結果具有穩定性。從回歸結果來看,解釋變量財政壓力與晉升壓力的主效應均與基準回歸結果不一致,參考格雷維特爾(中譯本,2005)和鐘熙等(2019)的解釋,可以理解為,顯著的交互效應掩蓋或歪曲了主效應。晉升壓力與財政壓力一次項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而與財政壓力平方項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表明財政壓力先強化后削弱了晉升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正向影響,即財政壓力對晉升壓力與公共服務質量之間的關系起“倒U”形調節作用,假設3得到驗證。
從政策具體操作層面來看,中央政府主要通過壓力傳導的方式推動地方民生任務的完成。具體來說,對于財政壓力相對較小的地區,依靠中央轉移支付和保民生目標,地方政府有動機和能力去支持公共服務發展,繼而改善公共服務質量,即一定范圍的財政壓力促使地方官員產生更強的政治晉升激勵去支持當地公共服務發展。但因公共服務項目前期需要大量財政投入,短期內卻不能帶來經濟效益,故對于財政壓力較大的地區而言,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已成為非此即彼的關系,此時晉升壓力對于公共服務質量的積極激勵效應有限,地方政府更看重的可能是保生存,避免財政嚴重虧空。總的來說,中央政府應針對財政壓力不同的地區實施差異化扶持政策。一方面,對于財政收支平衡壓力大的城市,必須發揮好中央政府在公共服務資源相對薄弱區域和基礎薄弱服務項目中的統籌能力,適度加大公共財政對與提升城市內生增長動力相關的服務項目的轉移支付力度。另一方面,適度財政壓力下,倒逼地方政府提高公共資金使用效率,避免地方政府對中央轉移支付的過度依賴。
(四)異質性分析
地方政府公共服務供給內容復雜多樣,涉及教育、醫療、環境與文化等多個領域,由圖1可知,教育支出相較于其他民生支出,增速較穩定,沒有出現大幅上漲的情況,而環保支出與教育支出情況相反,其年均增速為所有民生支出類別中最高。基于此,本文在對全國樣本進行基準回歸的基礎上,以公共服務內容中的教育和環保為例,探究財政壓力、晉升壓力的變化如何影響地方政府在公共教育和環境質量方面的行為策略,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
由表6第(1)列可知,財政壓力與教育質量之間的影響效應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關系,而晉升壓力回歸結果不顯著,說明教育質量主要受財政壓力的影響。原因可能是雖然不同地區間教育資源分布不平衡,但受限于地理位置和人口規模結構的差異,中央和地方政府難以統籌優化教育資源和結構,導致地區教育質量短時間內難以有突破性改變。因此,晉升壓力對于地方政府提升教育質量有一定約束但可能激勵性不強。此外,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2012年達到4%”。基于中央的政策要求,地方政府為完成上級設定的財政支出目標,短時間內傾向于擴大教育支出規模,從而改善地區教育質量。且分稅制改革加重了地方財政壓力,同時也易引致地方產生“公共產品和服務價格下降”的財政幻覺,進而可能會在短期內促使當地增加對教育類公共產品的需求,擴大教育支出規模(陳麗等,2022)。但攀升的財政壓力會導致地方面臨更大的財政收支缺口(郭平等,2021),此時地方政府為緩解財政壓力,傾向于將資源優先投入到短期效益更高的經濟建設領域,或者在民生領域采取保障社保就業支出、削減教育支出的“促穩定、輕人力資本投入”支出策略(楊得前和汪鼎,2021),上述舉措會進一步抑制當地教育質量的提升。
由表6第(2)列可知,財政壓力與環境質量之間關系不顯著,而晉升壓力對環境質量提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表明我國的財政體制并不是導致環境污染的罪魁禍首,這與He(2015)的研究結論一致,He認為地方官員在某種程度上是仁慈的,也會像當地選民一樣關心環境保護。自1996年以來,中央政府實行環境質量行政領導負責制,不斷加強環保調控力度,但在以GDP為核心目標的晉升激勵模式下,地方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沖突加劇,地方政府在環境治理上存在“逐底競爭”的行為傾向,或在環境類公共危機事件爆發之后采取突發式和運動式治理(姜國俊和羅凱方,2019)。隨著中央環保問責規范化和常態化,財政壓力對環境保護等約束性指標的影響大大削弱,梁向東等人(2021)提出,環境領域的財政支出更多的時候是為了提升地方環境管理水平和污染治理,這種“事后諸葛亮”的行為可能導致財政壓力對環境污染的影響并不顯著。而來自上層的政治壓力和環境規制強化了地方官員對環境治理的動力(曹婧和毛捷,2022),使得地方政府通過推動企業環保技術的創新與應用,以提升環境治理的效果。
(五)穩健性檢驗
為了驗證本文基準結果的穩健性和可靠性,本文分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穩健性檢驗。其一,變更被解釋變量的度量方式,通過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測度被解釋變量公共服務質量。首先利用Stata 17.0軟件得出包含15個基礎指標的公共服務質量指標體系的KMO值為0.835,Bartlett球形檢驗值小于0.05,表明適合做因子分析。繼而通過因子載荷矩陣計算出各指標權重,得到2011—2019年各地級市公共服務質量指標的測度值(PSQ_t)。其二,考慮加入更多的控制變量,本文在此加入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consumption),該變量反映了社會總需求和經濟發展情況。2020年我國《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使提振消費與擴大投資有效結合、相互促進”。黨的二十大報告又提出,“著力擴大內需,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一系列政策指導和社會實踐表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提高將積極拉動地區經濟發展,并進一步推動地區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表7第(1)、(2)列分別展示了變更被解釋變量的度量方式和加入更多控制變量后的回歸結果,結果表明,財政壓力與公共服務質量間仍然呈現顯著的“倒U”形關系,而晉升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具有積極的促進效應。綜上所述,由于測量方法和控制變量的不同,核心變量的回歸系數與基準結果存在一定差異,但系數符號及顯著性基本保持一致,說明基準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基于2011—2019年中國285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實證考察財政壓力、晉升壓力以及兩者交互關系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從而為地方政府改善公共服務質量提供了一個合理的解釋,其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在控制時間效應和地區效應后,財政壓力與地方公共服務質量間呈現顯著的“倒U”形關系。公共服務支出具有剛性,適度的財政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具有激勵作用,但隨著財政壓力的持續增加,地方政府傾向于優先發展高稅收行業,以提高自身財政收入。此時,財政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負向影響效應逐漸凸顯。(2)基于政治激勵視角發現,隨著官員晉升考核標準的多樣化,公共服務質量成為地方官員尋求晉升機會的重要政策工具,晉升激勵的積極效應促使地方官員更有可能改善轄區內的公共服務質量。此外,轄區居民對公共服務質量的感知與評價無形中構成外部壓力推動地方政府改善公共服務質量。(3)進一步考察共同作用于我國公共服務質量過程中財政壓力與晉升壓力的交互關系發現,財政壓力先強化后削弱了晉升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正向影響。適度財政壓力下,依靠中央轉移支付和保民生目標,地方政府有動機和能力去促進當地公共服務發展。但對于財政壓力較大的地區而言,晉升壓力對于公共服務質量的積極激勵效應逐漸弱化。(4)異質性分析發現,教育質量主要受財政壓力的影響,晉升壓力對于地方政府提升教育質量有一定約束但激勵性不強,而環境質量主要受晉升壓力的影響。
為推動我國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兩點政策啟示:
首先,從“財”的角度釋放地方財政壓力,強化民生服務保障的責任。面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可從“開源”和“節流”兩方面適當引導地方政府行為。“開源”方面,推動地方經濟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穩步提升,以經濟發展帶動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這就需要地方政府立足于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背景,加快綠色安全發展。在此基礎上,根據地區人口宏觀目標、產業規劃以及經濟發展等要素,綜合統籌、動態調整當地公共服務發展規劃,并對短期內經濟效益不顯著的公共服務領域給予專項轉移支付資金。“節流”方面,一方面,優化財政收支結構,通過積極穩妥推進地方減稅降費等政策,提高民生領域資金支付效用,不斷發揮財政政策的激勵效果;另一方面,積極引導地方政府運用“援助之手”,在不斷加大民生領域支出力度、避免財政生產性支出偏向的同時,注意合理引導群眾對公共服務的社會預期。
其次,從“人”的角度厘清央地責任劃分,完善地方考核指標和晉升機制。其一,引導形成綜合有效、科學的政績考核機制,中央政府應對不同公共服務項目采取差別式考核標準和策略,避免“一刀切”政策。如對于教育、文化和養老等投資長、見效慢的公共服務,適當減少考核的硬性約束,中央可給予更多宏觀指導,對于細節化的指標進行適當干預。但在環境保護和生態治理等方面,應嚴格規范考核,壓實地方各級黨委領導責任和政府主體責任,堅決對污染行為進行有效規制。其二,以“維穩”為基礎指標,從更宏大的視角和更長的時間周期對地方官員進行綜合考核,在考核維度設計上避免利益短期化,從而調動地方推動地區公共服務質量發展的積極性。
參考文獻:
[1] 陳曉光,2016:《財政壓力、稅收征管與地區不平等》,《中國社會科學》第4期。
[2] 陳麗、鄧微達、王智烜,2022:《財政可持續性與地方政府教育努力程度》,《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第2期。
[3] 陳碩,2010:《分稅制改革、地方財政自主權與公共品供給》,《經濟學(季刊)》第4期。
[4] 儲德銀、遲淑嫻,2018:《轉移支付降低了中國式財政縱向失衡嗎》,《財貿經濟》第9期。
[5] 曹婧、毛捷,2022:《財政分權與環境污染——基于預算內外雙重視角的再檢驗》,《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第4期。
[6] 鄧悅,2014:《我國質量公共服務評價結果差異及其分析——基于消費者滿意度的評價》,《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
[7] 董有德、夏文豪,2022:《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基于系統GMM和門檻模型的實證研究》,《上海經濟研究》第8期。
[8] 傅勇、張晏,2007:《中國式分權與財政支出結構偏向:為增長而競爭的代價》,《管理世界》第3期。
[9] 郭軍、張琛、馬彪,2021:《貧困地區脫貧質量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宏觀質量研究》第3期。
[10] 郭平、曾卓爾、徐麗,2021:《教育支出改革與財政壓力分析——基于斷點回歸方法的估計》,《財政研究》第10期。
[11] 郭平、曾卓爾、徐麗,2022:《財政壓力提高了地方政府財政汲取能力嗎》,《財經理論與實踐》第2期。
[12] [美]格雷維特爾著,鄧鑄、姜子云、蔣小慧等譯,2005:《行為科學研究方法》,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13] 胡玉杰、彭徽,2019:《財政分權、晉升激勵與農村醫療衛生公共服務供給——基于我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當代財經》第4期。
[14] 侯治平、吳艷、楊堃、賀正楚,2020:《全產業鏈企業國際化程度、研發投入與企業價值》,《中國軟科學》第11期。
[15] 姜曉萍、吳寶家,2022:《人民至上: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完善基本公共服務的歷程、成就與經驗》,《管理世界》第10期。
[16] 姜國俊、羅凱方,2019:《中國環境問責制度的嬗變特征與演進邏輯——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行政論壇》第1期。
[17] 吉富星、鮑曙光,2019:《中國式財政分權、轉移支付體系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中國軟科學》第12期。
[18] 林江、孫輝、黃亮雄,2011:《財政分權、晉升激勵和地方政府義務教育供給》,《財貿經濟》第1期。
[19] 林毅夫、劉志強,2000:《中國的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
[20] 梁向東、楊修博、周子超,2021:《財政分權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研究——以技術創新為中介變量》,《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第9期。
[21] 劉瓊、郭俊華、徐倪妮,2021:《科技公共服務質量對區域創新水平的影響——基于吸收能力的門檻效應分析》,《中國科技論壇》第6期。
[22] 劉樹鑫、楊森平,2021:《財政縱向失衡會影響地方政府支出效率嗎》,《當代財經》第7期。
[23] 蘭旭凌、范逢春,2019:《政府全面質量治理:新時代公共服務質量建設之道》,《求實》第4期。
[24] 劉紅芹、耿曙,2023:《地方政府短視問題再考察:財政聯邦、晉升錦標與地方支出結構》,《社會學評論》第4期。
[25] 羅黨論、佘國滿、陳杰,2015:《經濟增長業績與地方官員晉升的關聯性再審視——新理論和基于地級市數據的新證據》,《經濟學(季刊)》第3期。
[26] 馬海濤、秦士坤,2022:《財政壓力如何影響民生支出》,《經濟學動態》第10期。
[27] 皮建才,2008:《中國地方政府間競爭下的區域市場整合》,《經濟研究》第3期。
[28] 錢先航、曹廷求、李維安,2011:《晉升壓力、官員任期與城市商業銀行的貸款行為》,《經濟研究》第12期。
[29] 史衛東、趙林,2015:《山東省基本公共服務質量測度及空間格局特征》,《經濟地理》第6期。
[30] 孫玉棟、席毓,2021:《影響我國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率的因素研究——基于財政、晉升和發展壓力的視角》,《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第6期。
[31] 孫開、張磊,2019:《分權程度省際差異、財政壓力與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偏向——以地方政府間權責安排為視角》,《財貿經濟》第8期。
[32] 唐睿、劉紅芹,2012:《從GDP錦標賽到二元競爭:中國地方政府行為變遷的邏輯——基于1998—2006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公共管理學報》第1期。
[33] 王成、丁社教,2018:《政府購買居家養老服務質量評價——多維內涵、指標構建與實例應用》,《人口與經濟》第4期。
[34] 王家庭、李艷旭,2018:《晉升壓力能夠提高地方民生性財政支出效率嗎?——基于中國285個城市的DEA\|Malmquist分析》,《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
[35] 王宏揚、樊綱治,2018:《人口結構轉變與人身保險市場發展趨勢——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保險研究》第6期。
[36] 汪立鑫、王彬彬、黃文佳,2010:《中國城市政府戶籍限制政策的一個解釋模型:增長與民生的權衡》,《經濟研究》第11期。
[37] 翁列恩、胡稅根,2021:《公共服務質量:分析框架與路徑優化》,《中國社會科學》第11期。
[38] 吳敏、周黎安,2020:《財政壓力的多層級傳遞與應對——基于取消農業稅改革的研究》,《世界經濟文匯》第1期。
[39] 謝星全,2018:《基本公共服務質量:多維建構與分層評價》,《上海行政學院學報》第4期。
[40] 夏怡然、陸銘,2015:《城市間的“孟母三遷”——公共服務影響勞動力流向的經驗研究》,《管理世界》第10期。
[41] 楊得前、汪鼎,2021:《財政壓力、省以下政府策略選擇與財政支出結構》,《財政研究》第8期。
[42] 楊鈺,2020:《公共服務質量改進:國際經驗與中國實踐》,《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
[43] 閆坤、黃瀟,2022:《中國式分權、財政縱向失衡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研究》,《經濟學動態》第12期。
[44] 姚洋、張牧揚,2013:《官員績效與晉升錦標賽——來自城市數據的證據》,《經濟研究》第1期。
[45] 郁建興、高翔,2012:《地方發展型政府的行為邏輯及制度基礎》,《中國社會科學》第5期。
[46] 朱建軍、張蕊,2016:《經濟增長、民生改善與地方官員晉升再考察——來自2000-2014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經驗證據》,《經濟學動態》第6期。
[47] 趙晏、邢占軍、李廣,2011:《政府公共服務質量的評價指標測度》,《重慶社會科學》第10期。
[48] 趙永輝、付文林、冀云陽,2020:《分成激勵、預算約束與地方政府征稅行為》,《經濟學(季刊)》第1期。
[49] 趙永輝、羅宇,2022:《中央績效考核與地方民生治理:迎風而動還是巋然不動》,《世界經濟》第10期。
[50] 左翔、殷醒民、潘孝挺,2011:《財政收入集權增加了基層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嗎?以河南省減免農業稅為例》,《經濟學(季刊)》第4期。
[51] 張蕊、朱建軍,2016:《官員政治激勵與地方財政透明度——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經驗分析》,《當代財經》第1期。
[52] 張晏、龔六堂,2005:《分稅制改革、財政分權與中國經濟增長》,《經濟學(季刊)》第4期。
[53] 張騰、蔣伏心、韋朕韜,2021:《財政分權、晉升激勵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山西財經大學學報》第2期。
[54] 張嘉紫煜、張仁杰、馮曦明,2022:《財政縱向失衡何以降低公共服務質量——理論分析與機制檢驗》,《財政科學》第5期。
[55] 詹新宇、王蓉蓉,2022:《財政壓力、支出結構與公共服務質量——基于中國229個地級市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改革》第2期。
[56] 鐘熙、宋鐵波、陳偉宏、翁藝敏,2019:《CEO任期、高管團隊特征與戰略變革》,《外國經濟與管理》第6期。
[57] Brosio,G.and Ahmad,E.,2008,Local Service Provision in Selected OECD Countries:Do Decentralized Operations Work Better,IMF Working Papers,67:1\|35.
[58] Bover,O.and Arellano,M.,1997,Estimating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s from Panel Data,Investigaciones Economicas,21(2):141\|166.
[59] Chen,Y.,Li,H.and Zhou,L.,2005,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Turnover of Provincial Leaders in China,Economics Letters,88:421\|425.
[60] Cantarero,D.,Pascual,M.and Sarabia,J.M.,2007,Income Inequality and Population Health in Developed Countries,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Economic Research,13(1):116.
[61] He,H.J.,Ying,Y.Q.and Barry,R.W.,2005,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Federalism,Chinese Styl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89(9\|10):1719\|1742.
[62] Hayek,F.A.,1945,Time\|Preference and Productivity:A Reconsideration,Economica,12(45):22\|25.
[63] Li,H.and Zhou,L.A.,2005,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9(9\|10):1743\|1762.
[64] Montinola,G.,Qian,Y.Y.and Weingast,B.R.,1995,Federalism,Chinese Style: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World Politics,48(1):50\|81.
[65] Guenoun,M.,Goudarzi,K.and Chandon,L.,2015,Constri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Hybrid Model to Measure Perceived Public Service Quality (PSQ),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82(1):208\|230.
[66] He,Q.,2015,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Evidence from Chinese Panel Data,China Economic Review,36(2):86\|100.
[67] Tiebout,C.M.,1956,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4(5):416\|424.
[68] Zuo,C.,2015,Promoting City Leaders: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Incentives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224:955\|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