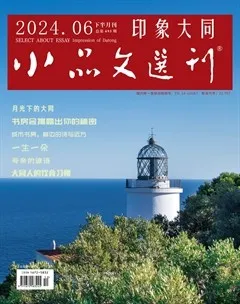一生一朵
葦杭

甫開眼,透過風(fēng)痕雨跡的玻璃窗,輒見美麗的白云天——說庸常也庸常、說神奇也神奇,隨你怎么想:開啟這平凡而又平常的一天,坐擁24小時的“豪奢”。這在天文學(xué)上有個別致的叫法,“一個太陽日”。真是令人耳目一新,仿若與太陽肩并肩。可否就此得寸進尺,把這海波也似的青空、悠悠往復(fù)的白云,作為這個“太陽日”熱情迎接我的前導(dǎo)隊?——腦回路果然比較清奇,與阿Q有得一拼,遂得大歡喜。一骨碌從榻上爬起,打開窗,與晨風(fēng)撞了個滿懷。風(fēng)中有庭樹、秋花的露氣煙光,點綴以珍珠、碎鉆也似的蟲鳴鳥唱——世界還可以比這再好一點嗎?
無限時空中,所謂漫長的人類史,較之天地日月、河流山川,也無非是電光石火;而飽經(jīng)滄桑的人世百年,置于歷史長河,無疑又是滄海一粟、蜉蝣天地。遂令人愈發(fā)珍視眼前的一切:一縷撲面的清風(fēng)、一片芳草地、一角白云天;衡門之下可棲遲,手中一卷,夜眠七尺,烏黑的漆碗里沏著白月亮;早起灶間的紫砂煲“炊金煮玉”,玉米金黃,稻谷流脂,一粥一飯,煙火人間……樁樁件件,都是充滿平和喜樂的“小確幸”。
不是一大早就發(fā)神經(jīng),而是昨天去了墓園掃墓,再一次直面生死,便有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悲大喜及“潮汐”過后的沉靜與反思。
畢竟,中元節(jié)近了。
墓里的先人,是我家先生的祖父母,我未曾謀面的祖公祖婆。肅立,行禮,相當(dāng)于向長輩請安,問好。擦拭墓碑上的灰塵,亦等同于為老人“灑掃庭除”。而后,擺好供果,恭恭敬敬上一炷香。
祭如在。
一直陰沉的天,飄起雨來。
在墓前撐起傘,注視著雨傘下的香火。
香火暗紅。一會兒,香灰就寸許長。香煙裊裊,先是筆直,隨著香灰無聲地“坍塌”,香煙也改了“路徑”,四散而去。
二人輪番執(zhí)傘,傾著身子,遮著祭臺,直到一炷香燃燼。
不知不覺間,如絲如縷的小雨,停了。
收了傘,視線從祭臺移開,沿山坡瞭望,但見墓碑林立,亦如城區(qū)一棟棟密密麻麻的“鴿子籠”……轉(zhuǎn)身回望對面的青山隱隱碧水迢迢,不知墓中人還能感知云起云飛,暮靄朝暉否……回來的路上,想起遠(yuǎn)在故土父母的墳塋,不知弟弟哪天去祭掃……到家后,便微信他。反饋道,早幾日就去了,一切安好,勿念……然后告知今日剛剛送走二姨家的表弟天貴兒,才進屋一小會兒云云……
一下子,我便愣在那兒了!
天貴兒剛剛四十出頭的年紀(jì),病了也就一年多的光景……雖然曉得這病的兇險,兇多吉少,但聽到噩耗還是嚇了一跳……想起與表弟的最后一面,還是兩年前的春天,在母親的葬禮上。那時,他看起來還很健康,跑前跑后,沒少幫忙。其后不久就聽說病了,在北京做的手術(shù)。費用自然是一大把,好在二姨家的兄弟姊妹多,平時也很抱團,遇事相互照拂,大家出手好歹湊夠了手術(shù)費。我雖未曾到京或回鄉(xiāng)探視,也微信轉(zhuǎn)去了一點心意,以示慰安。……孰料轉(zhuǎn)瞬間,就輪到送別正值壯年的他了……真是人生苦短,世事無常,素日司空見慣的一切,隨時隨地都可能成為永訣。譬如,今早的晴空與流云,拂過的葉露與花香,雜亂無章卻生機無限的鳥雀喧喧,于剛剛故去如天貴兒者,永不可得……
生命所為何來,如此匆匆忙忙,如時鐘的秒針,馬不停蹄,日夜兼程,奔向那未知的前途與萬古不易之目的地。漢語真是奇妙啊,充滿哲思。原來“目的地”,便是“墓的地”。發(fā)音完全相同,豈是偶然?
早晨的時光,寸陰寸金,容不得思想的野馬自由馳騁。趕緊“勒緊韁繩”,入洗手間盥洗、晨妝。涂護膚水、乳液;眉筆輕拈,淡掃雙眉,亦如遠(yuǎn)山長;旋出唇膏,雙唇輕染,亦如櫻瓣如玫紅如烈焰。生命,是一團火嗎?有光有熱,我們拿什么來助燃?
疫情以來,單位原則上要求零公交出行,我這公交一族,便改騎共享單車。每日出門,則抱著晨練的心情,迎著日出或風(fēng)雨,奔馳在車流人海。遂不以為苦。
照例在指定停車點交了車。步行,穿過橋洞,路過臨近的小學(xué)校。秋風(fēng)倏來,唰啦啦落了一地干枯的葉子,腳下一陣脆響。遂止步。側(cè)身仰望身旁這一排高大的白楊樹。樹冠仍是夏日枝繁葉茂的樣子,雖未見十分秋意,但足下分明落葉漸多,畢竟處暑已過,白露在望。在寒地冰城,總是率先感知秋的氣息。三三兩兩的小孩子,貌似一年級新生,小臉上罩著大口罩,在背包羅傘的家長悉心護佑下,雀躍著涌入校門。再一次駐足。目送這一波一波的孩子蹦蹦跳跳的小身影,在秋意漸濃的蕭瑟里,體味著活潑潑的生之歡樂。
等轉(zhuǎn)過街角,忽見旁側(cè)高高的鐵柵欄上爬滿牽牛花心形的葉子,枝枝蔓蔓,左盤右旋,沛然而下,如綠色的瀑流,朵朵煙藍(lán)的牽牛花,掩映其中,大好。好到,如孔夫子的“不知老之將至”。這盛開的牽牛花是“不知秋之將至”了,且是寒地的肅殺之秋。掏出手機,左拍,右拍,上拍,下拍,試圖留住這剎那芳華。
牽牛花,亦名“朝顏”,這名字未免動詩人愁懷。日本俳句有“牽牛花,一朵深淵色”,說的就是這種煙藍(lán)的牽牛花兒。島國人的審美總是很獨特,如“物哀”、“細(xì)柔”、“枝折”、“侘寂”……聽聽這名色,就如和歌與俳句,攜了島國的繽紛落櫻,粉淚簌簌。煙藍(lán)的牽牛花,是一朵——“深淵色”?此刻,我不是正凝視這美得駭人的“深淵”嗎?干嘛要凝視呢,是打算跳下去嗎,跳下去,則別有洞天,如費長房之追隨壺公?
實則,凝視時,我們已不知不覺在其中了。被侵染,被吸附,被旋舞,被塑型……深淵色,美得玄幻,深不可測,如天之藍(lán),海之深。“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說這話時藥山惟儼是面色凝重,還是云淡風(fēng)輕?
我卻只擷了這一朵,“深淵色”。在庚子年初秋這一日。彼此凝視。花非花,我非我;我亦花,花亦我。
沒有宋國的漆園吏格調(diào)高、口氣大。他說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而我眼下、手中,就這一朵。那就與這一朵“合而為一”吧。
一生一朵。
日本江戶時期的美學(xué)家本居宣長說,“知物哀的人,目之所及、耳之所聞,心便有所感,即便是對榮枯盛衰的草木也是如此。”又援引《源氏物語》中的一句話:“秋日到來,令人更加知物哀。”
緣何手中這一朵“朝顏”,而有了寂色?原來“我們最甜美的詩歌,表達(dá)的是最悲哀的思緒”,故而“朝顏”有寂色,是面對神放置在人類面前的巨大的沙漏——大自然律動性的、周期性的死亡警示的必然反映。
不知不覺,我用“寂色”,悄悄置換了“深淵色”。
畢竟,一生,一朵。
選自《新散文觀察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