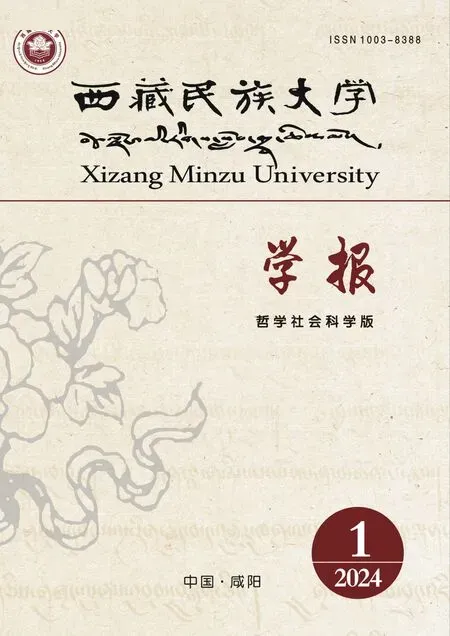農(nóng)牧結(jié)合地帶牧民的規(guī)則意識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意義
徐 燕
(中央民族干部學(xué)院干部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0094)
邊疆地區(qū)的治理,關(guān)系到祖國統(tǒng)一、邊疆鞏固、民族團(tuán)結(jié)、社會穩(wěn)定與發(fā)展等重大現(xiàn)實(shí)問題[1](P5-10)。農(nóng)牧結(jié)合地帶作為不同文化碰撞相交的場域,處于其中的各民族之間并不存在清晰堅(jiān)固的邊界,而是一種出于各種因素考量隨時會被跨越的“軟邊界”。發(fā)揮農(nóng)牧結(jié)合地帶在邊疆-內(nèi)地之間從生態(tài)到文化的連接交流功能,能夠加快實(shí)現(xiàn)邊疆長治久安的目標(biāo)。[2](P54-57)基于此,本文試圖以農(nóng)牧結(jié)合地帶牧民的身份嬗變與規(guī)則意識為切入點(diǎn),探討牧民的規(guī)則意識對邊疆治理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意義。
一、研究背景及問題提出
游牧(Nomadism)作為存續(xù)時間最為久遠(yuǎn)的一種生計(jì)方式,一直以來都受到人類學(xué)家的關(guān)注。20世紀(jì)80 年代以來,人類學(xué)界逐漸形成了一種將地方系統(tǒng)、民族國家、世界體系的影響與游牧社會對這些影響的反應(yīng)融于微型社區(qū)的研究范式,即“游牧-定居”的連續(xù)統(tǒng)。[3](P37-41)就“游牧社會對外在影響和變遷的反應(yīng)”問題而言,相關(guān)研究多運(yùn)用“抵抗-服從”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將牧民在應(yīng)對國家政策、市場經(jīng)濟(jì)等外在因素時表現(xiàn)出的“創(chuàng)造性策略”[4](P665-691)視為一種“權(quán)利意識”,將其歸結(jié)為一種類似于斯科特所言之“弱者武器”的變相反抗形式。但這種分析模式忽略了中國特有的政治語境和文化傳統(tǒng),亦沒有認(rèn)識到價值觀念、情感基礎(chǔ)等因素對作為“行動者”的牧民所產(chǎn)生的影響。
伊麗莎白·佩里(Elizabeth J. Perry)認(rèn)為在中國“行動者”中發(fā)現(xiàn)的所謂權(quán)利話語應(yīng)被理解為“規(guī)則意識”,而非對威權(quán)統(tǒng)治的挑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