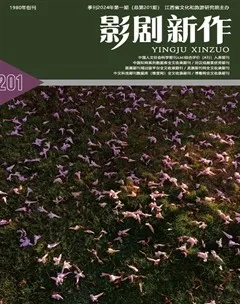病患題材、疼痛體驗與溫暖現實主義
孫力珍
摘要:作為韓延導演的“生命三部曲”的終章,《我們一起搖太陽》于2024年春節檔上映。該片延續了韓延一以貫之的“疾病”題材,講述了尿毒癥患者凌敏與腦瘤患者呂途之間因“征婚求腎”而發生的愛情故事。相較于三部曲的前兩部而言,該片在取材、敘事與主題的探索上展現出一定的新意,為當前中國病患題材電影創作提供了借鑒的可能。
關鍵詞:韓延 “生命三部曲” 《我們一起搖太陽》
引言
在韓延的創作生涯中,“疾病”是一個重要命題。2024年春節檔上映的《我們一起搖太陽》(以下簡稱《搖太陽》)與《滾蛋吧,腫瘤君》(以下簡稱《腫瘤君》,2015)、《送你一朵小紅花》(以下簡稱《小紅花》,2021)共同構成了韓延“生命三部曲”系列。該系列持續探討生命、疾病與疼痛等相關議題。實際上,從2012年開始,其執導的影片《第一次》已然開啟了疾病敘事的濫觴,片中主角宋詩橋(楊穎飾)身患家族絕癥。到2015年《腫瘤君》中漫畫師熊頓患有淋巴腫瘤;《動物世界》(2020)中,男主鄭開司的母親身患絕癥:2021年《小紅花》中身患腦瘤的韋一航與馬小遠。以上可以看出,疾病不僅成為韓延電影作品的核心元素,也是敘事的主要動力。值得注意的是,韓延的作品最大限度地壓縮了疾病所帶來的恐懼感和悲愴性,反而強化了個體面對疾病時的心路歷程。因此,韓延作品中的疾病帶有一種“暖色調”,呈現出鮮明的療愈特質。其新作《我們一起搖太陽》一方面延續了《小紅花》《腫瘤君》等影片中的病患設定;另一方面也更加真實地還原了病患的日常生活,以“溫情+喜劇”的外殼,包裹了一個充滿了生命關懷與溫暖現實的疾病故事。
一、現實關懷與去隱喻符碼的疾病敘事
有研究者認為,中國電影中的“疾病敘事被形塑成特殊的身體敘事,展示疾病身體的‘吸引力。”然而,在韓延的電影中并未著重展示疾病身體的“吸引力”,而是以患者面對疾病時的精神狀態以及疾病的現實性,形塑了一種具有現實共情的情感“吸引力”,這一方面得益于其對病患題材的選擇,另一方面是去隱喻符碼的疾病敘事。
在題材選取上,韓延的“生命三部曲”展現了其關注現實的一面。相較于前兩部分別改編漫畫和小說而言,《我們一起搖太陽》則取材于一則紀實報道文章《最功利的婚姻交易,最動情的永恒約定》,該報道講述兩個身患重癥的年輕人,因生命接力的約定,而互生愛意并攜手對抗重疾的故事。這就使得《搖太陽》既延續了導演一以貫之的病患題材,又在故事背景中注入了更為動人的真實感。據新京報采訪,在這則紀實報道當中,韓延看中的是兩位病患在疾病事件中展現出的愛意,善意,勇氣,以及跟生活死磕的勁兒,特別打動人。可以看出,韓延對這則紀實報道題材的把握,依舊沒有放在疾病帶來的苦情與憐憫上,而是著重病患面對疾病時展現出的從頹廢、喪氣向樂觀、積極態度的轉變上。從取材的角度來看,《搖太陽》既延續了“生命三部曲”中對病患題材的關注,也聚焦病患角色的生活處境,探討生命議題,并展現出積極樂觀的抵抗精神。
孟君指出,“病患題材本質上是一種現實題材,其創作必然遵從現實社會邏輯和現實主義原則。”現實主義的介入,也使得韓延的“生命三部曲”展現出去隱喻符碼的疾病敘事,打破了傳統認知中對于疾病的偏見。在思考疾病時,人們往往將其賦予各種意義,深化疾病隱喻,使其“從‘僅僅是身體的一種病轉換成一種道德評判或者政治態度”。因此,桑塔格認為任何令人恐懼的疾病“即使事實上不具有傳染性,也會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傳染性”。在此種意義上,韓延的病患題材電影中,疾病從被認為是身體的一種病的觀念,轉換成一種道德評判或者政治態度之后,又轉向一種情感的共情力。
于此,在韓延的“生命三部曲”中,疾病并非作為一個社會隱喻來呈現,而是將其作為一個敘事阻礙的元素,展現病患角色在面對疾病,甚至死亡時,其情緒的變化以及如何坦然地面對疾病。如在《搖太陽》中,無論是身患尿毒癥的凌敏對于“活下去”的執著;還是呂途面對腦腫瘤不斷復發時身心所受的折磨,都最大程度地展現出對病患狀態與精神面貌的表達,并非聚焦以往疾病的“道德上具有傳染性”,更不是展現福柯式疾病背后的權力系譜,而是追求一種具有積極向上的情感號召力。
作為一種現實主義題材,《搖太陽》強調創作遵循現實的邏輯與表達,在疾病的去隱喻化表達中,呈現去社會化的苦難敘事,即使《搖太陽》中增加了疼痛的視覺體驗,但其最終目的仍然是為病患角色的動機與轉變做鋪墊。
二、去社會化的苦難敘事與疼痛的視覺體驗
從古希臘修昔底德的“雅典瘟疫敘事”中疾病給人帶來的就是痛苦與恐懼。疾病敘事從某種程度上講是一種苦難敘事。但通常苦難敘事所“描寫苦難的意向一般都是讓人們感受一種貧窮和苦難一體化的壓抑,沒有太大區別,至于這些苦難是否讓人們感受到苦難中的振奮和壓抑中的光明,一般是不問的”。而韓延在“生命三部曲”中對疾病的呈現,跳出了苦難敘事的窠臼,轉而問詢的是疾病與疼痛背后病患的生命力與樂觀精神以及活下去的勇氣。
在病患題材的作品當中,病患角色的塑造往往帶有苦難的描述。韓延的“生命三部曲”當中,無論是《腫瘤君》“樂觀豁達”的漫畫家熊頓,還是《小紅花》中,馬小遠的樂觀態度感染了“沮喪”的韋一航,韓延對于病患角色的表達中,始終都展現出一種去苦難化的敘事。相較于這兩部作品,《搖太陽》更是將疾病疼痛帶來的苦難,轉向了病患對抗疾病的積極態度與精神樂觀。
在苦難轉向的過程中,病痛體驗的視覺呈現既增強了影片疾病敘事的真實性,同時也為病患的“征婚求腎”行為提供了合理的動機。例如凌敏作為尿毒癥患者,腎透析是她每周必須要進行的治療活動。影片多次以特寫的形式,呈現凌敏因透析而被扎的千瘡百孔的胳膊。而在與呂途的意外拉扯中,凌敏胳膊上的瘺管堵塞,醫生拍打凌敏的胳膊,凌敏因疼痛而失聲哭喊。最終因拍打無法疏通瘺管,只能忍痛重新造瘺。對病患疼痛的直觀呈現,使得疼痛體驗成為該片的一種“感知視覺”。在《搖太陽》中,韓延減少了人物內心的獨白,而是通過視覺,增強了患者的病痛體驗,這種病痛的展現,不僅使得凌敏的通過“征婚求腎”行為更為合理,也使得疾病敘事與病痛體驗之間的內部建立起更為緊密的聯系。利用疼痛建構起的“感知視覺”不僅夯實了尿毒癥患者“活著”的艱難,合理化其“征婚求腎”的動機,而且也為影片結尾兩人的轉變提供了令人產生共情的力度。因此,《搖太陽》中增加了病痛的視覺呈現,并非為苦難增色,而是為角色的轉變做鋪墊。
實際上,早在《小紅花》的拍攝過程中,韓延稱:“我特別明確要堅持自己的創作思路和風格一不直接展現病痛,那些展現病痛的畫面無論拍的多么真實,都不如現實生活中的的‘震撼。”病痛體驗在《腫瘤君》和《小紅花》中幾乎是缺失的。無論是患有淋巴癌的熊頓,還是患有腦瘤的韋一航和馬小遠,都沒有展現病患的疼痛體驗。病痛體驗的缺失,使得疾病敘事“輕飄飄地浮在半空中,并沒有緊密地和病痛的‘體驗本身結合在一起”這使得“垂死的病人只是用拒絕體驗的方式來進行逃避而已,”這也是《腫瘤君》《小紅花》在疾病的病痛體驗層面,無法引起觀眾認可的原因之一。
韓延影片中的疾病敘事,弱化了苦難敘事中的仇恨與丑惡,但其對于關注對象一《腫瘤君》《小紅花》《我愛你!》《搖太陽》——大都是少數病患群體而言,仍以一種積極向上的態度,壓縮了疾病帶來的苦難與悲愴性,強化了個體面對疾病時心態由消極轉向積極的過程。這使得韓延作品中的疾病帶有一種溫暖現實的色彩,呈現出鮮明的療愈特質。
三、群體共情的生命意識與溫暖現實主義
在接受采訪時,韓延稱自己并不想用那種特別苦情的手法去拍病患,因為自己本身是一個悲觀的性格,希望拍攝一些積極、樂觀的東西。在上述理念的支撐下,韓延的“生命三部曲”多以喜劇的外殼,講述病患之間相互激勵的溫情故事。《我們一起搖太陽》既保持了紀實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引起了群體共情的生命意識,同時也以虛構的表現手法,展現出病患之間的相互慰藉,在疾病與生命之間發掘人性的溫度。
首先,病患題材的電影本質上隸屬現實主義題材,其創作必然要遵從現實社會的邏輯,這樣才能使得觀眾對影片中展現的生命意識產生共情。《搖太陽》的真實性體現在影片以日常生活細節鋪陳病患角色的生活。這一點在韓延的采訪中也有體現。“在創作之初,韓延就為影片定下了一個基調:無限貼近生活,不沉重,充滿溫暖,底色是生活本身。”這就需要“大量的生活細節,真的慢性病人的生活細節,那是你編不了的。我們用了大概一年的時間做采訪,去了解這些病患的點點滴滴。”在影片中,凌敏作為病患,在飲食上的小心翼翼以及家中停電致使其生活節奏被打亂之后的崩潰;作為病患的家人,呂途的母親因其術后昏迷長達20多天的等待中,染上酗酒的毛病等等。在這一層面,《搖太陽》的疾病敘事既脫離了桑塔格意義上的疾病隱喻,也不同于福科在《瘋癲與文明》以及《不正常的人》中以權力機制闡釋疾病,而是“盡量貼合日常生活體驗的同時,極大程度地調動觀影者對疾病及其衍生的災難的恐懼,進而使觀眾對角色產生精神的共情。”無論是在《腫瘤君》中,熊頓在患病之后,仍然保持對生活的熱愛;還是《小紅花》馬小遠將活著的樂觀與希望傳遞給韋一航:《搖太陽》中凌敏與呂途之間的互相救贖,“生命三部曲”采用了“喜劇片的快樂共情,更為重要的是這里的‘笑不但中和了‘淚,還將故事主題推向了‘獻給積極生活的我們的社會情緒,”符合情感邏輯的真實,是影片能夠引起群體共情的重要原因。
其次,《我們一起搖太陽》以日常細節夯實真實的疾病敘述過程中,也以虛構的手法,奠定了影片的溫暖現實主義的基調。談到電影的“虛構”問題,一是“所指層面的虛構性”,二是“能指層面的虛構性”。前者指向的是故事的情感與意義,后者則是故事中的人物、敘述者以及事件等。在韓延的“生命三部曲”中,真實與虛構是疾病敘事的兩個相互依存的兩個方面。《搖太陽》也不例外,影片結尾,呂途在凌敏的勸說之下接受手術,并決定以一種積極的心態繼續等待腎源。這一團圓式的結尾,雖然與紀實報道當中故事走向較為一致,但結尾兩人縱情享受人生的情節設定,消除了病患所具有憔悴、虛弱,甚至疼痛的表達虛,構的情節設定在此弱化了角色在疾病面前的真實狀態,這在所指層面體現了創作者致力于展現溫情現實主義的意圖。這種溫情現實主義,也可以看作是對溫暖現實主義批判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即情緒的隱忍與克制以及對人本性的關注,但也缺少了對時代性的把握以及對社會發展中存在問題的病理性剖析,也就很難在更廣泛的領域中“疏解與引導人民情緒”。
影片《我們一起搖太陽》在表達的真實性與虛構當中,完成了引導人們關注社會熱點和關注弱勢群體。韓延執導的影片以積極向上的正能量觸摸生活的肌理,帶給觀眾人性的美好和溫暖,具有撫慰人心的力量,在體現創作者超然的生命體悟之余,實現了現實主義向溫情現實的躍迂。但其批判力度和廣度仍然需要進一步完善。
四、結語
正如在文章的一開始筆者所提到的,韓延在“生命三部曲”中努力的弱化疾病所帶來的悲苦體驗,以一種積極樂觀的姿態講述病患的情感世界、日常生活和社會位置。然而,2024年2月14日,聯瑞影業宣布《搖太陽》退出春節檔,原因是在檔期選擇上出現了重大失誤。其實,這不僅僅是一次檔期選擇上的失誤,其背后是疾病這一題材與受眾興趣點之間的錯位,在溫暖現實主義背后如何平衡“溫暖”與“現實”才是最主要的癥結,再次上映就一定能得到票房的回報嗎?答案仍是未知。截止本文寫作的的2月15日,春節檔上映的八部影片中,只有《飛馳人生2》與《熱辣滾燙》遙遙領先,現實題材的《第二十條》與《搖太陽》普遍遇冷。也許這也是一個癥候性的現象,在當前的語境中我們是否失去了對苦難的共情力?亦或者換個角度想,對于《搖太陽》的反思或許能夠為韓延接下來的創作提供一個更具中國式的創作方案。
責任編輯:劉華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