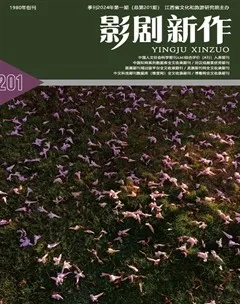苦楝葉的苦澀
邢軍
摘要:印度女導演蘭迪塔·達斯拍攝的《曼托傳》聚焦著名烏爾都語作家薩達特·哈桑·曼托生命的最后十年,以印巴分治這一歷史事件為背景,展示曼托作為一個成長在印度的穆斯林的情感撕裂。電影在記述作家生平重要事件的同時,還以敘事上的獨特手法完成了曼托作品與影片觀眾的“雙重對話”,曼托的精神世界由此獲得更為真實、深入的藝術再現。
關鍵詞:《曼托傳》 傳記電影 印巴分治 精神撕裂 敘事 雙重對話
2018年,印度女導演蘭迪塔·達斯(Nandita Das)拍攝的傳記影片《曼托傳》(Manto,也譯為《芒多傳》)獲得了當年第71屆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一種關注大獎(Un Certain Regard Award)的提名。影片主人公是二十世紀著名的烏爾都語作家薩達特·哈桑·曼托(SaadatHasan Manto,1912-1955)。他一生創作了二十二部短篇小說集、一部長篇小說、五個系列廣播劇、三部散文集和兩部個人速寫集。
1912年,曼托出生于英屬印度的一個穆斯林家庭,22歲時移居孟買開啟了寫作生涯,創作了多篇小說、電影劇本和廣播劇。這些創作為曼托贏得了聲譽,但其對印度底層現實生活尤其是妓女們悲慘遭遇的揭示卻引起巨大爭議。保守勢力以“淫穢”罪對曼托提起了三次訴訟,有的“進步作家”也指責他的創作不夠“光明”。但曼托堅信自己的作品是苦楝葉——“苦澀,但能凈化血液”。他希望他的創作能夠照亮社會的陰暗,能夠激發人們對現實的直視,進而促成當時社會對不公現象的變革。1947年,印巴分治。孟買這座城市開始出現對穆斯林的死亡威脅。曼托被迫離開定居在拉合爾,從印度人變成了巴基斯坦人。此后,他又因為寫作題材與語言觸犯禁忌而被告上法庭三次。作為被迫撕裂的“印度一巴基斯坦人”,曼托精神上的“流亡”體驗成為另一種意義的苦楝葉——他是穆斯林,可印度的影響又綿密地浸潤了他整個的人生。他無法凈化自己的穆斯林血脈,也無法割離印度之于他的深刻烙印。他所能做的,就是在這種撕扯的痛苦中用創作去宣泄、去質疑,以個體的思考抗爭政治利益斗爭的強制高壓。但也因此,他承受了更為巨大的痛苦與絕望,最終在窮困潦倒中死去。電影《曼托傳》就圍繞他這段經歷展開,敘述了他從1946年被指控“有傷風化”到1955年去世的十年人生。
一
作為一部傳記電影,導演蘭迪塔沒有全景式地追溯傳主曼托一生的起伏,而是以其最后十年人生經歷的片斷截取展開情節,包括曼托在孟買和拉哈爾經歷的訴訟官司,與電影制片廠和進步作家群體之間的沖突,與妻子及印度教好友由親密到疏離的痛苦。這幾個片斷的選擇緊緊圍繞1947年印巴分治的歷史背景,在看似松散、碎片化的情節背后是一條真實而殘酷的歷史線一這條線將印度次大陸割裂成兩個國家,也將曼托曾經充實、完整的生活割裂。在這幾個生活片斷的呈現中,除了展示作為作家的曼托的斗爭與痛苦外,導演還細膩地展示了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曼托在歷史巨變前的無力與脆弱。現代傳記電影最重要的一個特征就是剝離名人光環去展示其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生活層面,增加人物經歷的不同側面,使名人傳主以更真實、更豐富、更立體的樣貌呈現在觀眾面前。
影片前半段多次出現曼托與妻子、孩子在一起的場景。在印巴分治前,以“暴躁”“好斗”著稱的曼托在妻子莎菲亞面前溫柔、體貼,琴瑟和鳴。讓人印象深刻的場景是他們坐在草地上一起為陌生人編故事。這一段落中,導演不斷用中景與近景的交替傳遞二人表情中的溫存與深情,鏡頭語言浪漫、溫馨。在孟買期間,兩人經歷了長子早夭的打擊,互為依靠,曼托的寫作事業也得到了妻子的極大支持。夫妻間相濡以沫的情感平衡了曼托在與他人爭執中的易怒、急躁,也拉近了觀眾與曼托的距離,讓觀眾更容易理解人物性格的復雜與變化。而作為作家的曼托在文學創作中對女性的關注與細膩的體察,也可以在其與妻子的相處模式中找到部分緣由。但隨著印巴分治,拉合爾時期的曼托因為酗酒問題與妻子發生沖突。電影中,莎菲亞給曼托讀起他不愿拆開的、來自孟買老友的信。她深知丈夫的痛苦,希望丈夫能夠接受老朋友們的關懷與思念。但孟買的來信讓曼托更加失落。當曼托只為自己的創作焦慮時,莎菲亞直接而尖銳地質問“那活著和在你生命中的人又怎樣?你所有的同情心都用在你的角色身上。”與生命中的友人“一刀兩斷”是曼托無奈的選擇,因為印巴的深刻矛盾讓曾經溫暖的友情與記憶變成了苦澀的苦楝葉,他試圖用虛構的故事與角色來化解痛苦,但每每回到現實,卻發現創作帶來的短暫宣泄并不能帶給他真正的解脫。作為追求寫作藝術完美境界的作家曼托與作為普通穆斯林的曼托在印巴分治后陷入了更深的精神撕裂中。
在對曼托日常生活細節的選擇中,導演的意圖是將曼托生活中個人情感方面的變化與沖突加以集中虛構和再創造,借助其與身邊親人的行為互動和矛盾激化從側面展示印巴分治這一歷史性事件對作家個體心理的深刻影響。“在斯圖亞特·霍爾關于‘文化身份的雙重含義中,我們可以看到文化身份的共有建構性及其在發展過程中的斷裂性,它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包括國家、社會、性別、種族等多層面的身份。當個體對自我的文化身份無法確認,或難以對所屬群體完成判斷和認知時,人物就會產生強烈的孤獨感。”拉合爾時期的曼托與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四處碰壁,只能在酒精的麻醉中度日。導演通過許多中、近景鏡頭表現了曼托的面部表情——迷茫、困惑、痛苦與脆弱。這些表情共同指向了曼托精神深處的孤獨。女兒得重病后,曼托終于對妻子說出,“我會戒酒,為了你”。在極度的精神焦慮與創作困境中,曼托依然留住了對家人的愛,留住了作為丈夫和父親的責任。影片此處安排的細節值得玩味:曼托在去醫院前想最后再抱抱孩子,莎菲亞帶著憐愛與希望的目光,相信丈夫會回來。但為了趕車,曼托最終沒能擁抱到自己的女兒。這或許是作為父親的曼托生命終結前最后的遺憾。導演蘭迪塔在拍攝影片前曾經對曼托的家人進行過訪問。影片中這樣細碎的生活細節對其家人而言或許比他的寫作聲譽更值得被長久的懷念。
現代傳記電影之所以會大量增加對傳主日常生活尤其是與身邊人交往的情節,原因在于對普通觀眾而言,名人傳主的成就高高在上、缺少溫度只可仰望,而其作為普通人的細微而平常的情感起伏卻能喚起觀眾共鳴,讓觀眾與傳主平等對望,代入自己的人生經驗,尋找到與名人的某種同頻共振。《曼托傳》對曼托丈夫、父親與朋友身份的關注和刻畫為觀眾貼近曼托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可能。
二
提到印度電影,很多人馬上會聯想到波折的愛情、熱鬧的歌舞抑或《摔跤吧,爸爸》與“三傻”式的勵志煽情。而《曼托傳》這部影片打破了觀眾對印度電影的刻板想象,以一種“直面”的方式試探性地引導觀眾進入宗教、政治等更深的層面,對迄今仍在深刻影響印巴兩國的歷史事件進行思考。“(傳記)故事片的鏡頭主要集中在一個人物身上,這個人物是真實的,影片就是講述他的故事,同時也是在講述一段歷史”。在印巴沖突依舊不斷的當下,導演蘭斯塔致敬曼托的方式就是將影片創作變成“苦楝葉”,揭開印巴分治的歷史瘡疤,逼人直視,從而呼應曼托一生對文學創作的追求,將其個人經歷的影像回望與歷史深處的民族傷痛交織疊加,提升影片的思想深度。
從歷史上看,南亞次大陸宗教信仰錯綜復雜、影響巨大。“在這里,宗教不僅僅是一種信仰,它還是一種生活方式和民族認同的標識。”千百年來,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教徒的隔閡沖突不斷,攻伐仇殺不斷。盡管英國的殖民統治激起了印度民族意識的覺醒和各階層人民的反抗,但其“民族主義和教派主義這兩根藤幾乎同時發育、同時成長并相互纏繞在一起……(反帝)高潮一過,教派矛盾重新上升。”1947年,印度旁遮普爆發大規模教派暴力沖突并不斷蔓延至其他地區。而英國拋出的“印度獨立方案”使民族宗教矛盾進一步白熱化。在旁遮普的阿姆利則與拉合爾兩個城市發生了大規模的血腥暴亂,印度教徒、錫克教徒與穆斯林教徒之間互相屠殺。“8月17日,邊界判定結果公布后,很多人發現他們所在的地區已經不在‘自己國家,人們在驚慌中開始逃離自己的家園……在不到三個月間,有超過800萬旁遮普人在混亂和恐懼中跨過拉德克利夫邊界。”《曼托傳》所展現的社會背景正是這一時期。
影片開始于1946年,宗教矛盾與沖突尚未影響到曼托。他與印度教徒是好朋友,而他自己“也算不上一個真正的穆斯林”,喝酒吸煙、行為不羈。彼時他創作的焦點是印度底層平民的生活尤其是妓女的悲慘遭遇。這種關注沒有民族宗教的區別差異,而是源于曼托對普遍人性的關懷與悲憫,是作家的責任意識。影片突出了在曼托心中,印度次大陸是一個整體,是生于斯長于斯的故土,這片土地的苦難是全體人民的遭遇,而無論印度教還是穆斯林底層女性的命運是全體人民應當認清并洗刷的恥辱。他反擊批評他只書寫苦難的人,“如果你不能忍受我的故事,是因為我們生活在無法忍受的時代。”作為堅持人道主義的作家,民族主義意識和宗教信仰從未在曼托的內心動搖他的良知與堅持,也從未凌駕于他將人視為平等個體的觀念之上。
但隨著分裂態勢的發展,曼托敏感地意識到時局的變化與危機。導演利用兩個段落表現曼托的變化。一是在他與印度教徒出身的大明星阿肖克進入穆斯林區時,他擔憂阿肖克會被攻擊,拿出穆斯林白帽要戴在頭上,但穆斯林們并沒有攻擊阿肖克,反而熱情表達了對他的喜愛并給他們指出一條安全的道路。這段經歷讓曼托開始意識到分裂的根源不是來自于普通人。第二個重要事件是曼托的印度教好友希亞姆的叔叔一家遭到穆斯林追殺,一家人逃難到孟買。宗教分裂仇殺的事件如此直接真實又血淋淋地暴露在他眼前。希亞姆在激動的憤恨中,與曼托有了如下一段對話:
“那些該死的穆斯林!”
“希亞姆!我也是穆斯林!如果此時有暴亂,你可能會殺死我?”
“我有可能殺死你!”
在這段對話前,曼托正以詩歌的方式反思,“宗教的皮肉被剝去后,骨頭會在哪里燃燒或埋葬?”而希亞姆制止他用文學的語言去表達態度,因為在血腥的悲劇面前,詩歌的語言脆弱蒼白。曼托既感到文學面對殘酷殺戮時的無力,更被希亞姆暴怒下非理性的復仇言語所震驚。曼托明白分裂已不可挽回。他不顧希亞姆的道歉和阻攔,決定離開孟買。電影中二人的對話簡短卻道盡悲哀:
“你只勉強算是個穆斯林!”
“那也足以成為被殺的理由。”
不可彌合、不可逆轉的分裂傷痛就此在曼托的內心深處定格。他永遠告別了孟買,來到巴基斯坦的拉合爾。而他的家族幾代人生活的印度就此成為異國他鄉。他曾經的歡愉、理想、事業,都像被送行的希亞姆扔掉的、二人共飲的那瓶酒一樣,消失在混亂、恐懼、不知所措的逃難人群中。正如電影片頭中曼托名字的分割設計所象征的,曼托自此分裂成兩半。“從社會公眾層面而言,傳記電影往往是大多數人認識傳主、了解史實的重要方式”。電影借助曼托的人生,使印巴分治的民族傷痛再次顯影于歷史前臺,鏡鑒當下的世界。此外,觀眾也會發現在《曼托傳》中,導演蘭迪塔的創作重心不是對政治、宗教做出孰是孰非的評判,而是更關注如何用影像折射微小個體的生命史,將被歷史與政治話語遮蔽的個體生命的感知和價值放大,引發觀眾思考宏闊歷史之下個體命運的飄零和破碎。
三
在相對客觀的個人經歷與歷史呈現之外,《曼托傳》作為一部為作家立傳的電影也具有獨特的“文學氣質”。這氣質源于曼托的文學創作,是他精神維度的展現,也是他豐富、獨特,超越世俗日常的魅力所在。如何去展示曼托的作品,去揭示作家與其創作之間的聯系至關重要。曼托的作品在傳記影片中到底僅僅是一個背景、一種修飾,還是將其彼時的人生經歷與觀眾現時的思考與審美體驗相聯的關鍵?導演蘭迪塔做出了自己的敘述選擇。
在《曼托傳》中,蘭迪塔追溯了曼托作為一個現實主義作家的意義與深度。這也是在曼托去世半個多世紀后,又重新被讀者認可的根源。從敘事技巧上看,導演通過三種方式來全面呈現曼托的寫作與思想。一是通過曼托自己的陳述。比如曼托對自己一直備受爭議的創作題材的辯解和所堅持的創作觀就是通過法庭自辯的方式直接呈現。“文學從不淫穢。為什么不能把現實呈現出來?我只是寫出我知道和我看見的事。否認現實會讓我們成為更好的人嗎?我的故事是鏡子,讓社會看清楚自己的面目。”而面對妻子抱怨他過于關注創作時,曼托堅定地說出“最后剩下的只有故事和里面的角色”,則顯示出他對文學意義和力量具有永恒性和超越性的堅信。這種讓傳主自己陳述表達的方式直接、純粹,具有“現場感”和交流的意味,提升了電影對人物表現的真實性。
影片表現曼托創作的第二種方式就是“借他人之口”。電影中有一個段落是一個街頭小販給身邊人朗讀報紙上刊登的曼托的代表作《給山姆叔叔的信》:
我出生在一個現在位于印度的地方。我的媽媽葬在那里,爸爸也是。我的第一個孩子阿里夫也是埋葬在那里。但那不再是我的國家。現在我的國家是巴基斯坦。跟我的國家一樣,我為了自由被分裂。你可以想象,對翅膀被剪斷的小鳥,自由是什么。
耐人尋味的是,圍觀者在聽到這段詩時表現漠然,而在一旁的曼托的特寫表情卻充滿沉重與復雜。曼托作品在當時的社會與宗教語境下的接受困境可見一斑。同時,影片中還利用身邊的人與曼托的辯論或者報紙評論來展現曼托寫作的社會文化環境,凸顯他堅持自己創作方向的艱難。
《曼托傳》表現曼托作品的第三種方式就是讓他創作的故事直接“表演”在銀幕上,與電影對曼托人生經歷的敘述形成敘事上的并置。影片的開場就是曼托小說《呼吸》中的情節。許多不熟悉曼托的觀眾可能會對第一個敘事段落的跳轉很不適應,停頓一下才發現是曼托虛構的故事與其現實的人生之間的續接。整部電影共有四處采用了這樣的敘事方式,造成一種“戲中戲”的敘事效果。而電影結尾對曼托作品的借用,更是有意抹掉了現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以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療的曼托的視角直接引出他所創作的印巴在邊界交換精神病人的故事,制造出曼托也是故事中一員的錯覺:一車精神病人被拉到印巴邊界等待交換,其中一個印度教老人對自己的故鄉多巴代格辛格念念不忘,想要回家。印度軍人告訴老人多巴代格辛格現在屬于巴基斯坦,老人想過邊界,卻被巴基斯坦軍人制止。老人躺倒在兩國邊界間的空地上,徹底崩潰。而后作為故事作者的曼托進入到畫面,繼續敘說,“那個用雙腿站了十五年的男人,現在躺在地上。那邊,在帶刺鐵絲網后面是印度。這邊,在帶刺的鐵絲網后面是巴基斯坦。中間一塊沒有名字的土地上——就是多巴代格辛格。”隨后,印度斯坦、巴基斯坦的混亂聲音嘈雜響起,電影在曼托直視觀眾的悲愴而又審視的特寫目光中戛然而止,絕然有力。畫面上出現落幕的說明:“Saadat Hasan died at 42, Manto liveson.(薩達特·哈桑于42歲逝世,曼托繼續存活。)”這個喻指再明晰不過:曼托作為作家的藝術生命永久超越了他的肉體生命!同時也呼應了之前片中曼托倔強的聲明“最后剩下的,只有故事和里面的角色。”文學藝術創作的永恒性與超越性再次被強調,為曼托一生的追求做了最清晰的總結。
在電影中讓曼托的文學作品直接呈現,與曼托的真實生活交疊的敘事方式打破了現實層面的敘述連貫性,造成了一定的觀影障礙。而導演顯然希望能借此“錯位”實現對曼托作家身份意義的聚焦。在筆者看來,這種利用“戲中戲”模糊真實與創作、現實與虛構界限的方式在電影的內部敘事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雙重對話”。
首先一重“對話”是曼托作為作家與觀眾的對話。與采用人物敘述或畫外音介紹的方式不同,在呈現曼托生活層面故事的同時直接插入其作品,可以造成一種間離效果,使觀眾從人物現實經歷的觀看慣性中跳出,從作品的直接展示中思考文學創作的意義,而這恰好是曼托作為作家最為重視和在意的根本。
另一重“對話”是歷史記憶與當下觀眾的對話。這一層對話的形成源于曼托作品的現實性。他的作品都是對當時英屬印度社會現實和印巴分治中的社會動蕩的再現,曼托沒有回避殘酷與黑暗。導演讓曼托的小說直接在大銀幕展現,包括其中涉及的暴力場面,也是借助更具感官沖擊力的影像掀開歷史記憶的一角。曼托曾強調“我的故事是鏡子,讓社會看清楚自己的面目”。導演正是利用曼托作品的直接展示形成一面突破觀眾對名人生活好奇心理的“鏡子”,讓觀眾直面那個時代的社會悲劇,直面曼托作品中那些普通印巴百姓的苦難。
導演蘭迪塔在影片中對曼托作品與思想的多角度、多方式的展現,充分說明導演不僅僅是在獵奇一個名人的生平,更是在深挖一個作家的藝術追求與其所具有的時代意義。盡管在個別段落的轉場有失生硬,但導演明確的創作目的和對人物思想與文化意義的立體式構建依然值得肯定。
結語
作為傳記電影,《曼托傳》的時間設定局限在十年之間,省略了曼托成為作家前的經歷,也缺失了“是什么鑄就了這樣的曼托?”的追問,但影片以一種底色凝重又不乏激越的抒情方式將作為普通穆斯林的曼托與作家曼托一起呈現給了觀眾,完成了傳記類電影的核心功能——“引領人們從某個角度了解傳主的人生,進而產生對他或她持續跟進的興趣。”作為一個影響力受到語言與地域局限的作家,曼托能夠因為《曼托傳》而被異域的觀眾重新發現和了解,這是影片創作團隊對曼托的最好紀念和致敬。
從1947年印巴分治開始,兩國之間的紛爭依舊,平民仍然是教派撕裂的犧牲品。曼托的痛苦與追問至今仍具深意。曼托曾把自己的創作比作“苦楝葉苦澀,但能凈化血液”。而蘭迪塔·達斯顯然遵循著曼托的藝術之路,以影像藝術的方式祭奠了印巴之間如苦楝葉般苦澀的歷史記憶和政治傷痛,不制造虛幻、不回避沉重。蘭迪塔借助曼托的經歷在追問:七十多年過去了,曼托時代所遭遇的殘酷撕裂是否將成為南亞次大陸永久的瘡疤,永久的絕望?多少令人欣慰的是,作為巴基斯坦穆斯林的曼托去世幾十年后,欣賞他的作品,理解他的痛苦,延續他的思考,讓他的人生得到更多關注的蘭迪塔·達斯一來自印度。
責任編輯:王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