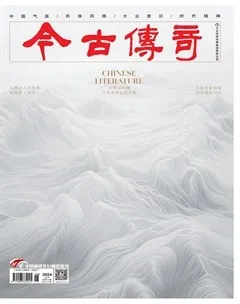范仲淹在鄧州
陽春
在來鄧州之前,我對這片土地充滿了好奇:這該是一個怎樣神奇的地方啊?讓范仲淹對它流連忘返、依依不舍,并且在這里寫下了震爍古今的名篇《岳陽樓記》!
我的好奇,跟隨著我一起來到了鄧州。短短兩天的行程里,伴隨著當地文化學者的講解,白天一步步實地參觀了重修的花洲書院,晚間在夜市攤點上感受著當地淳樸的煙火氣息,我此前的種種好奇仿佛也得到了答案。
范仲淹無疑是中華歷史上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文化人,元初一代文宗元好問曾經稱贊他:“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在朝廷則有孔子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
然而,誰又能想到,這樣一個能文能武號稱無所不能的“全才”,竟然還是一個“刺頭”和“杠精”呢?充斥在他前半生里最多的一個詞,就是“不和解”!
我能想象得到范仲淹從童年到少年時代的心路歷程。
他擁有的是一個“稀碎”的童年:兩歲跟隨寡母改嫁到朱氏,得名朱說。待他懂事后,朱家子弟直言,你不是我們朱家的后代,不配享受我們的錢財。范仲淹聽完后默然離開繼父的家,居住在寺廟里苦讀,期待有一天能金榜題名。
那個時候,在寺廟里每天只喝一碗稀粥的范仲淹,作為寒門學子的榜樣,親力親為地為后世讀書人創造了一個成語——斷齏畫粥;那個時候,面對唯有讀書才能改變自身命運的范仲淹,期待“東華門唱名”那一天的到來,以求改姓歸宗、迎母侍養;那個時候的范仲淹,就像一棵被大風吹到懸崖峭壁上的小樹苗,有可能存活,但是幾乎不可能成長為棟梁之材。我甚至能想象得到,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范仲淹,沒有心理扭曲、行事偏激,已經算是僥幸了。
事實上,這種環境下的副作用還是很突出的。那就是成年之后特別是科舉高中后的范仲淹一直以“懟人”的模式存在于朝廷之中。章獻太后劉娥執掌朝政的時候,范仲淹上書請求太后還政于仁宗。結果是范仲淹被貶。劉娥去世,仁宗執政后,將范仲淹召回。讓仁宗想不到的是,范仲淹這個“自己人”,返京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懟自己”:仁宗要廢黜郭皇后,第一個跳出來反對的竟是范仲淹。沒辦法,范仲淹繼續被貶。
好在,三年后返回開封擔任京兆尹的范仲淹這次懟的對象不再是皇帝仁宗了,而是一人之下的宰相呂夷簡。范仲淹進獻百官圖,直指呂夷簡任人唯私。好吧,范仲淹,您繼續被貶。
為此,好友梅堯臣寫詩勸他不要當個啄木鳥,他寫《靈烏賦》答復,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這就是范仲淹的個性。當然了,有本事的人不會永遠沉默。當大宋與西夏邊境戰事爆發后,范仲淹再一次被仁宗征召,經略陜西。當西線戰事逐漸平靜下來之后,范仲淹終于迎來了仕途上的最高光——返京擔任樞密院副使,后拜參知政事,這是副相的職位。
然而,這既是范仲淹仕途的巔峰時刻,也是他徹底走向落幕的開始。擔任副相的范仲淹這次“懟”的對象不再是臨朝執政的太后、仁宗和宰相,而是整個執政體系——他發動了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政治改革運動——慶歷新政。
結果自然不言而喻,一年的時間,慶歷新政失敗,改革人物紛紛被貶斥出京。也就在這個時候,范仲淹想起了鄧州,把這個地方當作了自己舔傷休養的蟄伏之地。
慶歷五年正月,五十七歲的范仲淹被罷免參知政事后,向宋仁宗上《陳乞鄧州狀》求解邊任,“伏望圣慈恕臣之無功,察臣之多病,許從善地,就訪良醫,于河中府、同州或京西襄、鄧之間就移一知州,取便路赴任”。
范仲淹向往鄧州的理由很充分:我的肺病一到了秋冬就發作,希望您讓我去鄧州附近尋醫療養。
鄧州,北宋的京輔之地,也是一代名醫張仲景的故鄉。按照醫術代代相傳的習俗,去名醫的家鄉尋找治病良方肯定是個不錯的方式。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鄧州“六山障列,七水環流,舟車會通,地稱陸海”,本身就是一個適宜病人療養的好地方。
就這樣,拖著帶病之身,范仲淹于慶歷五年十月十四日,帶著體弱的長子范純祐從陜西邠州南下,赴任鄧州。
這一刻,是范仲淹的幸運。這一刻,是鄧州的幸運。這一刻,是滕子京和岳陽樓的幸運。這一刻,更是范仲淹之后中華民族千千萬萬讀書人的幸運。
知鄧州的第二年也即慶歷六年六月十五日,范仲淹收到了至交滕子京的書信,滕子京在信中請求老友為他新修的岳陽樓寫一篇記文。擔心范仲淹拒絕,滕子京在信中言辭懇切,并且帶上了“感情綁架”的句子,“竊以為天下郡國,非有山水環異者不為勝,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甚至害怕范仲淹找理由推辭,他還妥帖地附上了《洞庭秋晚圖》供其參照。
滕子京不愧是范仲淹的至交,他深知此時的范仲淹也許有些心灰意冷,更不想在詩詞歌賦上鼓搗些是非風云。畢竟,此時的范仲淹已經五十八歲了。多次貶謫的宦海沉浮,加上肺病纏身,已經讓這個當年的“刺頭”少了許多棱角。這從他近些年在西北戍邊的詩詞里可見一斑:無論是《漁家傲·秋思》里的“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還是《蘇幕遮·碧云天》里的“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都可以看出此時的范仲淹不再有少年的蓬勃朝氣,而更像一個思念故鄉的垂垂老者。
那么,范仲淹的故鄉又是哪里呢?是他的祖籍陜西邠州?是父親生活的江蘇吳縣?是繼父朱氏生活的山東長山?或者是青少年讀書時候的河南商丘?都不是。這一刻,范仲淹真的是把寄身的鄧州當作了自己的家鄉。
在鄧州,范仲淹把昔日供達官貴人游玩的百花洲景區改造成花洲書院,以知州的身份,公務之余親自授課講學。在鄧州,范仲淹在原配去世多年后,還迎娶了新婚妻子,并且誕下了第四個兒子范純粹。一切的一切,都表明此刻的范仲淹似乎有醉心傳道授業、享受天倫之樂、寄情山水之間的退休狀態。
那么,不給滕子京寫關于岳陽樓的記文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事實是,范仲淹真的沒有給滕子京寫這篇記文。至少是整整三個月的時間里,范仲淹沒有去動筆。
也許,范仲淹真的是倦了前半生的貶謫流離,也厭了廟堂上的唇槍舌劍、邊塞上的刀光劍影。假設沒有三個月后的那場驚雷,假設沒有被驚雷震醒后的胸懷激蕩,假設沒有激蕩后的奮筆疾書,也許就沒有現在這么豐滿的范仲淹了。
也許岳陽樓在國人心目中的美名要直接腰斬一半。
也許鄧州就會變得平淡無奇,只是范仲淹貶謫路上眾多地名中不起眼的一個,而不是現在伴隨在范仲淹身邊最璀璨奪目的那一顆明星。
如果說蘇軾一生功業盡在“黃州惠州儋州”,而范仲淹一個“鄧州”就足以媲美。
好在,沒有出現假設。那場驚雷在三個月后的九月十五日還是降臨了,伴隨而來的還有那千古名篇《岳陽樓記》。那一出現就震動北宋文壇的《岳陽樓記》,那讓此后數百年間所有讀書人慷慨激昂的《岳陽樓記》,那讓今天所有中學生必須背誦的《岳陽樓記》,就這樣在鄧州花洲書院誕生了。
果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還是那個“自帶光芒不畏權貴”的“愣頭青”,還是《宋史》記載中那個“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的“刺頭”。
當然,和此前自己那些鋒芒畢露的諫言不同,范仲淹的這篇《岳陽樓記》雖然去掉了尖刺,卻依舊內蘊犀利,仿佛紅彤彤的鐵塊經過淬火后變成了堅韌的精鋼。
或許鄧州,就是讓范仲淹淬去火氣的那潭冷水。
三十多年后,蘇東坡寫下了“此心安處是吾鄉”的詞句。
鄧州,即是范仲淹的“吾鄉”。
(責任編輯 丁怡1596371626@qq.com)
也許,范仲淹真的是倦了前半生的貶謫流離,也厭了廟堂上的唇槍舌劍、邊塞上的刀光劍影。假設沒有三個月后的那場驚雷,假設沒有被驚雷震醒后的胸懷激蕩,假設沒有激蕩后的奮筆疾書,也許就沒有現在這么豐滿的范仲淹了。
- 今古傳奇·當代文學的其它文章
- 失蹤的父親
- 訪談
- 天山,蒼茫的不只是明月
- 去天山
- 天山行
- 日常生活的審美反思與吟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