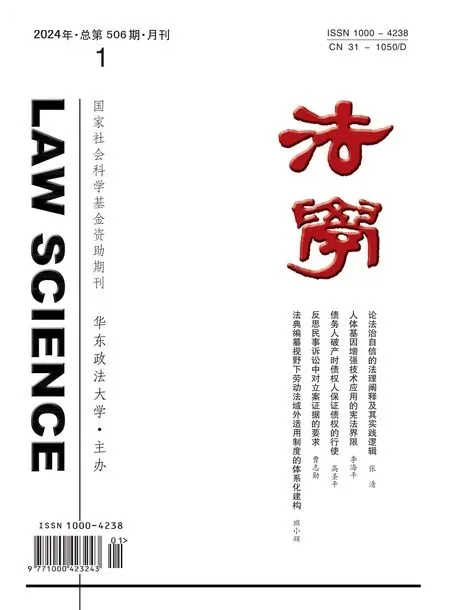反思民事訴訟中對(duì)立案證據(jù)的要求
●曹志勛
一、民事訴訟“立案難”中的立案證據(jù)問題
自2015 年立案程序改革以來,尤其隨著跨域立案、網(wǎng)上立案、移動(dòng)微法院等司法便民措施的逐步推廣,“立案難得到解決”〔1〕周強(qiáng):《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bào)告——2021 年3 月8 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ì)第四次會(huì)議上》,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lh/2021-03/15/c_1127212486.htm,2023 年11 月24 日訪問。成為在社會(huì)上得到廣泛傳播的基本判斷。法院系統(tǒng)聲勢(shì)浩大地“堅(jiān)決整治年底不立案,嚴(yán)禁拖延立案、限制立案、以調(diào)代立、增設(shè)門檻……群眾反映長(zhǎng)期存在的年底不立案得到有效整治”;〔2〕周強(qiáng):《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bào)告——2022 年3 月8 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ì)第五次會(huì)議上》,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51111.html,2023 年11 月24 日訪問。2023 年3 月最新發(f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bào)告》則不再認(rèn)為存在“立案難”問題,而是進(jìn)一步指出要深化改革,“在全面實(shí)行立案登記制、破解長(zhǎng)期以來群眾解紛立案‘門難進(jìn)’問題后,還要讓群眾化解矛盾‘事好辦’”。〔3〕周強(qiáng):《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bào)告——2023 年3 月7 日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ì)第一次會(huì)議上》,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91381.html,2023 年11 月24 日訪問。不過,上述整治運(yùn)動(dòng)的間歇性即體現(xiàn)出相關(guān)問題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在實(shí)踐中成為“保留節(jié)目”,成為當(dāng)事人和律師普遍“不吐不快”的真實(shí)問題。〔4〕參見河南省高級(jí)人民法院(2021)豫民再535 號(hào)民事裁定書(該案為“串案”之一)。這一問題在各地實(shí)踐中或者與某些金融企業(yè)或協(xié)調(diào)解決的“專班”有關(guān),或者與訴前調(diào)解的“靜置”捆綁,抑或?qū)ν粋€(gè)法院的AB 窗口、立案庭與審判庭也同樣適用。甚至在某些熱門地區(qū),審判法官不得不為當(dāng)年年底前審理完上一年立的案件而努力,而“簡(jiǎn)易轉(zhuǎn)普通”的程序選項(xiàng)則被(繼續(xù))用于合法地延長(zhǎng)審限。
如今,這一立案審查更可能因?yàn)榫€上立案的“遠(yuǎn)程”讓使用者感到被“程序”統(tǒng)治。潛在的當(dāng)事人通過在線系統(tǒng)登記立案時(shí)獲得了數(shù)字編號(hào)(而非案號(hào)),起訴被線上駁回時(shí)似乎也不會(huì)被計(jì)入法院民事案件的數(shù)量,進(jìn)而也無所謂保障當(dāng)事人對(duì)不予立案裁定的救濟(jì)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這類似于之前法院直接將當(dāng)事人的立案材料現(xiàn)場(chǎng)退回的做法,甚至進(jìn)一步凸顯了立案登記所立之“案”與法院立案受理所收之“案”之間的差異與錯(cuò)位。問題的背后浮現(xiàn)的仍然是立案審查制之爭(zhēng)。對(duì)于通過線上或者微信小程序要求立案而被駁回的當(dāng)事人來說,其所享有的至少看起來具有實(shí)體法上理由支持的訴權(quán)仍然無法得到司法救濟(jì)。即使考慮線上新技術(shù),仍需關(guān)注植根于我國司法土壤、關(guān)涉當(dāng)事人訴訟權(quán)利保障的底層問題。因而,即使2023 年最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仍未觸及這一問題,也仍有必要進(jìn)一步整理和拆解我國法上的起訴要求,以要件化和體系化的方式盡可能澄清其中的模糊之處,使立案程序的處理結(jié)果具有更大的可預(yù)測(cè)性。
其中,我國民事訴訟法長(zhǎng)期要求當(dāng)事人在起訴時(shí)就提供一定的證據(jù),即原告通常應(yīng)當(dāng)遞交訴狀和相應(yīng)副本以及提供證據(jù)信息(《民事訴訟法》第123 條第1 款和第124 條第4 項(xiàng))。而在我國多數(shù)學(xué)者看來,這種要求似乎與現(xiàn)行法及政策的內(nèi)在邏輯和比較法上的一般做法不同,立案程序中要求的證據(jù)應(yīng)當(dāng)至多限于程序性要件的證明,〔5〕參見李浩:《民事訴訟法學(xué)》,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202 頁;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學(xué)》,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 年版,第254 頁;王晴:《民事訴訟“起訴證據(jù)”辨析》,載《廣西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8 年第6 期,第70-75 頁。或者法院在立案審查階段根本不應(yīng)要求提交證據(jù)。〔6〕參見蔡虹、李棠潔:《民事立案登記制度的法理省思》,載《法學(xué)論壇》2016 年第4 期,第123-124 頁;熊秋紅:《保障當(dāng)事人訴權(quán) 破解“立案難”》,載《人民法院報(bào)》 2015 年4 月18 日,第2 版;胡亞球、章建生:《起訴權(quán)論》,廈門大學(xué)出版社2012 年版,第89-101 頁;段文波:《論民事一審之立案程序》,載《法學(xué)評(píng)論》2012 年第5 期,第144-145 頁。最高人民法院也指出,法院不應(yīng)實(shí)質(zhì)審查訴訟請(qǐng)求和證據(jù)。〔7〕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訴訟法修改研究小組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 年版,第253-254 頁。其在不同時(shí)期的裁判實(shí)踐中都曾指出,對(duì)應(yīng)現(xiàn)行《民事訴訟法》第122 條的內(nèi)容“是關(guān)于起訴條件的規(guī)定,依據(jù)該條第三項(xiàng)規(guī)定,起訴應(yīng)有‘具體的訴訟請(qǐng)求和事實(shí)、理由’,該條并未對(duì)證據(jù)提出要求。原告提供的證據(jù)能否證明其主張的事實(shí),并進(jìn)而支持其訴訟請(qǐng)求,屬于案件受理后對(duì)案件進(jìn)行實(shí)體審理部分的內(nèi)容”。〔8〕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終320 號(hào)民事裁定書。立案審查“只要求原告從形式上提供一定的事實(shí)、理由”,〔9〕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四終字第15 號(hào)民事裁定書。而不能“要求原告提供足以勝訴的證據(jù),也不應(yīng)在立案階段對(duì)原告訴訟請(qǐng)求能否成立進(jìn)行實(shí)質(zhì)性判斷”,〔10〕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15 號(hào)民事裁定書。不應(yīng)“混淆了訴訟成立要件和權(quán)利保護(hù)要件的區(qū)別”。〔11〕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終605 號(hào)民事裁定書。
在解釋論上固然可以主張《民事訴訟法》第124 條規(guī)定的立案證據(jù)制度只是注意規(guī)定,相關(guān)研究可以“偃旗息鼓”。但是從對(duì)我國法的實(shí)證考察出發(fā),由上述成文法定規(guī)則發(fā)散而來的司法實(shí)踐與個(gè)案裁判規(guī)則,至少相反地督促相關(guān)探討應(yīng)當(dāng)“重整旗鼓”。這不但有助于審視已踐行數(shù)年的立案登記制,而且立案司法審查中形式審查與實(shí)質(zhì)審查之爭(zhēng),也可能出現(xiàn)在案外人執(zhí)行異議的審理、不動(dòng)產(chǎn)登記審查、工商登記甚至創(chuàng)業(yè)板注冊(cè)制改革等領(lǐng)域,立案審查思路在其他領(lǐng)域中也具有擴(kuò)張和發(fā)散的潛質(zhì)。立案證據(jù)要求本身立足于民事訴訟的起訴與訴訟要件,但其影響顯然不限于此。位于訴訟程序建構(gòu)原理與證據(jù)和事實(shí)發(fā)現(xiàn)領(lǐng)域之間,立案證據(jù)要求也與民事訴訟各階段的功能界分和證據(jù)調(diào)查程序的體系優(yōu)化緊密聯(lián)系。
如果當(dāng)事人并未主動(dòng)提交立案證據(jù),法院在立案階段應(yīng)否要求其提交?如果原則上不應(yīng)收集,那么應(yīng)當(dāng)最早推遲到什么階段再收集?如果存在例外,其收集對(duì)象是什么,邊界何在?為了達(dá)到這一兼具駁論與立論的目標(biāo),有必要在關(guān)注比較法既有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上,找尋現(xiàn)有立案證據(jù)要求的規(guī)范基礎(chǔ)與理論定位,并確定民事訴訟類型化建構(gòu)中的“原則”與“例外”情形。在這一意義上,不應(yīng)滿足于比較法真正意義上的立案登記制不要求提交證據(jù)的“常識(shí)”結(jié)論,而需關(guān)注證據(jù)收集的應(yīng)然定位和由我國經(jīng)驗(yàn)出發(fā)可得的上述“常識(shí)”的例外。
二、現(xiàn)行法上的立案證據(jù)要求及其考察
(一)我國現(xiàn)行法對(duì)立案證據(jù)的要求
我國現(xiàn)行法對(duì)立案證據(jù)的要求具有相當(dāng)穩(wěn)定性。從1982 年《民事訴訟法(試行)》第82 條第1款、第83 條第3 項(xiàng)和1991 年《民事訴訟法》第109 條第1 款、第110 條第3 項(xiàng)的規(guī)定可以發(fā)現(xiàn),自改革開放以來,《民事訴訟法》就立案證據(jù)制度的規(guī)定未曾改變。最高人民法院對(duì)此的解讀是:“起訴狀中應(yīng)列明原告擬向法院提交的證據(jù)及證據(jù)來源,一般應(yīng)制作證據(jù)目錄,證據(jù)來源用于說明證據(jù)的合法性。原告申請(qǐng)證人出庭作證的,應(yīng)寫明證人姓名和住所。”〔12〕江必新主編:《新民事訴訟法條文理解與適用》(上冊(c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2 年版,第578 頁。
與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以下簡(jiǎn)稱《證據(jù)規(guī)定》)第1 條相同,2019 年修改后的《證據(jù)規(guī)定》第1 條繼續(xù)申明,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訴或者被告提出反訴,應(yīng)當(dāng)提供符合起訴條件的相應(yīng)的“證據(jù)”。在立案登記制改革的設(shè)計(jì)中,現(xiàn)行法同樣也規(guī)定原告應(yīng)當(dāng)提交相關(guān)“材料”[《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人民法院登記立案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以下簡(jiǎn)稱《登記立案規(guī)定》)第6 條]。在具體表述中被使用的“證據(jù)”“證據(jù)材料”“材料”或者“證明材料”看似存在區(qū)分不同概念及其含義的必要,但是,尤其應(yīng)當(dāng)考慮無論哪種代表性觀點(diǎn),都不要求法院將證據(jù)審查與評(píng)價(jià)“完全地”提前至立案階段。那么,即使認(rèn)為“證據(jù)”一詞通常應(yīng)當(dāng)是指法院審核后的證據(jù)/證明材料,在這一意義上理解上述條文中的用語也不可能。而且,針對(duì)2019 年《證據(jù)規(guī)定》第1 條的規(guī)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官方釋義書也將上述用語不加區(qū)分地混用,〔13〕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訴訟證據(jù)規(guī)定理解與適用》(上冊(c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72-78 頁。這部分體現(xiàn)了司法解釋起草機(jī)關(guān)的隱含見解。
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將提交證據(jù)的范圍限定于主要證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暫行規(guī)定》(以下簡(jiǎn)稱《立案規(guī)定》,已失效)第9 條前句],目前則將其限縮為“與訴請(qǐng)相關(guān)的證據(jù)或者證明材料”(《登記立案規(guī)定》第6 條第5 項(xiàng))。這種要求在特殊類型案件中仍然存在。例如,2020年修訂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以下簡(jiǎn)稱《民間借貸規(guī)定》)第2 條第1 款規(guī)定,為了證明借貸法律關(guān)系存在,起訴人應(yīng)當(dāng)提供借據(jù)、收據(jù)、欠條等債權(quán)憑證和其他證據(jù)。此處的其他證據(jù)包括書證以外的證據(jù),例如當(dāng)事人陳述和證人證言。〔14〕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 年版,第69、77-78 頁。在實(shí)務(wù)中,如果相關(guān)當(dāng)事人在起訴時(shí)拒絕提供結(jié)婚證證明婚姻關(guān)系存在,立案法官很可能直接退回立案材料。
同時(shí),立案證據(jù)的要求可能與訴前/立案前調(diào)解制度相關(guān)聯(lián)。由委派調(diào)解深化而來的訴前調(diào)解制度是我國司法機(jī)關(guān)近年來大力建設(shè)和推廣的一站式多元解紛機(jī)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也可能涉及對(duì)訴前證據(jù)的要求。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21 年發(fā)布的《人民法院在線調(diào)解規(guī)則》第26 條規(guī)定,立案前調(diào)解需要鑒定評(píng)估的,有關(guān)人員可以告知當(dāng)事人訴前委托鑒定程序。這種情況對(duì)應(yīng)的案件類型以2020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進(jìn)一步完善委派調(diào)解機(jī)制的指導(dǎo)意見》第7 條的初始規(guī)定和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訴前調(diào)解中委托鑒定工作規(guī)程(試行)》第3 條的擴(kuò)大規(guī)定為例,其代表是交通事故賠償、醫(yī)療損害賠償?shù)壬婕皩iT性問題的常見糾紛。這種訴前鑒定雖然并非法定必須提交立案證據(jù)的情形,但是如果相關(guān)法院?jiǎn)?dòng)了如上訴前調(diào)解程序,在客觀上就會(huì)使立案前證據(jù)成為法院正式啟動(dòng)民事訴訟的條件。如果考慮到立案前調(diào)解(訴訟調(diào)解亦然)被恣意啟動(dòng)或者久拖不決可能妨礙當(dāng)事人行使訴權(quán)的一些做法,那么此種對(duì)訴前鑒定的要求甚至在實(shí)然意義上會(huì)成為本文討論的立案證據(jù)要件的組成部分。
在司法實(shí)踐中,很多當(dāng)事人及其律師考慮到勝訴判決未來順利執(zhí)行的可能性,因而在起訴的同時(shí)提交財(cái)產(chǎn)保全的申請(qǐng)書。雖然就此而言財(cái)產(chǎn)保全也要求當(dāng)事人提供包括證據(jù)材料在內(nèi)的材料(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人民法院辦理財(cái)產(chǎn)保全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1 條第1 款),但是這并非民事訴訟立案程序的一般性要求,因而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之內(nèi)。
(二)立案證據(jù)要求的具體標(biāo)準(zhǔn)不明確
通常而言,立案前階段的起訴條件具有高階化〔15〕代表性觀點(diǎn),例見張衛(wèi)平:《起訴條件與實(shí)體判決要件》,載《法學(xué)研究》2004 年第6 期,第59 頁。的特征,原則上涵蓋大陸法系傳統(tǒng)下的所有訴訟要件,并且與立案后階段的審查適用同一套標(biāo)準(zhǔn)[《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jiǎn)稱《民訴解釋》)第208 條第3 款]。于是,被告答辯后法院在判斷案件應(yīng)否進(jìn)入實(shí)體審理時(shí)形成的裁判規(guī)則,在解釋論上也應(yīng)當(dāng)適用于立案前的起訴要件審查。易言之,縱使由于在被告參與與否、證據(jù)材料多少和審查時(shí)間長(zhǎng)短上的差異,裁判規(guī)則的適用場(chǎng)景可能有實(shí)質(zhì)不同,但是在不同訴訟階段也都適用相同的裁判規(guī)則。
在完全不審查起訴要件與達(dá)到實(shí)體勝訴標(biāo)準(zhǔn)的實(shí)質(zhì)審查之間,司法實(shí)務(wù)中可能存在不同的中間狀態(tài)。作為一種實(shí)務(wù)中通行的理解,我國最高審判機(jī)關(guān)曾在審查當(dāng)事人適格、特殊地域管轄的連接點(diǎn)、級(jí)別管轄標(biāo)準(zhǔn)時(shí)明確要求形式審查和初步證據(jù),即必須至少有一定證據(jù)支持。〔16〕參見曹志勛:《民事訴訟中的雙重相關(guān)事實(shí)——“初步證據(jù)”向“假定為真”的轉(zhuǎn)變》,載《環(huán)球法律評(píng)論》2021 年第1 期,第118-121 頁。根據(jù)2019 年《證據(jù)規(guī)定》第1 條,“說明原告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guān)系的證據(jù)材料、支持訴求之事實(shí)和理由的證明材料屬于作為起訴基礎(chǔ)條件的必要材料”,其“全部使命就是要證明民事權(quán)益爭(zhēng)議存在的客觀性、已然性和利益相關(guān)性”,法院“只是作一些法律上和形式上的初步審查,而不對(duì)其真實(shí)性作實(shí)質(zhì)審查”,同時(shí)其“有利于支持訴求的證據(jù)及其他材料,這些材料的多少及其證明效力不影響案件的立案受理”。〔17〕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訴訟證據(jù)規(guī)定理解與適用》(上冊(c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第75、78 頁。
但是,暫且不論諸如在線立案中是否必須將文件合并掃描或者必須掃描方向正確這樣純粹形式性、流程性的證據(jù)要求,前述標(biāo)準(zhǔn)應(yīng)當(dāng)如何認(rèn)定,常常因案而異、因人而異,缺乏統(tǒng)一的識(shí)別標(biāo)準(zhǔn)。例如,從否定起訴證據(jù)要求的角度看,“未能舉證證明存在借款關(guān)系”的情形本應(yīng)符合立案審查要件的要求(尤其是直接利害關(guān)系要件),案件應(yīng)當(dāng)進(jìn)入實(shí)體審理。〔18〕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四終字第32 號(hào)民事裁定書。就尾礦庫是否存在安全隱患的鑒定也屬于實(shí)體審理的內(nèi)容,而不宜作為立案審查要件的內(nèi)容。〔19〕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一終字第73 號(hào)民事裁定書。而在下級(jí)法院的司法實(shí)踐中,也有法院在立案階段就要求原告承擔(dān)證明責(zé)任,〔20〕參見北京市第二中級(jí)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終字第06274 號(hào)民事裁定書。或者在委托法律關(guān)系中,原告“沒有證據(jù)證明被起訴人的一方住所地或者合同的履行地在本院管轄區(qū)域內(nèi)”,將會(huì)被裁定不予受理。〔21〕廣東省高級(jí)人民法院(2019)粵民初33 號(hào)民事裁定書。再如,針對(duì)《民間借貸規(guī)定》第2 條第1 款的規(guī)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官方釋義書既強(qiáng)調(diào)“只審查起訴證據(jù)能否表明當(dāng)事人身份或者爭(zhēng)議的事項(xiàng)是什么……不考察起訴證據(jù)與本案事實(shí)之間有多大程度的關(guān)聯(lián)”,又將結(jié)果意義上的證明責(zé)任與裁定不予受理作為不提供相應(yīng)證據(jù)的后果。這至少從一個(gè)側(cè)面體現(xiàn)了上述認(rèn)識(shí)不統(tǒng)一的狀況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22〕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 年版,第66-68 頁。甚至在最高人民法院直接以“訴請(qǐng)所依據(jù)的事實(shí)并非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guān)系和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其訴求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為由裁定駁回上訴時(shí),〔23〕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終826 號(hào)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在審查再審申請(qǐng)時(shí)卻反而表示原告“未提供證據(jù)證明……存在平等主體之間的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和人身關(guān)系,……訴訟請(qǐng)求不屬于人民法院民事訴訟的受理范圍,原裁定認(rèn)定的事實(shí)具有證據(jù)支持”。〔24〕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5502 號(hào)民事裁定書。如果認(rèn)為裁定說理并非“套路”和“套話”,在來自同一法院不同合議庭的兩份裁定中,一份直接以相應(yīng)程序性事實(shí)超出法院主管范圍為由,另一份則進(jìn)而以缺乏證據(jù)為落腳點(diǎn),體現(xiàn)了兩者在提供證據(jù)是否必要這一問題上明顯不同的認(rèn)識(shí)。
(三)我國司法實(shí)踐對(duì)立案證據(jù)的需求
無論是從司法制度的外部視角還是從民事訴訟的內(nèi)部視角,司法實(shí)踐對(duì)立案證據(jù)的重視都有可以被理解的相當(dāng)理由。最具有共識(shí)的是,理應(yīng)重視“案多人少”的司法現(xiàn)象。這不但在實(shí)踐做法背后的司法邏輯中發(fā)揮決定性作用,而且充分體現(xiàn)在2021 年年底《民事訴訟法》修法的討論與爭(zhēng)議過程之中。無論從何種角度準(zhǔn)確定義“案多人少”,〔25〕參見程金華:《中國法院“案多人少”的實(shí)證評(píng)估與應(yīng)對(duì)策略》,載《中國法學(xué)》2022 年第6 期,第238-261 頁;張衛(wèi)平:《“案多人少”困境的程序應(yīng)對(duì)之策》,載《法治研究》2022 年第3 期,第91-99 頁;任重:《“案多人少”的成因與出路——對(duì)本輪民事訴訟法修正之省思》,載《法學(xué)評(píng)論》2022 年第2 期,第138-141 頁。對(duì)處于維護(hù)社會(huì)公平正義最后一道防線最前沿的基層人民法院和部分同樣大量行使一審訴訟案件管轄權(quán)的中級(jí)人民法院而言,法官現(xiàn)在的審判工作負(fù)擔(dān)大都是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減少進(jìn)入整個(gè)法院系統(tǒng)和個(gè)別法院的案件總數(shù),最直接的辦法就是自始減少/推遲進(jìn)入法院的案件數(shù)量。進(jìn)而,法院和法官還能避免諸如審限、司法責(zé)任制甚至上訴率帶來的顯性或者隱性壓力。這可以被理解為“規(guī)避”正式訴訟程序的手段,也體現(xiàn)為對(duì)源自現(xiàn)代西方訴訟傳統(tǒng)的對(duì)抗與判定結(jié)構(gòu)的“用腳投票”。在“案多人少”的背景下,負(fù)責(zé)立案的立案庭及其法官想方設(shè)法減少進(jìn)入法院的案件,并不僅僅是因?yàn)樽约盒枰笇彶榈陌讣啵浼瓤赡艿玫椒ㄔ侯I(lǐng)導(dǎo)出于法院整體利益考慮的“指導(dǎo)”,又可能承受由審判庭傳導(dǎo)來的案件審理壓力。立案審查只是整個(gè)法院工作壓力的外在表現(xiàn)。
在訴訟程序內(nèi)部視角下,在立案程序中要求提交證據(jù)在實(shí)踐中被認(rèn)為能夠防止濫訴。這并非說不要求提交證據(jù)就沒有其他機(jī)制能夠?qū)崿F(xiàn)類似功能,而是認(rèn)為如果要求當(dāng)事人在請(qǐng)求法院立案時(shí)就準(zhǔn)備好相應(yīng)證據(jù),會(huì)使其起訴行為更為審慎,而不太可能提出無理由的訴訟。在多數(shù)情況下,早在立案時(shí)就提出相關(guān)證據(jù)有助于澄清案情并盡早聚焦?fàn)廃c(diǎn),甚至可能說服當(dāng)事人沒有起訴的必要。此時(shí)形成的鑒定證據(jù)未來也有機(jī)會(huì)轉(zhuǎn)換為訴訟中的證據(jù)。但是,這種訴前鑒定對(duì)法官庭審的幫助其實(shí)更多地是隨后審前準(zhǔn)備程序中鑒定的功能,并非必須或者更應(yīng)當(dāng)提前至立案之時(shí)。〔26〕參見曹志勛:《民事訴訟中強(qiáng)制性訴前鑒定的反思與重構(gòu)》,載《證據(jù)科學(xué)》2022 年第2 期,第135-138 頁。當(dāng)然,無論原告在起訴時(shí)有沒有舉證義務(wù),都不妨礙當(dāng)事人基于訴訟策略,事實(shí)上提交了合同書、收據(jù)之類能夠證明案件要件事實(shí)/主要事實(shí)的核心證據(jù)。
司法實(shí)踐中至少在部分地區(qū)比較突出的是所謂“預(yù)立案”制度下的立案證據(jù)問題。如果將“預(yù)立案”理解為某種立案前的案件登記制度(而非類似到訪醫(yī)院前“網(wǎng)上掛號(hào)”的“預(yù)約立案”),那么其實(shí)立案證據(jù)尚未進(jìn)入民事訴訟框架內(nèi)的正式審查。恰恰由于其非正式的屬性,法院在“預(yù)立案”中對(duì)證據(jù)的要求可能多種多樣,本文暫且以證據(jù)要求由弱到強(qiáng)為標(biāo)準(zhǔn),總結(jié)出以下五種模式。其一,將“預(yù)立案”理解為立案前調(diào)解的“別稱”,〔27〕參見關(guān)家玉:《高州法院開啟“預(yù)立案”解紛模式》,載《廣州日?qǐng)?bào)》2022 年8 月29 日,第11 版。因而不強(qiáng)調(diào)訴訟證據(jù)要求的維度。其二,僅要求以表單方式提供大致對(duì)應(yīng)起訴狀內(nèi)容的信息,而不要求同時(shí)提交證據(jù)(“經(jīng)我院初步審查后,對(duì)于符合立案條件的案件通知當(dāng)事人準(zhǔn)備所需文書,證據(jù)資料”〔28〕《迎江法院網(wǎng)上預(yù)立案》,http://www.yjqfy.gov.cn/yuyuelian.html,2023 年11 月24 日訪問。)。其三,將立案審查及其證據(jù)要求區(qū)分為兩個(gè)階段,先是在線預(yù)約立案審查,其后“審核通過的當(dāng)事人或者代理人應(yīng)當(dāng)在規(guī)定的時(shí)間攜帶書面起訴(申請(qǐng))材料前往預(yù)約立案法院,由立案法官對(duì)網(wǎng)上提交的起訴(申請(qǐng))材料的真實(shí)性進(jìn)行審查”[2018 年《北京法院網(wǎng)上立案和微信預(yù)約立案工作辦法(試行)》(已失效)第2、15 條],〔29〕北京市高級(jí)人民法院:《北京法院網(wǎng)上立案和微信預(yù)約立案工作辦法(試行)》,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1905/t20190522_61167.html,2023 年11 月24 日訪問。類似做法,參見福建省高級(jí)人民法院:《網(wǎng)上訴訟服務(wù)中心》,http://ssfw.fjcourt.gov.cn/views/ApplyCase/Default.aspx?as3=1,2023 年7 月27 日訪問(其現(xiàn)已失效,新系統(tǒng)似乎采取了線上審存疑時(shí)轉(zhuǎn)為線下審的方式,參見http://ssfw.fjcourt.gov.cn/,2023 年11 月24 日訪問)。即分兩階段要求當(dāng)事人提交材料與審查材料的真實(shí)性。其四,要求當(dāng)事人實(shí)質(zhì)上提供立案審查需要的所有材料,只是在完成立案審查后暫時(shí)不完成正式立案。其五,同樣要求當(dāng)事人提供全部證據(jù),在完成立案審查后直接在線立案,“在我院確定立案后,當(dāng)事人需及時(shí)將紙質(zhì)材料通過快遞方式郵寄我院”。〔30〕金寨縣人民法院:《預(yù)約立案通道及操作指南》,http://www.jzfy.gov.cn/news/details/?id=5348,2023 年11 月24 日訪問。就此而言,當(dāng)然還可以根據(jù)在線立案后是否要求書面補(bǔ)寄而作模式上的進(jìn)一步區(qū)分。這些帶有地方特色的具體規(guī)則填補(bǔ)了立案登記制下立案證據(jù)制度的細(xì)節(jié),也體現(xiàn)了多數(shù)法院在重視立案證據(jù)的同時(shí)創(chuàng)新的努力。不過,如后詳述,從我國法的制度與法理邏輯出發(fā),立案證據(jù)原則上本就不應(yīng)構(gòu)成起訴要件。
三、立案證據(jù)原則上不應(yīng)構(gòu)成起訴要件
(一)立案登記制下的我國現(xiàn)行法解釋
在是否要求立案證據(jù)的規(guī)則分歧背后,隱藏的是現(xiàn)行法解釋、民事程序原理與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如果說在起訴時(shí)提供事實(shí)主張是必要的(分歧在于其具體程度),〔31〕參見曹志勛:《立案形式審查中的事實(shí)主張具體化》,載《當(dāng)代法學(xué)》2016 年第1 期,第130-139 頁。是否要求提交證據(jù)則是另一回事。無論司法機(jī)關(guān)將其審查稱為實(shí)質(zhì)審查還是初步證據(jù)審查,對(duì)證據(jù)本身的內(nèi)容進(jìn)行審查就意味著其不再屬于形式審查。〔32〕對(duì)于形式審查、依原告主張和初步證據(jù)的比較,參見嚴(yán)仁群:《管轄規(guī)范中的實(shí)體要素》,載《法律科學(xué)》2013 年第2 期,第163-164 頁。至于審查證據(jù)時(shí)證明標(biāo)準(zhǔn)上的差異,對(duì)于審查的定性來說并不重要。這種審查超越了前述現(xiàn)行法上“應(yīng)當(dāng)”條款的效力,提交證據(jù)不應(yīng)是起訴的必要條件。〔33〕相同觀點(diǎn),參見段文波:《起訴程序的理論基礎(chǔ)與制度前景》,載《中外法學(xué)》2015 年第4 期,第896 頁(隨后的限縮性觀點(diǎn),參見段文波:《起訴條件前置審理論》,載《法學(xué)研究》2016 年第6 期,第77 頁);劉敏:《功能、要素與內(nèi)容:民事起訴狀省思》,載《法律科學(xué)》2014 年第3 期,第163 頁。相反,本文認(rèn)為原告原則上只需在起訴狀中說明起訴階段必要的事實(shí)主張,法官不必依據(jù)證據(jù)材料核實(shí)這些事實(shí)主張的真實(shí)性和完整性。
這種理解與對(duì)《民事訴訟法》規(guī)則的解釋密切相關(guān),也是立案登記制的原則要求。“立案審查制改革的實(shí)質(zhì)不是對(duì)于起訴要不要審查,而是應(yīng)當(dāng)審查什么的問題”,〔34〕張衛(wèi)平:《民事案件受理制度的反思與重構(gòu)》,載《法商研究》2015 年第3 期,第8 頁。立案登記制的基本出發(fā)點(diǎn)在于減少立案階段審查的內(nèi)容。在這一目標(biāo)下,在解釋論上應(yīng)區(qū)分《民事訴訟法》第122 條與第124 條在法律虛詞使用上的區(qū)別。現(xiàn)行立案形式審查規(guī)則中“必須”與“應(yīng)當(dāng)”的不同表述,代表了立法者意志和效力的差異。從規(guī)范法學(xué)/法教義學(xué)/法解釋學(xué)的視角出發(fā),應(yīng)當(dāng)區(qū)分民事訴訟法文本中的“必須”條款和“應(yīng)當(dāng)”條款,重視規(guī)范中的法律后果對(duì)裁判者的強(qiáng)制程度。〔35〕參見曹志勛:《民事立案程序中訴訟標(biāo)的審查反思》,載《中國法學(xué)》2020 年第1 期,第286-287 頁。尤其是《民事訴訟法》和2019年《證據(jù)規(guī)定》中“應(yīng)當(dāng)”提供證據(jù)信息和“應(yīng)當(dāng)”提供符合起訴條件的相應(yīng)證據(jù)的規(guī)定,屬于立法者對(duì)當(dāng)事人訴訟行為的倡導(dǎo)性規(guī)定/訓(xùn)示規(guī)定。就此而言,《民事訴訟法》第126 條第2 句規(guī)定的正是“對(duì)符合本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的起訴,必須受理”,而同條第3 句第2 分句則從反面說明“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應(yīng)當(dāng)在七日內(nèi)作出裁定書,不予受理”,其適用對(duì)象十分明確。易言之,立法者有意區(qū)分了《民事訴訟法》第124 條與第122 條作為行為規(guī)范的效力。由于對(duì)應(yīng)立案證據(jù)要求的“應(yīng)當(dāng)”條款沒有附加任何后果規(guī)定,不滿足其形式上提出的行為要求,不應(yīng)使起訴行為無效。
同時(shí),《民事訴訟法》第124 條再次強(qiáng)調(diào)了訴狀只需“記明……事項(xiàng)”而非實(shí)際提交相關(guān)證據(jù),沒有理由認(rèn)為已失效的《立案規(guī)定》第9 條后句(“收到訴狀的時(shí)間,從當(dāng)事人補(bǔ)交有關(guān)證據(jù)材料之日起開始計(jì)算”)對(duì)未提交主要證據(jù)時(shí)訴狀起訴效力的否定仍然有效。或者可以認(rèn)為,起訴狀應(yīng)當(dāng)記明的事項(xiàng)與起訴條件并不能等量齊觀,“把能否提供證據(jù)作為衡量是否應(yīng)當(dāng)受理原告提起的訴訟并不合法”。〔36〕李浩:《民事訴訟法適用中的證明責(zé)任》,載《中國法學(xué)》2018 年第1 期,第87 頁。在這個(gè)意義上,最高人民法院在不同時(shí)期均認(rèn)為原《立案規(guī)定》第9 條的規(guī)定應(yīng)當(dāng)被限縮理解,以便區(qū)分起訴證據(jù)和一般訴訟證據(jù)。〔37〕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訴訟證據(jù)規(guī)定理解與適用》(上冊(c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75-77 頁;李國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的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 年版,第21-33 頁。此外,《登記立案規(guī)定》第4 條也重復(fù)了《民事訴訟法》第124 條的規(guī)則,其附錄的常見起訴文書樣式同樣未列明任何證據(jù)、證據(jù)來源或證人。〔38〕參見景漢朝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登記立案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 年版,第237-250 頁。換一個(gè)角度看,由《民訴解釋》第282 條第3 項(xiàng)對(duì)環(huán)境公益訴訟和消費(fèi)者公益訴訟中初步證據(jù)的特別要求以及對(duì)此類訴訟特殊性的反面解釋可見,對(duì)普通民事訴訟中初步證據(jù)的要求應(yīng)當(dāng)?shù)陀谔貏e規(guī)定的初步證據(jù)。
(二)立案證據(jù)要求的程序理論反思
在前述現(xiàn)行法邏輯之上,應(yīng)當(dāng)進(jìn)一步回應(yīng)我國司法實(shí)踐中的現(xiàn)實(shí)需求,包括立案證據(jù)要求在內(nèi)的各種法定條件都能夠被用于減少案件數(shù)量。不過,在發(fā)揮相似功能的制度中,立案證據(jù)的要求是在訴訟程序內(nèi)部對(duì)當(dāng)事人的訴訟行為提出/提高審查標(biāo)準(zhǔn),其目的是對(duì)試圖進(jìn)入法院的民事案件的過濾即防止濫訴。這區(qū)別于在訴訟程序外部發(fā)揮相似功能、直接化解糾紛的立案前調(diào)解制度。〔39〕參見周強(qiáng):《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bào)告——2022 年3 月8 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ì)第五次會(huì)議上》,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51111.html,2023 年11 月24 日訪問。除了具有減少案件數(shù)量的功能之外,訴前調(diào)解還能夠發(fā)揮比如預(yù)防性法律制度、合意解決紛爭(zhēng)、高效價(jià)廉等功能,這些都是立案證據(jù)的要求原則上所不具備的。從定性來看,立案證據(jù)的要求作為訴訟程序內(nèi)部的要件,與其他起訴要件/訴訟要件分享相同的程序法屬性。雖然這一要求并未出現(xiàn)在《民事訴訟法》第122 條的起訴條件中,而是隱藏在對(duì)起訴狀的要求上,但是兩者在現(xiàn)行法上具有一體性,都屬于法院審查起訴的“工具箱”。那么,對(duì)程序法上的法定要求完成要件化和體系化的理論提煉,甚至為了減少司法實(shí)踐中的濫用可能性,從解釋論上減少立案審查要件的數(shù)量(包括但不限于立案證據(jù)要求)也是改造我國立案實(shí)質(zhì)審查制的重要手段。〔40〕參見曹志勛:《民事立案程序中訴訟標(biāo)的審查反思》,載《中國法學(xué)》2020 年第1 期,第297 頁;王亞新:《立案登記制改革:成效、問題及對(duì)策——基于對(duì)三地法院調(diào)研的思考》,載《法治研究》2017 年第5 期,第60 頁。而在相關(guān)要件仍然具有程序法效力時(shí),一項(xiàng)持續(xù)具有重要性的理論工作是對(duì)要件內(nèi)容的準(zhǔn)確界定,以達(dá)到引導(dǎo)法官恰當(dāng)適用和給當(dāng)事人合理預(yù)期的雙重作用。與此相對(duì),包括立案前調(diào)解在內(nèi)、于各個(gè)訴訟階段達(dá)成的調(diào)解則以當(dāng)事人之間的合意為最核心條件,是獨(dú)立于訴訟法上要件體系的另一類規(guī)則。
從收集證據(jù)作為程序要件的角度來看,無論立案證據(jù)要求的具體內(nèi)容如何,都可能無法在民事訴訟的起訴受理階段得到妥善處理。在當(dāng)事人希望法院保護(hù)自己的權(quán)利,但是在起訴時(shí)仍沒有收集到相關(guān)證據(jù)甚至仍未具有收集證據(jù)的能力時(shí),立案證據(jù)要求具有的防止濫訴功能將遭受挑戰(zhàn)。如果法院以立案證據(jù)的要求為由裁定不予受理,可能嚴(yán)重影響當(dāng)事人司法救濟(jì)權(quán)/訴權(quán)的行使。〔41〕即使當(dāng)事人將來也許可以申請(qǐng)法院在立案前作出律師調(diào)查令,且不論其要件如何、有多少當(dāng)事人能夠成功申請(qǐng),此時(shí)將在法院形式立案前前置就是否作出該命令的司法審查,在程序上類似于獨(dú)立的訴前證據(jù)保全程序,可能會(huì)進(jìn)一步“疊床架屋”地影響案件立案的進(jìn)度。為了不違反我國登記立案制改革的基本精神與制度目標(biāo),法院原則上不能僅以審理效率為名限制原告的訴權(quán),而需要在同時(shí)滿足相應(yīng)要件和案件類型后,才能過濾掉完全因輕率提起的案件。畢竟,原告在主張權(quán)利的同時(shí)會(huì)對(duì)被告的程序利益產(chǎn)生影響,過于輕率的訴訟也可以被法院直接排除,以免浪費(fèi)公共司法資源。易言之,在現(xiàn)行法的邏輯下應(yīng)當(dāng)追求“擇案而審”,將司法實(shí)踐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實(shí)現(xiàn)的訴訟分流/過濾/減緩的功能轉(zhuǎn)移給調(diào)解和其他針對(duì)輕率訴訟的程序機(jī)制,而將立案證據(jù)限縮為特定列明的情況。
此處最關(guān)鍵的因素在于究竟哪些要件和案件類型足以證成對(duì)輕率訴訟的排除,或者說如何判斷輕率訴訟。一方面,對(duì)于起訴從實(shí)體法上看顯無理由的情形,除了在解釋論上應(yīng)以直接利害關(guān)系(當(dāng)事人適格)要件裁定不予受理/駁回起訴之外,在原告的主張本身滿足訴訟要件時(shí),在立法論上法院應(yīng)當(dāng)有權(quán)在立案階段直接判決駁回訴訟請(qǐng)求。〔42〕參見曹志勛:《民事立案程序中訴訟標(biāo)的審查反思》,載《中國法學(xué)》2020 年第1 期,第294 頁。就原告不具有債權(quán)人資格時(shí)裁判形式的持久爭(zhēng)議,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 年版,第76 頁。另一方面,在不要求審查立案證據(jù)的前提下,對(duì)于根據(jù)原告的主張就不可能滿足訴訟要件的案件,法院可以裁定不予立案。在此審查的不是證據(jù),而是事實(shí)主張本身。例如,就起訴人依其陳述不享有實(shí)體權(quán)利,而是以自己的名義為他人主張權(quán)利[即德國法上的“公眾訴訟”(Popularklage)]時(shí),各起訴人“雖在起訴狀中陳述了其與各被告之間的股權(quán)轉(zhuǎn)讓合同關(guān)系及履行爭(zhēng)議等,但在訴訟請(qǐng)求中明確主張被告向第三人龍?zhí)豆痉颠€銷售款,系為龍?zhí)豆镜拿袷聶?quán)益而提起訴訟主張,并非為保護(hù)自己的民事權(quán)益提起訴訟”,因而無論立案證據(jù)如何,也不滿足當(dāng)事人適格和訴訟實(shí)施權(quán)的要求,法院可以裁定不予受理。〔43〕參見福建省高級(jí)人民法院(2016)閩民初1 號(hào)民事裁定書。再如,起訴人主張其與被告之一之間簽訂的《買賣合同》已通過書面《解除協(xié)議》解除,并且雙方就此又簽訂了《抵債協(xié)議》,雙方還與被告之二簽訂《房產(chǎn)抵債確認(rèn)協(xié)議書》。法院認(rèn)為,原告不能基于其主張的《買賣合同》中的管轄權(quán)約定,起訴請(qǐng)求被告履行《抵債協(xié)議》和《房產(chǎn)抵債確認(rèn)協(xié)議書》。〔44〕參見遼寧省高級(jí)人民法院(2018)遼民初85 號(hào)民事裁定書。
在認(rèn)可法院于立案階段當(dāng)然具有審查權(quán)的同時(shí),通常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保留于立案審查階段的是可以通過形式審查處理的問題。否則,既無法實(shí)現(xiàn)宏觀上不同訴訟階段的合理分工(亦見下文對(duì)收集證據(jù)應(yīng)然狀況的討論),又可能使微觀上立案庭的任務(wù)與條件不相匹配。從立法論上確實(shí)可以考慮調(diào)整現(xiàn)有的起訴要件,將一部分起訴要件仍然交由立案庭形式審查,另一部分本應(yīng)作為訴訟要件/實(shí)體裁判要件的內(nèi)容則應(yīng)當(dāng)轉(zhuǎn)而由審判庭承擔(dān)。〔45〕參見唐力、高翔:《我國民事訴訟程序事項(xiàng)二階化審理構(gòu)造論——兼論民事立案登記制的中國化改革》,載《法律科學(xué)》2016 年第5 期,第80-89 頁;張嘉軍:《立案登記背景下立案庭的定位及其未來走向》,載《中國法學(xué)》2018 年第4 期,第217-237 頁;傅郁林:《再論民事訴訟立案程序的功能與結(jié)構(gòu)》,載《上海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4 年第1 期,第39-53 頁。主張也可保留獨(dú)立立案庭并由其審理訴訟要件的觀點(diǎn),參見段文波:《起訴條件前置審理論》,載《法學(xué)研究》2016 年第6 期,第70-87 頁。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提交證據(jù)和未提交證據(jù)這樣的極端情形才構(gòu)成可能由立案庭完成的形式判斷。相反,什么案件需要提交多少證據(jù)才符合該案的實(shí)際情況而不構(gòu)成輕率起訴,什么案件中的證據(jù)在立案時(shí)看似不充分但是在隨后的審前程序能得到補(bǔ)強(qiáng),都不是可以予以形式判斷的事項(xiàng),而必然與案件本身的實(shí)體審理有關(guān)。于是,立案證據(jù)的要求也不宜作為形式審查要件保留于立法論上改造后的立案庭。如果說只要提交了證據(jù)即可,而不需要考慮在民事訴訟的對(duì)抗程序中將要考慮的裁判邏輯/方法論和證據(jù)的“三性”,那么這樣的審查標(biāo)準(zhǔn)又不可能具有過濾案件的訴訟效果。抑或若將立案證據(jù)的要求理解為某種倡導(dǎo)性規(guī)范(“應(yīng)當(dāng)”規(guī)范),那么由于對(duì)其違反也不會(huì)產(chǎn)生程序法上的后果,其實(shí)就不再屬于嚴(yán)格意義上的起訴/訴訟要件。
(三)比較法經(jīng)驗(yàn)對(duì)立案證據(jù)的否定
與此呼應(yīng)的是,要求原告原則上在立案階段就提交證據(jù)并非比較法上的主流做法。這雖然常常被視為理論“常識(shí)”,但是仍應(yīng)當(dāng)從一手資料出發(fā),關(guān)注圍繞上述簡(jiǎn)單結(jié)論的整體制度安排。當(dāng)然,比較法上的一般原理與代表性做法并非當(dāng)然優(yōu)于我國司法實(shí)踐慣性,相反,如前所述,尊重現(xiàn)行法與政策的內(nèi)在邏輯并合理回應(yīng)現(xiàn)實(shí)需求的主張其實(shí)更為重要。
就此而言,大陸法系法院并不會(huì)要求原告在起訴時(shí)就必須附上證據(jù)。更抽象地看,立案證據(jù)與理論上的職權(quán)主義諸原則并無直接關(guān)系,其訴訟程序也不重視立案階段審查機(jī)制的有無及程度。在德國法上,只有(至少)在被告答辯后,法官才能明確雙方的事實(shí)爭(zhēng)點(diǎn),進(jìn)而當(dāng)事人才有提出證據(jù)申請(qǐng)并加以證明的必要。證據(jù)原則上是正式庭審〔46〕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主要審前準(zhǔn)備程序的先期首次期日可以當(dāng)庭轉(zhuǎn)化為正式庭審。參見曹志勛:《論普通程序中的答辯失權(quán)》,載《中外法學(xué)》2014 年第2 期,第486 頁。中的審理對(duì)象,結(jié)合民事實(shí)體法與程序法的法學(xué)教育也反復(fù)加強(qiáng)這種思維訓(xùn)練。具體而言,除了法官在準(zhǔn)備程序中調(diào)查外部證據(jù)(例如官方答復(fù)、書面證人證言、鑒定結(jié)論以及勘驗(yàn))之外,當(dāng)事人在口頭辯論期日中一般應(yīng)當(dāng)陳述其訴的聲明(《德國民事訴訟法典》第137 條第1 款、第297 條),并且相應(yīng)地通過當(dāng)事人陳述和參照訴訟書狀的方式(《德國民事訴訟法典》第137 條第3 款)表達(dá)自己對(duì)事實(shí)和法律問題的觀點(diǎn)(《德國民事訴訟法典》第137 條第2 款)。在有爭(zhēng)議時(shí),法院也常常會(huì)在陳述訴的聲明之前組織對(duì)訴訟要件展開辯論(《德國民事訴訟法典》第139 條第3 款、第280 條、第281 條和第282 條第3 款)。僅在實(shí)體問題有證明需要時(shí),法官才會(huì)在主期日中安排調(diào)查證據(jù)(《德國民事訴訟法典》第279 條第2 款)。如果本案爭(zhēng)點(diǎn)在之前的準(zhǔn)備程序中還沒有完全固定,那么法官也可以行使釋明權(quán)協(xié)助當(dāng)事人整理其主張及法律觀點(diǎn)(《德國民事訴訟法典》第139 條第1 款和第2 款)。在證據(jù)調(diào)查之后,法院仍然應(yīng)當(dāng)向當(dāng)事人解釋相關(guān)事項(xiàng)并在可能時(shí)分析證據(jù)調(diào)查的結(jié)果(《德國民事訴訟法典》第279 條第3 款),〔47〕Vgl.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18.Aufl., 2018, §§ 77 Rn.17 ff., 105 Rn.36 ff.; MüKoZPO/Prütting, 6.Aufl., 2020, § 279 Rn.7 f., 18, 21.當(dāng)事人也有權(quán)就證據(jù)調(diào)查的結(jié)果展開辯論(《德國民事訴訟法典》第285 條第1 款)。上述制度框架承認(rèn)的例外在于嫁接在證據(jù)保全制度(《德國民事訴訟法典》第485 條以下)中的訴前獨(dú)立證據(jù)調(diào)查程序。當(dāng)該程序確認(rèn)的對(duì)象涉及三類特定的鑒定事項(xiàng)或者有助于預(yù)防糾紛時(shí),當(dāng)事人才能滿足法定的法律利益要件(《德國民事訴訟法典》第485 條第2 款)。〔48〕Vgl.Z?ller/Herget, ZPO, 33.Aufl., 2020, § 485 Rn.6 ff.
在日本法上,訴狀被認(rèn)為兼具準(zhǔn)備性書面資料的功能,因此也可以記載證據(jù)和重要的間接事實(shí)(《日本民事訴訟規(guī)則》第53 條)。但是,訴狀不必包含證據(jù),該倡導(dǎo)性規(guī)定的目的是盡早確定爭(zhēng)點(diǎn)并促進(jìn)審理的充實(shí)性。如果未加說明或者說明不充分,不影響訴狀的完整性和效力。〔49〕新堂幸司『民事訴訟法』(弘文堂,2019 年)216-218 頁參照;松本博之=上野泰男『民事訴訟法』(弘文堂,2015 年)227 頁參照。我國臺(tái)灣地區(qū)也持與日本法相似的做法和理解,其雖然也建議當(dāng)事人在訴狀中就提交相關(guān)攻擊防御方法,但是這種要求不具有強(qiáng)制效力(我國臺(tái)灣地區(qū)“民事訴訟法”第244 條第3 款、第265 條第1 款和第266 條第1款第1 項(xiàng))。〔50〕參見邱聯(lián)恭講述/許士宦整理:《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二)》,2017 年自版發(fā)行,第43 頁;陳榮宗、林慶苗:《民事訴訟法》(中冊(cè)),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版,第6 頁。僅在例外情況下,日本法引入了訴前收集證據(jù)機(jī)制。雖然該制度自2003 年《日本民事訴訟法》修改后逐步得到我國學(xué)者的關(guān)注,〔51〕參見唐力:《日本民事訴訟證據(jù)收集制度及其法理》,載《環(huán)球法律評(píng)論》2007 年第2 期,第86-87 頁。但是其在該國實(shí)踐中的影響力卻相當(dāng)有限,也遭遇了不少制度障礙和實(shí)踐障礙。〔52〕參見趙清:《日本民事訴訟證據(jù)制度及對(duì)中國的啟示》,載《河北法學(xué)》2018 年第5 期,第142-146 頁。
在英國,為節(jié)約司法資源,現(xiàn)代司法被認(rèn)為也應(yīng)當(dāng)促使當(dāng)事人在起訴前盡早交換信息自行解決糾紛〔53〕See Carlson v.Townsend [2001] 3 All ER 663, CA, at [24], [28], [31], Brooke LJ.或減少法院審理的內(nèi)容與降低難度。〔54〕比如消除事實(shí)爭(zhēng)議,并通過《英國民事訴訟規(guī)則》第8 部分規(guī)定的訴狀,直接要求法官審理法律問題。See Juliet Wells( ed.),Zuckerman on Civil Procedure: Principles of Practice, Sweet & Maxwell, 2021, paras.4.66-4.71.在1996 年司法改革后,法院獲得了審查當(dāng)事人訴前行為的裁量性權(quán)力。在形式立案登記后,法官將審查當(dāng)事人在爭(zhēng)點(diǎn)與信息交換及自行糾紛解決時(shí)的誠意。如果當(dāng)事人的行為有悖于訴前行為準(zhǔn)則(pre-action protocol),法官就有權(quán)選擇制裁措施,例如予以費(fèi)用制裁或者在訴訟指揮中更為嚴(yán)厲,以發(fā)揮威懾和行為引導(dǎo)作用(《英國民事訴訟規(guī)則實(shí)務(wù)指南》訴前行為部分第4.6 條)。盡管如此,起訴時(shí)附上證人名單和書證也僅被規(guī)定為當(dāng)事人權(quán)利[《英國民事訴訟規(guī)則實(shí)務(wù)指南》第16 部分第13.3(2)、13.3(3)條]。這一規(guī)定的目的在于促使當(dāng)事人根據(jù)案情是否復(fù)雜自行判斷是否需要盡早舉證。〔55〕同上注,第1.116-1.120 段。即使英國的起訴狀和訴訟理由書應(yīng)當(dāng)就請(qǐng)求的性質(zhì)和原告作為依據(jù)的事實(shí)作簡(jiǎn)要陳述,無論從規(guī)則解釋還是實(shí)務(wù)做法來看,英國也不要求當(dāng)事人在立案前提交證據(jù)。〔56〕See Stuart Sime & Derek French (eds.), Blackstone’s Civil Practice 2019: The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para.24.19.
至于在美國,僅考慮到其司法行政意義上的立案登記制與傳統(tǒng)上通知訴答的要求,提交證據(jù)也并非原告起訴時(shí)必須滿足的條件。雖然民事司法中也安排了訴前證據(jù)開示機(jī)制[《美國聯(lián)邦民事訴訟規(guī)則》第27(a)(1)條],但是事實(shí)的發(fā)現(xiàn)仍然主要依賴立案后的證據(jù)開示。〔57〕See Neil Andrews, The Pre-action Phase: General Report - Common Law, in A.Pellegrini Grinover and P.Calmon (eds.), Direito Processual Comparado - XIII World Congress of Procedural Law, Rio de Janeiro: Editora Forense, 2007, p.226, n.120.在訴答程序于美國民事訴訟中被賦予較低重要性的同時(shí),廣泛的證據(jù)開示程序能使雙方當(dāng)事人在進(jìn)入正式庭審前獲取充分信息。其后果是,當(dāng)事人將明確其請(qǐng)求或者答辯是否有證據(jù)支持,從而決定是否自行解決糾紛;收集的證據(jù)信息也為可能的正式庭審奠定審理基礎(chǔ)。〔58〕See Richard D.Freer, Civil Procedure, Wolters Kluwer, 2017, p.424-425.
四、民事訴訟程序收集證據(jù)的應(yīng)然狀態(tài)
(一)民事程序功能與證據(jù)收集
立案證據(jù)的必要性也取決于民事訴訟不同階段尤其是立案審查階段與送達(dá)后答辯階段的定位和功能,不應(yīng)在立案階段收集證據(jù)的觀點(diǎn)能夠得到我國民事程序整體邏輯與訴訟原理的支持。在我國,法院在立案后才需要將訴訟材料送達(dá)被告(《民事訴訟法》第128 條第1 款第1 句)。立案階段發(fā)生在法院受理和送達(dá)被告之前,并以此顯著區(qū)別于法院受理后和被告獲得參與機(jī)會(huì)的訴訟準(zhǔn)備及管轄權(quán)異議階段。于是,不予受理裁定書上只需要出現(xiàn)起訴人(而非原告),不必寫明被起訴人,作出后也只送達(dá)起訴人一方。沿襲德日等大陸法系的做法,我國的立案程序顯著區(qū)別于英美法系的訴答程序,并不期待雙方當(dāng)事人在審前程序之前的對(duì)抗,也就沒有就相關(guān)程序性要件(無論究竟是立案形式要件還是訴訟要件)作出實(shí)質(zhì)性判定。〔59〕參見曹志勛:《立案形式審查中的事實(shí)主張具體化》,載《當(dāng)代法學(xué)》2016 年第1 期,第136 頁。這決定了原則上立案程序是面向原告的單方程序或者說是一方當(dāng)事人與法院之間的“雙主體”程序結(jié)構(gòu)。〔60〕參見李浩:《民事訴訟法適用中的證明責(zé)任》,載《中國法學(xué)》2018 年第1 期,第82-83 頁。實(shí)踐中較為例外的做法是,有的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前即向被告送達(dá)起訴狀及起訴材料,隨后被告就管轄權(quán)提出異議,最終受訴法院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裁定不予受理。〔61〕參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高級(jí)人民法院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分院(2015)新兵民初字第00003 號(hào)民事裁定書。雖然看起來原告起訴都是被程序性地駁回,但是無論是注意到實(shí)質(zhì)上管轄權(quán)異議可以額外導(dǎo)致移送管轄的后果還是形式上不予受理與駁回起訴裁定存在明顯差異,這種做法都并不可取。
如果說在立案階段嘗試過濾案件常常“時(shí)候未到”,那么立案后的被告答辯或者提出管轄權(quán)異議的階段可能才是“恰逢其時(shí)”。如不考慮以訴前磋商(其效果體現(xiàn)在《民法典》第195 條)和立案前調(diào)解(《民事訴訟法》第125 條)為代表的立案前機(jī)制,直到進(jìn)入訴訟準(zhǔn)備階段后,民事訴訟在程序構(gòu)造上才轉(zhuǎn)換為雙方當(dāng)事人參與的對(duì)抗程序。被告通過其程序性或?qū)嶓w性答辯活動(dòng),在民事訴訟內(nèi)部促成本案中爭(zhēng)點(diǎn)的形成。此時(shí)也是審查相關(guān)訴訟要件比較妥當(dāng)?shù)臅r(shí)機(jī),在制度和實(shí)務(wù)中主要表現(xiàn)為被告對(duì)法院(廣義)管轄權(quán)的挑戰(zhàn)。〔62〕相同觀點(diǎn),參見李浩:《民事訴訟管轄制度的新發(fā)展》,載《法學(xué)家》2012 年第4 期,第154 頁。甚至與其說此處涉及的僅僅是當(dāng)事人對(duì)管轄權(quán)提出異議之后法院的程序性審查,不如說這進(jìn)而代表了我國民事程序中所缺失的訴答程序以及在此基礎(chǔ)上訴答與審前準(zhǔn)備程序之間的有效區(qū)分。〔63〕參見傅郁林:《再論民事訴訟立案程序的功能與結(jié)構(gòu)》,載《上海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4 年第1 期,第51-52 頁。
與原有立案證據(jù)制度相比,這種理解將結(jié)合證據(jù)后更為深入的審查推遲至法院受理和送達(dá)案件之后。從大陸法系的視角看,雖然其沒有獨(dú)立的立案審查階段,但是立案形式要件與訴訟要件也都是案件送達(dá)被告后法官依職權(quán)審查的內(nèi)容,也當(dāng)然需要結(jié)合證據(jù)加以認(rèn)定。畢竟,原告所實(shí)施的證明活動(dòng)被認(rèn)為屬于自由證明(Freibeweis)的范疇,只是不受法定的證據(jù)調(diào)查程序和證據(jù)種類的限制,〔64〕參見占善剛:《論民事訴訟中之自由證明》,載《法學(xué)評(píng)論》2007 年第4 期,第79-83 頁。而非不需要證據(jù)。易言之,就在我國被作為起訴要件而在大陸法系構(gòu)成訴訟要件的事項(xiàng)而言,將與其相關(guān)的證據(jù)審查推遲至送達(dá)后,能夠達(dá)到與大陸法系相似的制度效果。而且,與諸如行政機(jī)關(guān)對(duì)登記事項(xiàng)的形式審查有必要在登記階段就得到補(bǔ)強(qiáng)不同,民事訴訟恰恰是動(dòng)態(tài)的,是案件中事實(shí)和法律關(guān)系逐步得到澄清的過程。在立案階段由于沒有被告的正式參與,即使要求原告提交證據(jù),常常也無法有效地完成證據(jù)調(diào)查,只能平添訴累。由于可預(yù)見的重復(fù)審查,訴訟資源也將被無謂浪費(fèi)。〔65〕更深入的類似分析,參見傅郁林:《中國民事訴訟立案程序的功能與結(jié)構(gòu)》,載《法學(xué)家》2011 年第1 期,第45、51 頁。相反,強(qiáng)調(diào)當(dāng)事人此時(shí)有證明其事實(shí)主張為真的訴訟義務(wù)的不同觀點(diǎn),參見王二環(huán):《登記立案制度之構(gòu)建與完善——兼議登記立案制度之功能》,載《政法論壇》2019 年第2 期,第112 頁。
(二)民事證據(jù)調(diào)查的應(yīng)然框架
除了涉及民事訴訟程序的功能分工之外,是否要求提交立案證據(jù),也與大陸法系傳統(tǒng)下民事訴訟證據(jù)調(diào)查的整體框架有關(guān)。這雖然超出我國法上立案證據(jù)制度的解釋問題,但是從立法論來看已具有一定理論共識(shí),應(yīng)當(dāng)體現(xiàn)在民事訴訟的進(jìn)一步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之中。證據(jù)調(diào)查通常在民事訴訟的正式庭審中展開,其不僅遠(yuǎn)遠(yuǎn)晚于立案階段,而且對(duì)其調(diào)查的必要性也應(yīng)當(dāng)在待證事實(shí)相對(duì)明確之后才顯現(xiàn)。例如,如前所述,德國的正式開庭程序原則上體現(xiàn)為“法庭辯論—法庭調(diào)查—法庭辯論”三階段,只有在辯論后存在事實(shí)爭(zhēng)點(diǎn)時(shí)才有展開證據(jù)調(diào)查的必要。〔66〕Vgl.Musielak/Voit, Grundkurs ZPO, 13.Aufl., 2016, Rn.718 ff.;松本博之=上野泰男『民事訴訟法』(弘文堂,2015 年)419-420 頁參照。這種做法最大的意義在于盡可能過濾事實(shí)爭(zhēng)點(diǎn)并減少法官收集證據(jù)的數(shù)量,從而提高庭審的集中度與效率。對(duì)比而言,我國采取的“法庭調(diào)查在先、法庭辯論在后”(《民事訴訟法》第141、144 條)的程序則被認(rèn)為存在明顯缺憾。這種強(qiáng)調(diào)階段劃分的程序會(huì)導(dǎo)致事實(shí)問題與法律問題的人為割斷,進(jìn)而使法庭調(diào)查的證明對(duì)象不準(zhǔn)確以及法庭辯論缺少必要的事實(shí)認(rèn)定結(jié)果,最終影響口頭辯論中事實(shí)發(fā)現(xiàn)的準(zhǔn)確性和程序推進(jìn)的效率。〔67〕參見張衛(wèi)平:《民事訴訟法》,法律出版社2023 年版,第368 頁。例如,之所以在我國實(shí)踐中可能發(fā)生“無謂鑒定”或者律師在審判庭或者仲裁庭開庭時(shí)質(zhì)證“漫無目的”的情形,一個(gè)重要的原因是,目前尚未完成先就事實(shí)主張組織辯論,在確定需要調(diào)查的事實(shí)爭(zhēng)點(diǎn)后再調(diào)查證據(jù)〔68〕參見吳澤勇:《證明責(zé)任視角下民間借貸訴訟中的借款單據(jù)鑒定問題研究》,載《法律適用》2018 年第9 期,第63 頁;段文波:《我國民事庭審階段化構(gòu)造再認(rèn)識(shí)》,載《中國法學(xué)》2015 年第2 期,第81-107 頁。的改革。于是,法官在證據(jù)調(diào)查階段收到反證方對(duì)本證方提出書證真?zhèn)蔚馁|(zhì)證意見后,覺得有道理就委托了鑒定機(jī)構(gòu)鑒定疑點(diǎn);在法庭辯論后,法官才發(fā)現(xiàn)是否做如上鑒定并不影響認(rèn)定案情,本應(yīng)否定待證事實(shí)對(duì)糾紛解決的必要性。〔69〕參見曹志勛:《對(duì)當(dāng)事人鑒定申請(qǐng)的司法審查——兼論書證真?zhèn)舞b定的特殊性》,載《法學(xué)》2020 年第12 期,第124-125 頁。對(duì)證據(jù)申請(qǐng)的上述審查,反過來說就是對(duì)證據(jù)調(diào)查范圍的確定。〔70〕參見李凌:《論民事庭審證據(jù)調(diào)查范圍之確定》,載《法制與社會(huì)發(fā)展》2021 年第5 期,第141-155 頁。就此而言,如果能參考2020 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fā)的《民事訴訟程序繁簡(jiǎn)分流改革試點(diǎn)實(shí)施辦法》第8 條第2 款和第13 條第3 項(xiàng)的試點(diǎn)規(guī)定,圍繞訴訟請(qǐng)求和案件要素開展審理,也許確實(shí)能代替目前仍然作為原則做法的階段式庭審結(jié)構(gòu)(《民訴解釋》第230 條),將開庭時(shí)的爭(zhēng)點(diǎn)整理也視為審判方法中的重要一環(huán)。〔71〕參見鄒碧華:《要件審判九步法》,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117-129 頁。反過來看,《民事訴訟法》第124 條第4 項(xiàng)就指明證據(jù)及證人的要求,既可能由于證據(jù)的證明目的并未成為本案中的待證事實(shí)而體現(xiàn)為“無用之功”,又可能由于未能圍繞隨后形成的待證事實(shí)展開而“掛一漏萬”。
同時(shí),拒絕在立案程序中收集證據(jù)也能夠得到大陸法系證據(jù)調(diào)查直接原則的支持。與我國通常主要由于“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現(xiàn)實(shí)問題(這經(jīng)過以司法責(zé)任制為代表的近期司法改革得以改觀)而將直接原則與言詞/口頭原則密切聯(lián)系不同,〔72〕參見李峰:《傳聞證據(jù)規(guī)則,抑或直接言詞原則?——民事訴訟書面證言處理的路徑選擇》,載《法律科學(xué)》2012 年第4 期,第139-145 頁;王福華:《直接言詞原則與民事案件審理樣式》,載《中國法學(xué)》2004 年第1 期,第69-76 頁。德國法在同樣強(qiáng)調(diào)兩者的同時(shí)對(duì)其的區(qū)分更為清晰。直接原則要求的是受訴法院(合議庭或獨(dú)任法官)不求助其他法官,在其法庭上組織口頭辯論和證據(jù)調(diào)查的直接性。〔73〕Vgl.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18.Aufl., 2018, § 80 Rn.1; Z?ller/Greger, ZPO, 33.Aufl., 2020, Vor § 128 Rn.13.雖然書面證言或者鑒定人證據(jù)不符合辯論的口頭原則,但是只要法官在法庭上加以調(diào)查并按照自由心證原則評(píng)價(jià)其證明力,這兩類證據(jù)也符合直接原則。〔74〕Vgl.Z?ller/Greger, ZPO, 33.Aufl., 2020, § 128 Rn.1.在理論上,完全會(huì)出現(xiàn)口頭但間接與書面但直接的情形,甚至在當(dāng)事人于法庭外通過受命法官或者受托法官的筆錄表達(dá)自認(rèn)時(shí),證據(jù)調(diào)查是書面且間接的。〔75〕Vgl.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18.Aufl., 2018, § 80 Rn.2.易言之,在直接原則及其例外之下,證據(jù)調(diào)查針對(duì)的主要是案件實(shí)體審理中的內(nèi)容,這是審判法官的任務(wù)。與此相對(duì),在立案程序中要求由立案法官調(diào)查證據(jù),既難以融入這套證據(jù)/證明法的系統(tǒng)思路,也不能在我國現(xiàn)行法上的證據(jù)收集與事實(shí)發(fā)現(xiàn)程序中找到恰當(dāng)?shù)奈恢谩?/p>
(三)立案時(shí)例外應(yīng)收集的證據(jù)
1.純粹程序性事項(xiàng)
從對(duì)外國民事訴訟理論的繼受來看,更為純粹地否定立案證據(jù)、以訴狀為準(zhǔn)的觀點(diǎn)更為直截了當(dāng)。如果我國未來改采純粹的立案登記制,由一個(gè)司法行政機(jī)構(gòu)負(fù)責(zé)形式上的案件登記(如美國法)或者額外再由審判長(zhǎng)負(fù)責(zé)審查有限的起訴要件(如德國法),以訴狀審查相關(guān)程序性事項(xiàng)似乎是完全可取的。但是,在目前的條件下,本文仍然認(rèn)為有必要保留實(shí)務(wù)中通常的做法,將純粹程序性事項(xiàng)作為例外需要收集立案證據(jù)的事項(xiàng)。以當(dāng)事人的住所或經(jīng)常居住地(《民事訴訟法》第22 條、第23 條和第34 條第3 項(xiàng))為例,此類事項(xiàng)與實(shí)體請(qǐng)求權(quán)是否成立無關(guān)(并非與實(shí)體和程序問題雙重相關(guān)〔76〕參見曹志勛:《民事訴訟中的雙重相關(guān)事實(shí)——“初步證據(jù)”向“假定為真”的轉(zhuǎn)變》,載《環(huán)球法律評(píng)論》2021 年第1 期,第117-131 頁。),因而不涉及在同一民事訴訟中重復(fù)認(rèn)定、需要立案庭與審判庭分工的問題。無論如何,這一管轄連接點(diǎn)需要在法院受理之前或者之后進(jìn)入實(shí)體審理前查明。在現(xiàn)有法院內(nèi)設(shè)機(jī)構(gòu)不相應(yīng)做進(jìn)一步調(diào)整的前提下,我國一貫的立案審查傳統(tǒng)以及立案庭的傳統(tǒng)配置都支持立案庭在立案審查時(shí)繼續(xù)承擔(dān)這一任務(wù),而不必延后至法院受理之后。尤其是立案法官通常可以在原告遞交訴狀時(shí)清楚地判斷上述問題。對(duì)比德國法可見,諸如被告住所(《德國民事訴訟法典》第13 條、第16 條和第17 條)和被告財(cái)產(chǎn)所在地(《德國民事訴訟法典》第23 條)也都屬于在被告抗辯后需要由原告提交證據(jù)加以證明的事項(xiàng)。〔77〕Vgl.MüKoZPO/W?stmann, 6.Aufl., 2020, § 1 Rn.25.只不過,德國法將其置于基于起訴要件形式審查的立案后階段,而我國法則將此類事項(xiàng)前移。在縮減了立案實(shí)質(zhì)審查的其他內(nèi)容后,由于在司法組織上立案庭獨(dú)立存在,我國的處理方式似乎更能尋求訴訟效率與程序保障的平衡。
與此類似,標(biāo)的物所在地(《民事訴訟法》第25 條和第35 條)、合同簽訂地(《民事訴訟法》第35 條)或者專屬管轄中的不動(dòng)產(chǎn)所在地、港口所在地和主要遺產(chǎn)所在地(《民事訴訟法》第34 條)作為單純的程序性標(biāo)準(zhǔn),同樣應(yīng)當(dāng)由立案庭直接審查。此外,對(duì)于當(dāng)事人能力、訴訟能力、訴訟代理權(quán)或者交納訴訟費(fèi)用來說,適用純粹程序性標(biāo)準(zhǔn)可能也沒有爭(zhēng)議,此時(shí)應(yīng)當(dāng)提供訴訟主體資格的資料和授權(quán)委托書等資料(《登記立案規(guī)定》第6 條第1 項(xiàng)和第2 項(xiàng))。〔78〕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訴訟證據(jù)規(guī)定理解與適用》(上冊(c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77-78 頁。就被告的明確而言,由于完全依賴原告提供被告信息可能導(dǎo)致送達(dá)困難和被告信息錯(cuò)誤,〔79〕參見劉強(qiáng):《芻議立案登記中“明確的被告”的形式審查問題》,載《人民法院報(bào)》2015 年5 月13 日,第8 版。這確實(shí)可能存在一定困難。但是,至少從現(xiàn)行法的規(guī)定來看,在立案階段顯然僅要求被告足以確定即可,即原告提供的被告姓名或者名稱、住所等信息具體、明確,足以使被告與他人相區(qū)別(《民訴解釋》第209 條第1 款)。這仍然是一個(gè)可以從形式上認(rèn)定的事項(xiàng)。〔80〕立法論上的相反主張,參見段文波:《論民事訴訟被告之“明確”》,載《比較法研究》2020 年第5 期,第164-176 頁。在“一對(duì)一”的簡(jiǎn)單案件中,當(dāng)事人明確的證據(jù)要求也許不難滿足;但是當(dāng)涉及多數(shù)當(dāng)事人時(shí),例如在遺產(chǎn)案件等構(gòu)成必要共同訴訟的情形中,此類程序性要求可能會(huì)導(dǎo)致當(dāng)事人反復(fù)往返于“導(dǎo)訴臺(tái)”前補(bǔ)充提交資料。從司法便民的角度來看,這顯然也并不可取。甚至在少數(shù)諸如網(wǎng)絡(luò)侵權(quán)的案件中,如果掌握被告信息的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不配合,原告確實(shí)很難自行查找被告的身份信息,但是這并不妨礙在立案階段僅要求以特定指稱明確被告。至于我國法上被告適格訴訟要件的“發(fā)現(xiàn)”,則并不是本階段需要重點(diǎn)關(guān)注的內(nèi)容。
于是,原告應(yīng)當(dāng)在立案階段就提供證據(jù)或者證明材料,并且通過自己的情況說明使法院認(rèn)為有關(guān)程序性事實(shí)存在的可能性較大(2019 年《證據(jù)規(guī)定》第86 條第2 款),例如被告在受訴法院轄區(qū)有住所或居所。如果原告的訴狀不滿足上述要求且無法補(bǔ)正,應(yīng)當(dāng)裁定不予受理。例如,2019 年《北京市高級(jí)人民法院關(guān)于立案審判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答(二)》第40 條規(guī)定,原告主張以經(jīng)常居住地或者主要辦事機(jī)構(gòu)所在地作為管轄連接點(diǎn)時(shí),應(yīng)當(dāng)提供其離開住所至起訴時(shí)已在經(jīng)常居住地連續(xù)居住一年以上或者其主要辦事機(jī)構(gòu)所在地位于受訴法院轄區(qū)的證據(jù)材料,例如公安機(jī)關(guān)出具的居住證、居住或辦公證明、房屋租賃合同等。尤其對(duì)于主要辦事機(jī)構(gòu)所在地的證據(jù)材料,立案庭應(yīng)全面、客觀地審查并綜合判斷,且相應(yīng)采取裁定不予受理、先行立案或者通過管轄權(quán)異議程序或依職權(quán)審查的解決方案。
從大陸法系證明理論來看,對(duì)訴訟要件所采取的自由證明不同于所謂的疏明,仍應(yīng)達(dá)到使法官完全確信的程度,并未降低待證事實(shí)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81〕Vgl.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18.Aufl., 2018, § 111 Rn.8 ff.; Baumg?rtel/Laumen, Handbuch der Beweislast: Grundlagen, 4.Aufl., 2019, Kap.2 Rn.25 ff.;新堂幸司『民事訴訟法』(弘文堂,2019 年)578-579 頁參照;松本博之=上野泰男『民事訴訟法』(弘文堂,2015 年)426 頁參照;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下冊(cè)),新學(xué)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版,第4-5 頁。由于相關(guān)程序性事實(shí)構(gòu)成訴訟要件的內(nèi)容,應(yīng)當(dāng)由法官依職權(quán)審查,當(dāng)然也不受當(dāng)事人提出證據(jù)的約束。〔82〕Vgl.BGH NJW 2019, 76, 78, Tz.34.易言之,在這種理解下,對(duì)這種程序性事項(xiàng)的證明并非僅要求可能性較大,而是完全證明。但是,我國法上將此類審查前移至立案審查階段,而且在隨后的管轄權(quán)異議階段,法院目前就訴訟要件常常也只要求初步證據(jù)。〔83〕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1718 號(hào)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1685 號(hào)民事裁定書。因此,似乎不宜照搬外國法上的處理方案,而是最多提供初步證據(jù)即可,即原告只需提出證據(jù),無需證明材料的真實(shí)性。特別是在立案階段原告常常難以收集涉及被告管轄連接點(diǎn)的信息,即使要求例外地就此提供立案證據(jù),也應(yīng)當(dāng)盡可能降低要求。
2.公益性特別規(guī)定
比較而言,我國法上的公益訴訟更多地出于防止訴權(quán)濫用的目的,對(duì)起訴證據(jù)有必要提出更高要求。這可以分為受保護(hù)的公共利益與起訴主體兩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原告在環(huán)境、消費(fèi)公益訴訟中提供社會(huì)公共利益受到損害的初步證據(jù)(《民訴解釋》第282 條第3 項(xiàng)),前者針對(duì)被告的行為已經(jīng)損害社會(huì)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損害社會(huì)公共利益的重大風(fēng)險(xiǎn)[《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jiǎn)稱《環(huán)境公益訴訟解釋》)第8 條第2 項(xiàng)],后者則以被告的行為侵害眾多不特定消費(fèi)者的合法權(quán)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費(fèi)者人身、財(cái)產(chǎn)安全的危險(xiǎn)[《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消費(fèi)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jiǎn)稱《消費(fèi)公益訴訟解釋》)第4 條第2 項(xiàng)]為代表。與此相似,《證券法》第95 條第1 款和第2 款規(guī)定了普通代表人訴訟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以下簡(jiǎn)稱《證券代表人規(guī)定》)第5 條第1 款第3 項(xiàng)就此規(guī)定,原告在起訴時(shí)需要提交證明證券侵權(quán)事實(shí)的初步證據(jù)。考慮到此類訴訟針對(duì)的是證券市場(chǎng)虛假陳述、內(nèi)幕交易、操縱市場(chǎng)等行為(《證券代表人規(guī)定》第1 條第1 款),常常涉及人數(shù)眾多投資人的權(quán)益和資本市場(chǎng)的合法健康發(fā)展,也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其中的初步證據(jù)要求,作為適用于不同案件類型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類似于前述私益訴訟中的初步證據(jù)要求。
另一方面,當(dāng)社會(huì)組織提起環(huán)境公益訴訟時(shí),應(yīng)提交社會(huì)組織登記證書、章程、起訴前連續(xù)五年的年度工作報(bào)告書或者年檢報(bào)告書,以及經(jīng)簽字并加蓋公章的無違法記錄的聲明(《環(huán)境公益訴訟解釋》第8 條第3 項(xiàng))。而在消費(fèi)者公益訴訟中,原告則需要提交消費(fèi)者組織就涉訴事項(xiàng)已履行公益性職責(zé)的證明材料(《消費(fèi)公益訴訟解釋》第4 條第3 項(xiàng)),包括就有關(guān)消費(fèi)者合法權(quán)益的問題向有關(guān)部門反映、查詢和提出建議(《消費(fèi)者權(quán)益保護(hù)法》第37 條第1 款第4 項(xiàng))以及受理投訴并加以調(diào)查、調(diào)解(《消費(fèi)者權(quán)益保護(hù)法》第37 條第1 款第5 項(xiàng))。在前述《證券法》下起訴時(shí)當(dāng)事人人數(shù)尚未確定的普通代表人訴訟中,希望參加訴訟的權(quán)利人在權(quán)利登記時(shí)也需要提供身份證明文件、交易記錄及投資損失等證據(jù)材料(《證券代表人規(guī)定》第8 條第2 款),以證明其滿足此時(shí)對(duì)起訴主體的特別要求。在前兩類訴訟中,司法實(shí)踐中抬高起訴難度的通常不是立案證據(jù)的要求。與當(dāng)下我國法對(duì)適格訴訟主體的限制可能產(chǎn)生的爭(zhēng)議相比,一定程度的立案證據(jù)要求其實(shí)恰恰符合此類訴訟的公益屬性。
與此類似,在第三人撤銷之訴中,除了飽受爭(zhēng)議的適格主體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84〕參見李浩:《第三人撤銷之訴抑或?qū)徟斜O(jiān)督程序——受害債權(quán)人救濟(jì)方式的反思與重構(gòu)》,載《現(xiàn)代法學(xué)》2020 年第5 期,第66-80 頁。就單一案件類型的研究,參見宋史超:《論股東對(duì)公司對(duì)外訴訟裁判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兼評(píng)最高人民法院指導(dǎo)案例148 號(hào)》,載《法學(xué)》2022 年第1 期,第112-127 頁。和程序定性〔85〕參見吳英姿:《我國第三人撤銷之訴的“神”與“形”——第148-153 號(hào)指導(dǎo)性案例研究》,載《政法論壇》2021 年第6 期,第54-69 頁。外,也需要提交滿足其啟動(dòng)要件的證據(jù)材料(《民訴解釋》第290 條)。例如,當(dāng)起訴人提出的《購船合同》載明合同雙方當(dāng)事人為被起訴人和第三人,并且約定了由起訴人承擔(dān)付清尾款的義務(wù)時(shí),《購船合同》被認(rèn)為并不能證明起訴人為合同當(dāng)事人,也不能顯示起訴人是否與被起訴人合伙購買船舶因而因另案判決遭受利益損害,于是不能滿足第三人撤銷之訴的起訴要求。〔86〕參見廣東省高級(jí)人民法院(2019)粵民初54 號(hào)民事裁定書。同樣地,起訴人未能提供證據(jù)證明因不能歸責(zé)于其本人的事由未參加該案訴訟,〔87〕參見河北省高級(jí)人民法院(2016)冀民初41 號(hào)民事裁定書。也可以導(dǎo)致不予受理的后果。
同時(shí),《民訴解釋》第291 條第3 款則規(guī)定起訴條件的審查期限為收到起訴狀及起訴證據(jù)之日起30 日內(nèi),此時(shí)立案審查的時(shí)間更為寬裕,相應(yīng)地也應(yīng)該能夠期待法院對(duì)這種作為特別救濟(jì)的起訴作出更為實(shí)質(zhì)的審查。此時(shí)僅就立案審查而言,法院也可以與一般訴訟中的做法相同,基于起訴人對(duì)起訴事實(shí)的主張,認(rèn)為起訴人作為另案生效調(diào)解書中債務(wù)人的普通債權(quán)人,不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的主體條件。〔88〕參見青海省高級(jí)人民法院(2016)青民初8 號(hào)民事裁定書;四川省高級(jí)人民法院(2015)川民初字第42 號(hào)民事裁定書。目前的主流實(shí)務(wù)見解,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3月公布的第148號(hào)至第153號(hào)指導(dǎo)案例以及《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huì)議紀(jì)要》(法〔2019〕254 號(hào))第120 條。當(dāng)“起訴人要求撤銷的相關(guān)內(nèi)容僅是對(duì)涉案專利發(fā)明過程的描述,并沒有對(duì)發(fā)明人的署名作出任何認(rèn)定或者改變”時(shí),除了撤銷內(nèi)容僅為裁判理由而非判決主文外,法院也可能認(rèn)為起訴人的民事權(quán)益不會(huì)受到損害。〔89〕參見北京市高級(jí)人民法院(2016)京民初31 號(hào)民事裁定書。
此外,也可以從實(shí)體法上尋找此類就立案證據(jù)的高要求,但應(yīng)當(dāng)繼續(xù)注意區(qū)分實(shí)體勝訴條件和起訴條件。這集中體現(xiàn)在對(duì)《民法典》第1073 條下確認(rèn)或否定親子關(guān)系之訴的訴訟法認(rèn)識(shí)上。從該條明確規(guī)定的“正當(dāng)理由”要件出發(fā),相關(guān)官方釋義書認(rèn)為,其立法目的是出于對(duì)“家庭穩(wěn)定和未成年人的保護(hù)”而“提高此類訴訟的門檻”。該官方釋義書認(rèn)為,一方面,該條并未具體規(guī)定認(rèn)定“正當(dāng)理由”的標(biāo)準(zhǔn)和方式,而將其交由法院具體處理;另一方面則未加論證地將“正當(dāng)理由”解讀為法院受理的要件和初步證據(jù)標(biāo)準(zhǔn)。〔90〕參見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解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159-160 頁。與此不同,在被立法者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具體解讀上述法條的最高人民法院看來,該條規(guī)定其實(shí)只是對(duì)實(shí)體審理的規(guī)定,“必須對(duì)當(dāng)事人提交的證據(jù)嚴(yán)格審核和認(rèn)定”,“請(qǐng)求確認(rèn)或否認(rèn)親子關(guān)系,應(yīng)當(dāng)提供充分證據(jù)予以證明”。〔91〕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shí)施工作領(lǐng)導(dǎo)小組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繼承編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第223-224 頁。至少在現(xiàn)行法的解釋論上,立法者也認(rèn)可解釋抽象法律概念/一般條款的權(quán)限在裁判者,此時(shí)應(yīng)當(dāng)以裁判者的解釋為準(zhǔn),上述官方釋義書的例舉與此存在沖突,不應(yīng)采納。因此,應(yīng)當(dāng)認(rèn)為《民法典》第1073 條并未包含對(duì)立案證據(jù)的高要求。從應(yīng)然的立法論來看,對(duì)“家庭穩(wěn)定和未成年人的保護(hù)”并不一定要通過提高立案證據(jù)的要求來實(shí)現(xiàn),實(shí)體勝訴要件中的“正當(dāng)理由”標(biāo)準(zhǔn)及其在司法適用中形成的類案標(biāo)準(zhǔn)也將具有示范/警示效力。而且,不允許當(dāng)事人通過起訴方式解決,并不意味著家庭矛盾就此不存在了。
五、結(jié)語
暫且不論目前司法實(shí)務(wù)界是否已經(jīng)習(xí)慣在起訴前就開始收集證據(jù)、在起訴時(shí)基于訴訟策略一并提交部分證據(jù),一旦提交立案證據(jù)被默認(rèn)為民事訴訟的必備要素,其合法性和正當(dāng)性都值得探究。立案登記制改革絕非曾要求的在收到訴狀和相關(guān)證據(jù)時(shí)登記并出具收據(jù),也不僅是原則上要將當(dāng)事人的起訴登記下來并加注案號(hào),而是對(duì)我國民事訴訟程序在整體上的調(diào)整。相應(yīng)地,這種變革對(duì)解釋論上的價(jià)值判斷、相關(guān)要件的內(nèi)容構(gòu)成和不同程序階段的功能定位也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基于對(duì)法院內(nèi)部架構(gòu)的制度安排和長(zhǎng)期本土實(shí)踐所形塑的路徑依賴,在現(xiàn)階段需要更多地提出有別于比較法經(jīng)驗(yàn)的中國方案。這不僅應(yīng)當(dāng)適用于傳統(tǒng)的民事訴訟形態(tài),同樣也能夠作為在電子訴訟與智能化訴訟背景下需要繼續(xù)遵循的基本規(guī)則。
無論如何,起訴與立案階段的司法審查直接觸及作為基本權(quán)利與人權(quán)保障的民事訴權(quán)。對(duì)通常不接觸司法訴訟的普通人而言,這更是對(duì)我國司法系統(tǒng)觀感如何的直接依據(jù)。除了要求特別重視相關(guān)審查條件的要件化與體系化外,民事訴訟法解釋中的基本立場(chǎng)與傾向也應(yīng)當(dāng)側(cè)重對(duì)當(dāng)事人起訴行為的支持與促進(jìn),規(guī)制、教化或者組織運(yùn)營(yíng)方面的考慮只能退而居其次。在復(fù)合的需求面前,本文更傾向于謝絕“非黑即白”式的簡(jiǎn)單答案,而偏好同一要件內(nèi)部的類型化努力,同時(shí)不忘追問其背后的道理。這種立案技術(shù)上的完善以及裁判技術(shù)和審理技術(shù)的精細(xì)化,除了有望促進(jìn)社會(huì)公平正義法治保障制度的健全,也能在呼應(yīng)與聯(lián)結(jié)以《民法典》為代表的實(shí)體法規(guī)則之外,繼續(xù)成為民事程序法學(xué)本體論的主要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