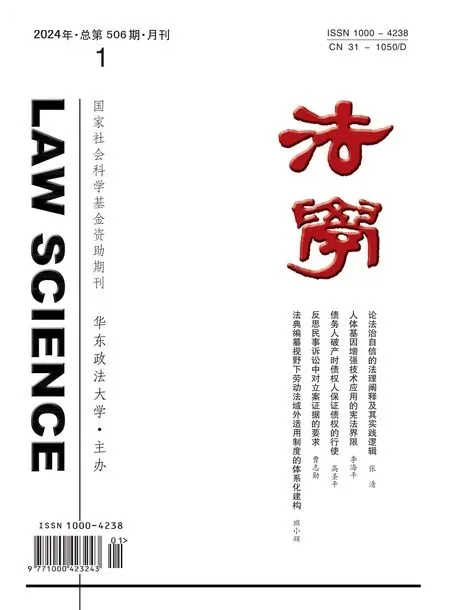債務人破產時債權人保證債權的行使
●高圣平
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或者發生當事人約定的情形,保證債權的實現條件成就。在非破產語境下,若保證人承擔的是一般保證責任,債權人不得在就債務人責任財產強制執行之前單獨起訴保證人,但可以同時起訴債務人與保證人;若保證人承擔的是連帶責任保證責任,債權人可以參酌具體情形,選擇向債務人主張主債權和/或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在債務人破產的情形下,債權人向債務人主張主債權體現為向破產管理人申報破產債權。債權人可否同時請求保證人履行保證債務?若可以,應如何防止債權人超額受償的問題?在債權人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時該如何適用保證期間和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這些均為破產實踐中的爭議問題。在《民法典》實施之前,原《擔保法》、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原《擔保法解釋》)、《企業破產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破產審判會議紀要》)在原有的保證規則之下對這些問題作了部分規定。《民法典》大幅修改了此前的保證規則,〔1〕關于保證規則修改的介紹,參見王利明:《我國〈民法典〉保證合同新規則釋評及適用要旨》,載《政治與法律》2020 年第12 期,第2-15 頁;崔建遠:《論保證規則的變化》,載《中州學刊》2021 年第1 期,第60-72 頁。《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以下簡稱《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囿于其調整范圍的限制,并未對上述問題作出全面回應。如此,基于原有保證規則所作的相關規定也就沒有得到全面修改,增加了司法實踐中的解釋困難。本文不揣淺薄,擬就此一陳管見,以求教于同仁。
一、債務人破產時債權人行使保證債權的途徑
在通常情況下,債務人破產并不影響債權人保證債權的行使。〔2〕See Roy Goode & Louise Gullifer, Goode and Gullifer on Legal Problems of Credit and Security, 6th ed., Thomson Reuters,2018, p.419.依據《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23 條第1 款,債務人破產之時,債權人可以在申報破產債權的同時或者之后請求保證人履行保證債務。在解釋上,債權人此際就其債權的實現并不僅以同時主張兩種權利為限,債權人尚可僅向破產管理人申報破產債權,還可僅請求保證人履行保證債務;債權人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的方式也不僅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為限,申請仲裁、直接向保證人主張權利等均無不可。
(一)債權人既申報破產債權,又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
就債務人破產時債權人行使保證債權的途徑而言,原《擔保法解釋》第44 條〔3〕該條第1 款規定:“保證期間,人民法院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的,債權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報債權,也可以向保證人主張權利。”該條第2 款規定:“債權人申報債權后在破產程序中未受清償的部分,保證人仍應當承擔保證責任。債權人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應當在破產程序終結后六個月內提出。”第1 款使用了“既可以……也可以……”的表述,但并未規定債權人可以同時申報破產債權和主張保證債權,因而在解釋上存在“擇一說”和“并行說”的爭論:“擇一說”認為債權人僅得選擇兩種方式之一而主張權利;“并行說”認為債權人可以同時主張兩種權利。〔4〕參見郁琳、吳光榮:《與破產法有關的幾個擔保問題》,載《法律適用》2021 年第9 期,第11-12 頁。我國實定法上類似表述的解釋論并不一致。例如,《民法典》第752 條(原《合同法》第248 條)中“可以……也可以……”的表述就被解釋為出租人僅可在兩種救濟路徑之間享有選擇權,但不能同時主張,明顯采取了“擇一說”的觀點;〔5〕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融資租賃合同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 年版,第17 頁;高圣平:《民法典上融資租賃交易的擔保功能》,載《政法論壇》2023 年第5 期,第95 頁。而《民法典》第688條第2 款、第766 條中“可以……也可以……”的表述卻被解釋為債權人在兩種救濟路徑之間既可以擇一主張,也可以同時主張,兩者之間不構成非此即彼的關系,即采納了“并行說”的觀點。〔6〕參見何穎來:《〈民法典〉中有追索權保理的法律構造》,載《中州學刊》2020 年第6 期,第68 頁;潘運華:《民法典中有追索權保理的教義學構造》,載《法商研究》2021 年第5 期,第183-184 頁;高圣平:《論民法典上保理交易的擔保功能》,載《法商研究》2023年第2 期,第14-16 頁。
原《擔保法解釋》第44 條第1 款的原意是采納了“擇一說”。在債務人破產時,債權人可以選擇向破產管理人申報破產債權或者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但不得同時主張。其一,若債權人選擇申報破產債權,在破產程序終結前,無法確定其自破產分配得以受償的具體數額,也就無法同時就其未受清償的部分向保證人主張權利,〔7〕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二終字第83 號民事判決書。因此債權人此際“暫時無權向保證人主張權利”,否則“會出現同一債務雙重受償的結果”。〔8〕李國光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理解與適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177-178 頁。相同觀點參見姜啟波主編:《擔保糾紛新型典型案例與專題指導》,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 年版,第188 頁;孫鵬主編:《最高人民法院擔保法司法解釋精釋精解》,中國法制出版社2016 年版,第190 頁。原《擔保法解釋》第44 條第2 款的適用以債權人已經申報債權為前提,僅在此種情形下,債權人才能就其在破產程序中未受清償的部分向保證人主張權利。因此,從該款的規定也可以反推出債權人不能同時向破產管理人申報破產債權和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的結論。〔9〕參見安徽省銅陵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皖07 民終997 號民事裁定書。其二,若債權人選擇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而不申報破產債權的,債權人應通知保證人,由保證人預先行使追償權,向破產管理人申報破產債權。債權人既未申報破產債權,也未通知保證人,致使保證人不能預先行使追償權的,保證人在該債權在破產程序中可能受償的范圍內免除保證責任(原《擔保法解釋》第45 條)。如此,這一問題在原《擔保法解釋》所確立的規則體系內部得到了相對圓滿的解釋,并得到較多裁判的支持。〔10〕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二終字第83 號民事判決書;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1)豫法民終字第19 號民事裁定書等。
但是,“擇一說”確實限制了債權人在債務人破產時的權利行使,大大延長了債權人向保證人主張權利的時間,增加了債權人權利實現的風險。〔11〕參見郁琳、吳光榮:《與破產法有關的幾個擔保問題》,載《法律適用》2021 年第9 期,第11 頁;何心月:《破產程序中保證債權的行使及其限制》,載《法學家》2023 年第1 期,第165 頁。其一,與非破產語境下債權人實現債權時的選擇權相違背。就連帶責任保證而言,在保證債權可得行使時,債權人可以請求債務人履行主債務,也可以請求保證人履行保證債務(《民法典》第688 條)。在解釋上,債權人還可以同時主張這兩種權利。〔12〕參見李國光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理解與適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425 頁;高圣平:《民法典擔保制度及其配套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21 年版,第118 頁。就一般保證而言,在債務人破產構成先訴抗辯權的阻卻事由之下,一般保證人的地位已與連帶責任保證人無異(容后詳述)。“擇一說”限制債權人的選擇權并無正當理由。其二,《企業破產法》就此并未作出例外安排。《企業破產法》第124 條的規定〔13〕該條規定:“破產人的保證人和其他連帶債務人,在破產程序終結后,對債權人依照破產清算程序未受清償的債權,依法繼續承擔清償責任。”并未將債權人向保證人主張權利限定于破產程序終結之后,也未將債務人破產時保證債權的行使范圍僅限于“依照破產清算程序未受清償的債權”,而是僅涉及“在破產程序終結后”主張保證債權這一種情形,并不涉及債權人選擇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的情形,也不及于債權人同時申報債權和主張保證債權的情形。由此可見,《企業破產法》第124條并不能作為采行“擇一說”的規范基礎。
在原《擔保法解釋》實施之后,司法實踐開始反思“擇一說”的弊端。《最高人民法院對〈關于擔保期間債權人向保證人主張權利的方式及程序問題的請示〉的答復》(〔2002〕民二他字第32 號)〔14〕該答復中指出:“對于債權人申報了債權,同時又起訴保證人的保證糾紛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在具體審理并認定保證人應承擔保證責任的金額時,如需等待破產程序結束的,可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五)項的規定,裁定中止訴訟。人民法院如徑行判決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應當在判決中明確應扣除債權人在債務人破產程序中可以分得的部分。”其中所援引的條文現為《民事訴訟法》第153 條第1 款第5 項,內容未作修改。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了“并行說”的觀點,即允許債權人在申報破產債權的同時或者之后訴請保證人履行保證債務,〔15〕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終字第117 號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546 號民事判決書;山西省朔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2)晉06 民終258 號民事裁定書。但“徑行判決”僅限于保證人于破產程序終結后對債權人未受清償的部分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不可判決由保證人直接承擔保證責任。〔16〕參見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浙03 民終2727 號民事判決書;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浙07 民終3817 號民事判決書;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8)津01 民終13 號民事判決書;曹守曄主編:《破產糾紛案件裁判規則(一):破產債權效力與破產財產》,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271 頁。由此可見,無論是“中止訴訟”還是“徑行判決”,均須首先確定債權人在破產程序中的受償數額,從而將保證人的責任界定為補充責任。〔17〕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執監885 號執行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837 號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676 號民事裁定書。破產程序復雜而冗長,這一答復意見不僅增加了債權實現的風險,而且使債權人蒙受了該期間停止計息的額外損失。因此,上述答復的意義僅在于賦予債權人起訴保證人的權利,并未在實體層面徹底解決債權人的權利實現難題,仍然會出現保證債權得不到及時充分實現的問題。〔18〕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 年版,第249-250 頁。
《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23 條第1 款已經改變了〔2002〕民二他字第32 號的司法態度。債權人自可在向破產管理人申報破產債權之時或者之后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依據《企業破產法》第46 條第1 款的規定,在債務人破產時,未到期的主債權即應視為到期,保證人原本基于從屬性可得主張的債務人的期限利益隨即喪失,債權人自可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此外,《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23 條第1 款采用了“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的表述,即意味著人民法院不僅應受理擔保糾紛訴訟,還應就債權人的主張予以實體審理并作出相應判決,而不應駁回起訴或者裁定中止訴訟。〔19〕同上注,第250 頁。因此,《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實際上采納了“并行說”。〔20〕參見郁琳、吳光榮:《與破產法有關的幾個擔保問題》,載《法律適用》2021 年第9 期,第13 頁。在“并行說”之下,債權人既可以從債務人破產程序中受償,又可自保證人處受償,債務人破產不影響債權人保證債權的行使,但也不能使債權人額外獲益。如此,債權人分別自債務人和保證人所獲清償不能超出其債權總額。由此可見,在債務人破產時所欲規制的是債權人超額受償,而非重復受償(雙重受償)。若債權人自債務人和保證人的重復受償之和并未超過其債權額,自應允許。至于其中可能出現的債權人超額受償的風險,尚須借助于其他制度予以解決,容后詳述。
(二)債權人申報破產債權,在破產程序終結后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
依據《企業破產法》第124 條的規定,債務人因破產而免責,但免責的效力并不及于保證人,保證人對債權人在債務人破產程序中未受清償的部分仍應“依法”承擔保證責任。〔21〕參見包曉麗、司偉:《民法典保證期間規定理解適用中的幾個問題》,載《法律適用》2021 年第1 期,第136 頁。尚存疑問的是,債權人在破產程序終結后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是否受到期限限制。就此,原《擔保法解釋》第44 條第2 款規定,債權人應當“在破產程序終結后六個月內”請求保證人履行保證債務;《破產審判會議紀要》第31 條延續了這一規定。之所以規定為6 個月,是因為保證期間被推定為6 個月。只不過,在正常情形下推定為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之日起6 個月,在債務人破產時改為破產程序終結后的6 個月。〔22〕參見吳光榮:《擔保法精講》,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23 年版,第237 頁。
在“擇一說”之下,債權人申報債權后即無法在破產程序終結之前向保證人主張權利。〔23〕參見李國光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理解與適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177-178 頁。保證期間在破產程序開始時尚未經過而在破產程序中經過的,“考慮到債權人在債務人破產期間不便對保證人行使權利,債權人可以在債務人破產終結后6 個月內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24〕《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就如何適用〈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四條請示的答復》(〔2003〕民二他字第49 號)。相關案例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569 號民事裁定書。也就是說,“該6 個月具有延長保證期間的作用”,〔25〕曹士兵:《中國擔保制度與擔保方法》(第5 版),中國法制出版社2022 年版,第215 頁。“保證期間一直持續至破產程序終結之日起6 個月”。〔26〕孫鵬主編:《最高人民法院擔保法司法解釋精釋精解》,中國法制出版社2016 年版,第181 頁。
關于“破產程序終結后6 個月”的法律意義,學說和裁判存在不同的認識。第一種觀點認為,“6個月”是債權人向保證人主張權利的寬限期,〔27〕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終字第99 號民事判決書。不能發生取代保證期間的效果,實質上具有延長保證期間的作用,〔28〕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3578 號民事裁定書。在性質上仍然屬于保證期間。〔29〕參見孫鵬主編:《最高人民法院擔保法司法解釋精釋精解》,中國法制出版社2016 年版,第183 頁。在債務人破產程序終結后,保證人的保證期間尚未屆滿的,債權人應當在保證期間內向保證人主張權利,不適用該“6 個月”期間的規定。在債務人破產時保證期間尚未屆滿,而在債務人破產過程中保證期間屆滿的,債權人在債務人破產程序終結后仍然享有6 個月的保證期間,〔30〕參見曹士兵:《中國擔保制度與擔保方法》(第5 版),中國法制出版社2022 年版,第215 頁。若債權人超過該期限主張權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31〕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041 號民事裁定書。第二種觀點認為,“6 個月”并非保證期間,而是保證人在保證期間經過之后仍須履行保證債務的特殊規定。除了適用于保證期間在破產程序開始時尚未經過而在破產程序中經過的情形之外,還應適用于債務人破產程序開始之前債權人已請求保證人履行保證債務,保證期間失效、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開始計算,訴訟時效期間內債務人破產等情形。在程序法意義上,“6 個月”期間屆至之前應屬《民事訴訟法》第127 條第6 項規定的“在一定期限內不得起訴的案件”的情形。若在該期限內起訴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裁定駁回起訴。〔32〕參見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2017)浙0204 民初786 號民事裁定書;陳雯雯:《債務人已破產時保證期間是否屆滿對債權人的影響》,載《人民司法?案例》2018 年第26 期,第6-7 頁。
這種基于“擇一說”的規則設計和學說發展帶來了難以化解的解釋沖突。本來具有保護保證人功能的保證期間制度,在債務人破產時卻失去了保護保證人的功能,造成了破產與非破產語境下的不同處遇,而這一不同處遇并無上位法的支撐。保證期間制度的規范目的即在于敦促債權人及時行使權利,降低保證人的代償風險。〔33〕參見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釋義》,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500 頁。在債務人破產程序中,債權人不積極行使權利而導致保證期間經過,債權人的保證債權即告消滅,但原《擔保法解釋》第44 條第2 款卻規定債權人在破產程序終結后仍可恢復行使本已消滅的保證債權,此與保證期間屬于不變期間,不因任何事由(包括債務人破產)發生中止、中斷、延長的既有政策選擇相沖突,不利于債權人與保證人之間的利益平衡。〔34〕參見郁琳:《“債權人可同時主張保證責任”的理解與適用》,載《人民司法?案例》2018 年第26 期,第9 頁。即使保證人不因債務人的破產而免責,也只是保證人不享有額外利益,但這并不意味著保證人責任的擴大,其承擔保證責任的范圍和強度在債務人破產的情形下仍然不得大于原來約定的范圍和強度,否則即違背了保證人在保證合同訂立時的合理期待。擔保制度的功能在于增強債權的效力,提高債權獲償的可能性,其真正發揮作用即在債務人破產時。若債務人具有足夠的清償能力,擔保制度的社會功能也就僅在于促成資金高效率運用。〔35〕參見謝在全:《擔保物權制度的成長與蛻變》,載《法學家》2019 年第1 期,第37 頁。由此可見,除非法律另有特別規定,在債務人破產時,民法典擔保制度當然具有普遍適用的價值。
正是基于此,《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23 條在采行“并行說”的同時,刪去了原《擔保法解釋》第44條第2款的前述規定。在原《擔保法解釋》已被廢止的情形下,其第44條第2款的內容因“已被《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23 條吸收并修改”而不在司法實踐中沿襲適用。〔36〕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 年版,第674 頁。基于該款的《破產審判會議紀要》第31 條第二句亦應停止適用。前述《企業破產法》第124 條規定中的“依法”當然包括保證期間和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等相關規則的適用。由此可見,在債務人破產的情形下,保證人仍受保證期間和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制度的保護,因此并無再設定其他期間予以保護的必要。〔37〕參見郁琳、吳光榮:《與破產法有關的幾個擔保問題》,載《法律適用》2021 年第9 期,第13 頁。在《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23 條未就債務人破產時保證期間制度的適用作出特別安排的背景下,債權人在債務人破產程序終結之后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自應適用保證期間和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一般規則。
(三)債權人不申報破產債權,僅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
在保證方式為連帶責任保證的情形下,《民法典》第688 條第2 款的規定即表明保證人對債務人而言并無順序利益,債權人在此享有充分的程序選擇權。〔38〕參見夏群佩、洪海波:《主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后連帶保證人的責任范圍》,載《人民司法?案例》2017 年第14 期,第78 頁。在“并行說”之下,債權人自可不申報債權而僅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
在保證方式為一般保證的情形下,保證人享有先訴抗辯權。在解釋上,盡管債務人破產即意味著對其破產財產的概括執行,但人民法院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即產生中止執行程序的后果,此際,債權人不能再通過強制執行程序向債務人主張個別清償,〔39〕參見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釋義》,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494 頁。債務人顯然已經陷于履行不能的狀態,若仍然允許保證人援引先訴抗辯權,將徒增債權人行使權利的成本費用。〔40〕參見許德風:《破產中的連帶債務》,載《法學》2016 年第12 期,第99 頁;包曉麗、司偉:《民法典保證期間規定理解適用中的幾個問題》,載《法律適用》2021 年第1 期,第136 頁。基于此,《民法典》第687 條第2 款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即構成先訴抗辯權的典型阻卻事由。但關于債權人如何向一般保證人主張權利尚存爭議。
第一種觀點認為,債權人只有在保證期間失效之后,才談得上是否阻卻先訴抗辯權的問題,而債權人尚須依法行使權利才能使保證期間失效。如此,在債務人破產時,債權人雖然在程序上不能對債務人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但仍須通過向破產管理人依法申報破產債權而使保證期間失效,轉而才能向保證人主張權利。〔41〕參見麻錦亮:《民法典?擔保注釋書》,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23 年版,第223 頁。這就意味著在一般保證的情形下,債權人若未向破產管理人申報破產債權,則無法向保證人主張權利。
第二種觀點認為,在債務人破產時,阻卻先訴抗辯權的行使僅在于程序上的意義,亦即債權人可以直接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但并不影響保證人實體上責任的承擔。喪失先訴抗辯權的一般保證人仍僅承擔補充責任,亦即保證人承擔的責任仍應扣減債權人自債務人破產分配中已獲清償的部分。〔42〕參見王欣新:《論破產程序中一般保證人的責任》,載《人民法院報》2019 年2 月28 日,第7 版。這就意味著在一般保證的情形下,債權人雖然無須向破產管理人申報破產債權而直接向保證人主張權利,但保證人具體承擔保證責任尚須以債權人已在債務人破產程序中受領破產分配給付為前提。
第三種觀點認為,在先訴抗辯權被特定事由阻卻時,債權人自可直接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43〕參見何心月:《破產程序中保證債權的行使及其限制》,載《法學家》2023 年第1 期,第164 頁。在債務人破產的情況下,一般保證即轉化為連帶責任保證,此時依據《民法典》第688 條之規定,自應允許債權人直接請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44〕參見鄭偉華、劉琦:《民法典保證期間相關規定在破產程序中的適用》,載《人民司法?應用》2022 年第4 期,第14 頁。保證人此時喪失順序利益,應債權人的請求即應承擔全部的保證責任。準此以解,在債務人破產時,保證人喪失實體和程序意義上的順序利益,債權人無須向破產管理人申報破產債權即可直接請求保證人履行保證債務。
本文贊成上述第三種觀點,理由如下。其一,債務人破產構成先訴抗辯權的阻卻事由,即意味著在債權人向一般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時,保證人不得以先訴抗辯權對抗債權人,一般保證人于此際的法律地位已與連帶責任保證人相同。〔45〕參見曹士兵:《中國擔保制度與擔保方法》(第5 版),中國法制出版社2022 年版,第212 頁。這也就意味著債權人無須向破產管理人申報破產債權即可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第一種觀點即不可采。其二,賦予保證人順序利益是先訴抗辯權制度的本旨,即保證人與債務人履行債務有順序之分,保證人履行債務即具有補充性,僅就債務人不能履行的部分承擔責任。〔46〕參見曹詩權、覃怡:《論保證人的抗辯權》,載《中外法學》1998 年第1 期,第72 頁;高圣平:《民法典擔保制度及其配套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21 年版,第106 頁。由此可見,先訴抗辯權兼具實體和程序的雙重意義。阻卻先訴抗辯權的行使即意味著保證人喪失順序利益,亦即在債權人主張保證債權時,保證人不得主張僅承擔補充責任。故第二種觀點亦不足采。
值得注意的是,在債務人破產程序開始之前,債權人已在保證期間內對債務人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保證期間雖已失效,但一般保證人仍受先訴抗辯權的保護,在先訴抗辯權消滅之前,一般保證人均可據此對抗債權人的權利主張。一旦債務人破產程序開始,一般保證人即喪失先訴抗辯權。此際,債權人無須等待破產程序結束即可請求保證人履行保證債務。〔47〕參見麻錦亮:《民法典?擔保注釋書》,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23 年版,第223 頁。如此看來,在一般保證的情形下,無論債權人在債務人破產之前是否依法對債務人行使了權利,一旦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債權人自可不向破產管理人申報破產債權,而僅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第三種觀點也就一以貫之地適用于一般保證的情形。
二、債務人破產時避免債權人超額受償的程序保障
在非破產語境下,債權人同時就對債務人和對連帶責任保證人的勝訴給付裁判,在同一執行程序中的執行目的均在于使債權人的債權獲償,具有同一性,不會出現債權人分別自債務人和保證人之處受償的總和超過債權總額的問題。在債務人破產時,債務人破產程序和就保證人的個別執行程序是兩個各自分離的程序,若債權人僅擇一向破產管理人申報破產債權或者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也不會出現超額受償的問題,但若債權人同時主張兩種權利,即可能出現債權人在破產程序中的受償額加上自保證人的受償額超過債權人債權總額的問題。〔48〕See Roy Goode & Louise Gullifer, Goode and Gullifer on Legal Problems of Credit and Security, 6th ed., Thomson Reuters,2018, p.412.在《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23 條第1 款采行“并行說”的情形下,該條第2 款、第3 款區分債權人是先自保證人受償還是先在債務人破產程序中受償,就破產程序與保證責任的銜接進行了規定。〔49〕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 年版,第250 頁。這兩款規定著力避免的不是債權人雙重受償,而是債權人超額受償,所秉持的仍然是債的擔保制度的本旨,即僅為確保債權的實現,而非使債權人額外獲益。
就債權人先在債務人破產程序中受償的情形,《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23 條第3 款、《企業破產法》第92、101、124 條均規定,擔保人仍須對債權人未獲清償的部分繼續承擔擔保責任。由此可見,盡管擔保人尚須就債權人未受清償的債權承擔擔保責任,但不會出現債權人超額受償的問題。就債權人的超額請求,擔保人自可主張本屬于債務人的抗辯——主債務已經部分消滅。債權人就其在債務人破產程序中未受清償的部分請求保證人承擔清償責任的,自應受到保證期間和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限制,已如前述。下文主要就債權人先自保證人受償時避免債權人超額受償的程序保障問題展開論述。
基于債權人的權利主張,若保證人承擔了保證責任,可能出現的情形包括以下三種:其一,債權人因保證人承擔全部或者部分保證責任而受全部清償;其二,債權人因保證人承擔部分保證責任而受部分清償;其三,雖然保證人承擔了全部保證責任,但債權人僅受部分清償[保證人依約定僅提供有限保證責任(如最高額保證)和部分保證責任(如僅擔保原本債權而不擔保從債權)]。在不同案型下,債權人、保證人的處遇并不一樣,但其解釋基礎應是相同的。
(一)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使債權得以足額清償的情形
在債權人已向破產管理人申報全部破產債權的情形下,保證人不得申報其追償權(《企業破產法》第51 條第2 款),否則將導致同一債權兩次申報的結果。〔50〕參見郁琳、吳光榮:《與破產法有關的幾個擔保問題》,載《法律適用》2021 年第9 期,第16 頁。禁止重復申報原則〔51〕禁止重復申報原則是破產法上長期存在的一項規則。英國梅里什法官(Mellish L.J.)在一起案件[Re Oriental Commercial Bank (1871) L.R.7 Ch.App.99]中指出:“該原則的真正意義在于,盡管可能存在兩份不同的合同,但對于實質上的同一債務,只能分配一份。”See Wayne Courtney, John Phillips & James O’Donovan, The Modern Law of Guarantees (English Edition), 3rd ed., Thomson Reuters, 2016, p.552.表明,債務人的破產財產不應用以清償就同一債務多重申報的債權,否則將扭曲平等的破產分配原則。〔52〕See Geraldine Mary Andrews & Richard Millett, Law of Guarantees, 6th ed., Sweet & Maxwell, 2011, p.533.在債權人已自保證人獲得足額清償的情形下,其雖然事先申報了破產債權,但該破產債權已因保證人的代償行為而消滅。此時,根據《破產審判會議紀要》第31 條前句,保證人不能再申報其追償權,只能請求債務人向其轉付債權人在債務人破產程序中應予分配的部分。〔53〕參見郁琳、吳光榮:《與破產法有關的幾個擔保問題》,載《法律適用》2021 年第9 期,第16 頁。其解釋基礎仍然是沿著保證人追償權的進路。
《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23 條第2 款前句規定,保證人代償之后自可“代替債權人在破產程序中受償”。此處的“代替”是對保證人清償承受權的經典表述,保證人代償后承受債權人在破產程序中的地位,可在債權人申報債權的范圍內直接獲得清償,不必另行申報。〔54〕參見李瀟洋:《論保證人清償后對主債權的承受》,載《東方法學》2023 年第1 期,第180 頁。此處的解釋基礎是《民法典》第700 條所規定的保證人清償承受權,而非該條規定的保證人追償權。基于《民法典》第700 條,保證人在承擔保證責任后享有債權人對債務人的權利。在解釋上,承擔了保證責任的保證人法定地承受債權人地位,對債務人享有權利。這也就意味著即使保證人承擔了保證責任,破產債權債務僅在債權人與破產管理人兩者之間相對地消滅,但仍然存續于保證人與破產管理人之間。〔55〕參見高圣平:《論保證人追償權的發生與行使——基于裁判分歧的展開和分析》,載《東方法學》2023 年第1 期,第162 頁。如此,保證人“可以代替債權人在破產程序中受償”。
此時的程序供給自然也就不僅限于《破產審判會議紀要》第31 條前句指出的“轉付”方式。已受足額清償的債權人已經不是破產程序中的利益相關者,其是否有動力充分行使本已由保證人承受的權利尚值懷疑。此時直接令保證人取代債權人,行使在破產程序中的權利,〔56〕參見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21)豫民再511 號民事判決書。如知情權、參與權、表決權,實為上選。就債務人的破產管理人而言,在保證人因代償而承受債權人權利的情形下,因保證人承受的債權與債權人的債權具有同一性,債務人的破產管理人也就無須對債權進行重復審查和確認。
(二)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僅使債權得以部分清償的情形
依據《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23 條第2 款,〔57〕該款規定:“擔保人不得代替債權人在破產程序中受償,但是有權就債權人通過破產分配和實現擔保債權等方式獲得清償總額中超出債權的部分,在其承擔擔保責任的范圍內請求債權人返還。”在債權人僅自保證人獲得部分清償的情形下,保證人雖因其代償行為而取得對債務人的追償權,但依據《民法典》第700 條,該追償權不得損害債權人的利益,〔58〕保證人追償權的行使是否受“不得損害債權人的利益”限制,尚存爭議。參見高圣平:《論保證人追償權的發生與行使——基于裁判分歧的展開和分析》,載《東方法學》2023 年第1 期,第167-168 頁。如此,保證人的追償權劣后于債權人的剩余債權而受償,保證人則不得就代償部分代替債權人在破產程序中受償,但有權請求債權人就超出部分在其承擔保證責任的范圍內予以返還。〔59〕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 年版,第251 頁。在程序法上,申報恒定原則要求債權人在申報債權之后即使自其他債務人獲得了清償,也無須對原申報數額進行調整。〔60〕參見許德風:《破產中的連帶債務》,載《法學》2016 年第12 期,第96 頁。
在我國法此前不承認保證人清償承受權的情形下,這一解釋路徑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債權人超額受償問題,但無法解釋其中的基本法理。例如,既然債權人已受部分清償,就表明該部分破產債權已在該債權人與破產管理人之間相對地消滅,緣何破產管理人不能降低該債權人的破產債權數額,仍然以其申報并經確認的原破產債權為基礎而清償?此時承擔了保證責任的保證人不能參與破產程序,僅能請求債權人返還超額受償部分,其請求權基礎何在?已經承擔全部保證責任但僅使債權部分清償的保證人,在債務人破產前后處遇不同的正當性何在?
保證人的追償權是因其代償行為而新生的權利,在債權人已經申報全部破產債權的情形下,基于債權人的債權與保證人的追償權(債權)的同一性,保證人已經無從再申報其追償權。與此相反,保證人的清償承受權僅為法定地承受債權人的權利,這一權利并非新生的權利,已經代償的保證人也就可以在破產程序中承受破產債權人的地位。在《民法典》第700 條所確立的清算承受法理之下,規制債權人超額受償的目標更容易達致,且能同時保護保證人的利益。在債權人已經申報全部破產債權的情形下,保證人的代償行為,無論是承擔全部保證責任還是承擔部分保證責任,若僅使得債權人的破產債權得到部分清償,保證人同樣承受債權人的法律地位,只不過是在其承擔保證責任的范圍之內。此時,債權人原已申報的破產債權由債權人和保證人共同享有(“準共有”)。就債務人的破產管理人而言,仍然將該破產債權作為整體予以確認和清償,而無須對整體債權額進行重新確認和調整。如此處理并不違背申報恒定原則。至于《民法典》第700 條所稱“不得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僅僅表明在該破產債權作為整體而獲得破產清償之后,在“準共有”關系內部優先清償債權人的剩余債權。但即便如此,也不表明承擔了保證責任的保證人不得承受債權人的地位,不得參與債務人破產程序。此時,保證人承受的債權,以破產分配款超過債權人剩余債權的部分獲得清償,是基于其破產債權“準共有人”的地位,而非請求債權人返還清償總額中超出債權的部分。至于該“準共有”的破產債權在破產程序中的行使,則類推適用《民法典》的共有規則。準此以觀,在債權人僅自保證人獲得部分清償的情形下,破產債權的行使和受償問題即可得到妥適的解決方案。
這一解釋方案以保證人的清償承受權為基礎,旨在于債務人破產程序中一次性地解決承擔了保證責任的保證人的權利保護問題,并不違背禁止重復申報原則和申報恒定原則。在債務人破產程序中,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未使債權人足額受償的,僅在其承擔擔保責任的范圍內承受債權人的權利,并無意調整債權人原已申報的債權,也就并未增加債務人的破產管理人的負擔。至于債權人和保證人等“準共有人”之間的內部分配關系,則非債務人的破產管理人這一外部人的職責范圍。即使認為債務人的破產管理人尚須確認同一破產債權內部債權人與保證人之間的分配比例或者分配數額,債務人的破產管理人也僅須基于保證人代償以及是否承擔了全部保證責任的簡單事實加以確認,尚未過分增加債務人的破產管理人的負擔。
《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23 條第2 款后句以保證人追償權作為解釋基礎,保證人不得作為破產債權人參與債務人破產程序,而僅能在破產程序終結之后請求債權人返還其受償總額中超出債權的部分。這一處理模式并不利于保護保證人的權利。一則,一旦債權人受領破產分配給付,即成為債權人的責任財產,構成其清償所有債權的財產基礎,而保證人此際僅為該債權人的債權人之一,該債權人是否有能力返還其受償總額中超出債權的部分存在不確定性。例如,債權人的債權總額為100萬元,保證人已經代償50 萬元,破產分配中債權人受償70 萬元。債權人在受領該給付之后,將其所有流動資金給付其債權人以清償債務,其中包括這70 萬元。此際,保證人的給付請求即有可能不獲滿足(設該債權人的所有固定資產均為他人設立了擔保物權)。二則,雖然保證人可以“待債權人超額受償的結果出現,要求債權人返還額外的受償金額”,但是這僅保護了保證人的“受償利益”,卻忽視了保證人作為破產債權人的程序利益,已經承擔了保證責任的保證人作為債權人依據《企業破產法》的規定享有一系列的程序性權利,諸如參加債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等。
尚存爭議的問題是,在保證人僅承擔有限保證責任(例如最高額保證)和部分保證責任(例如僅擔保原本債權而不擔保從債權)的情形之下,是否以及如何適用《民法典》第700 條所稱“不得損害債權人的利益”。《民法典》第700 條所規定的“不得損害債權人的利益”是《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23條第2 款的解釋前提,在保證人僅承擔有限保證責任或者部分保證責任的情形之下,承擔了全部保證責任的保證人的追償權據此將劣后于債權人的剩余債權而受償。但這一解釋結論有違立法本意。在債權人未獲足額清償的情形之下,盡管承擔了部分擔保責任的保證人亦取得對債務人的追償權,但該保證人追償權的行使“不得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如此,保證人的追償權將劣后于債權人的剩余債權而受償。其法理基礎在于,保證人就債權人的剩余債權仍應承擔保證責任,保證人行使追償權所取得的款項仍應向債權人清償,以履行剩余的保證債務。正是基于此,才破除債權平等受償的基本原則,令債權人的剩余債權優先受償。但本文認為,在保證人僅承擔有限保證責任或者部分保證責任的情形之下,保證人已經承擔了全部的保證責任,對于債權人剩余債權的清償并不再承擔保證責任,此時應回復債權平等受償原則,使保證人的追償權與債權人的剩余債權平等受償。如此,《民法典》第700條和《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23 條第2 款的適用應予限縮,僅限于保證人提供無限保證的情形。
設債權人甲對債務人乙有100 萬元債權,保證人丙提供50 萬元的限額擔保。若甲既申報破產債權,同時又向丙主張保證債權,在乙的破產程序中受償30 萬元,丙承擔了50 萬元的全部保證責任。依據《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23 條,甲獲償80 萬元(50 萬元+30 萬元),承受20 萬元的損失,丙承受50 萬元的損失。如采納本文的觀點,甲申報的100 萬破產債權由甲和丙“準共有”(各占50 萬元),破產分配的30 萬元亦由甲和丙“準共有”且按債權比例平等受償,各分得15 萬元。如此,最終不能從乙獲償的風險,甲承受35 萬元,丙承受35 萬元。
如此,不加區分地適用《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23 條,債權人的不同權利主張將導致不同的受償結果,且將不當地損及保證人追償利益。因此,即使債權人未受足額清償,此時保證人的追償權與債權人的剩余債權平等。保證人追償權的范圍也就并不限于“債權人通過破產分配和實現擔保債權等方式獲得清償總額中超出債權的部分”,而應與債權人的剩余債權平等受償。
三、債務人破產時債權人行使保證債權的時間限制
在債務人破產的情形下,債權人無論采取前述何種方式主張保證債權,均涉及時間限制的問題。在我國實定法采行保證期間強制適用主義的背景下,任何保證債務均有保證期間的適用。〔61〕參見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釋義》,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500 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施工作領導小組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理解與適用(二)》,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第1349 頁;李玉林:《民法典保證期間規則的理解與適用》,載《人民司法?應用》2021 年第16 期,第36 頁。若債權人沒有在保證期間內依法行使權利,則保證期間經過,保證債務消滅,自無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適用的空間;若債權人在保證期間內依法行使了權利,則保證期間失效,〔62〕本文將債權人未在保證期間內依法行使權利從而導致保證債務消滅的情形稱為“保證期間經過”;將因債權人在保證期間內依法行使權利而導致保證期間制度喪失保護保證人功能的情形稱為“保證期間失效”。參見麻錦亮:《民法典?擔保注釋書》,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23 年版,第196 頁。保證債權是否可得實現,則受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限制,只不過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起算因保證方式的不同而存在差異。在我國實定法未對破產情形下的保證期間作出特殊規定的情況下,債權人在債務人破產時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同樣應當受到保證期間和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約束。〔63〕參見郁琳:《“債權人可同時主張保證責任”的理解與適用》,載《人民司法?案例》2018 年第26 期,第9 頁。由此可見,無論債權人在何時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均有保證期間的適用;在保證期間失效的情形下,還存在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適用空間。
(一)債務人破產程序開始時保證期間已經開始計算的情形
在債務人破產程序開始時,保證期間已經經過且債權人未依法實施特定行為的,保證債務消滅,保證人無須再承擔保證責任,人民法院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的事實,并不產生恢復已經消滅的保證債權的請求力和執行力的效果。在債務人破產程序開始時,保證期間已經開始計算且并未經過的,由于保證期間為不變期間,不發生中止、中斷和延長(《民法典》第692 條第1 款),人民法院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的事實也就不影響已經開始計算的保證期間的繼續計算。由此可見,我國《民法典》就連帶責任保證和喪失先訴抗辯權的一般保證的保證期間計算之規定,并不與主債權債務關系的實際履行相勾連,債務人破產并不導致保證期間中斷計算,但對于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進行可能會發生影響。以下區分連帶責任保證與一般保證分別討論。
1.連帶責任保證的情形
就連帶責任保證而言,債權人在債務人破產程序開始之前已在保證期間內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的,保證期間失效,保證債務訴訟時效開始計算(《民法典》第694 條第2 款)。由于我國實定法采行主債務訴訟時效和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各自分別計算的方法,〔64〕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施工作領導小組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理解與適用(二)》,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第1361-1362 頁;高圣平:《民法典擔保制度及其配套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21 年版,第194-199 頁。人民法院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僅發生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的效果,債權人申報債權也僅發生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的效果,兩者對于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計算均不發生影響。無論破產程序是否終結,債權人若未在保證債務訴訟時效期間內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的,保證人對于債權人的履行請求均可主張時效經過抗辯權。
若債權人在債務人破產程序開始之前并未向保證人主張權利,人民法院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的事實對于保證期間的繼續計算并不發生影響。在破產程序開始后,債權人已在保證期間內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的,保證期間失效,開始計算保證債務訴訟時效;債權人未在保證期間內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的,保證期間經過,保證債務消滅。
2.一般保證的情形
就一般保證而言,債權人在債務人破產程序開始之前已在保證期間內對債務人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民法典》第693 條第1 款),或者在保證期間內基于依法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公證債權文書對債務人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27 條)的,保證期間失效。在非破產語境下,保證債務訴訟時效自保證人拒絕承擔保證責任的權利消滅之日起開始計算(《民法典》第694條第1 款)。但“人民法院已經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即意味著保證人拒絕承擔保證責任的權利消滅(《民法典》第687 條第2 款第2 項)。此際,人民法院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的事實對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計算發生影響,即保證債務訴訟時效應自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之日開始計算,而無須等到破產程序終結之日。
基于破產申請主體的不同,在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之日,債權人不一定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人民法院已經裁定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并進而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受到了侵害。《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28 條第2 款〔65〕該款規定:“一般保證的債權人在保證期間屆滿前對債務人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債權人舉證證明存在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七條第二款但書規定情形的,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自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情形之日起開始計算。”在此,“人民法院已經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屬于《民法典》第687 條第2 款但書規定的情形之一。“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情形之日”的規定仍然堅持了《民法典》第188 條所確立的主觀起算標準。〔66〕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 年版,第283 頁。具體起算的情形包括以下三種。其一,債權人提出破產申請的,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的裁定送達該債權人時,該債權人即“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情形”。其二,已經收到人民法院關于受理破產申請通知的債權人,即“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情形”,包括債務人提出破產申請情形下的已知債權人,以及債權人提出破產申請情形下的其他已知債權人。其三,未收到裁定或者通知的債權人,自其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受理破產申請的公告或者“人民法院已經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的其他事實,即“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情形”。
若債權人在債務人破產程序開始之前未依法實施特定的行為,人民法院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的事實對于保證期間的繼續計算并不發生影響,但使得一般保證轉變為連帶責任保證。債權人未在保證期間內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的,保證期間經過,保證債務消滅;債權人已在保證期間內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的,保證期間失效。此時,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計算與連帶責任保證相同。若債權人并不知道也不應當知道“人民法院已經受理債務人破產案件”的事實,并未及時調整其行權方式,而是在保證期間內對債務人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是否仍然可以產生保證期間失效的法律后果?此際,債權人系依據約定的保證方式在保證期間內行使權利,“既符合民法典之規定,亦符合當事人預期,應當對于債權人行為的效力予以認可”。〔67〕鄭偉華、劉琦:《民法典保證期間相關規定在破產程序中的適用》,載《人民司法?應用》2022 年第4 期,第15 頁。亦即此時仍應認為保證期間已經失效,并依照《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28 條第2 款確定保證債務訴訟時效的起算點。
(二)債務人破產程序開始時保證期間尚未開始計算的情形
當事人約定的或者法定的保證期間始期尚未屆至,債務人破產是否導致保證期間提前起算,不無疑問。在非破產語境下,保證期間的起算遵循以下規則。其一,保證期間的始期可由債權人和保證人約定;未約定者,推定為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之日(法定起算點)。其二,如約定的保證期間始期早于法定起算點,視其約定的終期是否晚于法定起算點而確定其效力:晚于法定起算點者,提早的保證期間始期約定沒有法律意義,保證期間自法定起算點至約定的終期;早于法定起算點者,視為沒有約定保證期間,保證期間自法定起算點起6 個月。其三,如約定的保證期間始期晚于法定起算點,始期約定有效。〔68〕參見高圣平:《特殊情形之下保證期間的計算三論》,載《法學雜志》2021 年第4 期,第1-2 頁。無論上述何種情形,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之日對于保證期間的確定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由于債務人破產構成一般保證人先訴抗辯權的阻卻事由,此時保證債務已喪失清償順序上的補充性,以下僅以連帶責任保證為中心討論保證期間與保證債務訴訟時效。
在債務人破產時,保證期間的始期尚未屆至的,尚須結合債務人破產的事實首先確定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之日,再依據前述規則確定保證期間的起算點。依據《企業破產法》第46 條第1 款的規定,即使在債務人破產程序開始時主債務履行期限尚未屆滿,也視為屆滿。此時,保證債務是否隨著主債務一起提前到期尚存解釋上的疑問。
第一種觀點認為,保證債務從屬于主債務,在主債務因債務人破產而提前到期的情形下,依據《民法典》第688 條第2 款,債權人可以向破產管理人申報破產債權,也可以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基于此,保證期間即應自債務人破產之日起開始計算。〔69〕參見許德風:《破產法論——解釋與功能比較的視角》,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346 頁;包曉麗、司偉:《民法典保證期間規定理解適用中的幾個問題》,載《法律適用》2021 年第1 期,第136 頁。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債務人破產雖然可以基于《企業破產法》第46 條的規定發生使主債務提前到期的效果,但保證人并不受該條的限制。債務人破產程序開始時主債務履行期限尚未屆滿的,保證人并無提前履行保證債務的義務,債權人須在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后方可向保證人主張權利。〔70〕參見王欣新:《破產法》(第4 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第217 頁。擔保的從屬性無法證成未到期保證債務因債務人破產而提前到期。由此所帶來的保證期間的始期晚于法定起算點,并不違反擔保的從屬性原則。〔71〕參見鄭偉華、劉琦:《民法典保證期間相關規定在破產程序中的適用》,載《人民司法?應用》2022 年第4 期,第12 頁。
此處涉及兩個層面的問題:(1)在債務人破產的情形下,債權人的保證債權可否行使;(2)若可得行使,保證期間自何時起算。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民法典》第681 條將保證債權的行使條件界定為“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以及“發生當事人約定的情形”。若債權人與保證人之間就債務人破產時債權人即可請求保證人履行保證債務作出了明確約定,保證債權在債務人破產時即可得行使,對此并無爭議。解釋上的疑問在于,債務人破產是否構成“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依據《企業破產法》第2 條,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是破產原因。就債務人的到期債權人而言,債務人破產同時構成《民法典》第681 條規定的“不履行到期債務”和《企業破產法》第2 條規定的“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即屬當然之理。就債務人的未到期債權人而言,雖不構成《企業破產法》第2 條規定的“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但債務人破產時視為到期,同樣構成《民法典》第681 條規定的“不履行到期債務”。如此,債務人破產的,“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這一保證債權的實現條件即已成就。
上述第二種觀點所謂“債權人須在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后方可向保證人主張權利”,在債務人破產的情形下,該如何認定“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是依據原約定,還是依據法律的直接推定?在解釋上,“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自應包括因債務人破產等導致主債務履行期限提前屆滿的情形。《民法典》第681 條允許當事人自行約定保證債權的實現條件,其中即包括債務人破產,此時即涉及保證人在原約定的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前履行保證債務的情形。若認為《民法典》第692 條規定的“主債務履行期限”僅指當事人原約定的履行期限,當事人的上述約定即因違反《民法典》之規定而被認定無效,這一解釋結論有悖立法原意。〔72〕參見劉琦:《破產程序對保證期間和訴訟時效的計算方式及銜接規則的影響》,載《第十二屆中國破產法論壇論文集》(第5 冊)(2021 年9 月?北京),第146 頁。
就第二個問題而言,依據《民法典》第692 條第2 款的規定,當事人可以約定保證期間的始期晚于法定起算點,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也就并不意味著債權人必須立即行使保證債權。〔73〕參見高圣平:《民法典上保證期間的效力及計算》,載《甘肅政法大學學報》2020 年第5 期,第89 頁;Geraldine Mary Andrews& Richard Millett, Law of Guarantees, 6th ed., Sweet & Maxwell, 2011, p.315.即使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債權人在保證期間的始期屆至之前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的,保證人可以主張保證期間的始期尚未屆至的抗辯。如此,《民法典》第688 條第2 款雖然規定在保證債權實現條件成就時債權人即可請求保證人履行保證債務,但其應限縮適用于保證期間自法定起算點起算的情形。若當事人約定的保證期間始期尚未屆至,即使保證債權實現條件成就,債權人亦不得對保證人主張保證債權。
準此以解,因債務人破產而導致主債務提前到期時,確定保證期間的始期存在兩種情形。其一,當事人約定的保證期間始期晚于法定起算點的,即使主債務因債務人破產而提前到期,保證期間亦應自當事人約定的始期開始計算,而不是自債務人破產之日起開始計算。其二,當事人約定的保證期間始期為法定起算點,或者當事人沒有約定保證期間的始期而推定保證期間自法定起算點起算的,債務人破產之日即為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之日(法定起算點),自此開始計算保證期間。至于當事人約定的保證期間始期早于法定起算點的,視為沒有約定,依前述推定規則,保證期間自債務人破產之日起開始計算。
四、結語
《民法典》雖然大幅修改了擔保規則,但囿于調整范圍的限制,未就破產程序中擔保權利的行使作出全面規定,由此出現了現有破產規則與《民法典》既有政策選擇相沖突的問題。在法律未作特別規定的情形下,在債務人破產時債權人保證債權的行使適用《民法典》的一般規則,諸如債權人實現其債權時的選擇權、保證期間和保證債務訴訟時效規則。破產程序作為總括強制執行程序,置重于所有破產債權的公平清償,〔74〕參見韓長印主編:《破產法學》(第2 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7-8 頁;鄒海林:《破產法:程序理念與制度結構解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3 頁。自有其特殊性。諸如,債務人破產構成阻卻先訴抗辯權的法定事由,如此一般保證人的法律地位已與連帶責任保證人相當。
至于債權人同時自債務人和保證人受償時所可能出現的超額受償問題,自可借助《民法典》增設的清償承受規則加以解決。首先,在債務人破產程序中,保證人的代償行為使債權人得以足額清償的,由保證人承受債權人地位而參與債務人破產程序。其次,保證人的代償行為未使債權人得以足額清償的,同樣由保證人在其代償范圍內承受債權人地位,債務人的破產管理人原已確認的債權由債權人和保證人“準共有”。其中,保證人承擔了全部保證責任的,保證人基于清償承受權所取得的債權與債權人的剩余債權的清償順位平等,由保證人與債權人按比例分配該“準共有”債權在破產程序中的分配額。最后,保證人僅承擔了部分保證責任的,保證人基于清償承受權所取得的債權劣后于債權人的剩余債權,就該“準共有”債權在破產程序中的分配額在優先清償債權人的剩余債權之后受償。這一解釋結論并不違反禁止重復申報原則和申報恒定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