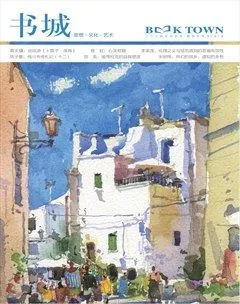一首寫給童年的挽歌
趙祎麟
小銀,從兒時起,我就本能地討厭寓言。寓言家們借那些可憐的動物之口可沒少說蠢話,所以我痛恨它們……長大后,小銀,寓言家讓·德·拉封丹終于讓我和那些會說話的動物和解了,他的話語有時候真的讓我仿佛聽到了烏鴉、鴿子或山羊的聲音。不過,故事結尾的寓意我是不讀的,因為那不過是一條枯燥的尾巴,是灰燼,是作者完稿時不慎留下的污漬而已。
——《寓言》
盡管《小毛驢與我》在兒童讀物的序列中早已膾炙人口,但不是所有人都有幸在童年便與毛驢小銀相逢,或是能準確憶起孩提時初見小銀的自己。百余篇散文詩讀罷,遇到《寓言》一篇,恍如在莫格爾的海天間驟然升起一道高墻,讀者不得不低頭沉思、向回折返——不是面向希梅內斯和小銀的反思,而是由紙頁折回的、朝向自我的反思。那些為了尋找深掩的意涵而剝開的字句,在審讀的目光中暴露板結,質詢著讀者對于寓意的開掘。不必失落于無從尋回的孩童目光,讓我們先輕輕掩上自省的熱忱,回到與小銀結識之前的時刻。
或許是為了給復返于此的成年人提供閱讀建議,又或許要向孩子們聲明自己不是童年時厭棄的那種寓言作家,希梅內斯在《小毛驢與我》的序中鄭重聲明:“我從沒寫過,也不會去寫給孩子們讀的書,因為我相信他們完全可以讀大人的書。”希梅內斯并不否認孩子與成年人讀的書之間存在區別,信任屬于童年的感知潛能,反而質詢了這一肯定話語背面的假設:如果《小毛驢與我》是專為孩子們而作的,那大人們又是否“可以讀”呢?當我們翻開這部充滿孩童般目光和筆觸的作品,當我們把小銀的故事“讀給孩子聽”時,我們自然代入的身份又是否會在某一刻產生動搖?
把手張開吧,讓大西洋的微風再次穿過指間,感受自我被遺忘抽離,就像第一次撫摸小銀脖頸上的茸毛那樣。撫摸是詩人的邀約,我們接受了邀請,不但成為撫摸小銀的手指,亦是手指撫摸的小銀。“它和我那么相像,和別人又那么不同,我甚至相信它和我做著一模一樣的夢”,詩人和小銀之間,不僅有摯友般無間的陪伴,亦有知己般投合的默契。在對小銀的抒情中,小銀的形象逾越了日常生活中的互動者角色,被賦予了詩人自我映射的色彩,通過書寫與小銀夢境的共享,詩人察覺到在眼下處境中隱隱爆發的不安,不僅把對于純真自我的駐留和對于知己的渴求寄托在小銀的形象之上,也透過理想化的小銀呼喚著書頁之外讀者的共鳴,來自未來的讀者對莫格爾的年輕詩人而言預示著一道與現實的裂隙,用來安放與周遭格格不入的歡喜與痛苦,為眼下的郁結尋找出路。詩人驚恐地察覺,明晃晃的暴力開始逐漸侵入故鄉的日常,上一秒還氣宇軒昂的馬駒,忽然被埋伏良久的人們按倒閹割,這段詩人稱作“暴力、圓滿又清晰的回憶”成為他溫柔筆觸下埋藏的痛點,似乎在莫格爾的靜謐中隨時會產生難以名狀的、“毫無理由的”破壞性的痛苦,現實的異化讓詩人與記憶認知中的故鄉之間產生罅隙,卻又無力從故鄉抽離來進行審視和判斷;當詩人目睹朋友在果園里為中彈的獵人療傷時,“混雜著焦油和魚腥”的海水氣味與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著“沒有大礙”的鸚鵡學舌填補了詩人失聲的空白,詩人借鸚鵡之口嘗試著撫平血腥畫面帶來的沖擊,反而使得血腥的效果在一次次的重復中加強。
與突發的暴力對詩人內心原有的故土秩序造成的沖擊相對應的,是徐徐展開的、籠罩在這片土地上的對往昔的思念和對失去的隱憂。當詩人與在院中親手種下的相思樹重逢時,卻再也感受不到昔日情感的再現,即使“曾經那么愛它,那么了解它”,重逢時卻“一言不發”,這片交織著詩意和記憶的土地,如今卻讓詩人感到陌生,詩人寫道,“我想逃離”,并非在空間上離開這片土地,而是回到那個為自己所熟識的故鄉和過往。當詩人向別人展示自己以前的小獵犬羅德的照片,卻無法得到記憶的回響時,只好無奈地向著小銀說,“不知道你會不會看照片”。當屬于過去的記憶陷入孤獨的回響,故鄉那為詩人所習慣的平靜的永恒被打破,詩人的目光里愈是充滿幸福,愈是蘊含著對分離的焦慮和失去的隱憂。面對終將到來的失去,詩人選擇通過寫作,讓當下的時光在未來獲得意義,來抗衡時間的力量和當下的短暫。正如詩人在埋葬著至親的“舊墓園”中向小銀講述逝去的親人與時光,他早在集子開篇處便已為小銀的“后事”做好打算,按自己理想中的童年場景為小銀描繪了永恒的樂土,小銀的身邊會有孩童玩鬧、水車潺潺和洗衣姑娘的哼唱,而詩人將為它“吟詠為孤獨而作的詩篇”。
再次讀到《寓言》一文時,我們或許會突然發覺,詩人之所以厭棄寓言的套路,不愿將自己的作品歸入寓言的行列,是因為他根本無意于以固化的成人身份施展教化,反而是希望通過寫作,在童年中尋找和重構自我。孩子們當然能夠閱讀,那也正是詩人所渴求的閱讀狀態,而成年人則是詩人穿過小銀柔亮透明的身體探出的手真正觸碰的讀者。當我們閱讀時感到心中某處異斥于身體的悸動,不必停留感懷求索,請繼續讀下去吧,那不過是奔跑的小銀在年輕的詩人瞳中愈發縮小的身影,或者說,是童年作為正在逝去的一切的縮影在記憶邊緣的閃爍。